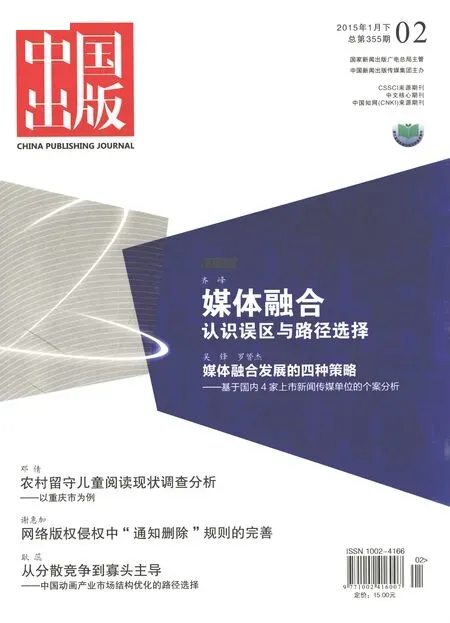人散曲未終
——讀《水滸人物甲午曲》
□文│徐慶群
人散曲未終
——讀《水滸人物甲午曲》
□文│徐慶群
說到中華文化之家珍,言必稱唐詩、宋詞、元曲。唐李白、杜甫,宋蘇軾、李清照……這些文學家家喻戶曉。且現代人對古體詩詞的創作也可謂精彩紛呈、綿延不絕。對于元曲,單從關漢卿、馬致遠等元曲家少量傳世名篇可窺見曲韻的端倪。
其實,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是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瑰寶,其興起都與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態聯系在一起,均是所處時代之經濟政治法治等發展的折射。元朝在民族文化上采用的是相對寬松的多元化政策,即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并鼓勵各民族之間進行文化交流和融合。比如,元朝還包容和接納歐洲文化,準許歐洲人在元朝做官、通婚等。歐洲著名歷險家馬可·波羅就曾是元朝的重要官員。
在這種自由開放、兼容并包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氛圍中,文學特別是通俗文學得到蓬勃發展,那么表達時代情趣的詩歌便蔥蔥郁郁。同時,散曲大盛于元和語言以及音樂的發展有直接的關系。比如,北方少數民族音樂傳入中原,也使與音樂結合的詩歌創作在格律上有所改變。正如王世貞在《曲藻·序》中所說:“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
在不同民族文化與文明的交融中誕生的元曲,可以說是最具有豐富內涵和綺麗風格的一種文學樣式。元曲分為散曲和元雜劇。散曲之所以稱為“散”,是與元雜劇的整套劇曲相對而言的。“散”即呈現出口語化以及曲體某一部分音節散漫化的狀態。比如,押韻較靈活,可平仄通壓,還可襯字。而襯字就具有明顯的口語化、俚語化的特點,使曲意明朗、活潑。但是也需要注意一定的格律。在藝術表現方面,更多地采用“賦”的方式加以鋪陳敘述。
但是近些年,連漢賦這種廟堂重器,以鋪排連篇、飾雕麗文華藻的高希之文也不常有人問津,這種生于草莽、傳頌民間、充斥俚語俗言的散曲,自更是“柴門少叩問”。
“也許出于‘焐冷灶’的個性使然,我久有寫一本散曲集的夙愿了。”謝德新先生自去年出版了《紅樓人物癸巳詩》舊體詩集,創作熱情如滔滔江水,忽發奇想要寫寫《水滸》,于是便有了這本《水滸人物甲午曲》(五洲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對于《水滸》,傳統文化功底深厚的謝德新先生是爛熟于心,人物、故事、場景、意象恍恍在腦、揮之不去。他說,水滸人物身上浸透的市井氣,也許更為適合散曲這種形式吧。但是在表達方式上,謝德新先生仍遵循自己寫舊體詩詞的一貫原則,盡量顧及散曲的格律規則,句式、對仗、押韻較為嚴格,韻律力爭取之,不因律害意。并且力求多采用一些曲牌,以讓世人看到散曲這種藝術形式的豐富多彩。
據《太和正音譜》載,現存曲牌350多個,該書即使用了320多個。且自選了一個高難動作,盡量使曲牌名與所吟唱的人物身份個性相對合拍協調,“巧也幸哉,大部分竟找到了,這也是始料未及的”。《笑和尚》之魯智深,《快活三》之李逵,《臉兒紅》之高俅,《風流體》之高衙內等與人物如此吻合,不得不為散曲曲牌之繽紛多彩擊節嘆也。謝德新先生說:“嘆之余也有憾,曲學規則一些曲牌僅限套曲、劇套,本不應小令吟唱,因水滸人物眾多,曲牌配之不易,也只好不拘束縛,冒犯規則,混而用之,留予專家批評的由頭吧。”曲有南曲、北曲之分,該書所用曲牌以北曲為主,南曲也挑用了些,還選用了南北曲雜用的套數,并有意選用了一些較寬泛、多樣表現手法的套路。
一言以蔽之,《水滸傳》寫的是封建男權視角下的男人的故事。我們現代人如何為水滸“譜”曲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一切都是我們的視角,跟水滸和施耐庵沒有關系。
我以為謝德新先生的這部作品,最重要的是讓我看到了他的態度,對曲的態度,對水滸的態度。
人散曲未終。也應該是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作者單位: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