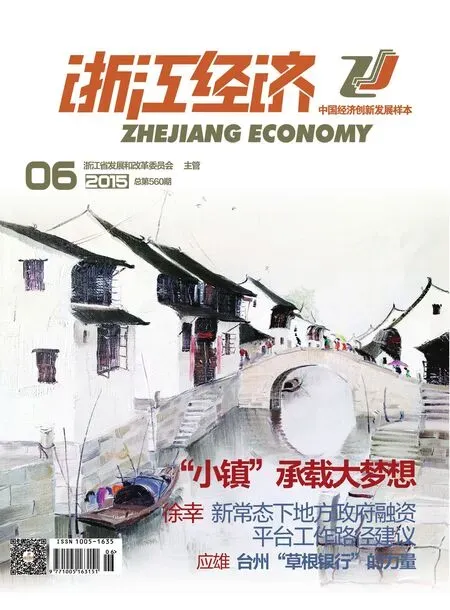果真是“失落的十年”嗎?
——2004-2013浙江發展指數測評
呂淼
果真是“失落的十年”嗎?
——2004-2013浙江發展指數測評
呂淼
2004年是浙江經濟增長的一道分水嶺。從這一年開始,浙江經濟增速從領跑全國一路下行,數年后幾乎跌至全國末位。十年來,浙江發展出現了“人老地少錢走”的問題,浙江經濟曾經的輝煌似乎漸行漸遠,網上有人稱之為“失落的十年”。事實果真如此嗎?
浙江經濟的無奈
縱觀改革開放36年,浙江經濟增長速度總體領先,居全國第3。特別是1978年至2004年,浙江經濟年均增長13.5%,高居全國首位。然而2004年后風云突變,2004至2014年浙江GDP年均增速跌至全國第27位。這10年,浙江深陷“兩難困境”——粗放增長缺土地、集約增長缺激勵,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浙江成全國建設用地增長洼地。根據歷年《國土資源年鑒》數據整理,浙江建設用地供給增長速度放緩。2004年至2012年,浙江國有建設用地供給年均增長速度僅2.1%。與此同時,全國國有建設用地供給年均增長高達13.5%,中西部地區甚至高達26.9%。在土地大幅增長等的支撐下,中西部地區紛紛以低地價、零地價向浙江等沿海地區招商,全國的粗放外延增長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浙江資本加速外流拖累省內經濟。10年間,中西部省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5.2%,高出全國平均3.4個百分點,亦大大高于其GDP增長。而浙江的投資速度明顯放慢,年均增長僅為15.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6.5個百分點,列全國倒數第3。在省內相對用地較少的情況下,浙江企業大幅向省外投資,幾乎在省外“再造一個浙江”。浙江絕大多數企業在省外繼續復制傳統產業,這既放慢省內經濟增長,又加劇全國粗放外延增長。
巨額地方債和轉移支付進一步推動中西部增長。中西部地區地方債和轉移支付扶搖直上。截至2013年6月,中西部省份地方債合計占全國的53.7%,比其GDP占全國比重高9.1個百分點。有3/4的中西部省份的地方債占當地GDP比重高于30%。而浙江地方債總額僅列全國第12位,占GDP的18.4%。中西部地區獲得的中央轉移支付亦大幅增長,其中凈轉移支付10年間增加了4.2倍。而據省發改所研究表明浙江上繳中央稅收占財政總收入比重逐年上升,多數企業稅收負擔較重。
創新增長激勵不足難以推動省內轉型。“三十年如一日”的產業結構和難以突破的轉型約束,使得浙江創新增長較慢。浙江產業結構調整滯后于經濟增長,傳統產業轉型舉步維艱。尤其是近10年,蘇滬地區大力發展機械制造等高新產業,傳統產業占比大幅下降,轉型速度均快于浙江。另外,老企業家們草根出身的文化背景,以及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天然薄弱性,成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制約。
10年放慢或是幸事
應該看到,浙江經濟增長回落并非發展的全部,結構優化、社會發展和人文進步,是這十年浙江發展更重要的故事。筆者分別從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發展質量、居民生活、城鎮發展、社會保障、文化教育、衛生健康、科技創新、環境保護、市場化等11個方面選取21項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計算,得出相應的發展指數,對各省市區十年發展情況進行綜合評價。數據表明,浙江雖失去了GDP增速領跑全國的地位,但在結構質量以及人文社會發展方面,毫不遜色。浙江發展指數得分從2004年的0.63提高至2013年的0.67,遠遠領先于中西部省份,排位穩居全國第四。
經濟增長率先適應新常態新要求。服務業主導和消費崛起的時代已經來臨。2013年浙江經濟結構排名較2004年前進5位。2013年,浙江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這一指標達到46.1%,連續9年增長速度快于GDP,且高于全國平均4.1個百分點,這表明浙江經濟轉型升級已有實際的重大進展,注重服務的年代正在開啟。居民消費占GDP比重較10年前提升3個位次,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不斷提升。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發展模式漸行漸遠。浙江發展質量自2007年起連續7年排名第六位,較2004年上移一位。其中,單位GDP能耗這一指標由2004年的第七位躍居為2013年的第四位,較10年前降低46.1%,這表明浙江10年來堅持可持續發展,節能降耗效果明顯。
社會發展水平持續走在全國前列。城鄉居民收入繼續穩居各省區首位。2004—2013年,浙江居民生活連續十年列各省區第一。201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全國的1.4倍和1.8倍,其中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速持續快于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斷調整優化。浙江的“被城市化”現象表現并不突出。2004—2013年,浙江城鎮化率累計提升10%,年增長速度為1.9%,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0.3個百分點。且浙江的城市化水平與城市化率顯示的水平具有較高吻合性。“藏富于民”的浙江傳統進一步延續。2011—2013年,浙江社會保障指標連續三年列全國前五。2013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0%,比全國平均低0.3個百分點。2004—2013年,浙江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年均增長15.4%,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
人文底蘊和創新內涵發生質的裂變。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明顯加快。2004—2013年,學齡人口中大專以上人口占比累計提升9.9個百分點,達17.3%,高于全國平均6.0個百分點,表明浙江人口文化素質提升。居民健康水平走在全國前面。浙江衛生健康指標持續保持增長態勢,得分由2004年的1.24提升到2013年的1.28,排位上升2位。自主創新逐步成為社會的自覺行為。科技創新指標由2004年的1.66上升到2013年的1.92,位居全國第二。科技投入逐年增加,規模以上企業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由10年前的0.2%上升至2013年的1.8%。科技成果穩步增長,浙江每萬人發明專利數10年來始終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2013年排名居全國首位。
轉型中的四個問題
浙江正歷經“轉型的煩惱”,部分指標排名下滑趨勢應引起注意。
深陷兩難困境的浙江經濟,增長速度回落超預期。浙江經濟10年來深陷于“粗放走不通,集約走不動”的兩難之中。一則省內集約增長難以有效展開。2013年,浙江建設用地面積已達1.2萬平方公里,占浙江陸域面積的11.8%。按前述數據推測,浙江平原起碼已有1/3以上面積為各種建設所覆蓋。二則浙江企業難以抵擋省外低價土地誘惑大批“出走”。正由于此,浙江經濟增長率逐步趨緩。浙江經濟增長指標排名10年間由第五跌至第22。其中,GDP指數得分從2004年的0.38跌至2013年的0.11,排名后退21位,人均GDP亦由2004年的第四位退至2013年的第五位。
產業轉型依然偏慢,勞動力素質堪憂。低層次崗位需求和自身低文化素質的雙重制約,使得外來人口長期被鎖定在浙江低端傳統產業中。根據“六普”數據,全省第二產業每萬元GDP需勞動力0.13人,位列全國第28位。傳統產業對于外來勞動力的旺盛需求,加上浙江各地良好的就業生活環境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素質較低人口流入浙江。10年來,每萬人口大學生數量排名下降9位至第19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排名下降2位至第八位。這兩個指標位次的變化,反映出浙江這10年仍是傳統產業低端鎖定的10年,嚴重影響浙江產業轉型升級和效率提升。
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雙重緊逼,環境容量加速透支。10年來,浙江不少地方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仍在走低效率、低產出、高消耗的粗放外延型發展道路,從而導致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突出。環境保護指標由2004年的第七位下降至2013年的第八位,排位下降1位。其中空氣質量達到二級以上天數占全年比重雖提升3位,但仍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6個百分點。近年來,口罩脫銷、搶水風波等環境事件幾乎都指向粗放發展模式,改善生態環境成為浙江人民迫切需求。
草根創業向知識創業轉型的空窗期,市場化進程放緩。草根經濟從“浙江增長主力”到“粗放外延增長典型”的角色變換是市場化進程放緩的一個主要原因。2013年,浙江民營經濟占GDP比重超65%,已是浙江增長的絕對主力。然而完成量的擴張后,浙江民營經濟仍處低成本、低技術、低檔次的初級加工階段。曾經帶動當地經濟的產業集群都面臨轉型問題。2004年,浙江市場化得分居首位,超出江蘇0.52分;2010年跌至江蘇之后為第二,2013年反被江蘇超了0.27分。浙江市場化改革的領先程度下降,市場化進程出現放緩趨勢。
尋找創新增長和美好生活的平衡點
目前,浙江經濟發展方式正在悄然發生積極轉變,未來如何在創新增長和美好生活之間找到平衡點顯得至關重要。
發掘增長新動力和投資新領域。浙江需進一步發掘增長新動力和投資新領域,實現創新增長。浙江當下存在大量富有潛力的新增長點,比如互聯網峰會后帶來的信息消費和創意文化產業發展;又如推進新型城鎮化、打造養老產業、啟動“五水共治”等民生創新舉措;再如承載浙江轉型升級重要功能的“特色小鎮”建設。
力推增量轉型和傳統外創新。浙江傳統產業雖短期內轉不動,但可以另辟蹊徑:采取增量轉型、傳統外創新策略,形成與以往不同的增長方式和動力機制。比如促進跨界新人和專業新人的崛起;又如強化依法治省和民資支撐,打造全中國最為有序的創新環境;再如促進一批“高大上”的產業落戶。
著力分配優化和消費崛起。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意味著政府需推出合理的政策來保證分配的優化和消費的崛起。政府需要推進勞動工資三方協調機制建設,促進勞動工資合理增長。同時也要引導資本節制,增強資本社會責任,優化社會分配機制。在分配優化的同時,需全面深化改革,積極提升消費信心和消費意愿。
作者單位: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