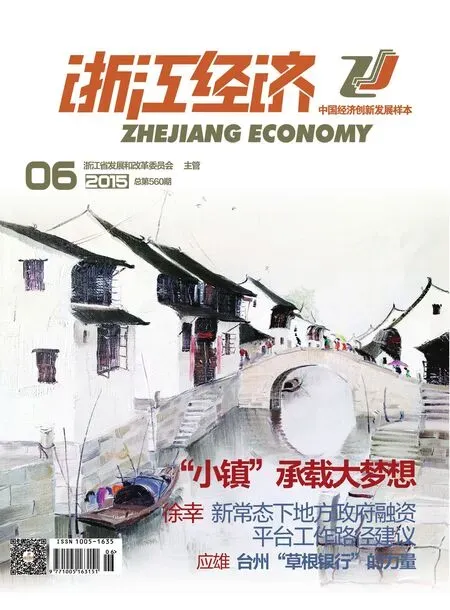“專車”模式之喜與憂
葛燕
“專車”模式之喜與憂
葛燕
“專人專車,隨叫隨到”、“今天坐好一點(diǎn)”……諸如此類的廣告語吸引著消費(fèi)者的眼球,2014年開始興起的“專車”模式在熱捧和爭議的交織中大紅大紫。筆者與大部分享受過“專車”的乘客一樣,不禁要對“專車”服務(wù)“點(diǎn)贊”。撇開各類爭議不談,“專車”服務(wù)模式至少讓我們看到了三點(diǎn)欣喜:
一是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的創(chuàng)新。我國有網(wǎng)民6.4億,移動寬帶用戶5.3億,網(wǎng)絡(luò)零售交易額近2萬億元,已超過美國居全球首位,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推動發(fā)展具有廣闊空間。“專車”服務(wù)是一項新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業(yè)務(wù),是通過信息均衡將智能化應(yīng)用的拓展。“互聯(lián)網(wǎng)+”的思維將部分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顛覆,多層次和差異化的需求在各類APP中得到滿足。“專車”服務(wù)模式以APP平臺為中介,緊跟產(chǎn)業(yè)鏈端互聯(lián)網(wǎng)化的新趨勢,讓曾經(jīng)多少次在風(fēng)吹雨打中苦苦等待出租車的人們嘗到了甜頭,已成為一種“潮”的出行方式。
二是“服務(wù)經(jīng)濟(jì)”意識的滲透。2014年,浙江服務(wù)業(yè)占生產(chǎn)總值比重首次超過工業(yè),全省服務(wù)業(yè)增加值增速連年快于GDP增速,表明“服務(wù)經(jīng)濟(jì)”時代已悄然來臨。“專車”服務(wù)模式是線上線下融合發(fā)展的典范,包含了預(yù)約、專車機(jī)場接送等服務(wù)內(nèi)容,便捷高效、個性定制等服務(wù)意識貫穿其中,與“服務(wù)經(jīng)濟(jì)”時代所提倡的理念不謀而合。
三是以資源整合提升效率的體現(xiàn)。“專車”服務(wù)模式目前主要分布在一二線城市,根據(jù)車輛來源及運(yùn)營方式的不同,大致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雇傭司機(jī)利用自有車輛運(yùn)營的公司化運(yùn)作方式,以神州為代表;另一種是通過車輛外包、支持私人車通過接受監(jiān)管的方式提供專車服務(wù),以Uber為代表;還有兩者兼而有之的滴滴專車、一號專車等。不論這些方式的利弊,它們實(shí)則都是對資源的整合利用,有利于提高市場效率。
“專車”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xiàn),無疑是來源于市場需求的驅(qū)使。然而,由于政策及環(huán)境的包容度來不及緊跟市場的瞬息萬變,加上新生事物終究需要有個摸索的過程,關(guān)于“專車”服務(wù)模式的“口水戰(zhàn)”不絕于耳,對“專車”模式發(fā)展的憂慮也著實(shí)不少。
——發(fā)展能否可持續(xù)?目前進(jìn)入“專車”市場的幾大巨頭,基本都是在“砸錢”。由于“專車”收費(fèi)基本是普通出租車的2-3倍,通過發(fā)放代金券、補(bǔ)貼等方式來開拓市場成為“專車”巨頭們不約而同的選擇。“砸錢期”過后,“專車”的生存之道在哪里?
——運(yùn)營是否踩“紅線”?目前爭論的焦點(diǎn)主要在于“司機(jī)是否具有客運(yùn)服務(wù)的從業(yè)資格?車輛是否取得營運(yùn)服務(wù)的運(yùn)輸許可?”這兩大方面。目前部分私家車參與“專車”服務(wù)、部分社會車輛掛靠到“專車”平臺參與運(yùn)營,這是否觸動了法律紅線?正是基于對其是否“合法”的考慮,2014年底,各大城市因“專車”服務(wù)涉嫌非法營運(yùn),紛紛對其喊停。
——風(fēng)險責(zé)任誰承擔(dān)?“專車”模式還存在著較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一旦出現(xiàn)風(fēng)險事故,參與“專車”運(yùn)營的車輛如何處理?損失由誰承擔(dān)?消費(fèi)者的利益誰來保障?這都是眼下“專車”運(yùn)營中難以明確的地方。
“專車”模式的積極作用不容置疑,它更是服務(wù)經(jīng)濟(jì)時代、“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潮流產(chǎn)物。當(dāng)前,放眼長遠(yuǎn)、規(guī)范理性地推動其有序發(fā)展,才能更好地發(fā)揮出其積極作用。一方面,要推動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化、規(guī)范化運(yùn)作。以市場為主導(dǎo),國家層面要適時對專車服務(wù)進(jìn)行立法規(guī)范,行業(yè)層面要對打車類APP進(jìn)行規(guī)范并制定相應(yīng)標(biāo)準(zhǔn),明確從事專車服務(wù)的汽車租賃公司、駕駛員勞務(wù)派遣公司、租賃車輛、駕駛員及網(wǎng)絡(luò)專車服務(wù)平臺等各方的責(zé)任。日前,合并后的滴滴、快的發(fā)布了《互聯(lián)網(wǎng)專車服務(wù)管理及乘客安全保障標(biāo)準(zhǔn)》,此舉填補(bǔ)了互聯(lián)網(wǎng)專車行業(yè)安全管理標(biāo)準(zhǔn)的空白,使專車服務(wù)有望實(shí)現(xiàn)“事前嚴(yán)格準(zhǔn)入,事中實(shí)時監(jiān)控,事后全程可追溯”。另一方面,要加強(qiáng)對“專車”市場的監(jiān)管。全國性的規(guī)范目前尚未出臺,但已有部分地方因地制宜作了探索,例如江蘇省交通運(yùn)輸廳下發(fā)的《汽車租賃經(jīng)營行政許可規(guī)范》,對汽車租賃市場的準(zhǔn)入和監(jiān)管進(jìn)行規(guī)范,依據(jù)這一規(guī)范,包括“專車”在內(nèi)的汽車租賃車輛,必須是租賃公司的自有車輛。同時,江蘇省揚(yáng)州市日前對來該市開展專車業(yè)務(wù)的“滴滴打車”進(jìn)行聯(lián)合行政指導(dǎo),明確專車第三方運(yùn)營平臺須對專車服務(wù)車輛運(yùn)營資質(zhì)進(jìn)行審查。未經(jīng)行政許可車輛通過平臺從事專車服務(wù),有關(guān)部門有權(quán)追究專車第三方運(yùn)營平臺的相關(guān)法律責(zé)任。這樣的措施從源頭上規(guī)范“專車”市場,有效保證了對專車運(yùn)營的后續(xù)監(jiā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