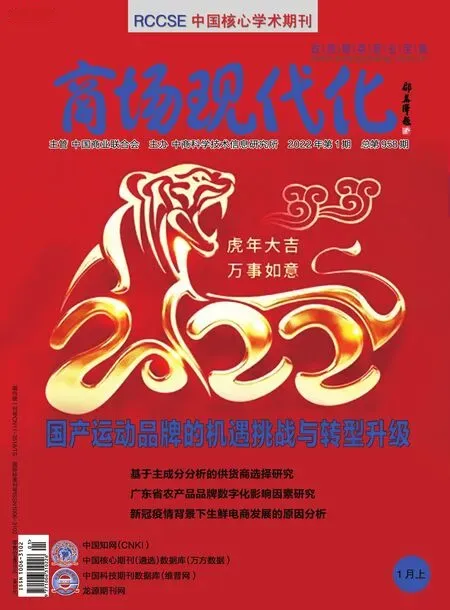公司法強(qiáng)制性與任意性邊界之厘定:一個(gè)法理分析框架
劉倚源
摘 ? 要:公司法規(guī)則的強(qiáng)制性和任意性尋求已經(jīng)成為理論和實(shí)踐共同面臨的基礎(chǔ)性命題,要在兩類規(guī)則的動(dòng)態(tài)均衡中保持公司法的正當(dāng)性。本文就規(guī)范對(duì)象和不同章程階段對(duì)強(qiáng)制性和任意性進(jìn)行了厘定,并分析了通過后續(xù)章程修改以“選掉”公司法的弊病。
關(guān)鍵詞:公司法;強(qiáng)制性;任意性;厘定
一、引言
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全面實(shí)施,拓寬了任意性和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的適用范圍,得到了學(xué)者的盛贊,但是新《公司法》中含糊的法條仍然有9處之多,給公司實(shí)踐帶來了困難,如何厘定其強(qiáng)制性和任意性成為了一個(gè)世界性的難題。
二、公司法強(qiáng)制性與任意性之厘定
1.就規(guī)范對(duì)象而言的厘定分類。大多數(shù)學(xué)者將公司法分為“公法”和“私法”,但美國(guó)法學(xué)教授艾森伯格的分類方法是以細(xì)致的公司結(jié)構(gòu)作為支撐,更加具有說服力,以此為基礎(chǔ)對(duì)公司法強(qiáng)制性與任意性進(jìn)行厘定則更加合理。
就規(guī)范對(duì)象而言,在理論上公司法規(guī)則分為結(jié)構(gòu)性規(guī)則、分配性規(guī)則和信義規(guī)則三種類型,本文認(rèn)為前兩者宜為任意性規(guī)范,而后者宜為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具體而言,結(jié)構(gòu)性規(guī)則只涉及公司內(nèi)部的權(quán)利分配,以形成運(yùn)作有序的公司治理架構(gòu),因此宜為任意性規(guī)范。分配性規(guī)則不涉及第三方利益,對(duì)公司財(cái)產(chǎn)在股東間的分配方式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規(guī)定,因此宜為任意性規(guī)范。而信義規(guī)則起著拾遺補(bǔ)缺的作用,規(guī)范了董事和控股股東的義務(wù),因此應(yīng)該類為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另一方面,公司法規(guī)則還可以分為賦權(quán)性規(guī)則、補(bǔ)充性規(guī)則和強(qiáng)制性規(guī)則,前兩者為任意性規(guī)則,其他的均為強(qiáng)制性規(guī)則。具體來說,賦權(quán)性規(guī)則包含“可以”、“還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規(guī)定”等字眼,授權(quán)公司參與各方設(shè)定規(guī)則,而公司法中出現(xiàn)“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等字眼時(shí)即為補(bǔ)充性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在各方未另設(shè)約定的情況下具有效力,由此可見,賦權(quán)性規(guī)則和補(bǔ)充性規(guī)則相對(duì)來說都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而強(qiáng)制性規(guī)則包括“不得”、“必須”、“應(yīng)當(dāng)”等字眼,這些規(guī)則對(duì)一些事項(xiàng)進(jìn)行了強(qiáng)制性的規(guī)定,不允許公司參與各方隨意修改。
2.在不同章程階段的厘定分類。公司章程作為自治性規(guī)范,是公司的內(nèi)部自治規(guī)則,不得與公司法之間存在抵觸性的界定,在章程制定的不同階段,約定“選掉”公司法都有的不同程度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
首先,初始章程與后續(xù)章程修改的過程中,“選掉”公司法的正當(dāng)性方面存在差異。初始章程是公司在成立時(shí)設(shè)定的章程,這時(shí)的章程要充分考慮投資者的利益,否則會(huì)是股票價(jià)格不斷下跌,因此,發(fā)起人不敢輕易在章程中加入對(duì)投資者明顯不利的條款。因此,這一階段所表現(xiàn)的市場(chǎng)機(jī)制作用就比較明顯,最終達(dá)成了最優(yōu)選擇。正如合同主義者認(rèn)為的那樣,公司參與方對(duì)公司具體事務(wù)的了解程度必然比立法者多,因此,這時(shí)法律的介入很可能不太適宜。但是公司法規(guī)則可以通過賦權(quán)性規(guī)則和補(bǔ)充性規(guī)則來“潛入”合約中,在充分考量了理性的協(xié)商安排后,使標(biāo)準(zhǔn)合同機(jī)制發(fā)揮得更加充分。但是,由于過于“無法無天”就會(huì)給投資者帶來擔(dān)憂,所以發(fā)起人不會(huì)在章程中“選掉”過多的公司法規(guī)則。除了初始章程,還要考慮后續(xù)章程的修改,如果參與方的合意不夠充分,投資者不滿意,就會(huì)拒絕購買股票,隨時(shí)會(huì)造成股東被盤剝的結(jié)果。管理層不必承擔(dān)全部的冒險(xiǎn)成本,極有可能修改章程,造成對(duì)股東不利的影響,這與初始章程的情況大不相同。
其次,初始章程約定可以通過章程修改來“選掉”公司法規(guī)則的分析。當(dāng)進(jìn)入了成長(zhǎng)期后,公司會(huì)根據(jù)內(nèi)外部環(huán)境變化對(duì)內(nèi)部治理規(guī)則進(jìn)行調(diào)整,公司規(guī)章制度的調(diào)整需要股東的一致認(rèn)可,但是這在現(xiàn)實(shí)中極難實(shí)現(xiàn),因?yàn)楣竟蓶|眾多,分布大江南北,要召集在一起將產(chǎn)生很大的成本,所以公司法規(guī)定2/3以上的股東票數(shù)即可通過。在公司的初始章程中,股東能夠自行設(shè)立一套修改章程的規(guī)則,允許其“選掉”公司法中的某些規(guī)定。但是一些公司會(huì)在初始章程中引入不同于公司法規(guī)定的章程,再在后續(xù)的修改過程中進(jìn)行“選掉”,這就引發(fā)了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公司能夠通過修改章程而排除一切相應(yīng)的公司法規(guī)則。這種情況會(huì)使遠(yuǎn)離公司經(jīng)營(yíng)的小股東面臨巨大的不安全感,從而放棄加入公司,所以這一問題只存在于理論上。第二,初始章程逐條舉例的方式能夠通過章程修改而排除公司法使用事項(xiàng)。在訂立初始章程之初,必須依靠公司法發(fā)揮規(guī)則補(bǔ)充作用,況且這時(shí)的股東各方合意也并不完全充分,面對(duì)的是公司長(zhǎng)期經(jīng)營(yíng)中的復(fù)雜多變的環(huán)境,因此這一設(shè)想根本無法實(shí)現(xiàn),不可能毫無遺漏的將章程修改所面臨的所有問題的進(jìn)行界定。
3.通過后續(xù)章程修改以“選掉”公司法的弊病分析。較大的市場(chǎng)壓力能夠避免在初始章程中設(shè)立不利于股東的條款,但是在后續(xù)的章程修改中則并不如此,通過修改章程可能會(huì)面臨意想不到的問題。首先,董事會(huì)提出的議案可能會(huì)損害股東利益。在大多數(shù)實(shí)際操作中,董事會(huì)和股東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信息不對(duì)稱,參與投票的股東并不了解董事會(huì)所提議案是否對(duì)股東有利,使得這些股東存在著很大的認(rèn)知困難。除非事關(guān)體大,否則股東很難進(jìn)行足夠的調(diào)查和分析,即便是知情的大股東向中小股東傳達(dá)了相關(guān)事項(xiàng),也會(huì)因?yàn)閭鬟f成本而望而卻步。甚至一些中小股東對(duì)獲知信息根本不感興趣,打消了大股東的積極性。其次,即使董事會(huì)提出的議案有損股東利益,也不一定能夠獲得股東的多數(shù)通過票。如果公司修改章程的議案不利于股東,股東意識(shí)到問題后,議案將不可能通過,但是這一論斷缺乏理論和實(shí)踐的檢驗(yàn)。股票價(jià)格反映了公司長(zhǎng)期經(jīng)營(yíng)和發(fā)展的變化,很難將市場(chǎng)對(duì)章程修改的反映單獨(dú)列出并加以分析。同時(shí),股票價(jià)格對(duì)章程修改的反映不是及時(shí)性的,而是一個(gè)逐漸顯現(xiàn)的過程,使得考查更為困難,只有市場(chǎng)預(yù)見到的章程修改議案才能通過,股票價(jià)格才會(huì)回落。在心理上,股東只有非常清楚的知道議案對(duì)自身不利才會(huì)提反對(duì)票,否則,輕易的反對(duì)票可能會(huì)對(duì)自身不利。綜上所述,在初始章程中寫入“選掉”公司法規(guī)則條款,有較強(qiáng)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而通過后續(xù)的章程修改則大大減少了正當(dāng)性基礎(chǔ)。
參考文獻(xiàn):
[1]羅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路徑與公司法規(guī)則的正當(dāng)性[J].法學(xué)研究,2010(2).
[2]吳弘,李霖.我國(guó)公司章程的實(shí)踐問題與法理分析[J].法學(xué)研究,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