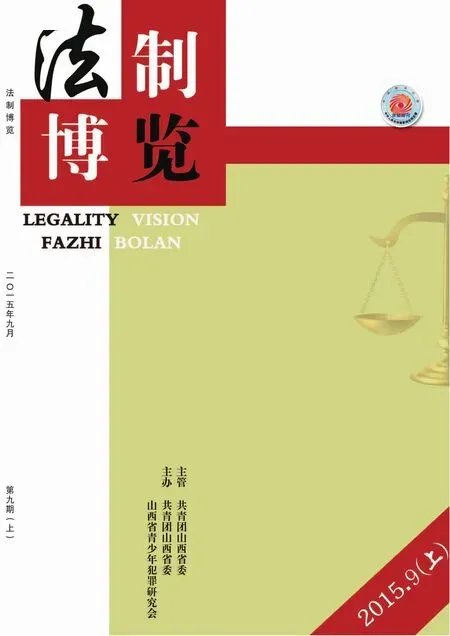犯罪化邏輯研究
犯罪化邏輯研究*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14YJC840031) :轉型期非理性犯罪調查研究。
溫建輝
天津科技大學法政學院,天津300222
摘要:犯罪化邏輯附存于刑事訴訟三大基本原則:證據充分、罪責自負和刑罰正當。其核心思想是:犯罪行為是犯罪結果發生的充分條件,刑罰是應對犯罪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責任自負原則的邏輯要求是共犯脫離的認定標準。刑法上的故意行為和過失行為都是犯罪結果發生的充分條件。共同犯罪包括共同故意犯罪和共同過失犯罪,各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應運用犯罪化邏輯具體分析。
關鍵詞:犯罪化;證據充分;責任自負;刑罰正當性;共犯脫離
中圖分類號:D914文獻標識碼: A
作者簡介:溫建輝,法學博士,天津科技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控告申訴處副處長。
犯罪化是危害行為被認定為犯罪的過程,它包括立法機關將危害行為規定為犯罪的立法活動和司法機關將危害行為認定為犯罪的司法活動。犯罪化作為確定罪與非罪的實踐活動,蘊涵著判斷大是大非的邏輯標準。大道至簡、以簡馭繁,探求和掌握犯罪化的邏輯規律,對于正確理解和準確適用刑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犯罪化的邏輯基礎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邏輯是法律的底線。犯罪化的邏輯附存于刑事訴訟三大基本原則:證據充分、罪責自負和刑罰正當。
(一)“證據充分”的邏輯要求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認定犯罪“證據充分”的要求。第五十三條規定,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1)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2)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3)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做出有罪判決。法律多處規定了“證據充分”的要求,這一定罪標準蘊涵了危害行為只能是危害結果發生的充分條件或者充要條件,最低要求是充分條件。否則,便不能達到排除合理懷疑。
(二)罪責自負的邏輯要求
刑法有一個罪責自負的原則,責任自負原則起始于反對誅連制度,已經發展為現代刑事法制的基本原則。責任自負的本質是反對刑及無辜,那么,排斥非由行為自身引起的危害后果的責任承擔,便是其應有之意。責任自負原則的意蘊和證據充分的要求異曲同工。因此,無論是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它們都是危害社會的充分條件。
對于片面停止共同犯罪的,能否成立犯罪中止,取決于繼行者的情況:如果沒有脫離者的先前共犯行為,繼行者的犯罪行為便不能得逞的,退出行為不成立共犯脫離;而如果沒有退出者的先前共犯行為,繼行者的犯罪行為仍然能夠得逞的,即繼行者的行為是犯罪結果的充分條件,這種情況下,認定退出者的退出行為成立犯罪中止,對繼行者犯罪行為的定罪處罰也不會冤枉無辜。例如,甲和乙合謀殺死丙,在去往丙居住地的路途上,乙突發善心,決意不再殺丙,與甲商議并勸說無效,單獨返回,甲則繼續前往并殺死丙。此案,倘若沒有乙的參加,甲依然決心殺丙,并且以單獨之力,殺死丙也是完全能夠實現,也就是甲的行為是殺死丙的充分條件,這種情況,乙成立犯罪中止,甲成立犯罪既遂。倘若無乙的先前參與,甲便不能夠以單獨之智謀和人力,得逞殺死丙的犯罪目的,這樣的情況,乙不能成立共犯脫離,而是和甲共同成立犯罪既遂。
(三)刑罰正當性的邏輯意蘊
一個危害行為的犯罪化,是否合理恰當,實質是看以刑罰應對該行為是否必要。比如某甲仇殺某乙未遂,就有必要對某乙施以刑罰來預防某乙的繼續殺人行為。如果刑罰不為應對該行為所必要,則該犯罪化就不是合理的。換言之,只有以刑罰應對該行為為必要條件的情況下,刑罰才是正當的。這就是犯罪化的基本邏輯。
犯罪化應當具備必要性的條件,即對犯罪行為施以刑罰是懲罰和預防犯罪結果發生所必要的。在邏輯的世界里,作為必要條件關系的后件,都是前件的充分條件,那么,犯罪結果的發生就是適用刑罰的充分條件。可見,刑罰正當性的內在邏輯就是犯罪行為、犯罪結果與刑罰之間的邏輯關系。具體而言,刑罰是應對犯罪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犯罪結果的發生是犯罪行為的必要條件。易言之,犯罪行為是犯罪結果發生的充分條件,犯罪結果的發生是采取刑罰措施的充分條件。
刑罰不僅存在用刑過當的問題,也有刑罰缺位或者不足的問題。倘若刑罰在應對可致重大危害結果的行為上缺位或者不足時,刑罰就不是合理的。例如,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調控僅限于食品的生產行為、銷售行為和監管瀆職行為。而食用農產品的種植、養殖以及食品的流通環節發生的食品安全問題,由于刑法沒有明確的規定而難以準確定罪處罰。[1]
刑罰的正當性游離于犯罪化與非犯罪化之間,在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存在兩可之時,應當優先非犯罪化。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相反相成,犯罪化的邊界由非犯罪化確定。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由立法者通過立法手段將某種原本為罪的行為剔除出刑法的規制范圍;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某種罪刑規范在刑法上并未發生變化,但司法機關通過相
關司法活動,對原本構成犯罪的行為,不按照犯罪處理的情況。[2]
二、危害行為的犯罪化邏輯
危害行為按照是否直接故意可以劃分為直接故意行為和非直接故意行為,因此,犯罪化也就是對這兩類危害行為的認定。
(一)直接故意行為的犯罪化邏輯
直接故意行為,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發生的行為。這種行為是一種積極追求危害結果發生的行為。這種行為在危害結果沒有實現之前,行為人是不會停止該行為的。不言自明,直接故意行為是危害結果發生的充分條件。
對危害行為的犯罪化,一定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避免一刀切而造成冤枉無辜。例如,“見死不救”從道德視角可分為三種:損人利己的見死不救;利人利己的見死不救和損己利人的見死不救。損人利己的見死不救,是嚴重違背道德的行為,必須入刑;利人利己的見死不救,是一定程度的違背道德的行為,可以入刑;損己利人的見死不救,并不違背基本道德要求,可不入刑。[3]
對于直接故意犯罪行為的刑罰適用,在危害結果沒有發生之前進入審判程序的,應當適用刑罰來預防危害結果的發生。這種情況主要適用于犯罪預備行為和犯罪未遂行為。因為對它們不施以刑罰措施,它們會繼續危害行為,直到危害結果的發生。而在危害結果發生后進入審判的,只能給予刑事懲罰。在危害結果發生之前采取措施預防危害結果的發生,自然比危害結果發生之后的懲罰要好,但在防不勝防的情況下,犯罪的危害結果發生了,也只能付諸于懲罰。犯罪中止行為通常造成的危害較小,所以應當減輕處罰;犯罪中止沒有造成損害結果的,就不應考慮懲罰,而從預防的角度而言,也沒有必要,所以應當免除刑罰。
(二)非直接故意行為的犯罪化邏輯
非直接故意行為包括間接故意行為、和過失行為,過失行為又包括過于自信的過失行為和疏忽大意的過失行為。對非直接故意行為的犯罪化,長期存在著危害結果發生就定罪、沒有發生就不定罪的聽天由命的宿命論思想,為了破除這種唯心主義觀念,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實踐中貫徹唯物主義決定論,切實做到罪責自負,就必需遵循犯罪化的基本邏輯。
對于非直接故意危害行為的犯罪化,為了貫徹罪責自負的原則,不致冤枉無辜,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充分的標準,就必須保證非直接故意的危害行為是犯罪構成結果發生的充分條件。這點與直接故意危害行為犯罪化略有不同,直接故意危害行為可以是犯罪結果發生的充要條件、充分條件或者必要條件。[4]這是因為直接故意犯罪是追求犯罪結果的發生,行為的目標是實現犯罪結果,即便直接故意的“危害行為”是犯罪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但直接故意的“犯罪行為”必然是犯罪結果發生的充分條件,所以,對直接故意的危害行為適用刑罰不會冤枉無辜。
三、共同犯罪的犯罪化邏輯
犯罪化的一般邏輯和認定共犯的特殊邏輯,共同構成了共同犯罪的犯罪化邏輯。
(一)共犯范圍的犯罪化邏輯
我國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這一規定是共犯理論通說的根據,它阻遏了共同過失犯罪成立的通道。正確理解此處的“共同故意犯罪”是理解成立共同犯罪的核心和關鍵。“共同故意犯罪”是一個偏正結構,即“共同故意犯罪=共同故意+犯罪”,而不能理解為“共同故意犯罪=共同+故意犯罪”。當前我國學者認為共同過失犯罪缺乏立法依據,就是基于這樣的誤解。[5]可見,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不僅是共同故意犯罪的立法規定,也是共同過失犯罪的法律依據。
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論處。此處的“共同過失犯罪”,應當理解為“共同過失+犯罪≠共同犯罪”,而不是“共同+過失犯罪≠共同犯罪”。這樣,就拋棄了對“共同過失犯罪”的誤解,理解了其真實的立法涵義,共同過失犯罪成立的立法障礙就解除了。因此,共同過失犯罪不僅沒有立法障礙,而且廣泛存在于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從犯等范圍。[5]
(二)共犯形態的犯罪化邏輯
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規定,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該款規定的邏輯意蘊是,首要分子的組織、領導作用是集團所有罪行和危害后果的充分條件,所以,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施以刑罰就是必要條件。第四款規定,對于第三款規定以外的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該款規定的邏輯也是顯而易見的,除了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之外的主犯以及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他們都是罪行和危害后果直接實施者和制造者,他們的行為是犯罪后果的充分條件,所以,對他們施以刑罰也是必要的。
第二十七條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對于從犯而言,如果他的行為既非犯罪結果的充分條件也非必要條件,那么,應當免除處罰;如果他的行為不是犯罪結果的充分條件,而是必要條件,那么,應當減輕處罰;如果他的行為是犯罪結果的充分條件,但不是必要條件,那么,應當從輕處罰。
第二十八條規定,對于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對于脅從犯而言,如果他的行為是犯罪結果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那么,應當減輕處罰;如果他的行為不是犯罪結果的充分條件,但是必要條件,那么,應當免輕處罰。
第二十九條第一、二款規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這是因為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而根據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對同樣犯罪應當給予同樣處罰,所以,為了保持刑罰總量與該共同犯罪相適應,就應當對教唆犯從重處罰。
參考文獻[]
[1]仝其憲.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分析[J].理論探索,2014(3) :116.
[2]賈學勝.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適用探討[J].理論探索,2013(2) :124.
[3]聶長建.“見死不救”的法律界限思考[J].理論探索,2012(3) :131.
[4]溫建輝.刑法因果關系新思考[J].理論探索,2014(1) :119.
[5]溫建輝.共同過失犯罪新解[J].理論探索,2015(4) :1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