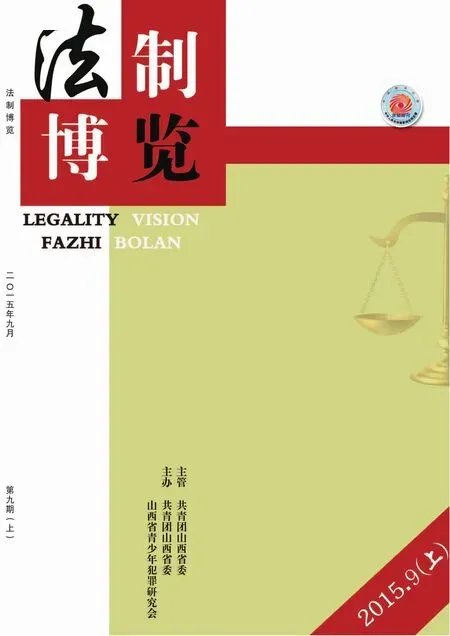淺談職務犯罪初查制度
王 睿
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檢察局,天津300000
隨著職務犯罪形勢的日益嚴峻,辦案難度自然也是越來越大,而初查的地位不斷提升,早已成為了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必經環節。盡管,職務犯罪案件仍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由于現在檢察機關查案越來越強調其主動性,初查質量如何往往就可以決定偵查行動的成敗。
一、初查制度的積極作用
(一)規范辦案活動,預防偵查權濫用
刑事訴訟應具有雙重功能,在控制、打擊犯罪的同時,要能保障公民人身權利不受偵查權濫用或隨意放大的侵害。檢察機關工作中一直面臨著雙重任務,那就是不僅要嚴肅查處貪污賄賂、瀆職侵權職務犯罪,而且還要切實保障人權。初查行為對不符合實際的舉報和線索反映予以排除,避免了單單憑借偵查人員主觀意志就認為存在犯罪事實而予以立案的現象,從而造成對公民權利造成侵害的結果。我們很容易看到,確立初查制度使得檢察機關偵查質量得以提升,立案起訴數量和比例也有了顯著的提高。
(二)加強了查處能力
職務犯罪案件一般沒有明顯的犯罪現場和危害結果,也沒有直觀易得的信息,犯罪嫌疑人有時涉及各個行業,反偵察能力突出,所以檢察機關的初查是以秘密為主、公開為輔。秘密的初查活動可以保證檢察機關收集證據、詢問證人可在不驚動被調查人的情況下實行,為檢察機關決定是否立案奠定的基礎。“相對偵查而言,初查具有時間上的優勢。在初查期間,被舉報人、被控告人未被驚動,對檢察機關的行動和意圖不知曉,缺乏思想準備,便于獲取可靠的證據材料。為立案鋪平道路。初查搞好了,可以有效排除各種阻力和干擾,加快辦案進度,提高辦案效率。”[1]職務犯罪案件大多數的舉報是根據表象推測的,而且舉報的動機不明確,所以內容夸張,失真現象十分普遍。檢察機關一旦盲目啟動偵查,很有可能冤枉了好人,甚至驚動真正的犯罪者,給整個偵查活動帶了極大阻力,然而通過初查,在一個相對自主寬泛的時間里而進行的活動,就可以為準確判斷是否有犯罪事實打好基礎。
二、初查制度的現實困境
(一)缺乏規范明確的操作規定
初查手段和其他偵查手段一樣其自身對公民權利是具有攻擊性的,如果運用上不加以規制,也很其可能被濫用,對公民權利造成侵害。“社會必須有權逮捕、搜查、監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這種權利運用得當,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衛者。但是這種權利也可能被濫用,而如果它被人濫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風。”[2]初查在實際操作中地位越來越高,內容也越來越豐富,理應有比較嚴密和具體的操作規范支持其運行,但是我國對初查活動的規定卻比較原則,很難涵蓋初查活動的具體內容。比如雖然有不得對被查對象采取人身強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但是對于如何防范實踐中容易發生的變相限制人身自由、處分財產的行為,卻沒有具體的操作規范。除此之外,各地的檢察機關結合自身實踐情況也制定了不少初查活動規范,但是由于這些規范還是很難突破現行法律和最高檢的原則要求,在平衡初查行為上并無太大作為。
(二)初查過程缺少有效的監督
每一種權力都需要必不可少的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就會瀕于失控,從而滋生貪污腐敗現象。職務犯罪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在初查的領域涉及到的人員大部分擁有一定的權力,甚至可能是國家機關的要害崗位,所以面對這些人員檢察機關的工作過程較為敏感,牽扯的權力力量也較多。故而,在實踐中,缺少有效監督的職務犯罪初查過程就極易被不法分子鉆了空子,成為私人打擊報復的工具或者成為保護腐敗的手段。職務犯罪初查本身的隱蔽性強、辦案手段彈性大,加之現在我國對職務犯罪初查還尚未明確規定的狀況,造成現如今內部監督的止于形式、不善監督、監督不到位的情況比比皆是。所以,職務犯罪的初查不僅僅要從法律上明確和細化,更要結合外部監督機制,例如社會監督、行政機關監督、權利機關監督等等,與內部監督形成一道關于職務犯罪初查的保護墻,共同作用,以確保對職務犯罪的監督立竿見影。
(三)初查手段對辦案效能的制約
初查期間,檢察機關收集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實的證據是可以采取詢問、調取書證、物證等多種手段的。但是在在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職務犯罪越來越智能化,犯罪嫌疑人反偵察能力越來越高,檢察機關采取的這些手段可以說是捉襟見肘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影響了初查工作的效率,如此窘境是與黨和國家反腐敗決心不相稱的,隨著法治的不斷發展,對檢察機關的偵查行為限制越來越多的同時,對偵查手段效能的呼聲也愈發強烈了。畢竟,將隱藏在暗處的犯罪分子挖出來是初查的首要任務,而如果其連最基本的有效性都很難充分實現,單單依靠偵查人員個人能力,甚至是運氣發現的話,無異于給一個過馬路的盲人帶上眼罩。
三、初查制度改革建議
(一)規范化建設初查制度
在我們國家,或許還需要一些時間準備完善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初查制度,而作為檢察機關應當做的是持續加強建設規范化,完善初查程序,規范初查方法,使得初查體現公正和效率的價值。初查的地位應體現在兩方面,也就是初查所獲得的證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和初查在公眾心里的認可度。對于任何一種制度,嚴格、規范的運作規則可以比隨意妄為的操作產生更大的威力,就像書面比口頭更有約束力一般,面對立法和相關制度不夠健全完善的局面,只有更細致明確的規則運用才能實現民眾廣泛認可的最大權威。當然,規范化應該是全方位的,除了對初查行為自身的規范外,我們平時還應該注重包括與初查相關的配套制度上的建立,比如,線索管理、初查和偵查評價機制等等。
(二)建立科學的偵查評價制度
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犯罪嫌疑人如此,偵查人員也是如此,偵查人員最后可以得到怎樣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其偵查行為的態度和方式。所以,偵查效益的評價制度對偵查制度在實踐中的操作起著關鍵的引導作用。一個不合理的評價制度,會產生不可小覷的副作用,甚至會是偵查行為背離法律的本意,一個好的評價制度是應側重于效益原則的。“職務犯罪偵查管理的優化,體現在偵查效益的差別上,就是要‘花最少的力辦更好、更多的案’”。[3]在實務中,我們的初查及偵查的評價制度,往往是唯立案為優,有時對撤案和無罪判決極端的否定。筆者認為,當前對初查及偵查的效益評價應該從兩個環節進行改進,首先是經過初查,如果排除了犯罪嫌疑,也應當將其作為評價的重要內容,因為刑事訴訟效益的評價不僅要關注查處了多少犯罪,也要注重避免了多少無罪之人可能受到的不當追究。其次,要建立完善撤案分級評價制度,偵查人員查明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不是作案者理應包括在立案偵查的結果中,撤案很正常,是檢察機關實事求是、公正執法的體現,容忍合理”錯案“也能使偵查人員保持良好的偵查心態,提高工作的整體效率。
四、結論
嚴格來說,初查制度現如今的地位或許與其實際的地位有些不相稱,畢竟世界上可參考的經驗也不是很多,刑事審前程序規范的優化無疑對國家打擊犯罪和保護公民權利有著積極的意義,筆者限于知識和能力,本文所析問題還停留在表面,不能觸及問題的根本性層面,但是筆者相信,隨著法治發展的不斷進步,初查制度也必將不斷得到推進。
[1]徐祖斌.案件初查工作探討[J].中國刑事法雜志,1995(3).
[2]丹寧勛爵[英].法律的正當程序[M].李克強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9.
[3]詹復亮.職務犯罪偵查熱點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