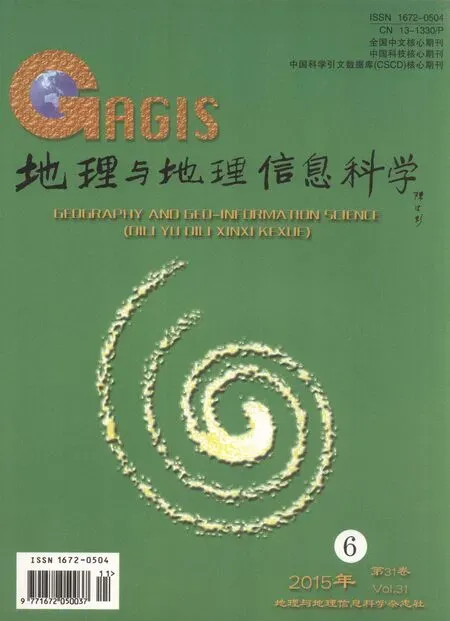不同比例尺地圖水系目標變化探測方法研究
王 曉 密,趙 彬 彬,2,鄧 敏*,彭 東 亮
(1.中南大學地理信息系,湖南 長沙 410083;2.長沙理工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4)
0 引言
現勢性是衡量空間數據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為保持空間數據的現勢性,需對地理空間數據庫進行持續更新[1,2]。在當前制圖綜合技術遠未達到自動、智能化的情況下,對不同比例尺地圖更新的一個有效方法是以現勢性弱的較小比例尺地圖為參考,基于現勢性強的較大比例尺地圖發現、探測變化信息并對較小比例尺地圖進行級聯更新,該方法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等優勢,其中一個關鍵環節是探測不同現勢性的不同比例尺地圖間的變化信息。因此,本文以水系目標為例,研究不同現勢性的不同比例尺地圖變化信息探測方法。
在不同比例尺地圖中,不同詳細程度的同一水系目標其幾何形狀、表達維度等差異較大,如小比例尺地圖中呈線狀,大比例尺地圖中呈面狀,因而需分別對線狀和面狀水系目標進行變化分類并研究其探測方法。目前,已有不少空間目標變化分類與探測方法[3,4],例如:唐爐亮等區分了新增、刪除、變化3種線狀圖形變化類型[5];吳建華等將面目標變化情況分為面積變化、移位、消失、綜合和新增[6];Claramunt等針對時空動態數據,將地塊數據變化類型分為8種[7];Zhou等綜合考慮時間上的不相鄰性,將變化類型歸納為出現、消失、屬性變化、擴大、縮小、變形、移動、旋轉和重現9種[8]。分析可知,目前方法主要集中在對相同尺度同一數據類別空間目標變化分類、探測的研究,對不同比例尺間不同數據類別共存的情況分析較少。然而,空間目標變化探測過程中,若忽略地圖尺度的差異,則將導致變化類型判斷錯誤,如圖1a所示,面目標A2的面積因制圖綜合操作產生的表達差異被誤判為真實變化;若忽略線狀和面狀目標的維度差異,亦將導致變化類型判斷錯誤,如圖1,較大比例尺地圖面目標A5因制圖綜合操作“降維”后在較小比例尺地圖無同名面目標,被誤判為“消失”。
為此,本文顧及不同比例尺地圖水系目標表達的幾何和維度差異,將線狀水系目標變化類型分為出現、消失、延伸、收縮4種,將面狀水系目標變化類型歸納為出現、消失、收縮、擴張、移動、旋轉、分裂、合并和先分裂后合并9種,該方法顧及線狀、面狀單目標及多目標變化類型,可推廣應用于居民地、湖泊等面目標數據以及道路、河流等線、面目標或線面共存的情況,本文分別探討不同比例尺地圖水系目標的各種變化類型描述與探測方法。

圖1 忽略地圖尺度和空間目標維度差異易導致的變化誤判斷Fig.1 Misjudging change types regardless of the scale and dimension
1 不同比例尺地圖線狀和面狀水系目標變化描述與探測
對于表達同一地區而現勢性不同的兩個比例尺地圖,現勢性強的較大比例尺地圖(記為ML)與現勢性弱的較小比例尺地圖(記為MS)中同名目標對應模式分為1∶0、0∶1、1∶1、1∶M、N∶1及N∶M6種[9]。受制圖精度限制,空間目標在不同比例尺地圖中存在表達差異,這6種模式綜合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地物真實變化和制圖綜合操作的作用(表1)。因而,在分析、獲取不同比例尺地圖空間目標變化信息時,須考慮制圖綜合的影響,即比例尺引起的地圖表達差異。下文分別描述線狀和面狀水系目標的變化信息,進而探討各種類型變化的探測方法。
1.1 線狀水系目標變化描述與判別
在較大比例尺地圖中,水系目標(如河流、溝渠)以條帶狀面目標表示,在中比例尺地圖中水系目標常以面目標和線目標結合的方式表達,在較小比例尺地圖中常以線目標表達[10]。為更準確地獲取線狀水系目標變化信息,對于同時涉及線狀和面狀水系目標的情形,則先對面狀水系目標進行“中軸化”[11]。表2列出了線狀水系目標的變化類型,具體判別流程如圖2所示。

表1 水系同名目標對應模式與變化類型映射關系Table 1 Mapping of hydrographic objects′corresponding mode and change classification
(1)出現。“出現”是指較大比例尺地圖 ML中的目標在較小比例尺地圖MS中不存在。根據制圖綜合過程中“選取”操作原則,若較小比例尺地圖MS上目標Be長度小于閾值δl則不被“選取”[12,13],當目標長度大于閾值δl時(如表2中B6),則判定為新出現的目標,判別規則為:
(2)消失。“消失”是指較小比例尺地圖 MS中目標Af在較大比例尺地圖ML中不存在。在表2中,較小比例尺地圖MS中目標A10是因氣候、降水量等原因而干涸的河流,在較大比例尺地圖ML中不復存在,變化類型即為“消失”,判別規則為:
1.2 面狀水系目標變化描述與判別
面狀水系目標的變化類型主要包括出現、消失、收縮、擴張、移動、旋轉、分裂、合并和先分裂后合并9種,變化類型判別流程如圖3所示,下文分別對各種變化類型進行描述。

圖3 面狀目標變化類型判別的具體流程Fig.3 Flow chart of change type identification of areal hydrographic objects
(1)出現。“出現”是指較大比例尺地圖 ML中目標在較小比例尺地圖MS中不存在。隨著地圖比例尺的縮小,受圖幅載荷量限制,大比例尺地圖中某些目標因制圖操作而被舍去,因此需區分真實出現及制圖操作影響兩種情況。通過對制圖綜合過程選取與刪除目標時應考慮的因素分析可知[12],在制圖概括時,將圖上面積小于閾值δS的目標進行綜合刪除處理[12,13]。因此,當1∶0模式的目標Be面積超出閾值δS時(表2),則判定為新出現的目標,判別規則為:
(2)消失。“消失”是指地圖 MS中的目標Af在地圖ML中不存在。如表2中,A1為因干涸等原因而消失的目標,在較大比例尺地圖ML中不復存在,變化類型即為“消失”,判別規則為:
(3)收縮。“收縮”是指地圖 MS中的目標Af在地圖ML中面積變小,考慮到同名目標的面積差異,當同名目標面積差異ω(Af,Be)在制圖綜合精度允許范圍ξ(Af,Be)內或者變化面積值在地圖最小面積閾值δS范圍內時[14,15],認為是制圖影響的結果,判別為無變化;反之認為發生了變化。其中,
參數ω(Af,Be)度量Af與Be的相交程度。相交程度越高,ω(Af,Be)值越小,即幾何形狀差異越大ω(Af,Be)值越大。ξ(Af,Be)表示制圖精度εS導致的Af與Be幾何形狀差異值,其中Bε、B-ε表示Be向內和向外建立的大小為ε的緩沖區。當ω(Af,Be)小于ξ(Af,Be)時,判定目標無變化,反之認為發生了變化。如表2中A11向內“收縮”1 km2,收縮程度用變化前后面積差值度量,其變化前后幾何形狀差異超出制圖精度允許范圍且變化后面積縮小了,則認為發生了“收縮”變化,判別規則為:

(4)擴張。“擴張”是指地圖 MS中的目標Af在地圖ML中面積變大,當“擴張”變化前后目標幾何形狀差異ω(Af,Be)超出制圖綜合允許范圍ξ(Af,Be),且擴張面積大于δS,則認為目標發生了“擴張”變化,如表2中MS中目標A0因蓄水量增加,其在ML中的同名目標B9面積增加,發生“擴張”變化,擴張程度用變化前后面積差值度量,判別規則為:

(5)移動。“移動”是指地圖 MS中的目標Af在地圖ML中位置發生變化,當目標位置變化前后幾何形狀差異ω(Af,Be)超出ξ(Af,Be),其平移距離大于制圖精度ε,認為發生“移動”變化,目標移動變化量用距離和方向度量,距離用變化前后目標中心點間距度量,方向則采用4方向法計算。表2中,A7向北(N)移動了10 m,判別規則為:
其中,AC和BC分別為Af和Be的中心,dir(AC,BC)為“移動”前后中心連線的4方向框架描述。
(6)旋轉。“旋轉”是指目標Af繞其中心旋轉角度θ,當目標旋轉變化前后幾何形狀差異ω(Af,Be)超出ξ(Af,Be),認為發生“旋轉”變化,包括旋轉方向和角度值兩個參數。旋轉方向包括順時針和逆時針,旋轉角度即目標繞其中心轉動的角度值,如表2,目標A4繞其中心逆時針旋轉15°,在ML中的同名目標B4整體亦發生旋轉,判別規則為:
其中,逆時針旋轉時,θ取正值,反之,θ取負值。
2 實驗及結果分析
以內地某市同一區域1∶2 000(面狀目標713個,線狀目標151個)和1∶10 000(面狀目標220個,線狀目標56個)的水系數據為實驗對象(圖4),根據表3中設 定 的 閾 值[13,14,17],并 按 上 述 的 變 化 探 測 與表達流程進行實驗,證明變化探測結果準確(圖5(見封2)、圖6),統計結果列于表4。

圖4 不同比例尺水系數據Fig.4 Hydrographic data at different scales

表4 水系數據變化探測結果統計Table 4 Summary of change detection results of hydrographic data
分析可知,該市水系變化類型復雜多樣,這與當地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決策下的人類活動密切相關[18]。如表4,共探測出111處變化,其中主要變化類型為“消失”,共40處,約占總變化數的36.0%,“分裂”、“收縮”、“移動”變化分別發生9處、11處、7處,約占總變化類型的24.3%,其他變化類型約占39.7%。通過對比確認,變化探測結果準確,未出現判別錯誤與遺漏現象,進而驗證了上述變化信息探測與判別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亦為環境監測、生態變化評估等實際應用提供了方法參考。
3 結語
變化探測是不同比例尺地圖數據級聯更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已有相關研究在變化類型劃分等方面差別較大,表達不一,為此本文顧及不同比例尺地圖空間目標維度等差異,將水系目標變化歸納為出現、消失、延伸、收縮4種線狀目標變化類型和出現、消失、旋轉、收縮、擴張、移動、分裂、合并及先分裂后合并9種面狀目標變化類型。不同比例尺地圖表達的詳細程度差異導致同一水系目標在不同比例尺地圖中幾何形狀、維度等不同,為此本文針對忽略地圖尺度和目標維度差異等的變化探測方法,分析了其局限性,指出其容易導致空間目標變化判別錯誤等問題,并在本文中予以解決。基于線狀和面狀水系目標變化類型劃分,對每種變化類型進行了詳細描述并提出了相應的判別規則,根據不同比例尺地圖水系目標對應模式,結合判別規則,提出了不同比例尺地圖水系目標變化探測方法及流程。通過不同比例尺地圖水系數據的變化探測實驗,結合實驗區相關文獻記載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證明了本文提出的變化探測方法的正確性和有效性,亦為類似空間目標(如道路等)的變化探測提供了方法參考。由于本文方法考慮的因素較多,還有待提高算法效率。
[1] 朱華吉.地理數據增量信息分類與表達研究[D].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2006.
[2] 應申,李霖,劉萬增,等.版本數據庫中基于目標匹配的變化信息提取與數據更新[J].武漢大學學報(信息科學版),2009,34(6):752-755.
[3] STEFANI C,LUCA L D,V RON P,et al.Reasoning about space-time changes:An approach for modelling the temporal dimension in architectural heritage[A].Proceedings of the IAD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puter Graphics and Visualization[C].2008.287-292.
[4] 徐文祥.基于空間特征碼的矢量要素變化檢測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1.
[5] 唐爐亮,楊必勝,徐開明.基于線狀圖形相似性的道路數據變化檢測[J].武漢大學學報(信息科學版),2008,33(4):367-370.
[6] 吳建華,傅仲良.數據更新中要素變化檢測與匹配方法[J].計算機應用,2008,28(6):1612-1615.
[7] CLARAMUNT C,THéRIAULT M.Managing time in GIS:An event-oriented approach[A].CLIFFORD J,TUZHILIN A.Recent Advances on Temporal Database[C].Zurich Switzerland:Springer-Verlag,1995.
[8] ZHOU X G,CHEN J,JIANG J,et al.Event-based incremental updating of spatial-temporal database[J].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04,11(2):192-198.
[9] 趙彬彬,鄧敏,徐震,等.多尺度地圖面目標匹配的統一規則研究[J].武漢大學學報(信息科學版),2011,36(8):991-993.
[10] 趙彬彬,鄧敏,劉慧敏,等.多尺度地圖的水系面目標與線目標匹配方法與實驗[J].地球信息科學學報,2011,13(3):361-365.
[11] 張立鋒,程鋼,白鴻起.基于Delaunay三角網的河流中線提取方法[J].測繪與空間地理信息,2006,29(4):80-86.
[12] 張偉.基于ARCGIS的土地利用制圖綜合方法研究——以浙江省海鹽縣為例[D].杭州:浙江大學,2006.
[13] 譚笑.基于知識的線狀水系要素自動綜合研究[D].鄭州: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2005.
[14] 國家測繪局測繪標準化研究所.GB/T 20257.2-2006,國家基本比例尺地圖圖式第2部分:1∶5000,1∶10000地形圖圖式[S].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2006.
[15] QI H B.Dete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Changes in Settlements for Automated Digital Map Updating[D].Hong Kong: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2009.
[16] 張利君.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圖綜合方法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1.
[17] 黃萬里,李虎,林廣發.尺度變化的土地利用類型數據的綜合研究[J].地理信息科學學報,2010,12(3):329-334.
[18] 劉新,何隆華,周弛.長江中下游30年來湖泊的水域面積變化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7(4):12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