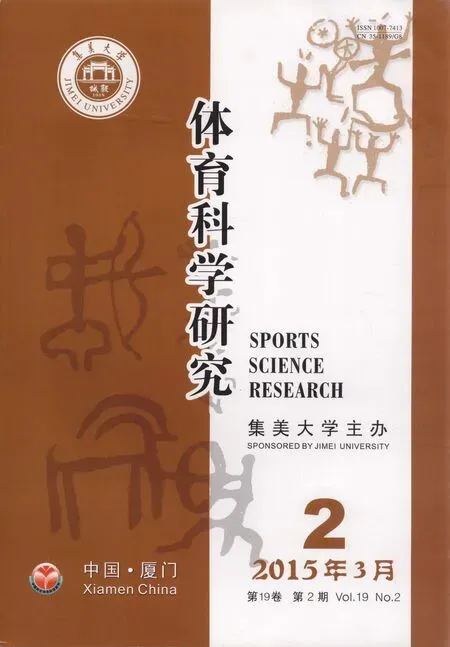弗·培根“假相學說”啟示下體育概念新思考
?
弗·培根“假相學說”啟示下體育概念新思考
李靜
(曲阜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體育概念當屬體育科學的邏輯思維起點,無數體育學者為能夠科學而準確地界定體育這一概念費盡心力。體育概念的研究是一個處于永無止境爭論的思想過程,遺憾的是至今為止學界尚無關于體育概念一致而科學準確的認識成果。本研究基于弗·培根“假相學說”解讀,對“洞穴假相”、“市場假相”、“族類假相”和“劇場假相”內在的基本思想進行剖析,繼而以對體育的正確認識作為基本切入點,沿襲著弗·培根的“假相學說”哲學思想軌跡進行新的思考。
培根在《新工具》中指出:“現在劫持著人類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刻的假相和錯誤的概念,不僅圍困著人們的心靈以至真理不得其門而入,而且即在得到門徑以后,它們也還要在科學剛剛更新之際聚攏一起來攪亂我們,除非人們預先得到危險警告而盡力增強自己以防御它們的猛攻”。人類的理解力不是按部就班的“電腦程序”,它是不安靜的,是充滿想象力的,這使得人們難以擺脫自身的主觀性和片面性,而毫無偏見的認識和理解體育。那么,人類的理解力在無法做到絕對的客觀與公正時,我們該如何正確認識和理解體育概念呢?解讀弗·培根“假相學說”,為我們提供思考的起點和認識體育概念的“新工具”。
1“假相學說”的提出
“假相學說”是為弗·培根的傳統歸納法服務的。培根生活的時代,科學和哲學的發展還受著舊傳統觀念和宗教神學的束縛,知識的狀況既不景氣,也沒有很大的進展。在他看來“現有的科學不能幫助我們找出新事功,現有的邏輯(三段論式)亦不能幫助我們找出新科學”。 被束縛的科學與哲學陷入了悲慘境地,究其思想認識根源,培根認為是“現在劫持著人類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相和錯誤的概念”, 導致人類理解力難以找到進入科學的秘密之門。
對于這些劫持人類理解力的元兇,培根稱之為“假相”。而要清除這些“假相”,矛頭必需先從刺向經院哲學(基督教神學)和古希臘哲學開始,正是它們將科學和哲學弄得一團糟,將人類的理解力變成聽其使喚的奴隸。對于經院哲學,他們把“亞里士多德的好爭而多刺的哲學很不相稱地和宗教的體系糅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極有規則的理論,來維護封建的統治。他們在學術研究上脫離實際、脫離自然躲在寺院中閉門造車,關起門來寫文章,玩弄概念、教條。將不含真理、不切實用的事物作為他們研究的對象,而這樣產生的知識與其說是增加了科學的力量,不如說是摧毀了科學;他們在爭論具體問題時,答案不是指向客觀的自然,而是“在文字上面,或至少是在通俗的概念上面”對一些無關大體的微情末節進行爭辯,最終使爭論變成了一場玩弄概念的文字游戲;對事物的認識他們“依靠于權威、同意、信譽和意見,而不依靠于論證”。他們僅僅“固守在幾個作家的陰洞中”,看起來令人生畏,實際上崇拜的只是虛偽殘缺的影像,結果卻是用一個人的智慧把許多人的才智給毀滅了,最終放棄自己的判斷而淪為他人的信徒,專門去做支持他人的粉飾工具。
然而,對于經院哲學建立的知識體系和古希臘哲學,人們像著了魔一樣地崇拜著,把他們當成權威,當成人類認識和發現真理的根本手段,使科學和哲學陷入了悲慘的境地。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培根寄希望于清除人類理解力中存在的假相和錯誤觀念,以便使人類能夠客觀公正地去認識和理解客觀世界。從“假相學說”的具體內容來看,它不同程度上存在于整個人類認識和實踐過程中,帶有很強的普遍性,所以有必要對假相如何阻礙人類準確認識客觀世界進行詳細分析。同時,也能為準確認識體育概念提供一定的啟示。
2“假相”案例分析
2.1 以往認識經驗之困
人類以往的認識經驗容易對認識新事物產生局限性,這便是洞穴假相。它是個體獨有的假相,人類依據個人所特有的性格、愛好、所處環境和所受教育出發來觀察事物,難免給事物一種“極不真實、極不適當的色彩”。好比人坐在受狹窄天地的限制“洞穴”中,因不能夠正確認識事物的本來面貌,致使自然之光(真理)發生曲直和改變顏色。這種現象的典型案例:體育概念之爭。學者龔正偉將學界對體育本質認識的分歧根源歸結為3個:觀察和認識的角度不同;中西方文字差異導致對體育的理解不同;定義方法的問題。然而學者張軍獻則認為,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張軍獻認為:“我們可以采用不同的角度對同一個事物進行定義,可能選擇的角度不同,使用的語詞不同,但是如果大家表達的是同一個概念,那么就不會存在分歧。”張軍獻“圓”概念來證明這一點:“同一平面內到定點距離等于定長的點的集合”、“平面內到定點的距離相等的封閉曲線”。張軍獻認為學術界雖然對“圓”(幾何學意義上的圓)的定義和本質表述不同,但并不影響我們對其概念的理解。然而,事實上問題并不是如此簡單。之所以不同的“圓”的定義,沒有影響學者們對“圓”的概念的認同,是因為學者們在理解力方面已經完全接受了“圓”概念。不光是學術界,即便是正常人,也知道“圓”(幾何學意義上的圓)是在一張紙上(同一平面內)畫的一個圈(封閉曲線)。正如培根的后繼者洛克所說的那樣,“人們如果對自己所推論、所探究、所爭辯的,都有了所謂確定的觀念,則他們會看到,他們大部分的疑惑和爭論將完全告終”。 體育概念當屬體育科學的邏輯思維起點,無數體育學者為能夠科學而準確地界定體育這一概念費盡心力。遺憾的是,每位學者都以自己心目中懷揣著的體育概念出發,來爭取獲得學界完全認可的體育概念,這樣的體育概念是不會得到完全的認可,究其原因就是人們心中沒有“所謂確定的觀念”。顯然大家追求的是同一個體育概念,最終目的也是要建立一個確定的概念。再者,上述對“圓”的概念的界定,果真本質不同嗎?只要我們認真分析其本質是相同的,只不過是語詞表達不同而已:封閉的曲線只能存在同一平面內;定長的點的集合形成的是直線,直線上的點到定點的距離相同,形成的正是一個封閉的曲線。因此,我們不能讓語詞迷惑我們的思維,只要是同一個事物,無論何種定義,它的真正區別性或者說真正的種屬區別性就應該相同。
2.2 語言對理解力約束之困
由于人類交際當中,語言作為先見對思維的約束限制作用,因不確定、不嚴格的語言概念,而產生思維混亂。培根稱之為“市場假相”。且說語詞,語詞的意義是照著流俗的能力(常人的理解)而構制和應用的。這種現象極為常見,以我國各個地方的村莊名稱為例,許多村莊的名稱來源或依據家族姓氏、地理方位、河流、土地顏色、人類生產生活等經濟活動、自然現象等等。人類往往相信自己的理性能管制語言,但同樣真實的是語言亦反作用于理解力。因此,我們常見學者們的崇高而正式的討論往往以爭辯文字和名稱而告終。
人們在交往中除了使用意義不明確、模棱兩可的語詞外,甚至還會出現同一詞在很多種意義上加以使用的現象。這類語詞往往是“急率而不合規則地從實在方面抽得的”。比如,“體育人文社會學”語詞,它就是典型的多種意義加以使用的語詞。它即可以指代一門學科,也可以指代一門專業,還可以指代一門科學。而這一語詞的由來,同樣是依據俗人(常人)的了解和能力確定的。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頒布《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二級學科、專業目錄》時,規定體育學專業之下只能設置4個二級學科,在這種情形下,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把當時所有的體育學專業學科都包容在這4個學科之中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關鍵。至于劃分的標準是否統一,在當時只能是其次的事情。也正因為此,“體育人文社會學”這個概念被我們創造,而且創造的極為模糊。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再列舉。
2.3 人類本性之困
人類往往采取已有的思想與觀念來理解和認識事物,導致事物的本性受到歪曲。它植根于人性本身中,并非某些人所獨有,被稱為“族類假相”,是針對人類種族具有的一種普遍假相。人類不論感官或者心靈的一切知覺總是依個人的量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尺,而人類理解力則如一面凹凸鏡,它不規則地接受光線,于是就在反映事物的性質時摻入了它自己的性質而使得事物的性質受到歪曲和改變了顏色。而人類思維的過程是利用“先入的判斷”或“跳躍著”來認識和理解事物。然而,培根對人類“先入的判斷”產生的想象極度蔑視。他曾鄭重地指出:“對于理解力切不可賦予翅膀,倒要系以重物,以免它跳躍和飛翔”。事實上,人類想要發現某種新事物或是解釋某種新現象,“先入的判斷”就會“跳躍”出來指導人類實踐。因為新現象新事物的發現、新科學的建立都是建立在已知知識的基礎上的。培根忽視假設,忽視“假設”這種科學方法能夠做出事功。現今,“假設”已成為體育學科中以調查問卷為主的實證研究的重要手段,調查問卷設計的每個問題對應的就是一個“假設”。 然而,不少碩士畢業論文的撰寫,不經過問卷“定義(假設)——調查——結論”的步驟,在調查問卷沒有制定出來的前提下,文章的結論已經寫出來了,當然,這些結論肯定是對他們的論文起到正能量的。然后根據這些結論再制定相應的調查問卷,以滿足自身論文的需要。這樣設計的調查問卷或是帶有很強的誘導性,從而影響了調查結果的客觀性,或是根本就不進行問卷發放,憑空杜撰“客觀事實”。
不只是問卷調查這種科研方法被異化,事實上,以問卷調查為主的實證研究方法也已經被異化,并且對體育學科發展所做的“事功”也是少的可憐。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某些核心類體育期刊上面發表的“實證性”研究論文,有許多是嚴格遵循SPSS統計研究的方法進行“抽樣”、“數據分析”、“數理統計”、“SPSS”曲線和表格進而得出所謂的研究結論,然而,對于從這些高深莫測的數據得出的結論,卻無任何創新和科學意義。例如有學者利用SPSS統計方法研究某地城鄉體育發展一體化得如下結論:
“從表14可知,某地體育組織化程度(SA2=1.683 5)的城鄉差異最大,是影響城鄉體育發展一體化的主要制約因素。中心城區體育鍛煉與活動、體育資源配置綜合評分要略好于遠郊區(縣)(SA1=1.318 9,SA3=1.230 5)”。
“社會體育指導員、體育專項場地設施、……體育法規政策8個二級指標得分大約在1~1.5之間,說明在這些指標下中心城區各項體育事業發展略好于遠郊區”。
且不論全文的實際價值如何,體育學者看到這兩條結論,有何看法?筆者認為體育學者看到此肯定不會驚訝“經濟發達地區的體育發展優于欠發達地區的體育發展”,他或許驚訝的是“SA”的數據是怎么計算得來的。
西方學者歐文·拉茲洛對實證研究在社會科學的過度應用提出了如下的評價:如果說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實證主義橫掃思辨理論,那似乎有可能(甚至應該)將有意義的論斷一一用可測量的“事實”檢驗一番,那么到20世紀中期,有遠見的科學家和哲學家便意識到這個計劃野心太大。因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由價值觀和動機主宰者,包括科學研究,說三道四也罷,置之不理也罷,都未解決問題,只不過把問題暫時敷衍過去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研究方法本身并無對錯、優劣之分,但是對研究方法的過度接受,甚至達到“崇拜”的地步,難免就會對科學的發展造成不良的影響。難免阻礙對體育概念的準確認識,影響著體育科學的發展以及體育科學體系的構建。
2.4 過度迷信權威之困
攪亂人類理解力最為嚴重的假相還不是市場假相,比市場假相更加麻煩的是劇場假相。所謂劇場假相是指人類盲目地接受哲學中的“權威”、“權威論著”、“某些教條”以及一些錯誤的論證法而形成的錯誤認識。培根警告人們要加以預防三種形式的劇場假相。或是建立在普通概念上,或是建立在少數實驗上,或是建立在迷信的各種體系的一些危害不淺的權威。過于迷信權威的劇場假相表現為:有人沉迷于經典理論中某些名詞術語的引用和注釋,有人沉迷于某些研究方法的使用,有人沉迷于某些權威,有人甚至沉迷于自己的思想觀念而沾沾自喜。無論沉迷于何種權威,人們最終將會放棄自己的判斷、放棄前進的動力而淪為權威的信徒,成為權威的粉飾工具。最可怕的是這種錯誤的假相混合前面的假相,最終變成為一種思想體系之后,便很難真正的清除它。
針對體育領域存在的劇場假相,筆者無法肯定地指出哪位體育學者就存在迷信權威的現象,只是想從看似繁榮實質“死氣沉沉”的體育學科發展,來反面證明劇場假相在體育學科中蔓延的很深。通過中國知網以“質疑”、“兼評”、“商榷”為關鍵詞檢索這些批判性文章就會發現,這些批判性文章多集中體育基礎理論某些觀點的“論戰”,沒有一篇文章是對文章“數據”進行質疑的。這些“數據”的可靠性我們不得而知。體育學者固然不可能針對每篇文章的數據去專門進行重新調查,即便是重現調查,由于體育這種社會現象的復雜性,數據往往也很難一致。數據的不一致并不能說明數據造假。從筆者上文談到的某些研究生畢業論文問卷調查的使用情況來看,有些文章的數據是靠不住的。針對“數據”造假問題,在自然科學領域,檢查是相當嚴格的。2009年人民網報道,我國學者在國際期刊《晶體學報》發表的70篇論文涉數據造假,而遭該國際期刊對文章的撤銷。[10]反看我們體育期刊,有的期刊對“實證調查”,且有數據支撐的文章青睞有加。然而,這些文章的數據來源的科學性是否經過嚴格檢查?對于這個問題,筆者不知道體育期刊在錄用文章過程中是否也對文章“數據”的準確性進行檢測,筆者只見識過對于文章過多引用別人數據而退稿的現象。
3結論與建議
根基于弗·培根“假相學說”哲學批判思維的深入探究,發現這些假相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體育概念的界定,進而影響了人們對體育的準確認識,隨后建議人們應當做到以下3點:夯實基礎,創新思維;踏實做學問,不做應景之文;實踐中批判,保證客觀。
第一、夯實基礎,創新思維。對體育概念的準確認識離不開體育基礎知識的普及,體育基礎理論知識的普及和運用,不僅能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基礎理論對未來體育學科發展的重要性,而且可以為無數體育學者提供邏輯思維起點,最終對體育概念的認識達到客觀和公正,推動體育科學的發展。現有的體育基礎理論中問題重重,許多的概念與理論都存在含糊不清的含義,亟待為它們準確定位。許多陳舊僵化的教科書已經再版了多次,其中許多已經引起爭論的問題仍然沒有更正并解決。無盡重復地說著和做著前人已經說過做過的東西,只會讓有志的明白人意識到,如今的體育知識是何等地饑荒和歉收。當缺乏創新的思維成為科學發展的主導,那么科學的進步就會就此終止。在普及基礎理論的基礎上,夯實基礎知識可以保證體育學者們擁有堅固的理論基礎、完善科研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保證日后客觀合理的認識和理解體育。體育學者在進行高深體系的建構之前,必須從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維與心靈精神,這是關乎體育能否向前發展的根本。尤其是對于在校的體育專業類的學生,打好基礎知識迫在眉睫。
第二、踏實做學問,不做應景之文。科學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標說來不外是這樣:把新的發現和新的力量惠贈給人類生活。然而,什么樣的時代社會大背景往往造就了什么樣的學風。社會對知識和學術的重視是其進步的表現,然而當人們急功近利地將學術與榮譽掛鉤時,容易導致學者為學術而學術,形成重明重利的浮躁心理,成就了看似繁榮的學術氛圍。因此,學者要具備“踏實做學問,不做應景之文”的學術素質,培養真科研態度,才能營造健康的學術環境。一個相對潔凈的學術界才會創造出大量的自主創新性科研成果。
第三、實踐中批判,保證客觀。如果在體育實踐中缺乏對其深切反思,體育科學必然會失去其正確的方向。學術批判是保證真理客觀的主要手段。假相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個學者當中,因此,體育學者有必要對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進行深思和質疑,發現思想體系中的缺陷和錯誤,并力爭改正之、完善之。[11]然而,體育學者太缺乏自我批判精神,鮮見哪位學者對自己的學術思想提出過批判并加以改正,他們往往按照自己的學術思想建構著屬于自己的學科體系。雖沒見到公開更正自己思想體系的學者,卻看到了公開支持自己思想的學者。有體育學者曾對其理論做過這樣的肯定:“體育是旨在強化體能的非成產性肢體活動。這是集40年專業思考而得出的明晰結論,不管別人認同與否,我的后續研究全都是基于這個迄今不曾撼動的支點。”[12]堅持自己的理論固然可敬,但不管別人認同與否,一味地堅持自己的理論難免就會走向劇場假相。“真理是時間的女兒”,隨著體育學科的不斷發展,理論的不斷完善,已有的理論定會遭受到新的理論的代替。而批判是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因此,維護好批判精神,體育科學才能健康、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培根.新工具·第一卷[M].許寶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2]武真.談培根的“四假相說”[J].齊魯學刊,1982(6):28-31.
[3]李靜,曹莉.體育學者究竟該如何認識和理解體育——基于弗·培根假相學說的思考[J].體育研究與教育,2014,29(5):24-27.
[4]龔正偉,劉湘溶.體育本質認識的分歧根源與真義求解[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5,4(1):96-98.
[5]張軍獻.尋找虛無上位概念——中國體育本質探索的癥結[J].體育學刊,2010,17(2):1-7.
[6]洛克.人類理解論[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8.
[7]劉建剛,徐亞青,連桂紅.體育人文社會學概念的邏輯辨析[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08,42(12):20-23.
[8]駱秉全,鄭飛.首都城鄉體育發展一體化指標體系與實證研究[J].體育科學,2010,30(11):24-33.
[9]歐文·拉茲洛.人類的內在限度:對當今價值、文化和政治的異端的反思[M].黃覺,閔家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5.
[10]趙亞輝,任江華.《晶體學報》中國論文風波調查:兩年高產70篇論文背后[N].人民日報,2009-12-30(11).
[11]盛輝輝,楊建華.讓學術批判真正成為學術繁榮的內生力量[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01-18(5).
[12]張洪潭.體育與哲學[J].體育與科學,2012,33(2):1-10.
[責任編輯江國平]
摘要:基于弗·培根“假相學說”解讀,對“洞穴假相”“市場假相”“族類假相”和“劇場假相”內在的基本思想進行剖析,繼而以對體育概念的正確認識作為基本切入點,沿襲著弗·培根的“假相學說”哲學思想軌跡進行了與之相應的解讀。研究認為應當做到以下3點:夯實基礎,創新思維;實踐中批判,保證客觀;踏實做學問,不做應景之文。
關鍵詞:弗·培根;假相學說;體育
The New Sports Concept under Francis Bacon’s“Doctrine of the Idols” of Enlightenment ThinkingLI Jing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Francis Bacon’s “Doctrine of the Idols” interpretation of “cave illusion”,“market illusion”,“race illusion” and “theater illu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then make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port as a basic entry point by following the Francis Bacon’s “Doctrine of the Idols” philosophy trajectory of its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Studies suggest that we should do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a solid foundation,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practice of criticism, to ensure objectivity; practical scholarship, not the occasion of the text.
Key words:Francis Bacon; Doctrine of the Idols; sports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413(2015)02-0033-05
作者簡介:李靜(1992—),女,山東菏澤人,在讀碩士。研究方向:體育人文社會學。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 (12CTYJ11)
收稿日期:2014-07-04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