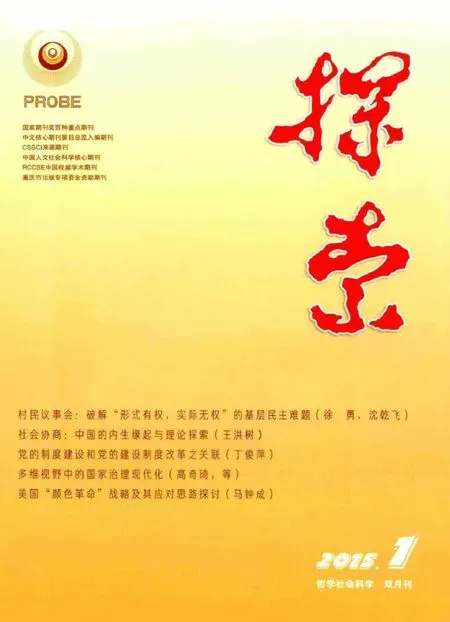國際媒體在非傳統(tǒng)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安全化的視角
(華東政法大學(xué)外語學(xué)院,上海 201620)
此次埃博拉病毒爆發(fā)似乎是從2013年12月6日在西非幾內(nèi)亞境內(nèi)的名叫Meliandou的村子住著的一位2歲男孩身上開始的。他在腹瀉和發(fā)燒后死去,之后被診斷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的母親、3歲的姐姐、奶奶相繼染病死去。然后病毒傳到幾內(nèi)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的居民中。在這之前,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中部和東部僅引起過幾次小規(guī)模的惡性爆發(fā)。此次埃博拉病毒進(jìn)入大爆發(fā)階段,并開始蔓延。然而這次的公共衛(wèi)生安全問題大規(guī)模暴露在國際公眾的視域之下是從2014年8月美國醫(yī)生感染埃博拉病毒事件開始的。國際媒體對此次大爆發(fā)的曝光最早是在2014年3月23日,英國的《星期日泰晤士報(bào)》、《星期日電訊報(bào)》均在3月23日分別刊發(fā)了《該死的埃博拉》(Ebola Blamed),《埃博拉在幾內(nèi)亞大爆發(fā)》(Guinea Ebola Outbreak)。澳大利亞的《澳洲廣告報(bào)》于3月24日刊發(fā)了題為《埃博拉病毒致死34人》(Ebola virus toll hits 34)的報(bào)導(dǎo)。再看看美國《紐約時(shí)報(bào)》的報(bào)道情況:它于6月9日刊發(fā)了第一篇有關(guān)埃博拉的報(bào)道《埃博拉在西非愈發(fā)可怕》(Ebola Gets Worse in West Africa),6月僅有2篇報(bào)道,7月有2篇報(bào)道,8月猛增為46篇報(bào)道,9月有40篇,至10月翻5倍增加至233篇報(bào)道,11月陡然下降仍有61篇報(bào)道。
對此現(xiàn)象,聯(lián)合國前秘書長安南評論說,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地區(qū)早已形勢嚴(yán)峻,但只有當(dāng)出現(xiàn)歐美患者時(shí)國際社會才“真正醒悟過來”。著名雜志《名利場》的撰稿人Andre Carrilho就西方媒體根據(jù)爆發(fā)地的不同和患者的國別區(qū)別,對待傳染病的現(xiàn)象提出了他的看法:“我覺得西方媒體將埃博拉分為第一世界疾病和第三世界疾病,后者的關(guān)注度取決于對我們有多大威脅,而不是以人類承受的苦難這個(gè)通用標(biāo)準(zhǔn)衡量。”[1]
真的只有當(dāng)病毒蔓延到美國和歐洲時(shí),埃博拉于我們才是威脅嗎?事實(shí)上,在全球化的時(shí)代,只要有一架航班出現(xiàn)問題,無論是太平洋的對岸還是另一端的南半球,都不會幸免于難。人們不禁思考:同樣的物質(zhì)性、客觀性的埃博拉病毒,在何時(shí)它是一種威脅,何時(shí)它又不是?又是誰在背后說它是威脅,或者不是?
再來細(xì)看埃博拉病毒被國際媒體高度關(guān)注之前與之后的報(bào)道:早期的媒體報(bào)道用“埃博拉是什么”、“埃博拉的癥狀有哪些”這樣的標(biāo)題,多以介紹埃博拉疾病為主,內(nèi)容深入、詳細(xì),強(qiáng)調(diào)疾病的可怕性。文章自然使用消極、負(fù)面為主的詞匯表達(dá),比如“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無藥可救,對大多感染者都是致命的”等。正如安南受訪時(shí)警告說,媒體持續(xù)“危言聳聽”地傳播埃博拉疫情,將為非洲帶來難以抹去的“陰云”。在兩個(gè)美國人被感染之后,報(bào)道的焦點(diǎn)迅速轉(zhuǎn)變?yōu)樵囼?yàn)藥物和治療方案。文章也以積極、正面的語言為主,比如“治療太了不起了,太迅速了,太立竿見影了”等。當(dāng)出現(xiàn)歐美患者時(shí),國際媒體的報(bào)道由對埃博拉癥狀的圖文介紹轉(zhuǎn)到了現(xiàn)代醫(yī)藥的治療和幸存者的故事[2]。
從關(guān)注的程度和關(guān)注的角度看,此次埃博拉大爆發(fā)的疫情被國際媒體如此區(qū)別對待,讓人們開始關(guān)注到國際媒體在公共衛(wèi)生安全領(lǐng)域的“干預(yù)”。“干預(yù)”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這是一個(gè)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人們可以隱約感到國際媒體在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的治理方面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是一個(gè)值得研究的議題,也是目前被學(xué)術(shù)界忽視的議題。
本文將以建構(gòu)主義安全觀的理論分支安全化作為視角,結(jié)合傳播學(xué)的5W理論和框架理論,論證國際媒體在建構(gòu)安全議題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以國際媒體對非傳統(tǒng)安全的重要議題之一恐怖主義實(shí)施安全化為實(shí)證案例,進(jìn)一步探討國際媒體如何建構(gòu)國際安全議題,評判其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中發(fā)揮的不可小覷的作用。
1 切入視角:安全化理論
1.1 安全化的定義
國際政治領(lǐng)域中的安全研究興起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冷戰(zhàn)結(jié)束,經(jīng)歷了以新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傳統(tǒng)主義安全研究、批評性安全研究和建構(gòu)主義安全研究。在建構(gòu)主義安全研究中,哥本哈根學(xué)派在近些年較受關(guān)注。該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奧利·維夫認(rèn)為,當(dāng)某事物在既定政治結(jié)構(gòu)下無法應(yīng)對,而國家需以超越常規(guī)的方式對待它時(shí),該事物會被建構(gòu)成為一種威脅。國家行為體打破既定的政治規(guī)則,建構(gòu)“存在性威脅”的出現(xiàn),并以“存在性威脅”為由要求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更特殊的權(quán)力治理這種“存在性威脅”。這個(gè)過程被稱為“安全化(Securitization)”。因此,安全化是一種實(shí)踐,是實(shí)施主體通過人為手段(包括言語行為)將客體建構(gòu)為安全議題的一種實(shí)踐。因此,安全化過程就是安全議題被建構(gòu)的過程,即安全建構(gòu)的過程。
1.2 安全化的分析框架
并不是當(dāng)一個(gè)問題被視為安全問題時(shí),它就是安全問題。一項(xiàng)成功的安全化實(shí)踐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聽眾。當(dāng)安全化行為主體對某客體實(shí)施安全化的時(shí)候,聽眾是被賦予權(quán)力的聽眾,他們需要接受和認(rèn)可主體對客體的“塑造”和“建構(gòu)”。從聽眾的角度出發(fā),一項(xiàng)安全議題的建構(gòu)可以從三個(gè)步驟進(jìn)行,而每一項(xiàng)安全化實(shí)踐中都包含五個(gè)基本要素:安全化行為主體、功能性主體、安全領(lǐng)域、指涉對象、威脅邏輯。
安全化的起點(diǎn)是建構(gòu)“存在性威脅”,即讓威脅出現(xiàn)。是誰宣布誰(或什么)威脅誰(什么)——安全化行為主體或稱安全化實(shí)施主體,是整個(gè)安全化過程的背后推手。它或它們都處在權(quán)威的位置。功能性主體是指安全領(lǐng)域內(nèi)有影響力的行為體。它是威脅來源,也即誰或什么是一種威脅。指涉對象就是威脅指涉的對象,具體可指受到功能性主體威脅的人或物。
安全化的第二階段是行為主體爭取在更廣的聽眾范圍內(nèi)傳播“存在性威脅”,即讓威脅蔓延。在這一階段中安全化的另外兩個(gè)基本要素安全領(lǐng)域和威脅邏輯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它們讓不同群體的聽眾真正相信“威脅”的出現(xiàn)以及它的持續(xù)存在,為安全化第三步的實(shí)施做準(zhǔn)備。
第三步便是“存在性威脅”應(yīng)對。在說服更廣范圍的受眾后,安全化行為體主體出臺解決方案、推行各項(xiàng)政策應(yīng)對“存在性威脅”。什么威脅決定了什么對策。因此,安全化框架可以細(xì)化為三個(gè)階段——威脅出現(xiàn)、威脅蔓延、威脅應(yīng)對[3]。
安全化的三階段會出現(xiàn)在任一項(xiàng)成功的安全化實(shí)踐過程中。在安全化實(shí)施的每一個(gè)階段都離不開安全化行為主體。主體的說服性和宣布的權(quán)利通常來源于其位置權(quán)力。原則上說安全化主體的范圍不受限制,即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安全化的施動者。但是施動者需具備一定的位置權(quán)力。那么國際媒體是否有成為安全化行為施動者的可能性呢?
2 國際媒體:建構(gòu)國際安全議題的重要主體
安全化是行為主體向聽眾建構(gòu)客體,編織關(guān)于客體的一張合乎邏輯的網(wǎng)絡(luò)。安全化實(shí)踐的本質(zhì)是信息傳遞的實(shí)踐,媒體傳播實(shí)踐是信息傳遞的過程。兩種實(shí)踐在信息傳遞模式和傳遞原理兩個(gè)方面均具有相似性。
2.1 信息傳播模式
傳播學(xué)中眾所周知的“5W”模式最早由美國政治學(xué)家哈羅德·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在《傳播在社會中的結(jié)果和功能》一文中提出。“5W”傳播模式影響極為深遠(yuǎn),具體是誰(Who)→說什么(Says What)→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
安全化實(shí)踐可以很好地理解為“5W”信息傳遞的過程:“誰”(Who)→宣布“什么問題”(On What Issues)→“在什么情況下”(Under What Conditions)→“威脅誰”(Whom)→“有什么后果”(With What Effects)。
在安全化實(shí)踐的信息傳遞模式中,“誰”是指安全化行為主體。在多數(shù)情況下,安全化行為主體等同于話語發(fā)出者。主體既可以是指單個(gè)的人,也可以是集體或?qū)iT的機(jī)構(gòu)。不論是個(gè)人還是集體,他們的共同特征是具有一定的社會位置和權(quán)力。在承載安全話語的政治話語中,話語發(fā)出者可以是政治精英們,也可以是政府部門或機(jī)構(gòu)。在這種情況下,話語發(fā)出者亦是安全化行為主體。在建構(gòu)安全議題的媒體話語中,情況略有不同。媒體是安全化行為主體。然而話語發(fā)出者則多樣化,可以是單個(gè)的人,也可以是集體或?qū)iT的機(jī)構(gòu)。這體現(xiàn)在媒體話語引用的多種消息源中。在這種情況中,媒體和被引用的話語主體都可看作安全化行為體主體。“什么問題”是指安全化行為客體,即對什么問題實(shí)施安全化,將其建構(gòu)為安全議題來應(yīng)對。“在什么情況下”、“威脅誰”、“有什么后果”,這些構(gòu)成威脅邏輯。“在什么情況下”是指“存在性威脅”所涉及的領(lǐng)域。“威脅誰”是安全化實(shí)踐中的指涉對象。這在國際層面的安全化實(shí)踐中是至關(guān)重要的,這直接決定安全化是否能成功從國內(nèi)層面向國際層面轉(zhuǎn)化,引起其他國家行為體受眾的共鳴和認(rèn)同。“有什么后果”是指“存在性威脅”給指涉對象帶來什么樣的后果,這直接關(guān)乎受眾是否能接受威脅邏輯。安全化信息傳遞過程中的“5W”對應(yīng)的是該實(shí)踐的五個(gè)基本要素:安全化行為主體、功能性主體、安全領(lǐng)域、指涉對象、威脅邏輯。
2.2 信息傳播原理
傳播實(shí)踐和安全化實(shí)踐的第二個(gè)相似性體現(xiàn)在傳播原理方面。大眾傳播的建構(gòu)原理可追溯到框架理論。框架的概念最初源自貝特森,由戈夫曼引入文化社會學(xué),后來再被引入到大眾傳播研究中。基于戈夫曼的象征互動視角和心理預(yù)期理論視角,瑟爾斯提出新聞媒介框架理論。該理論的中心思想是新聞媒介以各種不同的方法構(gòu)造新聞議題。它影響了受眾思考議題、處理和儲存信息的方式,將受眾的注意力引到事實(shí)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對某一議題長期的類似方式的報(bào)道會讓人們產(chǎn)生程式化的認(rèn)知,限制了人們對特定議題的主觀認(rèn)知。可以說,新聞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生產(chǎn)。
“安全”的本質(zhì)和新聞相同,都是一種社會建構(gòu)的產(chǎn)物。說“安全”是一種社會建構(gòu)并不是否認(rèn)對人們、國家或者文化價(jià)值觀造成威脅的客觀的、有形的物質(zhì)存在。準(zhǔn)確地理解,某種客體被安全化的過程是主體隱藏客體其他特征的同時(shí),側(cè)重客體的某些“威脅特質(zhì)”并予以激活和放大。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無法親身經(jīng)歷世界每一個(gè)角落發(fā)生的事件;即便發(fā)生在身邊的事情,也不一定能現(xiàn)場經(jīng)歷,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新聞供給機(jī)構(gòu)”去了解、去認(rèn)知。新聞機(jī)構(gòu)提供給人們的不是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的“鏡子式”的再現(xiàn),也不是信息的胡編亂造,更不是虛無事件的堆砌,而是傳播媒介通過象征性實(shí)踐對信息進(jìn)行選擇、加工、重構(gòu)后向人們展示的環(huán)境。人們通常意識不到信息的選擇、加工和重構(gòu)的活動,但是這種呈現(xiàn)實(shí)實(shí)在在是人類自身所為。因此,新聞報(bào)道中的戰(zhàn)爭、傳染病或者火災(zāi)并不必須是每一件事件的本身面貌。官方、專家們、受害者們對他們經(jīng)歷的、或觀察的戰(zhàn)爭、傳染病、火災(zāi)進(jìn)行描述。新聞報(bào)道是在這些描述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謹(jǐn)慎的、專業(yè)的信息加工和重構(gòu)后的產(chǎn)物。即便對那些活躍于政治領(lǐng)域的受眾而言,他們主觀世界中的“安全世界”也是二手的。美國對伊朗客機(jī)的破壞在美國媒體中也許被呈現(xiàn)為軍事行動中因技術(shù)失誤或技術(shù)失敗釀成的悲劇,而蘇聯(lián)對韓國客機(jī)的破壞也許被美國媒體描述成為蘇聯(lián)道德淪喪的一種體現(xiàn),更可能被呈現(xiàn)為一件涉及美國國家安全甚至國際安全的事件。可見,人們對“安全”的感知和認(rèn)知亦是一種社會性建構(gòu)。
如果說媒介框架理論是挑選了認(rèn)知事實(shí)(perceived reality)的某些方面進(jìn)行加工后,在受眾的認(rèn)知世界中呈現(xiàn)的一種主觀事實(shí),那么安全化可以看作框架理論在國際安全研究中的再應(yīng)用。它將某個(gè)議題的“威脅面”橫向或縱向地加以強(qiáng)調(diào),比如它是在國家行為體內(nèi)部還是在國家行為體之間作為一種“存在性威脅”出現(xiàn),又或它僅是瀕臨的語言、或是族群身份、抑或是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的威脅等,從而降低將它作為日常政治事件處理的可能性。從信息傳遞模式和傳遞原理兩個(gè)角度看,國際媒體完全可以成為安全化實(shí)踐的施動者。
3 案例應(yīng)用:《紐約時(shí)報(bào)》對“基地”組織實(shí)施安全化
本文選擇《紐約時(shí)報(bào)》對恐怖主義實(shí)施安全化的過程作為案例驗(yàn)證上文論述的國際媒體可以成為安全化行為主體,即對國際議題進(jìn)行安全建構(gòu)。研究的問題即是:《紐約時(shí)報(bào)》如何對恐怖主義問題建構(gòu)為安全議題。此問題可以分解為四個(gè)小問題:1)在對恐怖主義的報(bào)道中,《紐約時(shí)報(bào)》如何呈現(xiàn)安全化五要素——行為主體、功能性主體、指涉對象、安全領(lǐng)域、威脅邏輯;2)恐怖主義是以何種形象呈現(xiàn)在《紐約時(shí)報(bào)》中;3)在報(bào)道中,恐怖主義威脅了哪些群體;4)在報(bào)道中,恐怖主義如何被應(yīng)對。
3.1 研究設(shè)計(jì)
本文假設(shè)《紐約時(shí)報(bào)》對恐怖主義進(jìn)行安全建構(gòu)時(shí)呈現(xiàn)了安全化的三個(gè)階段——威脅出現(xiàn)、威脅蔓延、威脅應(yīng)對。本文使用從2001年9月11日至2011年9月10日的《紐約時(shí)報(bào)》對“基地”組織的新聞報(bào)道作為研究文本。
3.1.1 國際安全事件的選擇
筆者選擇恐怖主義作為本文國際安全研究的代表事件。恐怖組織登上國際舞臺,成為與國家行為體對抗的主角。恐怖組織制造的國際沖突一再改變了人們對國際關(guān)系的一些傳統(tǒng)認(rèn)知。“基地”組織在實(shí)施“9·11”恐怖活動之后,美國發(fā)動了全面反恐戰(zhàn)爭,這是國際舞臺上國家行為體第一次與非國家行為體發(fā)生的正面沖突。2011年5月美國在伊斯蘭堡擊斃本·拉丹使美國和巴基斯坦兩國出現(xiàn)了因恐怖組織引發(fā)的外交危機(jī)。從某種程度上講,恐怖主義改變了整個(gè)國際格局,已經(jīng)成為國際社會突出的問題。
3.1.2 樣本收集
樣本收集采取了“建構(gòu)星期”[4]的抽樣方法。在2001至2011年這10年期間,以隨機(jī)抽取日期的方式建構(gòu)了20個(gè)星期,每兩個(gè)星期代表了一年。在LexisNexis數(shù)據(jù)庫中以“Al-Qaeda”為關(guān)鍵詞在“標(biāo)題和導(dǎo)語”選項(xiàng)里抽取這140天的報(bào)道后,得到《紐約時(shí)報(bào)》10年數(shù)據(jù)共175篇報(bào)道,舍去社論和略及報(bào)道得到79篇有效新聞報(bào)道。
3.1.3 編碼程序
本文以新聞報(bào)道的自然段為單位,利用內(nèi)容分析法對樣本進(jìn)行9個(gè)指標(biāo)的統(tǒng)計(jì)分析——主題、長度、消息源、受恐怖主義威脅的國家或地區(qū)、威脅來源、威脅領(lǐng)域、威脅影響、反恐措施、展開反恐國際合作的國家或地區(qū)。
3.2 研究發(fā)現(xiàn)
《紐約時(shí)報(bào)》對“基地”的相關(guān)報(bào)道共有79篇,總計(jì)1 404個(gè)段落。其中報(bào)導(dǎo)恐怖主義的有效段落有1 155個(gè),占總數(shù)的82.3%。根據(jù)安全化框架三階段——威脅出現(xiàn)、威脅蔓延、威脅應(yīng)對,《紐約時(shí)報(bào)》在對“基地”實(shí)施安全化的過程中,威脅出現(xiàn)的部分共有523段,有效百分比為45.3%,威脅蔓延的內(nèi)容只有17段,僅占1.5%,威脅應(yīng)對的部分共有615段,占53.2%。
3.2.1 安全化五要素
安全化行為主體:作為安全化行為主體時(shí),媒體有著區(qū)別于其他安全化行為主體的特點(diǎn)。媒體中的消息源可被看作“隱性的”行為主體。這些隱性行為主體被引用出現(xiàn)在安全化三階段中的任一階段。在79篇樣本中,出現(xiàn)消息源共有819處,涉及10種不同的消息源——政府機(jī)構(gòu)及官員、軍事長官、匿名人士機(jī)構(gòu)及其他、專家學(xué)者、其他媒體、恐怖分子、美國領(lǐng)導(dǎo)人、其他國家領(lǐng)導(dǎo)人、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在實(shí)施安全化的過程中,政府機(jī)構(gòu)與官員是被引用最多的,共出現(xiàn)470次,占消息源總數(shù)的57.4%。美國的政府機(jī)構(gòu)及官員主要有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財(cái)政部部長、情報(bào)機(jī)構(gòu)高官及其他政府機(jī)構(gòu)的官員們。
指涉對象:報(bào)道中共涉及受威脅國家及地區(qū)51個(gè),共被提及1 181次。論被提及次數(shù),排在前十位的國家有:美國、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英國、肯尼亞、印度尼西亞、法國、埃及、意大利。美國作為恐怖主義的受害國被提及次數(shù)最多,共653次,占總數(shù)的53.8%,超過半數(shù)。這10個(gè)國家分布在全球4個(gè)洲,除北美的美國外,亞洲國家4個(gè),歐洲國家3個(gè),非洲國家2個(gè)。
功能性主體:報(bào)道中涉及的威脅來源有四種渠道:“基地”組織、普通人、一般恐怖主義者、其他恐怖組織。“基地”組織出現(xiàn)的頻率是最高的,占61%;普通人排在第二位,占15%;恐怖主義者和其他恐怖組織各占12%。普通人作為威脅來源,在報(bào)道中多為恐怖活動參與的嫌疑人,或者報(bào)道中未標(biāo)明身份的恐怖活動的參與人。
安全領(lǐng)域:報(bào)道中涉及的安全領(lǐng)域有軍事安全、經(jīng)濟(jì)安全、政治安全與社會安全。其中,社會領(lǐng)域的威脅排在首位,占41%;軍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緊接其后,兩者比例十分接近,分別為28%和27%;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威脅僅占4%。
威脅邏輯:恐怖主義造成的最大威脅是人身安全,占62%,遠(yuǎn)遠(yuǎn)超過排在第二位的生活方式(占33%)以及排在最后的個(gè)人財(cái)產(chǎn)(僅占5%)。
3.2.2 安全化三階段
威脅出現(xiàn):具有“新型恐怖主義”典型特征的恐怖組織。《紐約時(shí)報(bào)》將“基地”組織建構(gòu)為一種“新型恐怖主義”,具有“新特征”:全球范圍的襲擊目標(biāo)、先進(jìn)專業(yè)作戰(zhàn)技術(shù)、跨國多元的資金來源、交錯復(fù)雜的組織網(wǎng)絡(luò)。
威脅蔓延:“基地”的受害者從美國延伸到歐、亞、非各個(gè)洲的國家。威脅蔓延在英文報(bào)道中通過受恐怖主義威脅的國家和具體展開反恐合作的國家兩種方式體現(xiàn)。《紐約時(shí)報(bào)》中涉及的恐怖主義受害國和地區(qū)有51個(gè),排在前十位的國家有:美國、巴基斯坦、阿富汗、英國、伊拉克、肯尼亞、印度尼西亞、法國、埃及和意大利。在這51個(gè)受威脅的國家中共被提及1 181次,美國被提及653次,占53.8%,涉及共63篇報(bào)道,占總報(bào)道量的81%。
《紐約時(shí)報(bào)》提及的展開反恐國際合作的國家有46個(gè),共出現(xiàn)293次。排在前十位的國家有美國、巴基斯坦、阿富汗、英國、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索馬里、阿曼、巴拿馬。這10個(gè)國家共被涉及221次,占總數(shù)的75%。排在榜首的美國出現(xiàn)79次,占30%
與受恐怖主義威脅前十位國家的列表相比,兩個(gè)列表的前五位國家相同,均有美國、巴基斯坦、阿富汗、英國和伊拉克。不同的是,在開展反恐國際合作的列表中,英國在報(bào)道中出現(xiàn)得比伊拉克頻繁,超出3%的比例。
威脅應(yīng)對:軍事打擊和各國國內(nèi)政策并進(jìn)的反恐措施。報(bào)道中出現(xiàn)的反恐措施共有494處,主要分為軍事打擊、經(jīng)濟(jì)制裁、政治手段和各國國內(nèi)政策四種形式。軍事打擊和各國國內(nèi)政策兩種措施所占比例較多,各占43.9%和49.4%,經(jīng)濟(jì)制裁和政治手段所占比例很小,分別僅為2.4%和4.3%。軍事打擊的反恐措施在關(guān)于兩軍交戰(zhàn)和有關(guān)美軍加強(qiáng)武器裝備的報(bào)道中多有體現(xiàn)。經(jīng)濟(jì)制裁的反恐措施集中體現(xiàn)在兩篇報(bào)道中。政治手段出現(xiàn)的是盟軍與恐怖分子的談判以及幫助阿富汗建立過度政府。各國國內(nèi)措施主要是各個(gè)國家內(nèi)部針對恐怖主義實(shí)施的反恐政策,體現(xiàn)在各國當(dāng)?shù)鼐綄植婪肿拥淖ゲ?對預(yù)謀恐怖活動的破獲、對被捕恐怖分子的審判等方面。
4 結(jié)語
在國際媒體越來越強(qiáng)大的影響力以及國際話語權(quán)越來越引發(fā)關(guān)注的宏觀背景下,如何探討國際媒體在國際關(guān)系中的作用,一直是學(xué)術(shù)界探討的重要議題。本文從建構(gòu)主義安全觀中的安全化理論出發(fā),根據(jù)安全化的定義分析安全議題建構(gòu)的五要素和三階段,從信息傳遞實(shí)踐和傳播原理兩個(gè)角度論證國際媒體具有成為安全議題建構(gòu)主體的可能性,利用《紐約時(shí)報(bào)》對“基地”組織實(shí)施安全化的實(shí)證案例,進(jìn)一步驗(yàn)證了《紐約時(shí)報(bào)》在建構(gòu)恐怖主義這一安全議題的過程中呈現(xiàn)的安全化五要素——行為主體、功能性主體、指涉對象、安全領(lǐng)域、威脅邏輯和安全化三階段——威脅出現(xiàn)、威脅蔓延、威脅應(yīng)對。因此,文章認(rèn)為,國際媒體可以按照威脅出現(xiàn)、蔓延、應(yīng)對三階段建構(gòu)并治理非傳統(tǒng)安全議題,在國際安全研究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如果承認(rèn)國際媒體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的作用,那么可以思考在目前中國的周邊安全以及海洋安全等涉及國家核心安全利益的議題中,國際媒體是否也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中國的主流國際媒體應(yīng)該怎么作為能夠助推當(dāng)今引發(fā)國際熱議的海洋安全問題的解決。
文章使用了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shí)報(bào)》對恐怖主義實(shí)施安全化的實(shí)證案例,通過定量和定性分析驗(yàn)證了國際媒體建構(gòu)安全議題的三階段過程。案例使用《紐約時(shí)報(bào)》和恐怖主義問題分別代表國際媒體和國際安全議題,這使得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續(xù)研究可以在其他國際媒體的范圍內(nèi),針對其他國際安全議題進(jìn)行樣本采集,驗(yàn)證國際媒體對安全議題建構(gòu)的三階段分析框架,進(jìn)一步探討國際媒體在非傳統(tǒng)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西方媒體在報(bào)道埃博拉問題上的偏頗[EB/OL].http://jandan.net/2014/10/12/media-ebola-illustration.html.
[2]《外交政策》:美國電視媒體如何報(bào)道埃博拉[EB/OL].http://news.sina.com.cn/w/sd/2014-10-27/052531048687.shtml.
[3]方芳.安全化分析:國際安全研究新視角[J].理論探索,2014(6).
[4]Douglas A.Luke,Charlene A.Caburnary and Elissia L.Cohen.How Much is Enough?New Recommendations for Using Constructed Week Sampling in Newspaper Content Analysis of Health Stories[J].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Measures,20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