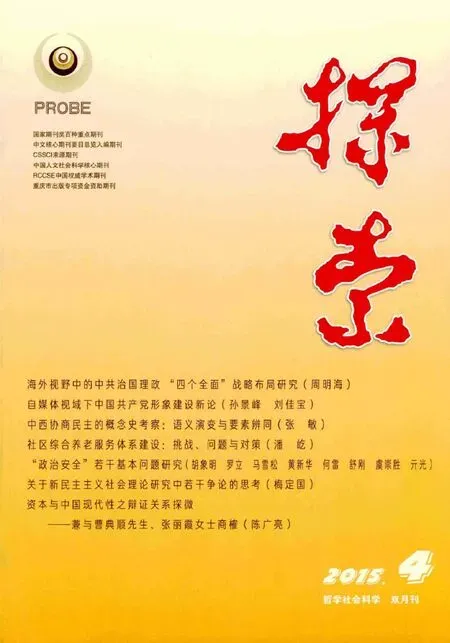影響“信任·合作”的因素分析
——基于一次博弈實驗的考察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公共管理學教研部,重慶 400041)
認同是信任的前提,信任是合作的基礎。合作基于信任,信任是指人與人之間,有關認知(理性)和情感(感性)的心理狀態。“信任”有兩個維度:一是“信”,反映理性認知維度。當對方在預期不確定性背景下,作出對自己有利的行為,這種假設、預期即是理性的信任,理性信任的出現,取決于對他人行為的風險性的預測,以及彼此之間的偏好和利益是否一致的信任認知[1]。二是“任”,反映感性情感維度,人在理性思考判斷時,也在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感性情感維度來度量信任,在此維度下,人們多運用直覺、經驗來判斷對方的行為、不確定性風險和預期利益等因素。
1 合作博弈實驗
體驗學習是一種觸及心靈的活動,體驗教學是通過精心設計的活動,讓學習者進行體驗,并引導學習者進行感悟,從而使其心智得以改善的一種教學方式。
1.1 博弈實驗實施
筆者曾經開展一次“體驗式教學”活動:以9名碩士研究生(中共重慶市委黨校)作為體驗者和調查者,在學校周邊街道向陌生人“借手機”打電話,以測試和體驗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程度和合作意愿。體驗活動的基本規則及程序如下:每位學生單獨在大街上向陌生人借用手機,撥打老師電話,接通后,老師記錄其姓名,計合格一次;每人合格10次即完成任務;記錄完成任務時的基本情況(是否被拒絕,被拒絕的情況,完成任務的時間、路段等);完成任務后,返回教室填寫問卷調查表,并進行思考:您選擇“合作”對象是如何思考?怎樣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度?對方對您的行為是如何進行判斷的?通過這次體驗活動,您認為社會信任與合作意識的狀況如何?這次體驗活動,您有什么感悟、收獲、體會?
1.2 博弈實驗調查
據筆者對學生問卷調查統計顯示(下文簡稱“筆者問卷顯示”):此次任務總共進行了136次,選擇對象為18-65歲的“陌生人”,獲得成功90次,遭到拒絕46次,成功率為66.2%,“借手機”活動過程中,均沒有向對方付費。學生普遍體會:這既是一次體驗活動,體驗現實中人們對理性認知與感性情感的認識,也是一次調查活動,調查現實社會人們對信任、合作的理解。體驗活動真正地讓學生去體驗、感受了現實社會中,不同人群、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文化、不同心態、不同情境、不同表達和不同儀態等,對信任與合作的詮釋。筆者問卷顯示:當問及“通過這次活動,您對合作、信任是否有新的認識?”時,55.6%的學生認為“有許多新認識”,44.4%的學生認為“有一些新認識”。
2 博弈實驗分析:影響“信任·合作”的因素
通過博弈實驗實施及探討研究發現: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合作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人格因素,主要是自身因素;二是情境因素,主要是合作對象和環境因素。
2.1 人格因素分析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建立在人們的互動過程之中,其信任是由態度信任、能力信任、權威信任、團隊信任和儀表信任等要素構成。
第一,態度信任。內心真誠、方式親切及態度誠懇是獲得信任的基礎,學生對此體會較深。當問及“您主要采取哪種態度?”時,選擇“親切”者占55.6%、選擇“誠懇”占44.4%、采用“哀求方式”的沒有;當問及“您借手機時,所陳述的理由是什么?”時,77.8%的學生選擇“說明真實理由”、22.2%的學生選擇“忘帶手機”,大部分學生說明真實理由,少部分學生屬于“真實的謊言”(因為學生上街都沒有帶手機)。也就是說,與人合作首先自己要誠實,表達自身的真實緣由;只有真誠、誠懇,才容易獲得對方信任并達成合作。
第二,能力信任。相比合作意識強的人,人們往往對競爭意識強的人評價更高。體驗活動過程中有一個有趣現象:九名學生中的八人都完成任務時,有一名學生始終不愿意去實施,認為“借手機”是“求人之事”,顯得無能,也擔心遭到拒絕(怕別人不信任),但在大家勸說下最終“求助”路人,十次“求助”均未遭到“拒絕”,這讓他體會深刻。要得到他人的信任,需要勇氣,這也是一種能力。現實社會中,非合作者之所以采取不合作行為,往往認為自己是強者,認為向對方示意合作,表明自己能力較弱。塞繆爾·亨廷頓這樣看待信任與能力:“社會文化中缺乏信任將給公共制度的建立帶來極大的障礙。那些缺乏穩定和效能的政府和社會,也同樣缺乏公民間的相互信任,缺乏民族和公眾的忠誠心理,缺乏組織的技能。”[2]24
第三,權威信任。韋伯認為,權威是獲得認可的權力。許多學生在求助路人時,都會表明自己是“黨校學生”或借手機是“老師安排的活動”。在此情況下,“黨校學生”或“老師安排”是一種“權威”,使人感到一種“神圣”和信任,加深人們的信任感。美國心理學家凱爾曼等人的實驗很好地說明這一點[3]:讓同一個人就青少年犯罪主題作三次相同的報告,但三次出場時,主持人介紹的身份不同,分別扮演法官、門外漢、名聲不好的人,實驗結果表明:以法官身份作報告的評價效果最佳;以名聲不好者身份作報告的評價效果最差。
第四,團隊信任。實驗中,學生被分到A、B兩條大街,A街的學生完成任務的情況明顯優于B街的學生。原因在于:前者形成團隊信任合作機制,后者“各自為政”。體驗活動中不僅存在顯性信任合作,即學生與路人間的信任合作,還存在隱性信任合作,即學生之間也存在信任協同行為。而B街的學生僅采用了前者,沒有意識到信任合作也是多元的;A街的學生采取了內部協作方式,互相支持和鼓勵,也減輕了畏難情緒和心理壓力,團隊協作產生活力,體現有效性。第一個完成任務的學生出現在A街,A街的學生也最先完成任務。筆者問卷顯示:當問及“通過這次活動,您對團隊、合作與信任是否有新的認識?”時,學生普遍認為“有許多新認識”或“有一些新認識”。
第五,儀表信任。行為科學認為:社會個體對權威人物的認同,往往是以其儀表為參照物的,要取得對方的信任,與自己的整體形象有關。合作行為以人的感覺為前提,如果雙方不“了解”對方,難以達成信任合作。所以給對方良好的印象,是達成信任合作的重要前提條件。筆者問卷顯示:當問及“成功率與對方對您的整體印像有無影響?”時,所有學生均認為“影響很大”或“有一些影響”。其中一位同學完成任務僅用了22分鐘,其外向的性格和良好的儀表,容易取得他人信任。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柴肯恩的實驗[3]同樣證明這一點:讓麻省理工學院的志愿者到街上,征求他們對某個社會組織的支持,結果表明儀表較好的志愿者比儀表較差的志愿者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2.2 情境因素分析
“情境”概念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W.I.托馬斯與F.W.茲納尼茨基提出,德國心理學家K.萊溫進一步探討行為與情境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產生信任的特定環境(如年齡性別、時機地點等)對活動、事件的成功與否有著重要影響。
第一,年齡因素。學生普遍認為,選擇合作對象與年齡有關。筆者問卷顯示:當問及“你在體驗中選擇哪種對象年齡最易成功?”時,100%的學生選擇“青年人”,尤其認為選擇學生成功率更高,因為他們都是“同齡”、“同學”,信任是基于認同。學生被年齡較大者拒絕率較高,中老年人聽聞“騙局”較多,自我防范意識較強。謝曉非教授研究表明:青年人認為,合作者與競爭者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能力和個性上;老年人認為,合作者與競爭者的差異主要表現在道德上[4]。也就是說,年輕人認為,合作是一種能力,是提高自己競爭力的要素;而老年人認為,合作只是一種道德層次的東西,對于自己屬于“奢侈品”。
第二,性別因素。選擇合作對象與性別有重要關系,筆者問卷顯示:女學生借用手機更易成功,本次體驗活動中第一個完成任務的是女生,女生整體感覺完成任務的難度低于男生。格雷厄姆·肯德爾教授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合作,當某一組是由一個女性與一個男性組成時,這個女性的合作概率只有34.2%;當某一組是由兩個女性組成時,合作的概率達到55%[5]65。不過女性合作意識強于男性受制于具體工作、學習等具體情境。學生在體驗中認為,在公共場所情境下(攤位或門面),相比“大嬸”而言,學生更易取得“大叔”的信任,“大叔類”更愿意在社會中接觸交往,尋求信任合作的機會,而“大嬸類”卻存在著“怕麻煩”情緒和“防范”心理。
第三,時機地點。學生普遍認為獲得成功與選擇地點有關,相對“靜”的地方容易獲得成功,如固定地攤、街道門面或校門附近等。相對穩定的情境下,對象更可能與學生進行簡短交流。其中有一位學生,有意識地去選擇不同“地點”、“對象”或“時機”,嘗試觀察對象的不同反應,也較好地驗證了這一點。此外,選擇對象還與文化程度有關,筆者問卷顯示:當被問及“成功率與您所選擇對象的文化程度有何關系?”時,66.7%認為對象文化層次高容易獲得成功,文化程度高者,其信任、合作意識強一些。
博弈實驗活動表明: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合作是一個系統,與他人相互信任、合作是多要素的集合,既有理性認知維度的因素,也有感性情感維度的因素;既有人格的因素,也有情境的因素。體驗活動的成功率遠高于心理預期,這讓學生們看到了現實社會中“信任”與“合作”的主流,也凸現出人的內心世界是向往“信任”、“合作”。合作意義重大,在精確定義公共價值之后,公共價值的生產可以通過合作遞送網絡來實現[6]。
3 啟示
現代教育理論以為:一個人今天的學習方式,應與他明天的生存方式是一致的。博弈實驗正是“學習方式”與“生存方式”的有機結合。
3.1 對“信任·合作”的啟示
從體驗到認知,從感性到理性,從否定到肯定,學生們通過這次博弈實驗,對“認同——信任——合作——均衡”進行了獨立的思考,得到了許多新的認識和感悟。
第一,信任合作是雙方交互的過程。策略是互動的,你的策略決定他的策略,他的策略決定你的策[7]。普林斯頓實驗研究表明:當得知對方選擇“對抗”時,只有3%的人選擇合作;當得知對方選擇合作時,選擇合作的人增加到16%。當對對方選擇一無所知時,合作的比率會上升為37%。這個實驗很符合“準神奇式”思考:通過采取某種行為,會對對方產生一定的影響。一旦人們被告知對方的選擇,他們就會意識到自己不可能改變對方的選擇。但是,當對對方選擇一無所知時,人們總會想用自己的行為去影響對方[5]73。如體驗中害怕被拒絕的學生實際上害怕別人拒絕,但實際并沒有遭到拒絕。現實社會中,取得他人的信任并非想象中那樣困難。
第二,信任合作是“利益”與“情感”的博弈。人們相互信任并達成合作基于兩種情況:一是理性考慮,基于利益關系;二是情感考慮,注重自己與對方的關系。一個爭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人,也要考慮他人利益,把別人的幸福當作自己的事情[8]。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偏重于前者,忽略情感要素,然而現實中人們不可能時刻都都能非常理性地思考“利益”。在不付費的情況下,“借手機”體驗活動成功率高達66.2%,就是一種真實而有力的例證。“借手機”博弈屬于一次性博弈,因成本較低,人們更傾向于情感因素;而在多次博弈中,人們更傾向于理性思考成本收益,更多地考慮長遠利益的實現。
第三,信任合作是“競爭”與“合作”的較量。競合關系的核心是共贏理念,即在互利互惠基礎上的競爭與合作。要達到共贏目的,必須以彼此的信任合作為基礎,牢牢樹立合作意識,在合作中進行競爭,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合作是提高競爭力的有效手段。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曾說:“如果說在過去還有可能一個人獨立完成諾貝爾獎項工作的話,那么,進入80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信息社會以來,沒有人們的共同參與、相關合作,任何重大發明創造都是不可能的。”[9]傳統觀念認為具有競爭意識的人能力更強,具有合作意識的人比較順從;而現代社會,合作意識及合作能力是現代人必須具備的能力。
第四,信任合作是需要培養塑造的意識。重慶“洋人街”景區,大街采取“無人銷售礦泉水”,據統計,“無人銷售礦泉水”的收益從剛開始的日均損失20%下降到4%,這表明人們的合作意識、合作行為正在逐漸地被“發掘”,“誠信無人售報亭”又于2011年亮相重慶“洋人街”。2015年,北京、杭州開始試水“無人超市”,這些創新營銷模式的創舉也是在引領更多市民遵守誠信的規則,是一次城市誠信大考驗,更是城市建設中培養塑造人們的合作意識、合作行為的一次“社會大培訓活動”。“借手機”體驗教學活動也是探索在學生范圍內進行合作意識、合作行為的塑造和培養。
3.2 對體驗學習的啟示
在體驗學習研究經典著作《體驗學習——讓體驗成為學習和發展的源泉》中,大衛·庫伯打破傳統“教學即傳遞”的教育觀點,提出學習是一種社會過程精心設計的體驗,認為體驗學習是包括具體體驗(concrete experience)、反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抽象概括(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和主動應用(active experimentation)四個基本階段構成的完整的學習系統,即“體驗學習圈”[10]9。
第一,體驗學習是親身“體驗”的過程。體驗學習實際上就是通過精心系統的情境設計,把學習者引入學習情境之中,讓其“身臨其境”地體驗學習。心理學大師伯特·海寧格(Bert Hellinger)認為,“想要在思維的層面去了解一種經歷過的體驗,就好像想抓住一團火一樣。如果你非要明確地詮釋它,到手的頂多只是一把灰”[11]132。費孝通在《社會學家派克論中國》一文中認為社會體驗“所給予人們的不是普通的知識,而是生命,一種能用以行動的知識。這種知識并非單由客觀的描摹可以獲得,一定要有主觀的深深體會才能得到”。不去體驗,就無法拋去原有的思維定勢和思維習慣,也就不能更新思維方式和思維理念。
第二,體驗學習是個人與社會交互的過程。體驗學習的關鍵在于,實現社會知識與個人知識之間的轉換。現代人生活在知識的海洋中,也生活在體驗的沙漠里。馬克思曾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12]。掌握理論的人比只有經驗的人肯定更聰明,但他們不一定比只有經驗的人更容易成功。如一個不會打網球的力學家,更懂得擊球的力學原理,但是他卻會輸給網球運動員。學生在體驗中感觸頗深:“體驗”使我們直接與社會“對接”,讓我們更加真實、深刻地感受現實社會。
第三,體驗學習是“行”與“知”互動的過程。體驗學習,從某種角度是在思考分析“體驗”(行為、行動)與“認知”(知識、理論)之關系,即中國教育探討的“行”與“知”的關系。陶行知有一段著名的論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傳統教學方式是“先知而后行”,現代教育方式是“先行而后知”。創新教學方式營造出室外實踐、室內思考的和諧氛圍,能夠提升學生理論聯系實踐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及及團隊合作能力。
第四,體驗學習是學習與研究的過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對60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進行調查,90%以上的人認為“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比掌握具體的知識更為重要”。方法是行動的前提,行動是方法的結果,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以及社會本質的東西,僅僅停留在“問卷調查”或“數據統計”顯然是不夠的,還需要我們采取“體驗式”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才能確保學習者深入、準確、真實地把握社會現象及其本質。通過“體驗式”學習與研究無疑是一種較好的嘗試。
參考文獻:
[1]Robinson L.Trust and Breach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J].Admisy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2).
[2]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
[3]丁煌.淺談政策有效執行的信任基礎[J].理論探討,2003(5).
[4]謝曉非,陳曦.合作意識的認知成份分析[J].心理科學,2002(3).
[5]阿維納什·K.·迪克西特,巴里·J·奈爾伯夫.妙趣橫生博弈論[M].董志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6]馬亭亭,唐興霖.公共價值管理:西方公共行政學理論的新發展[J].行政論壇,2014(6).
[7]陳建先,王超.新常態與領導“新思維”——基于博弈理念視角的分析[J].領導科學,2015(7).
[8]胡象明.當代中國政府與市場關系變遷的邏輯:理論、實踐及其規律[J].行政論壇,2014(5).
[9]雷興輝.基于合作意識培養的數學教學策略探析[J].價值工程,2011(20).
[10]大衛·庫伯.體驗學習——讓體驗成為學習與發展的源泉[M].王燦明,朱水萍,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11]林思寧.體驗式學習[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2]龐躍輝.誠信觀與社會認同意識[J].江海學刊,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