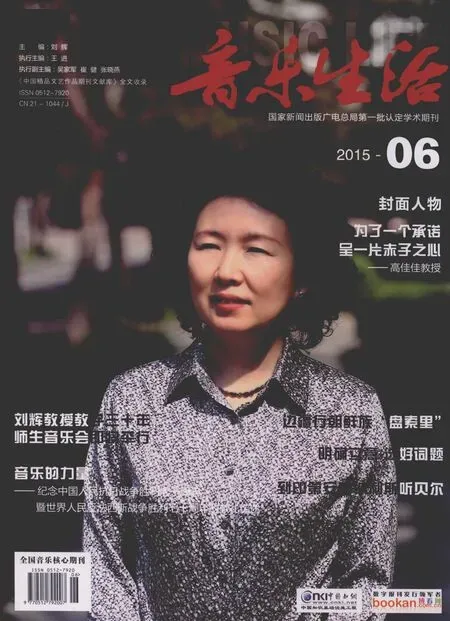他山之石能攻玉否
——對(duì)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介入中國(guó)音樂(lè)研究之宏觀層面的思考
文/陳金玲
他山之石能攻玉否
——對(duì)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介入中國(guó)音樂(lè)研究之宏觀層面的思考
文/陳金玲
近些年來(lái)中國(guó)的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語(yǔ)境下處于醒目的位置。通過(guò)理清西方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理論這塊“他山之石”的概念以及發(fā)展脈絡(luò),可見(jiàn)其能夠琢磨中國(guó)音樂(lè)研究這塊璞玉。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理論能夠協(xié)助中國(guó)音樂(lè)研究打破其自身的壁壘,走出以建立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理論和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遺產(chǎn)進(jìn)行收集整理為旨趣的“前學(xué)科”階段,進(jìn)入“音樂(lè)”與“文化”接通,以對(duì)象和問(wèn)題意識(shí)為導(dǎo)向的“跨學(xué)科”研究時(shí)期。中國(guó)音樂(lè)研究也正需如此。
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 中國(guó)音樂(lè)研究 跨學(xué)科
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作為一種合時(shí)入世的研究視野與中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大潮的匯入共同激發(fā)了藝術(shù)各學(xué)科與人類(lèi)學(xué)的合作與交流。回顧2006年12月中國(guó)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學(xué)會(huì)在北京成立,其宗旨即是在承認(rèn)人類(lèi)學(xué)文化多樣性的基礎(chǔ)上廓清藝術(shù)與文化、社會(huì)的關(guān)聯(lián)。正如王建民教授所言,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已經(jīng)卷入到了中國(guó)學(xué)界熱熱鬧鬧的集體文化運(yùn)動(dòng)中,對(duì)這種文化現(xiàn)象人類(lèi)學(xué)界以及藝術(shù)學(xué)界將如何思考與反思?中國(guó)音樂(lè)研究在論及音樂(lè)與文化相互打通時(shí),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能給予我們什么啟示?
考察“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Anthropology of art)概念的中西差異,涉及西方“art”的概念演進(jìn)、中西文化翻譯和人類(lèi)學(xué)對(duì)藝術(shù)研究的局限幾個(gè)方面。西方“art”涵義和中國(guó)的“藝術(shù)”并非一一對(duì)應(yīng)的關(guān)系。1992年版的《朗文英漢雙解字典》中“art”詞條這樣解釋道:“art”指技藝,與“skill”相通,另一個(gè)意思是美術(shù),尤其是繪畫(huà)(painting)類(lèi)的藝術(shù)品。再看1980年版的《辭海》對(duì)中文“藝術(shù)”的釋義:藝術(shù)即“通過(guò)塑造形象具體的反映社會(huì)生活,表現(xiàn)作者感情的一種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藝術(shù)通常分為表演藝術(shù)(音樂(lè)、舞蹈),造型藝術(shù)(繪畫(huà)、雕塑),語(yǔ)言藝術(shù)(文學(xué))和綜合藝術(shù)(戲劇、電影)”。因此,此“藝術(shù)”非彼“art”,把“anthropology of art”翻譯成“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使中國(guó)學(xué)者理所當(dāng)然地認(rèn)為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涵蓋音樂(lè)、舞蹈、繪畫(huà)等領(lǐng)域。西方“art”曾是一個(gè)變化的概念。符?塔達(dá)基維奇在《西方美學(xué)概念史》中對(duì)西方“藝術(shù)”概念的演進(jìn)有著清晰的表述:“在近代的運(yùn)用中,對(duì)‘藝術(shù)’的含義時(shí)常是有限制的,這一情形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亦即,或是將這一名稱(chēng)只保留在視覺(jué)藝術(shù)中,或者是將其保留在最高水平的、最優(yōu)秀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中。……在我們這一規(guī)定的意義上,藝術(shù)的全部領(lǐng)域被劃分為兩個(gè)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即視覺(jué)藝術(shù))才是被稱(chēng)作‘藝術(shù)’的。” 英國(guó)的雷蒙?威廉斯稱(chēng):“自從17世紀(jì)末,art專(zhuān)門(mén)意指之前不被認(rèn)為是藝術(shù)領(lǐng)域的繪畫(huà)、素描、雕刻與雕塑的用法越來(lái)越常見(jiàn),但一直到19世紀(jì),這種用法才被確立,且一直持續(xù)至今。” 《當(dāng)代西方社會(huì)學(xué)、人類(lèi)學(xué)新詞典》中“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詞條也明確指出:“人類(lèi)學(xué)對(duì)藝術(shù)的研究相對(duì)注重造型藝術(shù)與繪畫(huà)藝術(shù),而較少注意表演藝術(shù)。”因此,我們理解的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要遠(yuǎn)遠(yuǎn)大于西方“ anthropology of art ”的外延。
廣義的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在西方的發(fā)展有兩條脈絡(luò)可循。首先是發(fā)生在人類(lèi)學(xué)內(nèi)部的視覺(jué)文化人類(lèi)學(xué),以狹義的“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稱(chēng)謂。從人類(lèi)學(xué)古典進(jìn)化學(xué)派稱(chēng)那些視覺(jué)資料為“原始文化”,雖然此時(shí)的人類(lèi)學(xué)家對(duì)無(wú)文字社會(huì)和群體的藝術(shù)感興趣,并把它們納入了自己的研究視野,但并沒(méi)有另起爐灶把“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作為一門(mén)學(xué)科或是研究方法提出來(lái);第二條脈絡(luò)是西方的民族音樂(lè)學(xué)、審美人類(lèi)學(xué)和舞蹈人類(lèi)學(xué)。民族音樂(lè)學(xué)在西方的形成與發(fā)展來(lái)自人類(lèi)學(xué)的影響。雖然比較音樂(lè)學(xué)的文化類(lèi)型的概念已經(jīng)有了人類(lèi)學(xué)文化傳播論的影子,但真正地從價(jià)值觀到方法論的確立是發(fā)生在它過(guò)渡到民族音樂(lè)學(xué)之后。如果說(shuō)比較音樂(lè)學(xué)仍是文化進(jìn)化論的學(xué)說(shuō),那民族音樂(lè)學(xué)廣泛認(rèn)可音樂(lè)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而區(qū)別于比較音樂(lè)學(xué)。民族音樂(lè)學(xué)的領(lǐng)軍人物梅里亞姆是美國(guó)人類(lèi)學(xué)歷史學(xué)派赫斯科維茨的學(xué)生,他從老師那兒借鑒了實(shí)證主義方法和文化相對(duì)主義的價(jià)值觀用于音樂(lè)研究。他還受益于人類(lèi)學(xué)功能學(xué)派馬林洛夫斯基,注重田野工作的經(jīng)驗(yàn)材料,并運(yùn)用于自己的研究實(shí)踐。梅里亞姆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這本著作中總結(jié)出音樂(lè)的十大功能,也是受馬林洛夫斯基的功能理論啟發(fā)的產(chǎn)物。闡釋人類(lèi)學(xué)所提倡的 “文化分析不是尋求規(guī)律的實(shí)驗(yàn)科學(xué)而是一門(mén)闡釋意義的科學(xué)”,隨后應(yīng)用到原住民音樂(lè)和儀式音樂(lè)研究中。但民族音樂(lè)家們并不僅僅對(duì)人類(lèi)學(xué)理論隨意剪切、拼貼,也不滿(mǎn)足于直接借來(lái)為我所用,而是根據(jù)音樂(lè)對(duì)象本身的特點(diǎn)逐漸孕育出自己的孩子。從它誕生起不斷有理論推進(jìn),由此獲得獨(dú)立的學(xué)科品質(zhì)。其中包括梅氏的概念、樂(lè)音、行為的三重模式的理論基石,在賴(lài)斯三重模式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歷史的分析模式,因此音樂(lè)分析拓展成為歷史構(gòu)成、社會(huì)維持、個(gè)人運(yùn)用、象征體系的四級(jí)目標(biāo)模式等等。理論的推進(jìn)使得民族音樂(lè)學(xué)蓬勃發(fā)展并且研究成果豐碩。研究領(lǐng)域從非西方音樂(lè)到西方音樂(lè),21世紀(jì)民族音樂(lè)學(xué)拓展到城市移民音樂(lè)、女性主義音樂(lè)等等。
音樂(lè)學(xué)研究者并不滿(mǎn)足于人類(lèi)學(xué)把音樂(lè)當(dāng)做文化的載體看待,也不滿(mǎn)意社會(huì)學(xué)僅僅把音樂(lè)作為社會(huì)事實(shí)的說(shuō)法,他們認(rèn)為在人類(lèi)學(xué)與社會(huì)學(xué)的學(xué)科內(nèi)來(lái)看音樂(lè)現(xiàn)象,都把音樂(lè)當(dāng)做社會(huì)生活的附庸,涉及音樂(lè)的人類(lèi)學(xué)和音樂(lè)社會(huì)學(xué)只是“圍繞音樂(lè)”、而非“穿越”,仍有一定的認(rèn)識(shí)缺陷。音樂(lè)研究者研究音樂(lè)現(xiàn)象的內(nèi)在規(guī)律,既可通過(guò)音樂(lè)自身、也一再借助“文化”、“社會(huì)”的外力來(lái)看音樂(lè)事實(shí)。從學(xué)科發(fā)展史來(lái)看,兩門(mén)學(xué)科發(fā)展不均衡:人類(lèi)學(xué)在經(jīng)歷了古典人類(lèi)學(xué)理論探索人類(lèi)學(xué)普通規(guī)律的科學(xué)到“實(shí)驗(yàn)”的文化批評(píng)階段。而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的發(fā)展仍處在“前學(xué)科”時(shí)期,有著自身的學(xué)科關(guān)懷。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建立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理論以應(yīng)對(duì)世界音樂(lè)的現(xiàn)代性危機(jī),另一方面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遺產(chǎn)進(jìn)行收集整理。人類(lèi)學(xué)為藝術(shù)各門(mén)類(lèi)橫向拓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把它置于社會(huì)文化的語(yǔ)境中觀照,跨學(xué)科的學(xué)科邊界問(wèn)題以及如何在相互借鑒中達(dá)成以“研究對(duì)象”為導(dǎo)向的跨學(xué)科深度問(wèn)題在一定時(shí)期內(nèi)長(zhǎng)期存在。雖然人文學(xué)科之間的流動(dòng)性日益增強(qiáng),為概念和方法在多個(gè)領(lǐng)域的運(yùn)用成為可能,但學(xué)院體制的“專(zhuān)業(yè)化”是共同的。如此,在學(xué)院知識(shí)生產(chǎn)上,各學(xué)科背后有自己的目標(biāo)和追求,甚至學(xué)位論文的標(biāo)準(zhǔn)亦影響研究維度和結(jié)果,包括知識(shí)生產(chǎn)的權(quán)利關(guān)系和文化表征的反思,即布迪厄所謂的“作者是在何種權(quán)力場(chǎng)以及該權(quán)力場(chǎng)的何種位置上進(jìn)行寫(xiě)作。” 現(xiàn)代學(xué)科體制把世界知識(shí)碎片化,肢解了作為“整體知識(shí)”相互間的聯(lián)系。米爾斯以及克利福德?吉爾茲所認(rèn)為的各學(xué)科之間觀念與方法的流動(dòng)性正日益成為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趨勢(shì),是對(duì)現(xiàn)代學(xué)科分化的回應(yīng)。西方知識(shí)界所謂“知識(shí)碎片化”的反思則發(fā)生在上世紀(jì)80年代的“advance seminar”科學(xué)革命運(yùn)動(dòng) 。這一思潮使得有關(guān)“跨學(xué)科”的討論成為知識(shí)界的焦點(diǎn)。“世界需要完整地被表述”(馬爾庫(kù)斯)不僅是對(duì)人類(lèi)學(xué)面對(duì)現(xiàn)代意識(shí)批評(píng)的反映,以回到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相對(duì)主義的理想,也是對(duì)世界知識(shí)“現(xiàn)代性疏離”的呼吁。跨學(xué)科的要義則是反思現(xiàn)代學(xué)科的分化。作為“人”的科學(xué)應(yīng)是整體、犬牙交錯(cuò)的復(fù)雜系統(tǒng)。沃爾夫在《歐洲與沒(méi)有歷史的人民》也曾反思這種疏離:政治和經(jīng)濟(jì)學(xué)從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抽離的做法的結(jié)果造成“專(zhuān)業(yè)化社會(huì)科學(xué)摒棄了整體視角,他們也變得像古希臘神話中的達(dá)娜厄姐妹那樣,被判罰將水注入各自的無(wú)底容器中去。”
目前,“跨學(xué)科”已成為人文學(xué)科顯著特點(diǎn)。以對(duì)象和問(wèn)題意識(shí)為導(dǎo)向的研究有可能調(diào)和音樂(lè)本體研究取向和側(cè)重文化、音樂(lè)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民族音樂(lè)學(xué)之間的矛盾,那就是“問(wèn)題意識(shí)導(dǎo)向”的研究是以上兩種旨趣作為視角審視研究對(duì)象而各有側(cè)重。如是,應(yīng)更進(jìn)一步考慮“音樂(lè)”和“文化”如何接通。“音樂(lè)”作為文化的一部分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模糊其中任何一項(xiàng)、忽視它們之間真正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都難以接近研究對(duì)象的本質(zhì)。就個(gè)案研究看,民族音樂(lè)學(xué)的視野已從非西方重回西方、從異族到本族,精英音樂(lè)研究也漸獲合法地位。無(wú)論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精英音樂(lè),音樂(lè)家都是職業(yè)性的,社會(huì)、文化、儀式、語(yǔ)言層面也是研究者用“內(nèi)部持有者”、“文化系統(tǒng)內(nèi)部經(jīng)驗(yàn)”的眼光來(lái)體察的,他(她)的研究可取音樂(lè)或文化當(dāng)中的任何角度。如果從音樂(lè)層面來(lái)操作,即通過(guò)研究音樂(lè)本身即可澄清一些概念和事實(shí),這取決于研究者自身的問(wèn)題意識(shí)和研究旨趣。而作為時(shí)空上、精神上的“他者”身份進(jìn)入對(duì)象的“異族音樂(lè)研究”,或“非精英音樂(lè)類(lèi)型”研究,我們無(wú)法從文化內(nèi)部理解,那么在音樂(lè)之外的文化、社會(huì)中尋求解釋無(wú)不是最佳手段。從民族音樂(lè)學(xué)建立之初梅里亞姆就如此批評(píng)柏林學(xué)院派的、實(shí)驗(yàn)室的比較音樂(lè)研究:“我們對(duì)于音樂(lè)自身的聲音給予了很大的重視與強(qiáng)調(diào)……我們把音樂(lè)聲音作為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來(lái)看待,是一個(gè)靜止的狀態(tài)……”到今天對(duì)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去音樂(lè)化”的非議,無(wú)非是“音樂(lè)”與“文化”之間的制衡過(guò)程。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應(yīng)走出“前學(xué)科”階段,在扎實(shí)的個(gè)案研究中開(kāi)出理論之花。民族音樂(lè)學(xué)將聽(tīng)到盼望已久的、來(lái)自中國(guó)自己的聲音。到那時(shí),藝術(shù)各學(xué)科在人文學(xué)科中的意義將凸顯為:藝術(shù)可作為一枚棱鏡以透視出人類(lèi)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更需要的是一種打破學(xué)科壁壘的、學(xué)科間良性互動(dòng)交流的“去學(xué)科化”的廣闊視野和學(xué)術(shù)胸懷。
[1]《朗文英漢雙解詞典》[M]. 北京: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1992.65.
[2]《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shū)出版社,1980.550.
[3]符?塔達(dá)基維奇. 西方美學(xué)概念史[M].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1990.51-52.
[4]雷蒙?威廉斯.關(guān)鍵詞—文化與社會(huì)的詞匯 [M]. 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2005.17.
[5]黃平、羅紅光、許寶強(qiáng).《當(dāng)代社會(huì)學(xué)人類(lèi)學(xué)學(xué)新詞典》[M].長(zhǎng)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92.
[6]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編著. 寫(xiě)文化[M].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6.305.
[7]沃爾夫.歐洲與沒(méi)有歷史的人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
[8]Merriam,A.P.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M].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Pree,1964.36.
(責(zé)任編輯 霍 閩)
陳金玲(1982—)女,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音樂(lè)學(xué)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