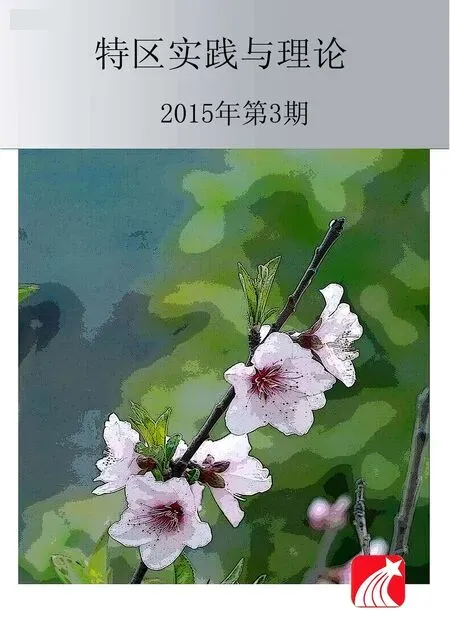確立公民的法治信仰是依法治國的基石
謝非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同時強調要“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要實現依法治國,首先需要全社會對法治精神的弘揚和公民法治信仰的確立,這樣才能“增強全社會厲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1]因此,培育與確立公民的法治信仰,是我國構建依法治國大廈的重要基石。
一、確立公民法治信仰的重大意義
目前我國學界對法治信仰這個概念有一些研究,但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界定,有的表述為“法律信仰”,有的表述為“法治信仰”,但筆者認為,“法治信仰”的表述更為明晰和準確,是公民對依據法律治理國家的高度認同,對法治深存敬畏、一切行為規范以法律為準則的一種比較穩固的社會情感、意志和心理的集合。我國法治建設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依法治國,這就需要公民真正從內心認同并堅定對法治的信仰,將尊法、守法、用法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才能形成一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理想法治社會。
我國自黨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以來,法制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立法工作的步伐邁進很快,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基本上都納入了法律調整的范圍,以往無法可依的局面已大為改觀。但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一個現實是,在法制建設迅速發展的同時,人們對法治精神的忽視和淡薄,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都缺乏對法治的真誠的信仰。一個社會若失去了民眾對法治的信仰與敬重,即使制定出千百部再好、再完備的法律,也難以內化為一種民族精神,更難以成為一種精神力量推動法治國家的建設。
培養公民的法治信仰已經成為建設法治國家的迫切需要。首先,一個國家要實現法治,公眾必須對法治有足夠的認同、尊重和接受,沒有這種認同、尊重和接受,即沒有社會公眾對法治的信仰,法律制度就會缺乏可行性,法律就只會成為沒有任何權威的一紙空文,如此一來,法治如何成為可能?其次,一個社會法治精神的形成源自于社會公民對法治的信仰,這是法治的“軟件”系統設立的基礎,如果沒有公民對法治的普遍信仰,社會就難以形成一種法治精神和意志。因而,從這一意義上講,培養公民的法治信仰,是一個社會法治精神形成和法治社會構建不可或缺的重要程序。最后,從法治的內涵來看,法治本身也包含了公民應該普遍具有的對法治認同的意識和觀念,這種意識和觀念能夠成為一種穩定的社會心態,使社會成員能夠把合法頒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作為至上的行為準則,這樣,法律制度才能維持其穩定性和普遍性,誠如美國學者伯爾曼所講,“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僅要求我們在理智上承認——社會所倡導的社會美德,而且要求我們以我們的全部生命獻身于它們,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飛躍,我們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則具有普遍性”。[2]
二、我國公民法治信仰缺失的現狀及其成因
從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已開啟了對“依法治國”的探索,但是,取得比較大的突破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方略之后,我國的法治建設才有了較大的發展。至2011年,我國已經形成以憲法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很大的改觀,對法治的信仰也開始萌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為人們的美好愿望和期盼。
盡管目前人們對法治有了一定的認識,但是,離法治成為公民的信仰還有很遠的距離。社會治理仍然出現大量人治而非法治的現象,追根探源,造成我國公民法治信仰缺失大致有幾種原因:
一是我國封建社會長期“人治”和“德治”的影響。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其社會治理一直是以“人治”和“德治”為核心,法治只不過是一種輔助手段。“人治”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就是形成特權階層,錢權交易盛行,人身依附成為常態,社會的不公平、不公正現象大量產生。傳統社會的“德治”,雖然對社會治理產生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德治”畢竟是一種軟手段,對統治者(治理者)的約束力非常有限,而且對“德”的判斷標準也是由統治者來決定,這樣“德治”與“人治”的結合,更加削弱了社會治理中的公正維度,人情關系、親屬化、圈子化交織形成一種社會關系網,吞噬著社會的公平正義,銷蝕著法律的權威。
二是當前我國法治運行的低質量和低效率。改革開放后,尤其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以來,我國加大了法制建設力度,立法力度空前加強,大力推進全民法律普及教育,開展法治文化建設。但我們也要看到,以立法為目的的法制建設只是注重了速度和數量,卻忽視了最為重要的質量和效果。法制宣傳普及教育的重心只放在了公民守法教育之上,而沒有把權利意識、主體意識、自由意識和憲政意識等現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法律價值作為宣傳教育的核心和重點。
三是行政權力對司法活動的影響。目前我國的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決定了司法活動受制于行政權力。由于法院的財政經費有賴于行政部門的撥給,人事上受制于同級黨委或者上級黨委,一些重大或爭議案件的最終決定權接受同級黨委政法委的“協調”,使得人們通過司法謀求社會正義的愿望難以實現。依法行政在實際執行中也存在走樣和變形,各級政府部門可以通過變相立法和解釋等種種手段將政府意志轉換成為法律,使得法律的地位下降、法律權威也大打折扣。
四是司法實踐中大量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現象,嚴重阻礙了公正、秩序、效益、自由等法律價值目標的實現,極大地破壞和污染了形成公民法治信仰的環境和土壤。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屏障,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公正的司法能通過嚴格的法律程序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社會公平與正義的不斷累積,就能成為公民樹立法治信仰的最有效的催化劑。
三、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主要途徑
要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必須激發公眾內心對法治的信賴、信任和尊重的情感,形成對法治的忠誠和信仰。這是一種精神和價值的培養,在一定程度上比法律制度建設的難度更大,因此,需要全社會從多個方面做出共同努力。
一是加強社會公眾權利意識的培養。公眾權利意識的確立是法治被信仰的感情基礎。權利是法的核心,如果沒有公眾對權利的追求,那么,公眾對法的需求和渴望也就無從產生。要加強普法教育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教育,培養公民的權利意識。法治認知是法治信仰的前提,但普法教育不僅僅是對公民普及法律的知識和內容,更重要的是教會公民樹立自己的權利意識。公民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是互相推動的,權利意識的增強必然會導致社會公眾對法治的認同及對法律所含價值的褒揚,從而萌發對法治的信仰;而公民法治意識的增強又會鞏固權利意識,公民的法治信仰在兩者的相互作用下不斷成長。另外,在社會主義法治實際運行的過程中,要通過合法的程序彰顯公民的權利,使公民的權益得到有效保障,這樣才有助于喚起社會公眾對權利意識的重視。權利意識的增強必然會激發公眾對法律的渴望和熱愛,使公眾對法律有強烈的依賴,從而自覺去守法護法信法,逐漸形成對法治的信仰。
二是不斷增強立法的科學性,提高立法質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治建設側重于迅速改變“無法可依”的局面,立法的速度很快,但立法的質量卻差強人意,在執法和司法等環節出現種種棘手問題,不但無助于公民法治信仰的形成,也延緩了法治進程的推進。科學立法,不僅在內容和程序上要體現合理性,在法律條文的設計安排和立法技術上都要體現科學性;要廣泛聽取和采納公民的意見,加強對相關學科的研究和論證;不斷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和立法評估制度,從而提高立法質量,讓法律真正為公民服務,為公民帶來更大的福利。
三是強化執法和司法的公正性,增強法治的權威性。法律能被信仰不僅在于它的科學性、正義性,還在于它的效益性。其正義性、效益性要通過公正的執法和司法才能體現出來。當人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作為正義之劍的法律能使公民的權益得到保護,社會的正義、公正才能得到體現,只有這樣,才能喚起人們對法治的至高信仰和崇拜的激情。當前,我國無論是在執法或司法領域還存在著種種問題,執法不公、司法腐敗等問題像毒素一樣危害著社會的法治環境。公正的執法和司法是培育法治信仰最有效的途徑,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監督制裁機制,嚴查嚴辦執法人員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行為;通過大力推進司法制度改革,讓司法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社會各界的有效監督下,公開、公平、公正地行使。
四是加強對國家公職人員特別是司法人員的教育和管理,增強其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國家公職人員作為由人民委托執掌一定權力的代表和法律衛士,是法律的具體執行者和操作者,如果執法者沒有使命感和責任感,就很難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公正司法,社會的法律權威就會蕩然無存,公民的法治信仰就難以確立。所以,培養法治信仰和法治精神,一方面要切實加強對公職人員的職業素質教育,增強其使命意識和責任意識;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健全民主監督、民主考核評估等各種制度,以制度約束法律工作者的職業行為,為公民法治信仰的確立培植更好的制度環境。
五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中國傳統文化中“法即刑”的觀念深入人心,再加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的政治運行制度,法律基本上是只為統治者服務,使老百姓形成了“懼訟”、“恥訟”、“厭訟”的心理,這樣就難以建立起社會主體對法治的敬畏、信任和崇拜,人們習慣于用情感和倫理來協調人際關系和調整社會關系,對法治的信仰自然就難以在這樣的土壤中產生。新中國建立后歷次政治運動的“洗禮”,使社會的法律制度遭受極大的破壞,法治不斷地被粗暴摧殘,公民的權利在“無法無天”中被剝奪,更加劇了公民對法治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走到極端就是對法律的藐視和挑戰,從而又在整個社會中引起惡性循環。因此,需要通過加強法治文化建設,用法治文化引領公民學法、信法、崇法,以法治文化肅清我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等級觀念、人治思想、權力至上、官本位等封建遺毒,打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環境,促進公民法治信仰的養成。
[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4-10-28.
[2][美]伯爾曼著.法律和宗教[M].北京:三聯書店,199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