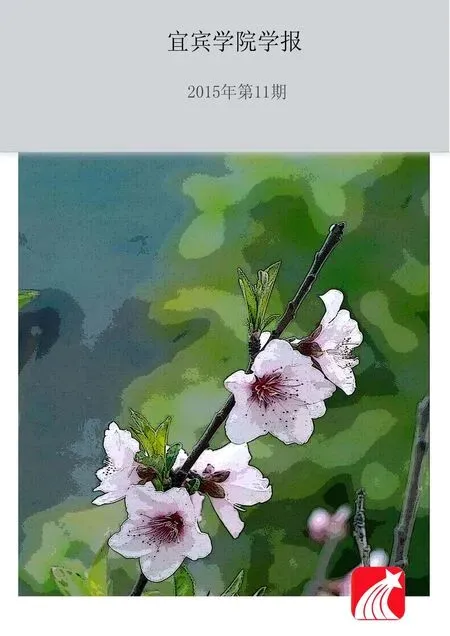女性無愛人生的愛情言說——再論張愛玲散文《愛》之內涵
余 玲
(樂山師范學院,四川樂山614000)
?
女性無愛人生的愛情言說
——再論張愛玲散文《愛》之內涵
余玲
(樂山師范學院,四川樂山614000)
摘要:張愛玲散文《愛》具有極大的愛情迷惑性。作者雖試圖以“愛”闡釋愛情的內涵,事實卻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女子單向的愛情臆想故事。小說從愛之建立基礎的空缺、“回憶-夢”的愛情重構方式以及女性敘述視角三個方面體現了女子愛情自我言說的單向情感故事。無愛的人生和孤獨的女性愛情境況依然是張愛玲筆下女性真實的存在方式。
關鍵詞:張愛玲;《愛》;女性
張愛玲散文《愛》,1944年4月刊載于上海《雜志》,全文342字,對于兩性情感內涵和女性生存境況的表現言簡意豐,堪稱張氏作品經典,時年張愛玲不到24歲。研究者對于《愛》文本解讀甚多,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兩種觀點較為典型:一是溫情派,認為“亂世才女,卻有著一種理想愛情觀。她追求的是一種脫離現實的純粹愛情,一種不問緣由,不問經歷永恒的真愛”[1];或認為文本中表現的愛的形式“就是作家所欣賞與強調的一種具宗教色彩的神圣愛情、超拔于愛欲之上的兩性純潔情感”[2]。另一種觀點則是從文字中感受到強烈的悲劇意味,認為《愛》表現出愛的荒涼、蒼涼、無奈和虛無。如《體悟愛的荒涼》[3]《以“愛”“悟”空》[4]等。兩種觀點雖未針鋒相對,亦大相徑庭。但無論哪種觀點,都將文本中的男女主人公設定為愛情關系的兩個主體,且都認定男女之間存在一種“愛情”關系,分歧僅在于對兩性主體之間情感關系的判斷和認識存在主觀差異而已。
在結合張愛玲的創(chuàng)作思想、創(chuàng)作風格以及小說文本的背景上再仔細研讀《愛》,文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整個文本中始終未建立愛情關系,女主人公未獲得愛情主體地位,他們之間的關系用“愛”來命名實為牽強。根據文本敘述,《愛》中男子的確曾出現在女孩的生命中,但作為愛情關系而言,他始終處于缺席位置,從未參與過女孩的愛情行為,更進一步說,《愛》中的情感關系只不過是女孩單方面的愛情臆想、愛情言說。從這個角度切入文本,《愛》就是一個女性莫須有的單向情感故事,甚至連單戀都談不上。之所以將《愛》視作女性單向的情感故事,女性愛情的自我言說,或者說是女性的愛情獨角戲,主要基于以下幾點:
一愛之建立基礎
文中女孩與男子之間的緣分,始于而且也止于一次碰面、一句問候:“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地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她沒有說什么,他也沒有再說什么,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5]
這就是女孩與男子全部的交往,見過一次面,打過一次招呼,四目相對的時間極其短暫。而且作者隨即強調——“就這樣就完了”,還沒開始就已結束。此后他們生活再無交集,連回憶和思念都沒有交集。僅有的一次見面即讓女孩終身念念不忘,無限懷想,甚至以愛的情感心理在幾十年后不斷回憶,這在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絕無僅有。《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感情經歷稱得上驚世駭俗,但時長也有二十四小時,而《愛》僅只一面。就張愛玲其他創(chuàng)作來說,男女見面時間當屬《封鎖》最短。吳翠遠和呂宗楨電車里打盹似的逢場作戲最不濟也有幾站路的時長,而且男女之間的心理回合幾起幾落,比起《愛》中生澀無言的情境,內容算得上十分豐富。若論情感關系,張愛玲小說中有結成夫妻的男女、相親的男女,戀愛未果的男女,但像《愛》這樣驚鴻一瞥擦肩而過的感情卻是唯一的。這樣短暫的時間,前無鋪墊后無結局的偶然一面,難免為這女子的愛情悲劇埋下隱患。
當然,論者也不能武斷地以時間長短去否定文中男女之間不存在愛情。判斷愛情存在最關鍵的因素在于當事男女的主觀感受和體驗,一見鐘情的可能性也有完全存在的可能性,相反,真正的愛情從來不因時空的阻隔而中斷或變質,反而成為檢驗真愛的試金石。但從《愛》的文字表述中,讀者很難推定“這一面”于他倆來說是有情味的。因為沒有心靈的碰撞,就只能是一次普通的碰面,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獨特性和排他性。她和他既是鄰居,具有近水樓臺的優(yōu)勢,如果他喜歡她,見面、說話的機會自然會比別的男性多。但是他“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不打招呼或許出于害羞、怯懦,也或許覺得沒有打招呼的必要,可有可無。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這個男子都無所作為,未向女子做出任何主動性的積極表示。當然如果有“愛”雙方也完全可以藏于心,但當女子即將嫁作他人婦的關鍵時刻,這個年青人依然無動于衷。“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張愛玲曾經說過“一個男子對一個女孩最隆重的贊美就是求婚”[6]85,但即使有很多媒人做媒,卻沒有這個男子的提親。如果他愛她,一定會有所作為,可他沒有。即使在那個春天的晚上,女子獨自立于門后,手扶桃樹的絕佳時刻,他也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原來你也在這里嗎”?男子的行為究竟是愛、懦弱,還是根本無愛?因此,從男子的種種表現推斷,她與他的那次見面也只是一次偶然相遇,一聲禮貌的問候。
二被美化和重構的“愛”
當初的一次無心問候,年老時卻以“回憶-夢”的方式得到美化和重構,并成為《愛》的主要內涵。轉身之后再也沒有交集的人生,是什么力量促使女孩在“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5]是因為不能忘情的愛、超越時空的真愛?答案理應否定。能支撐女孩在時隔幾十年后仍然回憶起那次見面的,只能是女孩對愛的期盼以及無愛之后的愛情補償心理。根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當女孩正當的情感需求被壓抑阻礙之后,必將會轉化為一種更隱蔽的潛意識存在,當這種潛意識情感需求不被現實承認和滿足時,她勢必會在現實中尋找一種替代性補償。回憶——則是女孩在自己多年后找到的情感補償方式。每一次回憶,都是對自己情感的釋放和替代性滿足。能將一次可有可無的碰面、一個無動于衷的男子,以一個懷春女子般的溫情脈脈地去回憶,并在感情的推動下主觀營造出桃紅色的浪漫背景和情意綿綿的對話,可見女子內心對愛情和異性的渴望。越是在年老時回憶起當初的愛情癡心,越能暴露出這女子愛情經歷的蒼白。
在回憶中臆想“愛”,自我重構“愛”無情地顯示出女性無愛人生的尷尬和無奈。“很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甚為蹊蹺的結局,已然為女性的悲劇埋下伏筆,果不其然“后來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xiāng)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5]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省略了女子人生中多少辛酸屈辱,顛沛流離,孤苦無依。原本如花似玉的少女轉眼淪為待價而沽的肉體商品。原本祈望的靜好歲月、安穩(wěn)人生悉數被生生摧殘,生命異化使她支離破碎,更遑論幸福。那些猙獰歲月中的男性,即是女孩的不堪過往。本著趨利避害的心理,當一切風平浪靜之后,他們都被屏蔽在女孩自我認可的生命記憶之外,而她認可的,她愿意回憶的惟有“那一個”年青人,這一微乎其微的話——“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對于一個卑微、渴望異性和在愛情里九死一生的女子而言,也具有發(fā)聵震聾的心靈震撼和感情慰藉。何況這個男子出現在她最美的年紀,最憧憬愛情的時節(jié)——十五六歲。至于回憶中的其他要素——春天、晚上、手扶桃樹,身穿月白的衫子,在幾十年光陰的阻隔下,是真是假,無人知曉。文中的“那年”“她記得”字樣,表明當年相遇的一幕不過是主人公在事過之后的自我追憶,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完全不排除她用一個完美的愛情故事來重構、美化當年的一幕。在男子缺席的前提下,女子肆意地進行自我言說、自我暗示、自我安慰成為可能。女子手扶桃樹是少女祈望愛情的姿態(tài)。對于一個懷春的無愛女子,哪怕只是一句話也會發(fā)酵成一句愛情表白。只可惜“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6]117。
三單一的女性敘述視角運用
單一的女性敘述視角在寫作上成全了女子的愛情臆想。完整的愛情行為雖是兩性之間的身心交流與互動,但愛情體驗卻是基于個人之上的私人情感。《愛》即是采用了女性單一敘述視角的個人愛情體驗和認知。這種視角的選擇決定了男性在《愛》中只是一個女性主觀情感支配下的被敘述對象,男性主體形象缺失,淪為一個符號空洞存在,男性在兩性愛情中的行為和主觀態(tài)度完全存在著被女性改寫和重構的敘述可能。這種敘述視角也為女孩以“回憶-夢”的方式重構那一次的見面提供敘事學的可能。因此單憑女孩的自我言說難以確認兩者之間真實的關系以及見面時的真實情味。但是盡管男性缺席也不能阻礙女子作為單戀主體的愛情臆想和在臆想中獲得一種替代性的情感滿足。因此,文中的那個年輕人,他姓甚名誰,身處何方,甚至他是否愛她……關于男性主角的一切信息對于女子而言都不重要。他只需要作為異性符號、女子情感的對應物存在即可。她臆想中的他一定與事實中的他相差甚遠,但這也無所謂,女子本沒有任何現實的功利目的,她既不會去求證、尋找,也不會去期圖再次相遇。她需要的只是回憶,以回憶的方式做夢。在夢境里,臆想一種莫須有的情感和莫須有的情人,并以此慰藉心靈。一個女子在臆想中的單戀行為,不是愛,如果說單戀是愛,那也是一種不完整的、殘缺的、迫不得已的愛。
結語
綜上,《愛》實則是一個無愛的感情故事。將一個無愛的見面臆想成有愛的回憶,把一個無情的男子假想成有情的情人,如果說這是那個歷經磨難的女子對于愛的委曲求全、聊勝于無,那么聰明如張愛玲,大概不會不知這一空前絕后的“一面”難以承載“愛”的內涵,且這殘缺的單戀對于女性人生的殘酷?可作者偏要把這女子的情感方式命名為《愛》,并特意配上煽情的文字,但是無論再華麗、驚險的奇遇也難以改變男女主角無話可說的、擦肩而過的慘淡結局。愛情從來沒有降臨過,愛情在哪里?愛情只在對愛情的期待中,在每一個期盼愛情的人心里。張愛玲在《愛》中十分隱晦地表達出:男性缺席和無所作為是導致女性人生無愛的重要原因,加之現實生活中諸多偶然和無常因素造成了女性情愛世界的孤獨。
聯系張愛玲的其他作品,讀者會發(fā)現,她在《愛》中表現出這樣的愛情觀、兩性關系、女性生存體驗絕非偶然。綜觀張愛玲全部的小說創(chuàng)作,少有真正意義上兩情相悅的男女:《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 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留情》,其中男女皆因各種現實的利益和需要,成為戀人、情人、夫妻。葛薇龍、白流蘇、曹七巧,王嬌蕊、敦鳳,哪一個女性的情感經歷不委屈?即使遇到彼此相屬的男女,也會因各種現實障礙而半路夭折:如《十八春》《多少恨》,曼楨、家茵已經彼此表明心跡的男女一樣最終天各一方;又有多少女子在兩性關系中遭遇尷尬、侮辱甚至飲恨而死,如《連環(huán)套》《封鎖》《花凋》《色戒》里的霓喜、吳翠遠、川嫦、王佳芝,她們的情感經歷更加不堪,生命越發(fā)似一襲爬滿虱子的華美的袍。無數無法圓滿的男女和情感,構成了張愛玲情感世界的殘缺圖景。因此張愛玲如是嘆息:“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7]211。
盡管如此,愛和婚姻對于女性,特別是傳統(tǒng)女性,尤其是那些以愛而謀生的、做不了“女打字員”只能做“女結婚員”的女性,結婚就是她們人生的重要內容。“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5]以男人為中心,向男人討愛、討生活,這不是女性的軟弱依附,沒有獨立性,造成女性這種生存局面的是女性特定的性別角色、文化內涵、歷史地位。但在女性一廂情愿的兩性關系中,多數男人并未帶給女子期待的愛和幸福,相反卻屢屢傷害女性。女性空有一腔感情,事實卻是“對于這個世界她要愛而愛不進去”。女性的愛情被無情地懸置了,女性的失意人生亦不可避免,愛情也因現實中的種種兩性悲劇成為可遇不可求的水中月、鏡中花。這樣殘缺的愛情觀以及女性愛情悲劇命運,是張愛玲對于女性生存狀態(tài)最真實的理性認同和情感體驗。雖殘酷,事實卻如《愛》的開篇——“這是真的”。
只有認識到生命的殘酷,愛情如霧里看花,才能深刻理解張愛玲在文末煞有介事的抒情:“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5]前半句常為后人引用,以此形容男女千載難遇的命運機緣,后半句卻戛然而止,欲說還休。生命的熱情、愛情的熱盼,被生生地阻隔在一句隔靴搔癢的話中。不是含蓄,不是此時無聲勝有聲,而是“沒有別的話可說”,非不能言,是無言。盡管文字溫柔,問候看似情意綿綿,也難掩女性巨大期待后的心理失落,以及失落后聊以自慰的無奈情感。是的,“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愿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5]。但難能可貴的是,張愛玲的《愛》在看透愛情的虛無、生命的蒼涼后,依然采用一種溫情的寫作調子,不點評是非、不褒貶男女,不露愛憎、不顯悲喜,在更高的生命層次上獲得和解,不為別的,只因張愛玲擁有“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的悲憫情懷,這也是《愛》能成為經典,獲得無數讀者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1]張曉琴.荒涼意境中的追尋者:由散文《愛》透視張愛玲創(chuàng)作的情感世界[J].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1):103-107.
[2]劉莉.一個豐富的精神分析文本:張愛玲散文《愛》的寓意解說[J].名作欣賞,2008(12):40-42.
[3]冉芳,高衛(wèi)華.體悟愛的荒涼:解讀張愛玲的散文《愛》[J].名作欣賞,2006(17):94-96.
[4]楊學民.以“愛”悟“空”[J].名作欣賞,2009(5):86-89.
[5]張愛玲. 張愛玲文集:四[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6]張愛玲.張愛玲文集:二[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7]張愛玲.張愛玲文集:一[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責任編輯:王露〕
Love Expression of a Feminine Life Without Love :
on Essences of Zhang Ailing’s Prose Love
YU Ling
(LeshanNormalUniversity,Leshan614000,Sichuan,China)
Abstract:Zhang Ailing’s prose Love is hugely confusing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love. The autho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l(fā)ove”, but she tells a story about a woman’s one-sided love. It describes the woman’s one-sided lov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a deficiency of the foundation of love, a reconstruction of “memory and dream”, and a narration from feminist perspective. Lovelessness and lonely living condition are still the truth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Zhang Ailing’s works.
Key words:Zhang Ailing; Love; femininity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365(2015)11-0090-05
作者簡介:余玲(1974-),女,四川樂山人,副教授,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