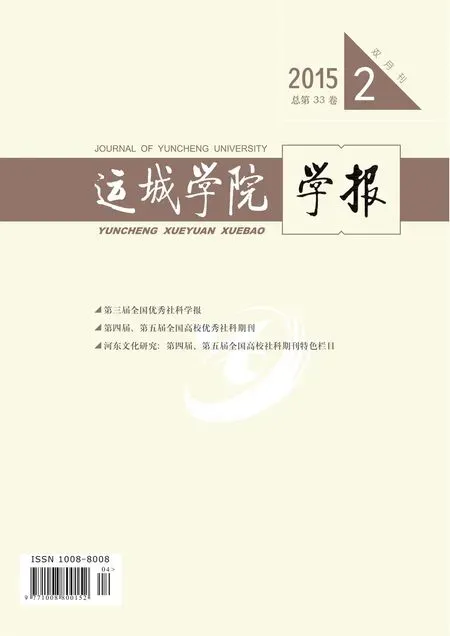李商隱移居永樂的地域因素及時間
智宇暉
(瓊州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海南三亞572022)
李商隱移居永樂的地域因素及時間
智宇暉
(瓊州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海南三亞572022)
河東道永樂縣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早期寓居之地,創作詩歌數十首,在其創作歷程中據特殊地位。他選擇永樂置別業,受時代風氣的影響,與永樂地近長安的地理方位密切相關。他隱居永樂的起始時間,也是需要考察的問題。
李商隱;永樂;地域因素;時間;次數
李商隱生平數度至河東道,或從幕,或寓居,留下了生命的足跡,其中以大和六年至七年在令狐楚河東節度使幕府和會昌四年至五年在永樂閑居時居留較長。尤其是永樂閑居時創作詩歌數十首,表現了他這一時期特定的感情軌跡和別樣詩風,留下了永樂文化的因素。他選擇永樂為閑居之地,與永樂的地理方位密切相關。
一、李商隱永樂寓居的地域因素
李商隱選擇蒲州永樂縣作為寓居之地,與永樂縣地近京師的地理位置有直接關系。永樂縣行政設置沿革,新舊唐書之《地理志》和《元和郡縣圖志》均有記載,以《元和志》為詳。《志》云:“永樂縣(文中小注:次畿,北至府九十里),本漢河北縣地,周明帝改河北縣為永樂縣,武帝省永樂縣,以地屬芮城縣。武德二年,分芮城于縣東北二里永固堡重置永樂,屬芮州,七年移于今理,貞觀八年改屬。”[1]328-329永樂縣位于蒲州府最南端,北倚中條山,南鄰黃河,《元和志》云:“中條山,在縣北三十里。河水,經縣南二里。”[1]329永樂背山臨水,環境優美,岑參《題永樂韋少府廳壁》云:“大河南郭外,終日氣昏昏。白鳥下公府,青山當縣門。”[2]138閻防《與永樂諸公夜泛黃河作》云:“煙深載酒入,但覺暮川虛。映水見山火,鳴榔聞夜漁。愛茲山水趣,忽與人世疏。無暇然官燭,中流有望舒。”[3]583永樂作為楊玉環的籍貫地為人熟知,雖隸屬于蒲州轄區,而處于蒲州與虢州的交接地帶,與虢州僅一河之隔,在歷史上曾一度隸屬于虢州管轄。《新唐書·地理志》云:“永樂,次畿。武德元年置,本隸芮州,州廢,隸鼎州,貞觀八年來屬,后又隸虢州,神龍元年復故。”[4]1000永樂縣至長安之交通路線有距離相近的兩條,一條是向北90里至蒲州府駐地之河東縣,再向西4里過蒲津關,入同州境南下達長安。蒲州距長安320里,則永樂經此路達長安途程為410里;另一條是從永樂縣直接向南渡過黃河,達虢州之湖城縣,向西經潼關入長安。湖城縣東緊靠虢州,虢州西至長安430里。這樣特殊的地緣,便于居住在這里的士人既能隨時往來于京師與居住地,及時獲得京城的政治信息,干謁政治上層人物,拓寬人際交往的渠道,又不像長安生活費用高,能夠在尋求仕進機會與維持家庭生活方面取得協調。實際上,后一方面的問題曾經困擾著李商隱,開成四年由秘書省正字出為弘農尉,即有離開京城降低生活費用以養家的因素。開成五年作《與陶進士書》云:“去年(開成四年)入南場作判,比于江南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啟與曹主,求尉于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5]435實際上,在唐代,因地緣關系寓居永樂的士人非李商隱一人。
盛唐詩人岑參,幼童時代曾隨父母居河東道晉州十年,十余歲即隨母徙居他處。成年以后又曾在永樂縣定居。岑參有詩《夜過盤豆隔河望永樂寄閨中效齊梁體》云:“盈盈一水隔,寂寂二更初。波上思羅襪,魚邊憶素書。月如眉已畫,云似鬢新梳。春物知人意,桃花笑索居。”[2]134-135盤豆即盤豆驛,屬湖城縣,與永樂隔河相望。按諸詩意,岑參游歷在外,夫人獨居永樂閨中,作詩以寄夫妻之情。
中唐宰相武元衡亦曾在永樂寄居,其《使次盤豆驛望永樂縣》云:“山川不記何年別,城郭應非昔所經。欲駐征車終日望,天河云雨晦冥冥。”[3]1161-1162
與李商隱同時稍前之李石,晚唐宰相,會昌三年末至四年初為河東節度使,在永樂有別居。《酉陽雜俎》《玉泉子》《北夢瑣言》皆有記載,《酉陽雜俎》續集卷十云:“三枝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6]晚唐詩人薛逢有《送李倍巡官歸永樂舊居》,據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李倍為李涪之訛誤,《文苑英華》正作“涪”。據《新唐書·宗室世系上》大鄭王房條:李福子涪。李石李福兄弟為唐宗室,于永樂建別宅,至李涪時尚居于此地。
李商隱友人劉評事、韋評事亦曾寄居永樂。義山先后有詩《和劉評事永樂閑居見寄》、《大鹵平后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二公嘗于此縣寄居》、《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劉、韋二人姓名不詳,應為與李商隱同時交游的下層文官。
稍后于李商隱寓居的尚有罷幕士人盧穎。高元謨《侯真人降生臺記》記述大中五年永樂縣中條山道靜院有道士侯道華修道升仙事,中有“忽有范陽盧穎自蒲罷幕,寄居永樂,閑游道靜,因詰削松枝者誰,曰‘道華’。盧君詬責,欲請邑宰治之”[7]云云。
晚唐宰相張濬亦曾于永樂居住。《北夢瑣言》云:“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中前行,后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回顧,乃是此道人。相國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人勉其入蜀,適遇相國圣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后歷登臺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8]《新唐書》本傳所載與《北夢瑣言》異,傳云:“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泛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為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4]5411兩書所載,應以《新唐書》為是。黃巢之亂以前,張濬已經楊復恭推薦入仕,黃巢亂后避走長安以南之商山。綜合兩書記載,黃巢入長安,張濬返回永樂居所奉母南下至商州山中避難,后仕至宰相。永樂縣境有五老峰,為道教名山,永樂境內神仙信仰氛圍濃厚,前述侯道華成仙事為晚唐時轟動朝野之新聞,侯道華成仙羽化后,時人“瞻禮稱嘆,焚香供養,日有千眾,歲余不絕”。《宣室志》卷九云侯道華仙去后,院中道士相率白節度使鄭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齋絹五百匹,賜御衣,修飾廊殿,賜觀名‘升仙院’”[9]。張浚由處士而富貴顯達,為鄉人所艷稱,道士利用此事造作傳說,宣揚神仙道術。可以推測,張濬能夠“以捭闔干時”,獲得政治高層人物的青睞而步入仕途,與其寄居地鄰近京師有重要關系。
由以上簡略考察可知,李商隱選擇永樂作為閑居之所,并非個人的偶然選擇,有時代氛圍的影響。反過來說,正是由于永樂縣特殊的地理位置,才使得李商隱在此處創作了數量可觀的詩歌,映射著永樂縣一定的地域文化背景。
二、永樂寓居的次數與時間考察
李商隱會昌中寓居永樂的時間,馮浩《玉谿生年譜》、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和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附《李商隱年表》,皆屬之會昌四年春至會昌五年春之間,然而是否首次寓居永樂及寓居永樂的起始日期則異說紛紜。以下稍作辨析,以明確李商隱與永樂的具體關系。
李商隱會昌四年以前曾寓居永樂,為多數研究者持有之觀點。馮浩《玉谿生年譜》《玉谿生詩集箋注》、葉蔥奇《李商隱詩歌疏注》、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傅巧英《李商隱在山西的行蹤及其詩作系年考證》皆主此說,其主要依據是《大鹵平后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二公嘗于此縣寄居》詩中的相關表達:“驅馬繞河干,家山照露寒。依然五柳在,況值百花殘。昔去驚投筆,今來分掛冠。不憂懸磬乏,乍喜覆盂安。甑破寧回顧,舟沈豈暇看。脫身離虎口,移疾就豬肝。”[10]479-480馮《箋》謂“其云‘依然五柳’,又云‘昔去’、‘今來’,則其前必已居之”。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更明確而言:“‘五柳’顯指舊宅,詩云‘依然在’,重返故居口吻顯然。……且上句云‘家山照露寒’,更可證永樂為義山舊居。”[10]486劉、余《集解》又以《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手種悲陳事”句為義山曾經寓居永樂的輔助證據,云“義山經營永樂所居,恐不自居喪移家之日始,而永樂之為義山舊居亦可進一步證實”[10]500。傅巧英《李商隱在山西的行蹤及其詩作系年考證》亦以《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詩題為補充證據,認為無論此詩作于會昌四年或五年,新栽種的樹木長至枝繁葉茂,非短期所能達到,故李商隱在會昌四年之前肯定曾經在永樂寓居[11]49。張采田基本持相反觀點,《玉谿生年譜會箋》謂:“詩云‘依然五柳在’者,以陶令閑居自比。‘昔去驚投筆’,謂從前歷佐方鎮。‘今來分掛冠’,謂此后自甘閑費。”又明確言:“義山從前未嘗于永樂寓居,‘昔去’句不過泛言當日入幕耳。‘依然五柳在’句,自指二公(按:指劉韋二評事)舊居而言。”[12]相較而言,主張李商隱會昌四年之前曾經寓居永樂之說證據較為充足,張采田對詩歌的闡釋過于忽視詩人詩句中蘊含的與創作地點的情感聯系,其說不能成立。此外尚有另一首詩《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的內容也傳達出李商隱曾經在永樂寓居的信息,詩中有“滿壺蟲蟻泛,高閣已苔斑。想就安車召,寧期負矢還。潘游全璧散,郭去半舟閑”[10]506之句,表明作者曾經與韋評事同居永樂縣,同游共飲,而此際兩地暌隔,仕隱異途。
關于李商隱寓居永樂的起始時間,諸家之說各有不同。馮浩《玉谿生年譜》定長慶三年父喪除服后,李商隱即移居永樂。其理由是,據《祭裴氏姊文》記載,其父親去世后,“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祔故丘,便同逋駭。生人窮困,聞見所無。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數東甸,傭書販舂”[5]814。“占數”即占戶籍之數,蒲州在西京東北三百里外,貞觀中升為四輔,故曰東甸。后會昌四年移家永樂,有“昔去驚投筆,今來分掛冠”句,則“占數東甸”指移居永樂。然馮氏于“永樂說”亦無把握,又提出“懷州說”加以補充,游移不定[13]。張采田《年譜會箋》和劉學鍇《李商隱生平若干問題考辨》不同意馮浩觀點,就“東甸”又分別提出“洛陽說”和“鄭州說”,二說對馮浩之說無有力之反駁,而是圍繞各自主張提出許多正面的論據,其中尤以劉學鍇之“鄭州說”最具說服力。馮浩此說尚有可疑之處,據李商隱會昌四年至五年寓居永樂所作詩歌,其前期的永樂寓居距離會昌四年為時不會太久。《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味題意,永樂居所的一草一木都是自己曾經親自栽種的,到今年春天都已經長得非常茂盛了。如果是長慶三年即移居永樂,距會昌四年已15年之久,此時的樹木早已圍拱參天,不宜如此口吻。詩題所言應是栽種花木時間尚未太久,詩人即欣喜已經長得繁茂,故作詩達情。又據《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中回憶與韋評事的飲酒暢游,且云“共誓林泉志”,應是成年以后情事,長慶三年李商隱方始十二歲,到十八歲入令狐楚幕府,少年時代不可能有此種生活情致。再者,李商隱《大鹵平后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二公嘗于此縣寄居》稱韋評事為前輩,非少年時代好友的口吻。可以說,李商隱前期寓居永樂已經成年。是否可以說,少年時移居永樂,到成年時方始栽種草木,與友人游賞宴飲呢?這種推測過于紆曲,而且最關鍵的是,在有關李商隱早期生活居住地的文獻記載中,鄭州、懷州、洛陽在他本人的記述中都有可循的蛛絲馬跡,而唯獨無永樂之記載,這應該也是一個反面的證據。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在肯定義山會昌四年之前即寓居永樂為事實的同時,對于其始居時間則持存疑態度。傅巧英《李商隱在山西的行蹤及其詩作系年考證》又提出了開成四年說,理由有二。第一,李商隱開成四年《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中有“思子臺邊風自急”句,懸想母親對游子的思念,永樂縣與盤豆驛隔河相望,而岑參又有詩《夜過盤豆隔河望永樂寄閨中效齊梁體》,因此極有可能此時李商隱母親即居住在永樂。第二,據《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樹木從栽種到繁盛茂密需五六年的時間,從開成四年至會昌四年相隔日期正與樹木生長期相符,故定會昌四年為宜[12]49-50。傅氏此說有牽合比附之嫌疑。實際上,尚有堅實證據表明,開成二年至開成五年,李商隱家居濟源。張采田《年譜會箋》引錢楞仙說,據開成二年《上令狐相公第六狀》中“雖濟上漢中,風煙特異;而恩門故國,道里斯同。北堂之戀方深,東閣之知未謝”[5]118之句,濟上即濟源,義山母親時居濟源。又會昌四年作《祭裴氏姊文》云:“小侄寄兒,亦來自濟邑。”[5]815-816同年作《祭小侄女寄寄文》又云:“寄瘞爾骨,五年于茲。”[5]830則寄寄開成五年夭折于濟源,商隱弟羲叟其時同居于濟源,故寄寄暫時埋葬其地。因此,傅巧英開成四年之說亦誤。
考之李商隱生平,有關早期永樂寓居正面證據不多,實難確切考索,選出行跡明確且地理空間上與永樂相近、時間上與會昌四年相隔不太久遠的人生階段,或許可以推測早期寓居永樂的可能線索。按既然少年時代“占數東甸”非屬永樂,且開成元年之前的寓居時間距離會昌四年久于十年以上,所以考察李商隱早期寓居宜限定在開成元年之后。開成二年登第之后,李商隱曾經東歸濟源省母,可知開成元年已經在濟源居住,直至開成五年十月,又由濟源移家長安。會昌二年,母親去世,會昌三年在京守喪,又因岳父王茂元去世及親屬遷葬事宜,往來奔波于洛陽、河陽、懷州等地,三年底即赴太原李石幕府。(參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年表》)此八年時間,先居濟源,又遷居長安,似無寓居永樂的可能。以往研究者執著于同一時間居住地唯一性的前提,非此即彼,故永樂寓居撲朔迷離。事實上應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即李商隱在家居濟源或長安的同時,亦有可能于永樂另置別宅。準此思路,再考察李商隱此期行蹤,任職弘農尉與入周墀華州幕府與永樂地理相近,弘農縣與華州皆與永樂隔河相對,一在永樂東南向,一在西南向,且居留時間都一年以上,有在永樂置宅之可能。李商隱任弘農尉為開成四年春夏至開成五年九月,十月得到河陽節度使李執方資助,即由濟源移家長安,如在弘農尉任已置永樂居所,必無緊接著由濟源遷居長安之理。相較而言,開成五年年末至會昌二年春在華州幕的時期,置永樂別居的可能性較大。首先,在周墀幕,未有幕職,且時往來于華州和長安之間,李商隱有余暇短暫閑居永樂;其次就時間上言,會昌元年距離會昌四年再次寓居永樂時間未久,與《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詩題所表達較為相符,故李商隱極有可能在會昌元年(841)至二年(842)在華州刺史周墀幕府時首次寓居永樂。
[1]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M].成都:巴蜀書社,1995.
[3]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第二冊)[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4]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5]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2.
[6]段成式.酉陽雜俎[M].北京:中華書局,1981.
[7]董誥.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
[8](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56.
[10]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1]傅巧英.李商隱在山西的行蹤及其詩作系年考證[M].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2).
[12]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3](清)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責任編輯 咸增強】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Time of Li Shang-yin's moving to Yongle
ZHI Yu-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Qiongzhou University,Sanya572022,China)
Yongle County in Hedong area was Li Shangyin's early residential place where he composed dozens of poems.This county was important for his poem writing.He chose to stay seclusively in Yongle because of the then social influence and its favorable geographical position which was near Changan.But from when he began to live in Yelong is still a question.
Li Shang-yin;Yongle;geographical factors;time;times
D638
A
1008-8008(2015)02-0022-04
2014-10-21
智宇暉(1976-),男,山西太谷人,瓊州學院人文社科學院講師,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