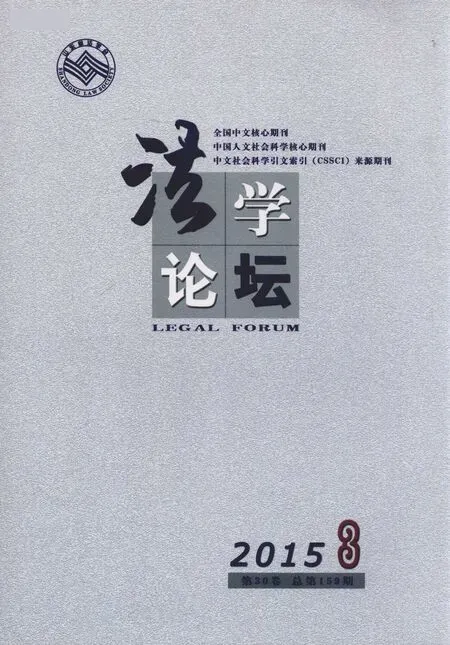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焦津洪 高 旭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北京100020)
一、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概述
(一)由巴克萊公司證券欺詐案看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
1、紐約州首席檢察官訴巴克萊公司證券欺詐賠償案。巴克萊公司是一家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擁有眾多投資者的公司,是英國排名第三的四大私有銀行之一,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最有實力的金融機構之一,其業務范圍涉及金融、機械、造船、航海等諸多領域,在世界50多個國家有分支機構并開展業務。該公司為了獲取更多的投資利益,采取了場外交易的做法,建立所謂的“黑池”吸引投資者投入資金,并向投資者承諾在“黑池”內的交易購買其股票的客戶將獲得在場內交易更為豐厚的利益,并且保護客戶的資金安全。而實際上,巴克萊公司將來自投資客戶的股票幾乎全部放在“黑池”進行交易,而不是在法定的交易所完成。由于數量巨大,所以可以達到擾亂和操縱證券市場的目的。紐約州的首席檢察官,認為巴克萊公司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證券欺詐行為,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掠奪了投資者的財富,使廣大投資人蒙受損失,所以2014年6月23日在紐約州對巴克萊公司提起了證券欺詐賠償訴訟。
2、美國檢察官在證券欺詐賠償案件中的作用。在美國的檢察制度中,檢察官承擔控訴職能,這主要是針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對于經濟糾紛,檢察官多數情況下并不涉足,然而當經濟領域內的行為過分違反社會公正或者嚴重影響社會效率以至于會使社會整體福利下降時,檢察官則可以對不法行為以私訴的方式發起訴訟。①參見張鴻巍:《美國檢察制度研究》(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0頁。在證券領域之內,發生欺詐行為往往會涉及眾多受害者,而且所受損失巨大,單憑投資者個人之力往往難以達到使受害群體整體利益得以恢復的效果,檢察官此時提起私訴則能夠實現使更多受害者得到救濟的目的,此種私訴在理論上通常被稱為檢訴制度。在美國的證券欺詐賠償訴訟中,檢察官也可以介入,此時檢察官的作用有兩個:一是,能夠通過私訴方式使在證券欺詐過程中受害的當事人的損失得到最大限度的救濟;二是,檢察官的私訴可以使已經被破壞的證券交易秩序得以恢復,從而實現社會資源得到公平的再分配,以使社會整體效率和福祉得到提升。
(二)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的價值
1、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的應然價值。法的應然價值是一項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目標,是法律制度在內容和形式上所追求的理想狀態。①參見[德]羅伯特·阿列克西:《作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頁。同理,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的應然價值應當是該項法律制度在內容和形式上所欲達到的理想狀態。從內容層面看,美國檢察官提起私訴有著嚴格的條件,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介入訴訟,而具體到證券欺詐領域內,還需要同時滿足《證券交易法》第10節和第11節的相關規定,這些規定構成了完整的體系,將檢察官啟動證券欺詐賠償私訴限定在一定的范圍,既可以為證券投資人提供一條新的救濟路徑,又可以防止檢察官濫用訴權,達到行權與控權相互制約相互發展的目的。從形式層面看,美國檢察官提起私訴是受害人個人提起私訴的一種補充形式,主要用于證券欺詐可能會極度影響社會公正的情況,而且其啟動程序也有著嚴格的要求,這不僅使受害投資者的權益能夠得到更為廣泛的救濟,同時也豐富了訴訟的種類,如同普通法和衡平法之間的關系一樣,受害人在一種訴訟程序下難以得到充足的救濟時可以轉而尋求另一種救濟模式。②參見[美]羅斯科·龐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高雪原、廖湘文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頁。
2、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的實然價值。法的實然價值是一項法律制度在實現的過程中所實際發揮的效果。③參見嚴存生:《法的價值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09頁。在美國的訴訟領域之內,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的實然價值是檢察官提起的證券欺詐賠償訴訟所能夠發揮的積極效用。美國是市場經濟非常發達的國家,市場機制的調節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而在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看來,社會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資源需要以一種市場化的、公開競爭的方式進行分配,以形成一種秩序,從而使社會財富實現最大化,法律尤其是公法僅僅是維持該種秩序的一種手段。當市場機制自身難以完全解決實際矛盾時,則需要公法的介入。④參見[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七版),蔣兆康譯,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37頁。所以,美國社會對交易秩序和交易效率極為重視,經濟法律制度的設計以及規則的運用也圍繞秩序價值和效率價值所展開。⑤參見[美]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法律缺失與經濟學:可供選擇的經濟治理方式》,鄭江淮、李艷東、張杭輝、江靜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具體到證券欺詐賠償訴訟,檢察官介入所能夠發揮的實際效果是使證券交易秩序得到強力恢復,使交易行為能夠在高效率環境下運行,進而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
二、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程序啟動條件的法律經濟學考察
(一)證券欺詐賠償檢訴程序啟動的成本
在美國訴訟程序中,啟動一項訴訟會耗費較多社會資源,所以將社會資源控制在最小化,就成為訴訟所追求的目標之一。⑥參見[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第六版),史晉川、董雪兵等譯,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頁。對于訴訟成本而言,可以分為管理成本和彌補錯誤的成本兩大類,⑦[美]理查德·A·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徐昕、徐昀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以上文所述的巴克萊公司證券欺詐案為例,受害人啟動訴訟的管理成本是所有的受害人為維護自身受損利益而消耗的成本總和,當然管理訴訟的成本總和越少,則受害投資人所耗費的社會資源則越少,這是每一位受害者都希望達到的目標。由于每一個人都可能犯錯誤,所以受害人在提起訴訟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疏漏,從而為之付出一定代價,該代價為彌補錯誤的成本。在證券欺詐訴訟中,受害投資人眾多,若每一受害主體均提起證券欺詐賠償訴訟,其中一些受害主體由于缺乏法律常識或者不具有專業性犯下各種錯誤在所難免,所以彌補錯誤的成本會客觀存在。檢察官作為法律專業人事,相對于普通投資人而言更加了解訴訟程序,對證券公司提起證券賠償訴訟可以將管理訴訟的成本和由于疏漏而額外支出的成本降到最低,所以檢察官提起證券欺詐賠償訴訟是社會資源消耗最小的一種方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美國并非全部場合檢察官都會以私訴方式介入經濟糾紛,而是在管理成本和彌補錯誤的成本能夠大幅度降低的情況下,檢察官會選擇考慮提起私訴。
(二)證券欺詐賠償檢訴程序啟動所能獲得的收益
對于受害的投資者而言提起證券欺詐賠償訴訟是為了挽回自身的經濟損失,具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法院的支持需要看證據的提供以及訴訟技巧等多方面因素,由于證券欺詐是行為人通過自身對信息資源掌握的絕對優勢而侵害投資人的利益,而受害投資者在證據的獲取方面處于劣勢,在訴訟對抗程序中處于不利位置,從而影響訴訟收益的程度。①參見[美]斯蒂文·薩維爾(Steven Shavell):《法律經濟分析的基礎理論》,趙海怡、史冊、寧靜波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頁。在美國,檢察官提起私訴很好地解決了這一矛盾。在檢察官提起證券欺詐賠償訴訟中,檢察官不僅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獲得更多的訴訟利益。同時在制度層面美國的檢察官在提起私訴的過程中可在一定范圍內行使調查取證權,②參見張鴻巍:《美國檢察制度研究(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頁。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證據弱化效應,所以在訴訟收益方面可以獲得一定提升。不僅如此,檢察官提起證券賠償欺詐訴訟,還可以獲得社會公正價值的回歸以及市場交易秩序的矯正這樣的訴外收益,這類收益雖然不屬于訴訟請求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是訴訟目的價值的重要內容。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只有檢察官提起私訴后所獲得的社會收益遠遠大于受害者個人提起的訴訟時,檢察官才會提起私訴,因為值得提起,所以一般情況下檢察官提起私訴基本上針對大規模侵權事件。
(三)證券欺詐賠償檢訴程序運行的效率
關于法律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在美國社會中有著較為深刻的詮釋,認為法律是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輔助手段之一,③參見[美]羅賓·保羅、馬洛伊:《法律和市場經濟——法律經濟學價值的重新詮釋》,錢弘道、朱素梅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頁。目的是通過法律對市場中不規則行為的矯正使市場秩序得以恢復,使社會資源得到有效的再分配,提升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最終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因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法律規則與經濟效率和社會財富分配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④參見[美]斯蒂文·G·米德瑪:《科斯經濟學——法與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羅君麗、李井奎、茹玉驄譯,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頁。從制度層面看,在訴訟領域之內,檢察官提起私訴是公權以訴訟方式在私權領域內的滲透,其目的是對被破壞的市場秩序的強力糾偏,以恢復市場秩序、提升經濟效率,進而實現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促進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從實踐層面來看,以巴克萊公司證券欺詐案為例,檢察官提起的私訴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調查取證的成本,而且這種節約在受害群體眾多的情況下尤為突出,同時在管理訴訟方面的成本以及彌補錯誤疏漏付出的成本也會相應減少,而由此獲得的收益卻有所提升,當然這種提升在受害者眾多的侵權訴訟中十分明顯。由于“訴訟效率=訴訟收益/訴訟成本”,⑤參見[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第六版),史晉川、董雪兵等譯,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頁。很明顯,檢察官提起證券欺詐賠償訴訟可以得到訴訟效率的提升,從而可以促進證券市場交易秩序的盡快恢復,以實現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社會財富向最大化方向提升。因此,在美國的市場經濟中,若檢察官提起私訴可以促進訴訟效率的提升和促使市場經濟秩序得到恢復,則可以行使這一訴權。
(四)證券欺詐賠償檢訴程序啟動的公平正義觀
以法律經濟學的觀點看,美國的訴訟體系中,檢察官提起私訴要滿足的經濟條件無非是三個:(1)所提起的訴訟能夠帶來司法訴訟成本的大幅度降低,節約司法資源和社會資源的配給。(2)可以獲得更多訴訟利益,這些利益既包括了訴訟標的本身這樣的顯性利益,同時也包含了市場秩序的恢復、經濟效率的提升等隱性收益。(3)能夠獲得訴訟效率的提升,從而獲得社會資源的高效率再分配,促使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可以說,經濟條件是美國檢訴制度啟動的重要條件,但絕非唯一條件,在美國這樣普通法與衡平法都高度發達的國家,檢察官對于公平正義的考量也是檢訴制度啟動的一個重要誘因。因為在美國,檢察官有著非常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只要其認為社會公平正義遭受嚴重侵害時,就可以提起私訴。當然,美國著名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看來,在法律經濟領域內所謂的公平正義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整體財富的最大化,這不可避免地會使一些人的利益無法得到全部的滿足,因而就有了“對正義的追求不能無視代價”這樣的公平正義觀。⑥參見熊秉元:《正義的成本:當法律遇上經濟學》,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頁。所以,以證券欺詐賠償檢訴程序的啟動為例,檢察官除了要考量經濟因素之外,還會從法律均衡的角度來考量公平正義,即將所有投資人對于賠償的需求看成是一種法律需求,而將訴訟制度看成是一種法律供給,當法律供給難以滿足多數人的法律需求時,就會出現法律供需失衡,從而影響社會整體對法律制度的懷疑和不信任,公眾會認為此種情況下的公平正義被破壞,這時就需要檢察官提供一種特殊的救濟程序來滿足受害投資人對法律訴訟的需求,此時檢訴程序得以啟動。
三、從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審視我國證券欺詐賠償訴訟
(一)證券欺詐賠償訴訟的成本過高
早在《證券法》通過之時,我國便已經建立起證券欺詐民事賠償體系,將證券欺詐的類型歸結為發行欺詐、市場操縱、內幕交易、欺詐客戶、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重大遺漏等7種基本行為。①參見宋曉燕:《證券法律制度的經濟分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頁。在司法實踐中,我國法院系統近些年來審理了不少關于證券欺詐賠償的訴訟案例,然而證券欺詐的受害投資人眾多,如何提起訴訟就成為實踐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就立法而言,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頒布了《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12-16條中規定了受害人可以提起個人訴訟也可以提起共同訴訟,此訴訟形式規定為人數不確定的共同訴訟。現實中,證券欺詐民事賠償案件中受害人為所有投資人,從理論上講屬于受害人人數確定的共同訴訟而非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因而如何適用法律提起共同訴訟在實踐中一直存在爭議。而在2015《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77條中依然沿用了“人數眾多在起訴時不確定”的表述,對于證券欺詐民事賠償案件而言,依然存在能否參照人數不確定的共同訴訟適用法律的問題。若參照適用則需要按照該解釋的規定選取代表人參與訴訟,此時管理訴訟的成本雖然比所有個體獨立訴訟的成本總和有所降低,但是受代表人管理訴訟能力的限制無法將管理成本降至最低,而且受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以及取證能力的限制,在訴訟過程中勢必也無法將錯誤率降至最低,而且被委托的代表人多是令眾多受害投資人信任的人,這些人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代表受害投資人參與訴訟也會消耗更多的機會成本,這些不利因素都使得證券欺詐訴訟的成本高居不下。
(二)證券欺詐賠償訴訟的收益與效率較低
與證券欺詐訴訟成本較高相對應的是,目前我國實踐中證券欺詐訴訟的實際收益并不高。從法律經濟學角度來看,收益可分為顯性收益和隱性收益兩類,顯性收益是訴訟結果,往往由于起訴人對于證券訴訟業務并不精通或者證據掌握不充分而導致訴訟結果并不理想,如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年11月14日判決的佛山照明證券欺詐案,平均每位投資人也僅得到了損失數額47% -50%的賠償金。②參見宋一欣:《從五糧液案看證券維權訴訟難點》,載《證券時報》2014年11月29日。而隱性收益是證券交易秩序的恢復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以目前的證券欺詐訴訟的發展現狀來看,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對證券市場交易秩序起到糾偏作用,但是從其賠償力度上來看這種糾偏的作用還有很大提升空間,所以隱性收益并未達到最高。由此可見,現行證券欺詐賠償訴訟的總收益還比較低。另外,證券欺詐賠償訴訟的效率不高。根據《規定》第5條和第6條的要求,證券欺詐侵權行為的訴訟時效從欺詐行為被采取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罰之日起計算,對同一欺詐行為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并存時,以先前處罰來計算訴訟時效。這一規定意味著證券欺詐侵權訴訟須以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為“前置”程序,而根據《規定》第11條的要求,在審理證券欺詐民事賠償案件過程中,若被處罰人不服行政處罰而引發申請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程序啟動時,法院須中止審理民事賠償訴訟,若行政處罰最終被撤銷或者歸于無效,則須裁定終結訴訟。如此的訴訟模式,會使證券欺詐賠償訴訟的風險加大,本來該類訴訟的成本就高而且收益并不樂觀,訴訟風險又比較大,此種情況下的訴訟效率顯然并不高。
(三)證券欺詐賠償訴訟的法律供需失衡
《規定》對證券欺詐的管轄權、訴訟方式、侵權認定、賠償與免責、損失認定等細節問題都給予了充分詳細的說明,雖然可操作性較強,但《規定》中僅針對虛假陳述和與虛假陳述關系緊密的行為給予了解釋和定義,并且也相應地規定了法律后果和民事賠償請求權行使的程序,而與虛假陳述關系較遠的市場操縱行為和內幕交易行為則并未做規定。從理論上講,法律對市場操縱和內幕交易兩類證券欺詐行為未做詳細規定等于限制了受害投資主體行使賠償請求權的權利,而在實踐中對于操縱市場和內幕交易這兩類證券欺詐行為的受害主體即被侵權人的合法權益保護得并不充分,很多情況下要么勢單力孤無法提起訴訟,要么掌握證據不充分無法完成訴訟,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所以,就目前的證券欺詐案件而言,有一部分受害投資人對于法律的需求無法得到全部滿足,至少是不會很順利地得到制度供給的救濟,這種供需矛盾凸顯出我國法律制度層面對于證券欺詐賠償訴訟的構建還不完善。
四、我國檢察機關證券欺詐公益訴訟職能拓展與設計
(一)我國檢察機關證券欺詐公益訴訟制度探索
眾所周知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公益訴訟制度,但是對于行使主體和行使對象以及行使條件都未作相應規定,故而未徹底解決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問題。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這為檢察機關進行制度性規范和開展公益訴訟活動提供了政策基礎。那么檢察機關能否將公益訴訟的觸角延伸到證券欺詐訴訟領域之內,我們完全可以從美國的檢訴制度中找到借鑒。
首先,從制度的發展來看。在美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高度依賴市場機制調節而盡力限制公權力行使的社會里,都不排斥檢察官對證券欺詐提起私訴,我們拒絕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其次,從制度的本質來看。美國的檢訴制度從本質上講可以實現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我國的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毋庸置疑也可以收到異曲同工的效果,將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職能擴展到證券欺詐領域之內,也是眾望所歸。最后,從制度的實施來看。無論是公益訴訟制度的制定還是實施,目前我國的立法技術以及法律實施能力都已經具備一定實力,制定相應的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并非不可能,將訴訟范圍拓展到證券欺詐領域之內也一定能夠實現。當然在制度設計時要對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民事賠償公益訴訟的宏觀條件有一個總體的把握,這樣才能增強該項制度的可操作性。
(二)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的司法成本考量
民行檢察是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司法職能的一個重要領域,但現行法律對該項職能的規范并不充分,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后各級檢察機關對于公益訴訟的探索和嘗試如雨后春筍般地開展,當然探索的重點基本上都放在了環境損害領域,原因是環境問題是全社會目前廣為關注的問題。而證券投資領域投資人會遍及全國,一旦發生欺詐案件,其惡劣影響也將遍及全國,必定會對正常的證券交易秩序造成損害,投資者對于證券投資的信任度也會大打折扣。而證券投資平臺是我國大型企業融資的重要渠道,關系到經濟發展的命脈,若證券投資交易秩序被破壞對市場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可小覷。①參見宋曉燕:《證券法律制度的經濟分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頁。此時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賠償訴訟,相當于對社會經濟秩序行使維護職能。當然,檢察機關將公益訴訟的探索向證券欺詐領域內延伸需要遵循一些原則,其中成本最小化原則應當設定為基礎性的原則,作為首要考慮的目標。在訴訟中需要耗費時間成本、取證費用、交通費用、公告費用等顯性金錢利益,而且還會耗費機會成本,即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方面投入了力量就必然會喪失將這些力量投入到其他方面所獲得的利益,②參見馮玉軍:《法律與經濟推理——尋求中國問題的解決》,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頁。這些成本的總和必須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圍。
具體而言,考量標準有兩個:(1)可承受標準。檢察機關若提起證券欺詐民事賠償公益訴訟,事先應當有一個初步預算,這些成本須是檢察機關可以承受的。(2)可預期標準。檢察機關若提起證券欺詐民事賠償公益訴訟,投入成本之后應當能夠達到可預期的目標,而且這一目標是合理的、可以實現的,若達到預期目標有困難、難以實現或者實現目標還需追加投入更多成本而總成本可能會超出檢察機關承受預期的,則不應當選擇提起證券欺詐民事賠償公益訴訟。因此,針對實踐中受害投資者提起的證券欺詐賠償訴訟成本過高的現狀,檢察機關雖然可以較小的成本完成訴訟,但還需要進行總體成本核算,將核算結果作為提起公益訴訟的基礎。
(三)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的司法程序收益估量
證券欺詐社會影響面廣,對證券交易秩序造成的破壞力不可小覷,而對于受害投資人而言,人數眾多且分布于全國各地,證據的獲取困難、訴訟的專業性不足、證據使用的準確率較差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單憑幾個個人的力量發起賠償訴訟,往往難以收到實際效果。檢察機關在調查取證、訴訟的專業性、訴訟低失誤率等方面較個人而言均具有先天優勢,以公益訴訟的方式來維護證券市場交易秩序成本低、效果好。但是,檢察機關在提起證券欺詐公益訴訟之前應當先對訴訟的預期收益進行評估,只有在收益能夠獲得預期值時才能夠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
一般而言,應當考慮三個方面的收益:(1)顯性收益。主要是訴訟標的的總量以及可實現程度,若總量較小或者可實現程度較小,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必要性的基礎則會喪失。(2)隱性收益。主要是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公益訴訟后可以實現恢復證券市場交易秩序的程度以及證券客戶信任恢復程度等隱含的可期待利益,若這些可期待的隱性收益較大,則值得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3)收益最大化。收益最大化是檢察機關在對提起公益訴訟后可期待的收益進行評估后,認為所能夠獲得的最大收益。在法律經濟學中,收益最大化是使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①參見[德]漢斯—貝恩德·舍費爾、克勞斯奧特:《民法的經濟分析》(第4版),江青云、杜濤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頁。即當檢察機關額外追加的單位成本投入與獲得收益的單位增加量相等時,則可以得到最大收益。換言之并非一味投入成本就可以獲得最大收益,同理對收益最大化的追求也應當考慮成本的投入。因此,對于實踐中證券欺詐賠償訴訟收益差強人意的現狀,檢察機關應當對上述三個方面進行全方位考慮之后方可作出是否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的決定。
(四)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的司法效率效果評估
實踐中證券欺詐賠償訴訟的效率并不高,與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直接關系,將行政或者刑事處罰作為民事訴訟的“前置”程序,無疑增加了訴訟的風險,從而降低了訴訟效率。檢察機關若決定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除了要衡量成本投入和收益率這樣的經濟指標外,“前置”程序在民事訴訟中的風險也是在起訴前應當考慮的。若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罰被撤銷的可能性較大時,則不宜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關于此類信息的獲取,檢察機關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檢察機關在核算成本后將成本控制在理性的最小范圍,而能夠獲得的利益達到理性最大,又可以將訴訟風險控制在可控范圍之內,則可以提起證券欺詐公益訴訟。當然,受害人的利益是法律上值得保護的利益,在訴訟中訴的標的可以表現為訴的利益,②參見[日]原田尚彥:《訴的利益》,石龍潭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而訴的利益本身具有獨立性,應當盡量依靠自身的程序來加以實現。
換言之,民事訴訟中訴的利益應當盡量依靠民事訴訟自身來解決,現行法律規范中,將受害證券投資人為實現利益而提起的民事訴訟能否完成取決于行政或者刑事程序的變更與否,顯然是不合理的。事實上,無論是行政法還是刑事法律體系中,均會涉及民事責任,均無一例外地規定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的承擔與否均不影響民事責任的承擔,這也是在處理法律責任問題上的一個思維傳統。因此,建議立法在對證券欺詐賠償訴訟修改時,取消“前置”程序的規定,以減少訴訟提起者的訴訟風險。
(五)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的司法目標設計
維護公平正義是檢察機關的使命,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法律領域內社會總體公平正義的實現要求法律的供給能夠及時滿足民眾對法律的需求實現法律均衡。③參見[美]理查德·A·波斯納:《正義/司法的經濟學》,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頁。從實踐來看,由于證券欺詐賠償訴訟具有受害人眾多,信息極度不對稱,調取證據困難而且成本高昂,受害投資人專業素質不足等諸多不利因素,這就愈發使得受害投資人需要以一種特殊的法律程序來實現自己的利益保護。所以,從理論上講,此時法律若能夠提供公益訴訟的供給,則能夠實現供需均衡,因此,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實現了供需均衡也就實現了社會整體的公平正義回歸。而從立法來看,現行立法對于證券欺詐訴訟的客觀方面限制過窄是存在缺陷的,未能實現法律需求的供需均衡,這有待日后的立法予以補充。
單就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公益訴訟而言,除了考量成本、收益、效率等經濟指標外,還應當考量法律供需均衡指標,要將提供法律供給作為實現公平正義的一項重要要素來對待。若證券欺詐行為造成的影響極其惡劣,嚴重影響社會公正,而提起證券欺詐公益訴訟可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回歸,那么檢察機關可以考慮提起證券欺詐公益訴訟。當然,對公平正義的判斷本身雖然沒有固定標準,但是對于極端情形卻可以找到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故不必過分擔心由于公平正義標準不明晰而導致檢察機關濫用訴權的情況,畢竟還有成本、收益、效率等要素對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公益訴訟的行為加以約束。
五、結語
2014年6月紐約州首席檢察官對巴克萊公司提起證券欺詐賠償訴訟,引發了我們對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的思考。美國的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是由檢察官提起的一種私訴形式,此種私訴方式能夠實現強化市場公開競爭、恢復公平交易秩序,促進社會財富實現最大化的目標。在美國這樣一個將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發揮到極致的社會中,法律制度的制定以至實施都充斥著交易成本、效益、效率、均衡、公平正義這樣的關鍵詞匯,所以法律經濟學成為美國法律領域內分析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方法。從該方法角度出發,可以看出,美國的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的啟動能夠節約更多的管理訴訟成本和彌補錯誤疏漏的成本,在收益方面則可以獲得比個人訴訟更多的隱性收益,所以訴訟效率是提升的,從而也促進了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然而美國證券欺詐檢訴制度的啟動并非僅僅看這些與經濟相關的指標,法律還賦予了檢察官相對寬松的自由裁量權,只要其認為證券欺詐行為會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時,也可以提起私訴。從美國這些制度性規定來審視我國的證券欺詐民事賠償訴訟,可以看出在成本的控制、收益的獲取、訴訟效率的提升、法律制度供需均衡的把握等幾個方面都差強人意,可提升的空間巨大。與美國檢察官提起私訴的做法相類似的是我國的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開啟了一扇窗戶,這使得我們看到借鑒美國的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建立我國的檢察機關提起證券欺詐賠償公益訴訟制度的可能性。當然,制度是社會規則博弈的產物,①參見[日]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周黎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在建立這一制度時須考慮諸多因素,要從節約司法成本、擴大社會收益、提升司法效率、維護公平正義等幾個不同層面來設定程序啟動的條件,便可以為我國的證券欺詐賠償訴訟設計出一條新的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