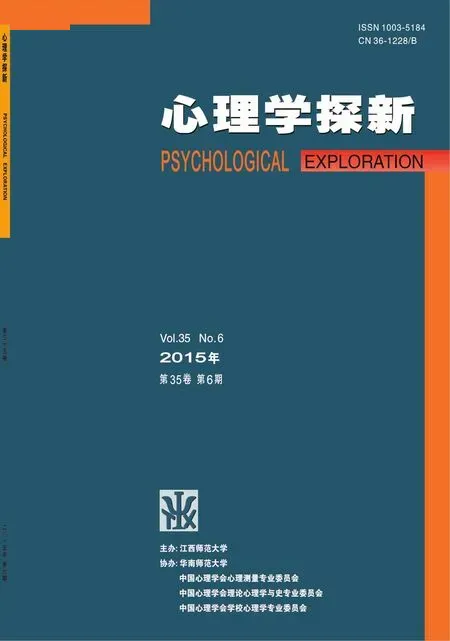中國現階段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的新趨勢*——以山東省未成年犯問卷調查為基礎
徐淑慧 蘇春景 劉若谷
(魯東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煙臺 264025)
?
中國現階段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的新趨勢*
——以山東省未成年犯問卷調查為基礎
徐淑慧蘇春景劉若谷
(魯東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煙臺 264025)
摘要:采用問卷調查法,以山東省2013年和2014年即將出監未成年犯為被試,對即將出監未成年犯的心理健康水平進行調查分析。結果表明:(1)即將出監未成年犯的心理健康水平顯著高于全國常模。(2)強奸罪的未成年犯與故意傷害或殺人罪及搶劫罪的未成年犯,在SCI—90的若干因子上存在顯著差異。(3)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年齡組的未成年犯在SCI—90的若干因子上有顯著差異。(4)暴力犯和非暴力犯在SCI—90的多數因子上存在顯著差異。結論: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水平較高,不同類型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異。監獄對不同類型未成年犯進行教育矯正應更有針對性。
關鍵詞:未成年犯;SCI—90;心理健康;暴力犯
*基金項目:山東省2015年度青少年研究規劃重點課題(SDYSA150205)。
1問題的提出
刑滿釋放人員的社會回歸問題解決是否得當關系到這些人員是否會重新犯罪。社會回歸問題涉及到安家落戶、工作安置、正常人際關系恢復等,諸多問題的一個基礎性問題便是這些刑滿釋放人員需具備健康的心理,這是他們回歸社會的通行證,也是繼續社會化的前提。關于刑滿釋放人員是否重新犯罪,與刑法學中的犯罪人再犯可能性,即罪犯人身危險性密切相關。目前有關影響人身危險性的因素中,人類學因素始終與社會學因素和自然因素并排為三大因素之一,且心理因素是其中重要的一項評估指標。犯罪心理學認為,消極情緒可導致犯罪行為及再次犯罪的發生。由于監獄管理嚴格、罪犯自由被剝奪及強壓下個體的需求長時間得不到滿足,罪犯往往表現出多種情緒問題(張雅鳳,2007)。研究表明,在未成年犯中,犯罪經歷超過2次的罪犯占到未成年犯總體的56.9%(張遠煌,姚兵,2010)。一般認為,監獄具有控制服刑人員再次犯罪的作用,但也有研究認為監獄的消極功能會促使服刑人員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比如服刑人員之間的孤立或崇拜會成為特定服刑人員再次犯罪的心理因素(Southerland,2002)。長時間被消極情緒所籠罩的個體,容易在特定的情境中滋生犯罪動機,并進而轉化為犯罪行為(張雅鳳,2007)。基于此,對即將出監的未成年犯進行心理健康調查意義重大,一方面是對未成年犯這個特殊群體的人文關懷;另一方面,也是對監獄工作的調查與監督,同時也是預防犯罪的一個過程。
2方法
2.1被試
山東省未成年人管教所2013年和2014年即將出監的未成年犯522人,全部為男性,年齡從16歲到26歲,平均年齡為20.2±2.17,但18到23歲占到總人數的85.2%。其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為129人,占到總人數的24.7%;初中文化程度有346人,占總人數66.3%;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有47人,占總人數9%。通過對每個未成年犯出監前一個月進行心理健康狀況測查。問卷的回收率為100%。
2.2工具
工具有一般資料調查問卷,主要包括被試的年齡,文化程度及犯罪類型;以金華(2010)等修訂的癥狀自評量表,簡稱SCI—90,用以評定被試的心理健康水平。該量表包括十個因子,一般以總分超過160分,或者任一因子分超過2分可以考慮篩查陽性,做進一步的檢查。該量表廣泛用于各類群體,具有較高的信效度。本次研究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為0.94。
2.3施測程序
對每個即將出監的未成年犯在出監前一個月進行心理健康狀況調查,由具有心理學專業知識的人員進行個體施測。最后,將2013年和2014年出監未成年犯的施測結果統一整理,并采用SPPSS19.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
2.4研究思路
研究1:首先對即將出監未成年犯的心理健康狀況和全國常模進行比較研究;其次依據法院判決,將未成年犯分為若干類型。為了增加數據的說服力,把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這種嚴重危害他人生命健康權的罪犯統計到故意傷害或殺人罪群體內;對于復合型的罪犯,比如搶劫加搶奪,或搶劫加尋釁滋事等,統計數據的時候統一于搶劫罪群體內;并基于使得研究的結果具有可推論性,將會剔除掉人數小于10的犯罪類型。再次,將不同犯罪群體進行比較分析。
研究2:基于研究1的結果分析,從心理學角度,進一步對犯罪群體進行分類。使得研究結果具有更好的生態效度。
3結果1
3.1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與全國常模的比較
即將出監未成年犯的SCI—90測驗結果與SCI—90全國常模樣本的平均數進行t檢驗,結果(見表1)顯示,出監未成年犯的各項因子均顯著低于全國常模。

表1 未成年犯與全國常模SCI—90評定結果比較s)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2刑法學上不同罪名的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

表2 不同類型未成年犯SCL—90評定狀況
通過四類罪犯SCI—90測驗結果兩兩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強奸罪的未成年犯與故意傷害或殺人罪的未成年犯,在人際關系和敵對因子上有顯著差異(t1=-2.45,p<0.05,d1=0.41;t2=1.72,p<0.05,d2=0.33),即強奸罪犯的人際關系水平要高于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罪犯的人際關系水平,其他因子均無顯著差異;強奸罪未成年犯與搶劫罪未成年犯,在人際關系、焦慮和敵對因子上顯著差異(t1=2.47,p<0.05,d1=0.27;t2=-2.60,p<0.05,d2=0.27;t3=-2.84,p<0.01,d3=0.32),即強奸罪犯的人際關系水平優于搶劫罪犯的人際關系水平;強奸罪犯的焦慮和敵對水平低于搶劫罪犯的焦慮、敵對水平。其他因子均無顯著差異。盜竊罪犯和搶劫罪、強奸罪、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罪犯的t檢驗不顯著。
3.3不同文化程度的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

表3 不同文化程度未成年犯SCL—90評定結果狀況s)
將不同文化程度的即將出監未成年犯SCI—90測驗結果兩兩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小學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與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在總分、軀體化、抑郁和恐怖因子上有顯著差異(t1=2.14,p<0.05,d1=0.33;t2=2.52,p<0.05,d2=0.38;t3=2.65,p<0.01,d3=0.42;t4=3.72,p<0.001,d4=0.54),即小學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比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總體心理健康水平更低,且感受到更多的身體不適感、情緒更加抑郁、對未來生活有更多的不確定感,其他因子均無顯著差異;初中文化程度未成年犯與高中文化程度未成年犯在軀體化、人際關系和恐怖因子上有顯著差異(t1=2.41,p<0.05,d1=0.31;t2=2.17,p<0.05,d2=0.28;t3=3.49,p<0.001,d3=0.37),即初中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較高中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有更多的身體不適感、更不良的人際關系水平及對未來生活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感,其他因子均無顯著差異。小學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t檢驗不顯著。

表4 不同年齡的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s)
通過對五組未成年犯SCI—90測驗結果兩兩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20~21歲年齡組的未成年犯在總分、總均分、軀體化、人際關系、抑郁、敵對、恐怖和偏執因子與22~23歲年齡組存在顯著差異(t1=-1.99,p<0.05,d1=0.26;t2=-3.29,p<0.001,d2=0.44;t3=-2.44,p<0.05,d3=0.32;t4=-2.11,p<0.05,d4=0.28;t5=-2.68,p<0.01,d5=0.35;t6=-2.54,p<0.05,d6=0.33;t7=-2.24,p<0.05,d7=0.28;t8=-2.12,p<0.05,d8=0.28),即20~21歲年齡組的未成年犯在心理健康整體水平高于22~23歲年齡組的未成年犯,且報告為更少的軀體不適感、更為良好的人際關系水平、抑郁程度、敵對、恐怖和偏執性都更低。其他各年齡組在統計學意義上無顯著差異。
4結果1分析與建議
4.1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與全國常模的比較
研究結果表明,與全國常模相比,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在十個因子及總均分上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且健康水平顯著高于全國常模。這與以往的研究不同(周正懷,何如一,李科生,2009;羅勇,王偉力,肖則蘭,2009;李俊麗,梅清海,于承良,2006;胡捷,隋景旺,林邢波,2012;徐淑慧,蘇春景,2015),出現這種情況的最大可能性原因就是以往研究的對象都屬于正處于監所內的服刑人員,而此次調研的對象為即將刑滿釋放的未成年犯。其次,這種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表明監獄對未成年犯教育矯正的良好效果。這種情況和之前的研究一致(陳卓生,韓布新,2006),隨著時間的推移,罪犯的消極情緒有所改善,并趨于穩定。那么通過在監所內的教育矯正、個體心理輔導、團體心理治療等活動,確實提高了未成年犯的心理健康水平。未成年犯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全國常模,這是一個值得研究者深思的問題,建議學者以積極心理學所倡導的“發展性視角”對這個群體進行研究;同時,社會也應以積極的態度反饋給他們,在雙向積極互動中共同建構和諧社會,促進個體和社會的“雙贏”。
4.2不同罪名的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的比較
由表2可知,強奸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明顯高于其他三類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通過t檢驗的結果得知,強奸罪的未成年犯群體較故意傷害或故意殺人罪的未成年犯群體有更好的人際關系以及更低的敵對性,這種差異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強奸罪的未成年犯較搶劫罪的未成年犯在人際關系、敵對和焦慮因子上有更低的得分,這表明強奸罪的未成年犯與搶劫罪的未成年犯相比有更加良好的人際關系,更低的焦慮感及更少的攻擊性。我國刑法將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及強奸罪以犯罪的同類客體為標準,將之歸類為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而將搶劫罪以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這類的社會關系而將之歸為侵犯產罪。但本研究將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和搶劫罪歸為一類,統稱為暴力犯罪。依據就是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直接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健康權,故將之定性為暴力犯罪是沒有異議的;而搶劫罪雖然犯罪客體為財產所有權和人身權,但其為占有目的而必然采取暴力手段,故亦將之歸類為暴力犯罪。關于強奸罪,我國刑法是以“暴力為基礎”的傳統立法模式,本文對此持不贊同意見。本文更加認同英美法系中的以“不同意為基礎”的立法模式,并認為“不同意”才是強奸罪的本質(趙秉志,1991)。這樣就可以解釋本次調研的結果了,因為搶劫犯和故意殺人或傷害罪為暴力犯,而強奸罪為非暴力犯,那么較之暴力犯其有更好的人際關系及更低的敵對水平也是顯而易見的。已有實證研究表明,將強奸罪作為暴力犯與非暴力犯進行對比研究,結果并未發現強奸犯對負性刺激,如攻擊性詞匯存在更高的注意偏向(Price & Hanson,2007)。這說明,將強奸犯劃分為暴力犯的類型有所不妥。此乃其一。其二,由于此次調研的強奸罪加害人是未成年,結合其生理心理發育特點:生理性意識覺醒,而心理相對不成熟,大腦的前額皮層區發育不成熟進而導致其控制力低下(Steinberg,Albert,Cauffman,Banich,Graham,& Woolard,2008)。則其在特定的情境下容易做出犯罪行為,但這種犯罪行為會隨著時間的遷移,心理生理的成熟而趨于消失。所以未成年所犯的強奸罪更多的是一種青少年期內的風險行為表現,其并不會成為終身持久性犯罪人。故矯治效果更好。暴力型罪犯是和其攻擊性相聯系,研究表明,早期的攻擊行為可穩定的預測后期的暴力行為及犯罪行為,二者之間存在很高的正相關(r=0.68)(Huesamann,Leonard,Eron,& Walder,1984;Olweus & Dan,1979)。那么,主要的暴力犯罪類型中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和搶劫罪其具有更高的敵對性和較差的人際關系也是合乎情理的。其三,再結合被害人來看,我國刑法中,強奸罪的犯罪客體是女性的性自由權利,較男性而言,一般女性從體力上遠遠弱于男性,這對男性加害人來說,亦是一個加害的有利因素。搶劫罪和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罪,犯罪客體為他人的生命或者健康權,犯罪對象涵蓋面更廣,不僅僅限于女性,將攻擊性波及面投射于全人類,其危害性更大。
從表2亦可得知,盜竊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也高于強奸罪,而幾乎與搶劫罪犯和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罪犯的得分持平,雖然沒有達到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但這一描述統計學上的差異,也值得進一步思考。現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這是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對盜竊罪做出的新規定,增加了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和扒竊三種行為方式,并且成為三種獨立的定罪行為方式,打破了盜竊罪以“次數”和“數額”為標準的定罪模型格局。我們刑法中的“入戶盜竊”行為,在西班牙和菲律賓刑法典中構成了搶劫罪(潘燈,2004)。日本刑法中的盜竊罪包含了大多數的搶奪罪(劉明祥,2001)。這表明,從理論上來講,盜竊罪的本質,不僅僅是對財產的秘密侵占,從各國的立法來看,它是否也包含一定的暴力性呢?隨著國際化的發展趨勢,統一的立法是否會將盜竊罪的暴力型因素考慮進去呢?第二,我們再來看看《刑法修正案(八)》之后,盜竊罪的一些實證數據: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后的九個月內,寧波市檢察機關盜竊案比前三年同期的案件數增長了135%,人數增長了123%,且新三類案件是主要增長點,其立案523件,涉案人數為664人(章國田,姚嘉偉,2012)。本次研究以法院判決為準,對于未成年犯屬于盜竊罪中的何種行為方式并未作出區分。但基于數據的正態分布規律,未成年犯中盜竊罪屬于三種新增特殊盜竊行為的數量也不低。第三,盜竊罪三種獨立定罪行為方式,由于其更大的社會危害性,如其“入戶盜竊”,直接將個體的最后生存的安全范圍予以瓦解;“攜帶兇器盜竊”一方面意指針對人身危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暗含著犯罪行為性質轉變的巨大可能性,比如轉化搶劫罪的可能;“扒竊”,這種行為更多的發生于公交車或者人群密集的公共場所,這種犯罪行為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并且具備“專業素質”的系統性、組織性與團伙性,這對不特定的多數人造成極大的財產隱患和人身安全的危害性。這三種新型的盜竊罪行為方式本質上不再是“秘密性”,更多潛藏著對社會的“攻擊性”與“暴力傾向性”。故,基于此本研究2將盜竊罪亦劃分為暴力犯罪類型中。
4.3不同文化程度的即將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
研究結果表明,小學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較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會有更多的身體不適感、更加覺得生活沒有意義可言、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更強烈。他們在心理健康總體水平顯著低于高中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初中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較高中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有更多的身體不適感、更差勁的人際關系及對生活的恐懼感。這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更高的文化程度一方面有利于他們對監獄教育矯正活動的理解并加以認同;另一方面由于在學校受教育時間更長,其受到正向積極影響更多。而小學或初中一方面其文化水平受限,對其教育活動并不能順利進行,另一方面更早離開學校,人格成長也就脫離了良好環境熏陶機會,亦是未成年與重要的社會機構—學校依戀的一種斷裂,過早走向社會成為“無所事事”青少年直至未成年犯,這也是學生在學校邊緣化的一種結果。
4.4不同年齡的出監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狀況
由表4表明,20~21歲年齡組的未成年犯在心理健康水平的大對數因子上得分均低于其他年齡組,相反22~23歲年齡組的未成年犯在心理健康水平的大多數因子得分均高于其他年齡組;且20~21歲年齡組的未成年犯在總分、總均分、軀體化、人際關系、抑郁、敵對、恐怖和偏執因子與22~23歲年齡組存在顯著差異。這就是說較20~21歲年齡組的未成年犯,22~23歲年齡組的未成年犯心理健康水平更低。心理學家阿柰特(Arnett,2000)提出18到20多歲的一種成年初顯期的發展理論。他認為這是個獨立存在的時期。丹尼爾·萊文森(Daniel Levinson,1986)提出17~22歲是個轉折期。在這個時期中,大部分人會形成一種可以指引自己未來的理想信念及較為完備的自我。我國學者研究得出,大學生成年初顯期特征對幸福感有預測作用,并認為重要喪失、社會實踐和人際關系是影響其成年初顯期目標的主要生活事件(段鑫星,陳會昌,2009)。那么,未成年犯在22~23年齡段SCI—90各個因子得分顯著高于其他年齡段,可認為是其成年初顯期特征的表現,在這個過渡期各種不穩定因素的顯現及其成年初顯期生活目標受阻的結果,如其戀愛、人際交往及正常的為未來職業籌備條件的喪失。
5結果2

表5 暴力犯罪與非暴力犯罪心理健康水平差異分析s)
通過對暴力罪犯和非暴力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見表5)顯示,暴力犯和非暴力犯在人際關系、焦慮、敵對和偏執因子得分顯著高于非暴力犯。其他因子上,暴力犯得分也高于非暴力犯,但不具有統計學上的差異。
6結果2討論分析
由表5表明,盜竊、搶劫、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聚眾斗毆等暴力犯較強奸罪等非暴力罪犯人際關系更加不良、焦慮感和敵對性更高、更為偏執。實證研究證明,暴力犯較非暴力犯對負性情緒信息的敏感度更高,但這種敏感度對正性和中性的情緒信息不起作用(李志愛,彭程,CodyDing,張慶林,2014)。所以,暴力犯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更易捕捉負面信息,這種認知風格導致其人際關系水平不佳及具有更高的攻擊性。而焦慮性這種負面情緒可能是導致其人際關系不佳的一個因素,也可能是人際關系不良的結果。同樣,高攻擊性既可能是導致其暴力犯罪的因素,同樣也可能是其人際關系不佳的因素之一。研究證明,冷酷無情特質(CU)在反社會和暴力行動中較為穩定的一種人格特質,并且有著其特有的生物學基礎,如皮質醇水平較低、杏仁核在加工負性情緒面孔時激活減弱等等(肖玉琴,張卓,宋平,楊波,2014)。這一方面說明,人格特質和遺傳基因是暴力犯的根源,另一方面暴力犯的高攻擊性水平是其冷酷無情特質的延續。
7結論
(1)即將出監未成年犯的SCI—90測試結果顯示:即將出監未成年犯的心理健康水平顯著高于全國常模。(2)強奸罪的未成年犯與故意傷害或殺人罪的未成年犯,在人際關系和敵對因子上有顯著差異;強奸罪未成年犯與搶劫罪未成年犯,在人際關系、焦慮和敵對因子上顯著差異。(3)小學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與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的未成年犯在SCI—90的總分、軀體化、抑郁和恐怖因子上有顯著差異;初中文化程度未成年犯與高中文化程度未成年犯在軀體化、人際關系和恐怖因子上有顯著差異。(4)20~21歲年齡組的未成年犯在SCI—90的總分、總均分、軀體化、人際關系、抑郁、敵對、恐怖和偏執因子與22~23歲年齡組存在顯著差異。(4)暴力犯和非暴力犯在SCI—90的人際關系、焦慮、敵對和偏執因子得分顯著高于非暴力犯。
參考文獻
陳卓生,韓布新.(2006).服刑時間對罪犯個性特征的影響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4(3),312-314.
戴曉陽.(2010).常用心理評估量表手冊(pp.13-19).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
段鑫星,陳會昌.(2009).成人初顯期的特征、生活目標及其與幸福感的關系.第十二屆全國心理學學術大會論文摘要集,158.
胡捷,隋景旺,林邢波.(2012).監所內未成年犯心理健康調查分析及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貴陽中醫學院學報,34(1),42-45.
李俊麗,梅清海,于承良.(2006).未成年犯的人格特點與心理健康狀況和應對方式的相關研究.中國學校衛生,27(1),75-76.
李志愛,彭程,CodyDing,張慶林,楊東.(2014).暴力犯罪者對負性情緒信息注意偏向的ERP研究.心理科學,37(4),936-943.
劉明祥.(2001).財產罪比較研究(p.181).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羅勇,王偉力,肖則蘭.(2009).監所內未成年犯心理健康調查分析.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17(1),87-88.
潘燈.(2004).西班牙刑法典(p.90).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肖玉琴,張卓,宋平,楊波.(2014).冷酷無情特質:一種易于暴力犯罪的人格傾向.心理科學進展,22(9),1456-1466.
徐淑慧,蘇春景.(2015).男性未成年犯家庭教養方式與孤獨感的關系研究.中國特殊教育,(06),91-96.
張雅鳳.(2007).罪犯改造心理學新編(p.330).北京:群眾出版社.
張遠煌,姚兵.(2010).中國現階段未成年人犯罪的新趨勢——以三省市未成年犯問卷調查為基礎.法學論壇,25(1),90-96.
章國田,姚嘉偉.(2012).新三類盜竊案件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思考.中國刑事法雜志,(7),56-61.
周正懷,何如一,李科生.(2009).人際關系對重刑犯心理健康影響淺探.現代生物醫學進展,21(9),4122-4125.
Arnett,J.J.(2000).Emergingadulthood:Atheoryofdevelopmentfromthelateteensthroughthetwenties.Washington: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55,469.
Huesamann,L.R.,Leonard,D.,Eron,M.M.,&Walder,L.O.(1984).Stabilityofaggressionovertimeandgeneration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120.
Levinson,D.J.(1986).Aconceptionofadultdevelopment.American Psychologist Association,41,3-13.
Olweus,D.(1979).Stabilityofaggressivereactionpatternsinmales.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86,854-855.
Price,S.A.,&Hanson,R.K.(2007).Amodifiedstrooptaskwithsexualoffenders:Replicationofastudy.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13,203-216.
Southerland,E.H.(2002).“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criminal behavior”.InS.Cote(Ed.),Criminological theories,thousand(pp.132-133).Oaks:SagePublications,Inc.
Steinberg,L.,Albert,D.,Cauffman,E.,Banich,M.,Graham,S.,&Woolard,J.(2008).Agedifferencesinsensationseekingandimpulsivityasindexedbybehaviorandself-report:Evidenceforadualsystemsmodel.Developmental Psychology,44(6),1764-1778.
TheReportabouttheMentalHealthStatusofChineseMinorOffenders
WhowereabouttoLeavethePrisonatPresent
XuShuhuiSuChunjingLiuRuogu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LudongUniversity,Yantai264025)
Abstract: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minor offenders’ metal health conditions,by using questionnaires to survey 522minor offenders.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1)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 minor offende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norm.(2)the murderers and the rapist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some factors of SCI—90.The same situation occurs in the robber and rapists.(3)As for the degree of different culture and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minor offenders,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ome factors of the SCI—90.(4)the violent crime and non-violent crime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st of factors of the SCI—90.The authors conclude the following:the prisoners,who were about to leave the prison,have higher psychological health level,differences between mental health level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riminals.Prison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inor offenders and the correction should be more targeted.
Key words:minor offender;SCI—90;mental health;violent offender
通訊作者:蘇春景,E-mail:suchunjing63@163.com。
中圖分類號:B8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84(2015)06-056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