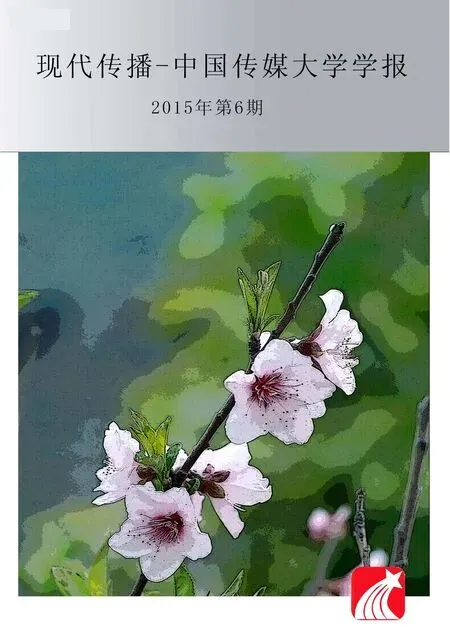論國內電視真人秀節目建構的城鄉文化生態
——基于生態美學的視角
■張愛鳳
論國內電視真人秀節目建構的城鄉文化生態
——基于生態美學的視角
■張愛鳳
從生態美學的視角來看,在當下熱播的城鄉角色體驗類真人秀節目中,城市和鄉村被建構成一種嚴重失衡的文化生態關系。在自然生態上,農村通常優于城市,而在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上,城市則以雙重優越于農村的姿態出現在節目中。為了強化城鄉矛盾和情節沖突,節目中的城市人和農村人在貧富、人物形象及價值觀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對立性,且這種城鄉對立的文化生態關系在傳播中被進一步模式化、刻板化。本文基于生態美學視角的文化批判,旨在推動媒體進一步思考和探索真人秀節目的創新和完善。
電視真人秀;城鄉文化;生態美學
真人秀節目是當下中國內地衛視一個炙手可熱的電視節目類型。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共有70多檔不同類型的真人秀節目在內地衛視頻道播出。從《超級女聲》到《中國好聲音》,從《爸爸去哪兒》到《奔跑吧兄弟》,從《漢字英雄》到《中華好詩詞》,中國內地的真人秀節目大致經歷了興起模仿、海外模式本土化、本土原創模式三個發展階段。真人秀節目一般強調參與主體的大眾性、參與過程的規則性、記錄的真實性和內容的可觀賞性。從2000年至今,經過近15年的發展,真人秀節目已成為當代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4年10月,天津衛視的《囍從天降》和江蘇衛視的《明星到我家》掀起的版權模式之爭,讓城鄉角色體驗類真人秀節目在《變形計》之后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從生態美學的視角關注真人秀節目建構的城鄉文化生態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問題,但也是當下真人秀節目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問題。
一、生態美學視域下的真人秀節目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體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及其作用機理的科學,在開創初期,它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自然界。20世紀初,生態學被逐漸運用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中,形成了很多交叉學科,如社會生態學、民族生態學、文藝生態學、傳媒生態學等。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進入轉型期,也進入“矛盾凸顯期”。一方面,城市化加快進程,經濟迅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另一方面,環境破壞、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分化、人際關系異化等問題日趨明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生態美學是“在世界范圍內由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轉型和各種生態理論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由中國學者提出的一種嶄新的美學觀念。它以人與自然的生態審美關系為基本出發點,包含人與自然、社會以及人自身的生態審美關系。”①
曾繁仁被認為是中國生態美學的奠基人,他認為生態美學“是一種人與自然、社會達到動態平衡、和諧一致的處于生態審美狀態的存在觀,是一種新時代理想的審美的人生,一種‘綠色的人生’。而其深刻內涵卻是包含著新的時代內容的人文精神,是對人類當下‘非美的’生存狀態的一種改變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更是對人類永久發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切關懷,也是對人類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園與精神家園的一種重建。”②
西方從古希臘羅馬開始就形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這一思維模式中,主體/客體、感性/理性、肉體/精神、人類/自然等兩個方面始終處于對立狀態。
最早興起的野外生存類真人秀節目便是以多元的生態審美關系作為節目創意主題的。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于2000年5月推出的《幸存者》(Survivor)是最早被中國觀眾認識和接受的野外生存類真人秀節目。該節目從近萬名應征者中挑選出16名參賽者,把他們送到無人居住的海島或荒山野嶺生活39天。劇組全程跟拍,記錄選手們在野外生存及相互競賽的過程,最終獲勝者將獲得100萬美元的獎金。為強化“人與自然”的沖突,此類節目錄制的地點多選擇在與世隔絕、人跡罕至的荒島或原始森林等。自然環境越原始,生存條件越艱難,選手面臨的挑戰越大。為了自己的生存和最終獲得勝利,選手不得不與自然做斗爭,與對手相競爭。在這樣的真人秀節目中,“人與自然”“人與人”被設計成對立的關系。
和西方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關系不同,“天人合一”是中國古典哲學、美學中的重要思想。季羨林曾指出:“在天人的問題上,西方與東方迥乎不同。西方視大自然為敵人,要‘征服自然'。東方則視大自然為親屬朋友,人要與自然‘合’一。”③近幾年,由野外生存類節目發展演變而來的中國戶外真人秀節目,建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逐漸由“征服與被征服”的沖突型關系轉向親近自然、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型關系。在《爸爸去哪兒》《人生第一次》《囍從天降》《明星到我家》等真人秀節目中,選手與自然、鄉村形成親密、和諧共處的關系,選手之間競賽的過程減少了殘酷、艱險的成分,多了溫情、趣味、協作的內容,觀眾在收看的過程中心態更加輕松。
湖南衛視的《變形計》《爸爸去哪兒》、天津衛視的《囍從天降》、江蘇衛視的《明星到我家》,都是當下熱播的電視真人秀節目。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將節目拍攝的場景從城市轉向了廣闊的農村。在這些節目中,城市/農村、城里人/農村人、明星/大眾以不同的形象出現在電視節目中。為增強節目的沖突性和可視性,此類真人秀節目有意強化建構了城市和鄉村沖突型的文化生態關系。
二、真人秀節目建構的城鄉文化生態關系
城鄉之間的文化生態關系包括自然及物質生活環境、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等。媒介對于現實生活的反映從來不是鏡子式的,而是有選擇、有目的地建構。按照傳播學的理論,媒介建構的是一種“擬態環境”,是媒介真實,而非客觀真實。
(一)客觀真實:日趨脆弱的城鄉文化生態
城市化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深刻的背景。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口號就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城市化是“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④歐美發達國家用了近200年的時間,完成了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的轉變,這其中也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不斷發生變化的歷程。
相較于歐美發達國家,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起步晚、速度快。據《中國環境報》消息,截至2009年底,我國城鎮人口為6.22億,城市化率達到46.6%,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據預測,2015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52%。⑤但中國的城市化東、中、西部發展嚴重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化率高,城鄉差異不斷縮小,而西部地區城市化率低,城鄉差距依然很大。同時,躍進式的城市化帶來的生態系統破壞、環境污染、城市病等問題也日趨嚴重。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近年來,隨著工業的大發展,能源被大量消耗,霧霾天氣呈現頻發性、全國性態勢。2015年2月28日,由中央電視臺前調查記者柴靜率團隊獨立完成的節目《霧霾調查——穹頂之下》在網絡推出后的24小時內,視頻點擊量已破億,并引發全民對生態環境的熱議。
此外,大規模、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也迅速改變了中國社會以農業和農村為主的面貌,“最近十年,全國每天有80個村落因城鎮化消失。”⑥一方面,農村的大量耕地被征用,以建造工廠、高速路、商品房等;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村青壯年離開土地和村莊,進入城市謀職求生,也在農村形成了大規模的“留守兒童”。全國婦聯發布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000萬,總體規模仍在擴大。⑦此外,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以及伴隨而生的消費主義及都市價值觀,也正深刻地改造著鄉村文化。“由于生產與消費主要以城市為中心展開,而且主要是城市本身的精神結構,它不僅迅速地掃除著歷史上一切美好的精神遺產,也迅速地敗壞著它周邊廣大的、尚殘存著樸素人性的農村地區。”⑧大量農業高素質勞動力和人才不斷從農村流向城市,也使得鄉村文化最新鮮有力的載體喪失,當一種文化失去了自我傳承與創新的主體之后,這個文化的生命力也將枯竭。當前,農村的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后繼乏人,瀕臨絕境。城市化進程在文化領域表現出的一道深刻的斷裂層便是“都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的斷裂,前者強勢,后者弱勢。盧岑貝格指出:“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那么我們就需要一個完全不同于現在的倫理觀念。我們就不可以再無所顧忌地斷言,一切都是為我們而存在的。”“我們需要對生命恢復敬意”,“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和認識自己”。⑨
(二)媒介真實:真人秀建構的“美麗”“破敗”交織的鄉村文化生態
當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受到高房價、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城市病”之困擾。為此,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⑩
1.距離建構的“美麗”鄉村
“鄉村”在漢語中,是一個富有詩性的詞匯,很多大詩人如陶淵明、王維、孟浩然等都把鄉村田園當作自己精神靈魂的棲息地。為滿足當下城市觀眾對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的向往,《爸爸去哪兒》《人生第一次》《囍從天降》《明星到我家》等真人秀節目將拍攝地選擇在風景優美的鄉村。如《爸爸去哪兒》《人生第一次》第一、二季中選擇的外景地都是風景優美、自然生態極好的地方。北京門頭溝區的靈水村,整個村莊處于群山環抱之中,古樸、寧靜;寧夏中衛沙坡頭位于騰格里沙漠東南邊緣處,集大漠、黃河、高山、綠洲為一處,兼具西北風光之雄美和江南景色之秀美;“魚米之鄉”云南文山普者黑被譽為“世界罕見、中國獨一無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園風光”,此外還有山東威海雞鳴島、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雪鄉、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浙江省麗水市云和縣農村、云南省麗江市海打漁村等。天津衛視于2014年9月推出的《囍從天降》,采用了明星體驗農村生活的真人秀模式。該節目邀請當紅女藝人分別進入普通的農村家庭,進行農村生活體驗。《囍從天降》選定的拍攝地也是風景優美、民風淳樸的中國農村。在目前已播出的節目中,有甘肅會寧山村、四川黑水藏家還有廣西防城港漁村等。江蘇衛視于2014年10月10日起每周五晚10點播出的新家庭生活體驗真人秀《明星到我家》節目也是如此,張柏芝、黃圣依、秋瓷炫、李金銘這四位嘉賓以“媳婦”的身份“嫁入”云南普洱地區寧洱縣農家,與婆婆們同在屋檐下,一起勞動一起生活。當明星們初到農家時,都表露出對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生活和優美自然環境的喜愛。在航拍的畫面上,遼闊的黃土高原、層層的梯田、壯觀的山巒、茫茫的草原等,都讓這些來自大都市的女明星們情不自禁地興奮贊嘆“真美”,這是因距離產生的美感。
2.現實直面的“破敗”鄉村
當審美的距離消失后,在這些節目中,農村究竟是如何呈現的呢?在《囍從天降》2014年10月25日第一期的節目中,來自城市的女明星們在農村面對的是這樣的生態環境:甘肅省會寧縣陽山村,地貌特殊,是一個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大峽谷邊上的村莊。“滿眼望去是黃土,降水量少,土地收成有限,農民的主要經濟來源是養羊。通訊基本靠吼,看家基本靠狗,出門基本靠走”。實際她們需要面對的生活環境更加艱苦:繁重的農務、閉塞的交通、落后的通訊、簡陋的生活設施、凋敝的文化氛圍等。受高原氣候影響,甘肅會寧常年干旱少雨,村民難得洗澡。當賈玲得知當地老人72年未曾洗澡,面露鄙夷的神色,并想要盡快回到北京去。節目組有意讓這些平時生活在光鮮亮麗的城市中、在聚光燈下光彩奪目的女明星們一方面贊嘆農村優美的自然風光,另一方面又要“遭受”農村勞動生活的“折磨”。節目設置的“趕羊大賽”“挑水大賽”“犁地比賽”對明星們來說只是一場游戲,節目組希望達到的是生活優越的城里人與農村艱苦的環境之間形成強烈反差的效果,同時也通過選擇性的建構,讓高速城市化進程背后的貧困農村以更形象直觀的方式呈現在城市觀眾的面前。
在另一檔節目《變形計》中,節目選取的城鄉環境更是有著強烈的反差和對比。節目主人公選擇變形的城市多以大城市為主,如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慶、長沙等。在一般的影視劇和電視節目中,城市通常的形象是:高樓林立、霓虹閃爍、琳瑯滿目的商場、悠閑自在的公園等;而變形的農村,通常都以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閉塞、居住條件簡陋、生活內容單調的貧困地區為主,如甘肅會寧、貴州岜沙苗寨、陜西八仙鎮、云南文山壯苗自治州等,這些地方均為中國目前的貧困地區。
在當下涉及城鄉關系的電視真人秀節目中,城市和鄉村形成一種嚴重失衡的文化生態關系。在自然生態上,農村通常優于城市,而在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上,城市通常以雙重優越于農村的姿態出現在節目中,為了強化城鄉矛盾和沖突,節目有意選擇較為貧困落后的農村作為城市人體驗的環境,這種城鄉之間對立的文化生態關系在節目的傳播中進一步模式化、刻板化了。
三、真人秀節目建構的“城市人與農村人”的文化生態關系
人與社會、人自身建立的生態平衡是生態美學重點關注的內容。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上講是一種典型的農耕文化。近代以前,中國社會還保持著良好的城鄉連接關系。在20世紀初期“西學東漸”的學術背景下,中國的鄉村成了傳統、愚昧、落后的代名詞,成為向西方學習現代化的過程中最需要試行改造和拯救的地方。晏陽初認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可以概括為四個字“愚、窮、弱、私”(11)。1958年之后,我國采取了犧牲鄉村發展城市的工業化戰略,在行政主導下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我國的城市和鄉村很長時期呈分離狀態發展。在人們的思維定式中,城里人文明、富足、有教養,而農村人,從高曉聲筆下的“陳奐生”到當代影視劇中塑造的農民形象,通常與貧困、愚昧、落后等概念連在一起,成為城里人忽略、鄙視的對象。
《變形計》是湖南衛視播出的一檔生活類角色互換節目。這檔節目尋找有特點的人物,安排他們進行角色互換,節目組全程每天24小時跟拍,剪輯后播出。在這個節目中,為強化角色、環境之間的沖突以及變形前后人物性格的對比,從第4季開始,節目專做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的角色互換。該節目建構的“城市人與農村人”的關系總體呈現出一種明顯對立的狀態。
首先是城市人與農村人貧富的對立。在《變形計》2014年的節目中,來自農村的張凱龍,他的爸爸在城里打工,因為缺乏技術,只能在工地做搬運工,背一趟水泥僅掙兩塊錢;而北京的孩子胡政堯還在五年級的時候,就創造了兩天花完5000元的記錄。城里孩子劉珈辰一頓早飯就花了300元,還抱怨沒吃飽,熱衷買名牌鞋,一年花銷近20萬;而留守兒童12歲的農村孩子楊杰獨自當家,要照顧爺爺奶奶還有弟弟妹妹,每周上山砍柴,半月生活費只有14元等。節目中選擇變形的城市家庭,多數是物質富裕的家庭,而農村家庭通常都很貧困,父母在外打工,家中的孩子成為留守兒童。在《囍從天降》節目中,明星進入的幾個農村家庭也非常困難,家中沒有青壯年,多為老人和孩子留守,生活非常艱苦。賈玲不滿農村太窮,發出這樣的感慨“我想過挺苦的,但沒想過這么苦。”
其次是城市與農村人物形象的對立。在《變形計》中,為了強化人物變形的難度和沖突性,有意選擇個性突出的人物。參加節目變形的城市孩子,家境富裕,平時嬌生慣養,惡習頗多。如叛逆頑劣的重慶少年李錦鑒,在紛繁復雜的游戲世界中迷失自我;北京問題少年胡政堯暴力、狂躁、反叛、爆粗口,面對農村孩子,心理優勢明顯;施寧杰是富二代,最多的時候一天花三萬,每天都在瘋狂地飆車和酒精的刺激中揮霍著青春;鄭州富家子弟趙迪厭學、逃課、打老師、恐嚇同學,頻繁闖禍。節目中參加變形的農村孩子,家境貧困,多為留守兒童,但成熟懂事。廣西山里娃韋志忠的生活簡單卻很快樂,三兄妹分一盒飯擠一張床,這樣的生活讓他們學會了謙讓;云南大山里的孩子和志軍成熟懂事,會照顧同學和家人;楊杰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小小年紀就承擔了家庭重擔。在《囍從天降》節目中,賈玲初到甘肅會寧農村時,對農村艱苦的生活環境非常不滿,時時表現出一種無法忍受的情緒。但節目中的農村人雖然家境貧困,但多數性格善良、溫和。王田娥、王田丹小姐妹是孤兒,與奶奶相依為命,但性格善良天真,總想“把最好的東西留給明星喝。”
在節目中,“城里人-農村人”的人物形象形成強烈的對比,一方面是節目剪輯以增強沖突及可視性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下中國城市和鄉村不同環境塑造的人物性格特征。在《變形計》《囍從天降》等真人秀節目中,城市和鄉村成為貧富反差極大的生活場景,而城里人和農村人具有明顯對立性的形象就刻印在這樣的生活場景中。
再次是城市人與農村人價值觀的對立。當代中國社會進入轉型期后,各方面的改革向縱深推進,以現代都市文明為特征的城市文化和以傳統鄉土文明為代表的鄉村文化也在不斷發生沖突。在真人秀節目中,城里人物質富裕,崇尚拜金主義、消費主義。在《變形計》中,出現問題的城里孩子,都生活在衣食無憂、生活富足的家庭,從小被父母嬌寵,并在耳濡目染中深受都市消費主義的影響,揮霍無度、生活奢靡。而在農村,尤其是在貧困的山區,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淳樸的鄉土環境保持得比較好,節目中出現的農村人大多表現出勤儉、善良、淳樸的一面,他們的所作所為常常讓城市人為之感動,這也更多體現出未被都市文明改造的農村對鄉土文化重情、仁義等傳統價值觀的一種遵守。
艾凱在《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一書中,概括了96個區分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概念之維。常見的維度有:農村人的生活是比較容易滿足的,城市人的生活是不滿足的;農村人的生活具有比較高的倫理性,城市人的生活是物質至上的;農村人的生活是聯合的,城市人的生活是分裂的;農村里面人是處于核心地位的,城市里面機器處于核心;農村是禁欲主義的,城市是享樂主義的,等等。(12)盡管這樣的維度區分過于絕對了,但確實也能部分地與當下真人秀節目中建構的城鄉文化生態吻合。
四、反思真人秀:“基于城市中心主義立場的內容生產”還是彌合“城鄉差距”?
在200多年的城市化進程中,西方文化的傳播和研究是以都市文化為核心的。李歐梵指出:“歐洲自19世紀中葉以降的文學幾乎完全以城市為核心,尤其是所謂現代主義的各種潮流,更以巴黎、維也納、倫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為交集點,沒有這幾個城市,也就無由產生現代西方藝術和文學,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說:西方現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惟在城市,城墻以外就只有野蠻和無知;不論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沒有這個城市,世界就無法生存。”(13)
與歐美國家不同,中國的農業人口占大多數。自2003年年初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之后的10多年來,“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實現城鄉與工農同步協調發展,這是習近平“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精髓。“城鄉一體化”的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中,更體現在文化生產和傳播中。
但是從當前的情況來看,當下的電視節目生產因為有收視率和廣告經營的壓力,節目的生產由“生產者為中心”轉向以“消費者為中心”。對于廣告商來說,他們的目標觀眾主要是城市人。因此,節目制作方通常站在城市中心主義的立場進行節目的策劃和營銷,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在《爸爸去哪兒》《囍從天降》《明星到我家》等節目中,為其提供贊助的商務用車英菲尼迪豪華七座SUV,別克通用商務車,為《人生第一次》冠名的貝因美奶粉,顯然目標群體是城市中高端消費人群。在這些節目中,農村往往只是人物活動的一個場景,觀眾關注的重點仍然是明星和城市人。農村在鏡頭前展現了自然生態的優美,也袒露了生活的艱難、留守兒童心中壓抑的痛苦、農村獨守老人心中的哀傷等,為了節目的制作,這一切不得不都在鏡頭前展露出來。農村人的淳樸、善良使得他們不會也不敢對節目組說不。如果美麗的農村是和貧困、孤獨、哀傷聯系在一起,只是為城市人的游戲活動提供一個場景,為節目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拉動收視率增加一個籌碼,為明星們體驗新鮮的農村生活提供一個機會,而對如何保護農村的自然人文生態、關愛留守兒童的精神世界、拯救日漸凋敝的鄉村文化不作進一步思考,這樣的立場是否有失偏頗?正如網友“久伴愛人”評論說“我想說《變形計》其實主要目的是為了城市孩子的成長。而那個被挑選的農村孩子也不過是你們完成任務的一個工具,一個犧牲品罷了。”
在《變形計》《囍從天降》《明星到我家》等真人秀節目中,最終都是以城市人和農村人的互相認同、和諧相處、情感交融的關系作為結尾的,但事實上,城市和農村、城市人和農村人之間從物質到精神、從生活到心靈的差距和隔閡遠遠不是7天或1個月就能彌合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和農村傳統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在新形勢下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逐漸演變成土地、教育、文化、福利保障等多方面的“新剪刀差”問題。
從生態美學的視角來看,無論是人與自然,還是城市和鄉村、城市人和農村人之間都應當建立一種尊重、平等、和諧、互助的關系。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大的風險是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城市快速發展而農業和中西部農村發展嚴重滯后,城市人和農村人差距不斷拉大。對媒體而言,如何通過議程設置和文化傳播,多創新一些面向農村、促進城鄉之間積極平等溝通和互往的電視節目,對改善城鄉文化生態起到積極的作用,這是媒體和學者都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文化問題。
(本文系江蘇省“青藍工程”優秀青年骨干教師項目、揚州大學“拔尖人才”成長計劃項目資助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 曾繁仁:《當代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生態美學觀》,《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
② 曾繁仁:《試論生態美學》,http://www.cssn.cn/zhx/zx_mx/201404/t20140425_1125455.shtml。
③ 季羨林、張光璘編選:《東西方文化議論集》(上冊),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頁。
④ 廖明君、劉士林:《中國都市化進程的理性觀察與人文關懷——劉士林教授訪談錄》,《民族藝術》,2008年第2期。
⑤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城市化》,《中國環境報》,2010年12月30日。
⑥ 馮驥才:《全國每天有80個村落因城鎮化消失》,《北京晨報》,2013年12月24日。
⑦ 全國婦聯:《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6000萬》,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10/c_115720450.htm。
⑧ 劉士林:《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
⑨ [巴西]盧岑貝格:《自然不可改良》,黃鳳祝、劉麗榮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57-58頁。
⑩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提出六大任務》,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1214/c1004-23841511.html。
(11) 宋恩榮:《晏陽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頁。
(12) 艾凱:《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注意》,張信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0頁。
(13)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12頁。
(作者系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
【責任編輯: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