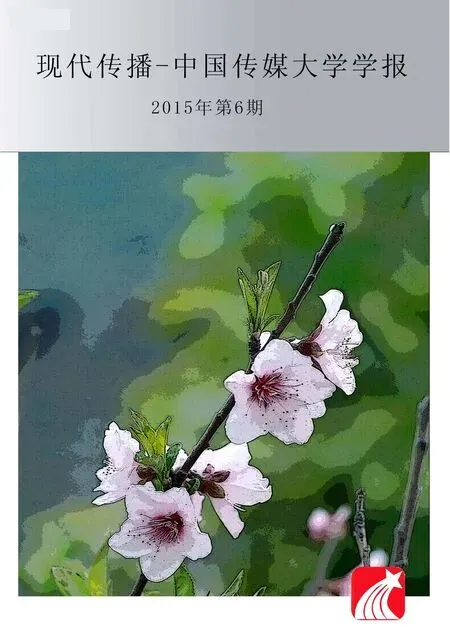大陸電視劇中海外移民的身份認同及其演變*
■王玉瑋
大陸電視劇中海外移民的身份認同及其演變*
■王玉瑋
【本文以身份認同為理論視角,從海外移民的身份焦慮、身份的凸顯以及身份的重建等三方面來考察大陸電視劇中海外移民的心理變化。移民身份認同在不同時期被劇作者賦予了不同的內涵與特點,這是中國海外移民心路歷程的一種真實寫照,同時也反映出移民對異域生活的向往以及與異質空間中的國人群體差異。
電視劇;海外移民;身份認同;演變
身份認同是文藝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主要指的是個人對主體自身特性的認識,或者與某一特定群族之間所用的共同觀念,這其中就包括民族認同、文化認同以及群族認同等。中國海外移民對自身身份認同的強烈訴求,長期以來隱現在移民題材電視劇的文本中;這種身份認同作為中國電視劇題材的重要一支,與本文所針對的問題尚待梳理和把握。不論是再現血淚史的中國早期華工,或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描寫的知識分子技術移民,亦或是新世紀以來呈現的多樣化海外移民,當代熒屏將鏡頭對準當下,或推延至現代歷史,展現出中國海外移民的運動歷程,進而揭示其身份認同的變遷。
一、“身份”的焦慮:移民形象的“他者”審視
移民的“身份焦慮”是指其身份的沖突性及其不確定性,也就是移民與其所居住地的政治環境、文化風俗以及社會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由此產生理念、心理及其行為的沖突與斗爭。作為文化“他者”的中國海外移民,一直苦苦地尋求著個人精神層面的身份認同。
1.憧憬與想象:當夢想照亮了現實
“異國形象應被作為一個廣泛且復雜的總體——想象物的一部分來研究。更確切地說,它是社會集體想象物(這是從史學家們那里借用來的詞)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對他者的描述。”①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物質生活條件匱乏,移居國外的動機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沖著“淘金夢”而奔赴日本及歐美。然而,想象與現實之間常常存在著巨大誤差,大陸海外移民到了日本及西方之后面臨著諸多的政治、文化差異及其生存的考驗,這其中或許有的移民圓夢了,但更多的移民也許只是夢斷異鄉。1993年,中央電視臺和美國芝加哥電視臺聯合制作的20集電視劇《新大陸》講述了張海平、江建國、李芷、文倩等八位來自中國的旅美留學生在美國土地上生存、發展以及創業的故事。然而,由于東西方文化有著各自不同價值觀與人生觀,八位留學生在經歷了種種挫折與磨難之后,最后各自選擇了自己的人生路途,其中有的在美國創出新天地,有的回到養育自己多年的中國大陸。在由鄭曉龍、馮小剛執導的21集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王啟明原本是個知識分子,并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拉大提琴的藝術家,然而和大多數人一樣懷揣著美好的夢想來到美國,盡管有人說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獄。初到紐約,王啟明也的確見識了美利堅的盛世繁華:“紐約燈光閃爍,就象是一座海市蜃樓;立體交叉公路,望不盡的車燈,排更整齊耀人眼目;一座又一座摩天大樓像一個又一個不動聲色的龐然大物,低頭俯視著在它們腳趾縫間鉆來鉆去的密密麻麻的人群和車隊。”②然而,這一切又似乎顯得那么虛幻與遙遠,因為王啟明發現自己和普通人毫無區別,最終只得放棄大提琴的音樂夢想,到餐館洗盤子、洗衣服。事實上,王啟明從踏入美利堅土地的那一天起,其身份就出現了變化,成為美國文化的“他者”。“自我身份的建構——因為在我看來,身份,不管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法國的還是英國的,不僅顯然是獨特的集體經驗之匯集,最終都是一種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每一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造自己的‘他者’。”③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為大陸觀眾勾畫出一個撲朔迷離的“美國夢”,而這種夢其實正是當時大陸民眾渴望發財致富,并企圖融入世界以及追求欲望等需求的一次想象性滿足。
2.沖撞與磨合:移民的身份認同危機
“如果我們從整個文化體系來考察就會發現,文化適應是一個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過程。當一些新的文化特質納入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現存制度及其功能體系時,文化適應實際上是一種建立新文化體系的問題,它不僅存在風俗、信仰、制度等等的再解釋,而且存在著目標與價值、行為與規范的再取向。”④面對陌生的國家和環境,語言的不熟悉、政治的隔閡以及文化價值的差異,中國海外移民似乎顯得有些惶恐與不安。在電視劇《紐約麗人》中,率直、單純的美國青年杰森是湯潘的同班同學,也是她的第一任男朋友。杰森不僅給予湯潘快樂甜蜜的愛情,還有豐厚的物質基礎。然而,由于杰森完全不知道英國對中國清政府發動過二次鴉片戰爭這段慘烈恥辱歷史,湯潘只得黯然與毫無共同語言的杰森分手。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與財產安全,這在中國人眼里是一種美德,因此,在電視劇《窮爸爸富爸爸》中的出租車司機王富貴看來,“抓小偷”是他義不容辭的職責。然而,在澳洲人眼里,似乎不完全如此,因為小偷造成的損失畢竟可以由保險公司來承擔,而個人的生命安全大于一切。王富貴百思不得其解,并固執地認為,假如每個人都缺乏嫉惡如仇的精神,那社會不是失去了公平與正義嗎?其結果是登門偷盜的“小偷”竟然以假摔騙取到保險公司的巨額經濟賠償,而王富貴反受牽連,意外地陷入官司漩渦。“近百年來,中國文化在與海外西方文化的相遇中,總是處于被動的位置,主要是以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化為其中心任務,實際上沒有可能與西方文化在相同的層面上平等交流與對話的基礎。”⑤在《綠卡夢》中,幾位留學生為獲得“綠卡”有的被迫賣身,有的遭受遣返以致發瘋,有的甚至選擇自殺身亡。而鄒易面臨要在黃種人姜建明和白種人奧斯卡這兩個男人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一開始顯得有些顧忌重重,但最后她還是毅然選擇了白人奧斯卡,因為很大程度上來說奧斯卡畢竟是來自于“仍然相當大地從內心至外表給人帶來不同影響”的另一種文化。鄒易只得感嘆,在異鄉生活實在艱難,而要融入這種文化就更難。其實,鄒易所感嘆的還是中國大陸移民們出于生存發展渴求融入異質文化,然而又難以真正融合的兩難選擇。
3.“懷鄉”與“返鄉”:移民的艱難抉擇
“原鄉之于異鄉,正如異鄉之于原鄉,是一正一反的關系,宛如鏡中映像。”⑥海外移民帶著不同的傷痛和期望在異域文化沖撞中苦苦拼搏,甚至遍嘗生活中的種種酸甜苦辣。在電視連續劇《金山》中,方家三代人的返鄉沖動與懷鄉意識不斷對抗,構成了中國海外移民情感寄寓和理想追求的內在悖論。作為第一代移民者,質樸、勤勞的方得法從小就離開家鄉,在美國西部舊金山開過洗衣店、修過鐵路、撿過垃圾,歷盡千辛萬苦,因為他心中所渴求的是“衣錦還鄉”。然而最終事與愿違,他依然一無所獲。兒子方錦河勸其回到自己的家鄉中國廣東,方得法義正言辭地拒絕:“你和你阿哥在開平住兩年,就讓阿爸在金山再做兩年生意——就不信一輩子運氣都是這般衰……”因為方得法堅信,只要勤奮努力,這塊異國土地遲早會讓他獲得榮華富貴,有朝一日肯定能換來光榮的還鄉。然而結果正如他在家書中所寫:“此番回鄉,歷年在金山之儲蓄,業已虛空,萬事需從頭開始。”⑦就是在“懷鄉”與“返鄉”這兩種敘述的雙向互動和交鋒中,中國海外移民決然遠走“他鄉”,而這也必將注定是個漫長而曲折的歷程。“開始在異鄉你的生活被求生的現實問題制約,而且很為新的環境所左右。一旦闖出路來,再仔細想想,你會發現代價高得驚人。你獲得的很多,但失去的也很多,你是否真的到達了彼岸,是否真正離開了家鄉,這是一個不容易確定的問題。家鄉,過去,歷史是你的一部分。既是你的財富,又是你的負擔。”⑧曾經奢望擁有十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生活環境,然而面對一落千丈的反差,受挫之后的失落、沮喪、混亂甚至后悔,中國移民不少人甚至萌生打道回府的念頭。在孫皓導演的20集電視連續劇《夫妻時差》中,林楠和毛奇一對感情和睦、生活甜美的白領夫妻,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兒子樂樂玩耍時因意外從窗戶跌下而死,這給他們平靜的生活帶來了重重煩惱。為挽救因喪失兒子樂樂出現的婚姻沖突,林楠和毛奇決定遠赴加拿大。在加拿大,善良而又單純的林楠為了盡快讓毛奇擺脫枯燥的家庭日常生活瑣事,拿出家庭的全部資產給毛奇辦了份報紙。然而,事與愿違,辦報紙不僅沒有給毛奇帶來快樂,反而卷入了重重煩惱之中,甚至一度被黑社會的人帶走。具有“北京大爺”氣質的毛奇顯然無法忍受這種行為,無法真正融入當地的文化習俗以及競爭環境,只得和林楠先后回到北京。
二、身份的凸顯:尋找和恢復自身的種族文化
“華人新移民第二代的整體身份認同表現為他們是華裔美國人,對自身的定位受兩種文化的影響,具有雙重認同的特征。一個華人可能在族群身份上有華人的認同,在社區和國家政治身份上認同于居住國,而在語言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多重認同,在價值和文化取向方面同樣也是混合的認同狀態。”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環境全面改善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全面提升,中國海外移民開始重新追憶自己的種族文化,尋求取得群體感和認同感的立足點。
1.民族文化傳統的依戀與固守
“傳統以過去為導向,致使過去對現在產生重大影響,或者更確切地說,過去被用來對現在施加重大影響。……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傳統也顯然關系到未來,因為業已確立的習俗是組織未來時間的一種方法。”⑩在電視劇《迷失洛杉磯》中,北京普通百姓孫子旺遠涉美國,其目的就是尋找一對龍鳳胎兄妹。然而,面對著張大年的重重猜忌與誤解,孫子旺以其“真、善、美”的情懷以及“以情動人,以理服人”的真情行為,獲得了與他毫無血緣關系的龍鳳胎福蘭克和安琪拉的尊重與理解,同時這種行為也深深感動了他的美國房東孟小蕓。
電視劇《小留學生》中的裘知文、劉莼、熊立以及溫小小等四個小留學生身處異鄉,加上家庭經濟條件較弱,他們不得不依靠“打工”來維持生活。在華人餐館,他認識了同樣出生在上海的羅賓斯老人。受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感知,裘知文主動去照顧一個人獨自生活的七十多歲的羅賓斯,裘知文中國式的耐心與真情不僅使羅賓斯感受到親人般的溫暖,同時也讓他獲得了好人有好報的結果。
在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為了脫離初到紐約時的經濟窘境,王啟明只得努力學會美式的生存法則,并不懈地追逐金錢和名利。然而,在獲得了豐富的物質財富之后,王啟明卻與妻子郭燕似乎漸行漸遠,女兒也在美國文化的熏陶中完全走樣變形。王起明只得無奈地對女兒寧寧說:“我們中國人來到美國,不要什么都學,要保持我們中國人的好傳統……”寧寧說:“爸爸,我真不明白了。我剛到美國時,你嫌我土,沒見識,要我跟上趟,趕快適應美國……可是現在呢,你又要我,別學這個,別學那個,要保持中國人的本色。保持中國人本色,我老老實實在北京呆著不就行了么?到紐約來干什么呢?我真不明白,你到底希望我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此刻的王啟明只得認真而又嚴肅地用中國傳統方式勸導女兒:“我認為,家庭觀念,倫理道德,還是咱們中國的好。我這意思是說,你該有自己的主見,堅持該堅持的東西。”(11)的確,王啟明用美國人的奮斗方式贏得了事業上的成功,可他卻嚴格要求自已的女兒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國人,是北京人,根應該在中國,因為,作用于移民族群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早已深深地影響著這些移民的價值取向、思維定勢以及文化心態。
2.與異質文化的親近和共融
“跨境移民移居異文化社會后自身會發生什么變化?外來移民是否必須、是否能夠融入主流社會?允許跨文化移民保持其文化自決的多元文化主義,是社會進步的標志還是可能導致社會分裂的隱患?這是貫穿20世紀始終的社會現實問題,也是西方移民學界孜孜探討的重要理論問題。”(12)上世紀九十年代,電視劇逐漸淡化了早期文化鄉愁和文化沖突的移民主題選擇,而是轉向以一種積極、進取的身份觀念去接納并融入西方主流社會。電視連續劇《蝴蝶》中的段嶺是一位在國內從事于蝴蝶學研究的研究員,在忍受了多年同丈夫莊五一分居兩地的生活之后,她決定前往加拿大與莊五一辦理離婚。然而,天有風云不測,就在段嶺辦完手續即將回國之際,莊五一卻因在駕車期間接電話這個過失而造成嚴重車禍,陷入深度昏迷。不幸的是,在事故發生的另一輛車中,腦外科大夫約翰遜的女兒也在這場車禍中罹難。約翰遜決定尋找出兇手,一心為女兒報仇。面對著執意復仇的約翰遜以及處于深度昏迷的莊五一,段嶺決心放棄回大陸的學術研究,而是要認真地維持起這個她曾經想要放棄的家。最后,段嶺用自己的堅強與耐心以及真摯情感喚醒了莊五一的回歸,同時也讓曾經自私和固執的約翰遜感到問心有愧。劇作一方面著力展現出中國女性的堅韌與寬容以及無私奉獻的美好精神,同時也通過約翰遜與擅長中醫的“小陜西”的矛盾沖突,展現了中國移民與原住民美國人之間的理念沖突到相互理解以及融合的過程。中國移民題材電視劇用犀利的目光認真打量著東西方文化的優點與缺陷,讓它們在碰撞過后慢慢積淀,而后互相接納,互相融合。
在電視劇《摩登家庭》中,由于肖家媽媽竭力阻止兒女與外國人結婚,其結果是大女兒肖云楚孤身來到馬來西亞,二兒子肖云天決定打消娶韓國姑娘的念頭,三女兒肖云舒去了澳大利亞。思想上經歷了反復斗爭,肖家媽媽最終還是接受了兒子肖云天與懷了身孕的韓國姑娘樸燕姬以及肖云舒的澳大利亞籍丈夫勒內爾。中國人的善良、堅強、純樸等個性,西方人崇尚自由、強調個體利益以及尊重個性等品質,在《摩登家庭》中得到很好體現。海外移民對中國傳統文化擁有信心以及對異質文化逐漸認同,這兩種文化平等對話交流的情境逐漸得到觀眾的認可。
三、身份的重建:對“世界公民”形象的闡釋
新世紀以來,熒屏中出現的中國海外移民很多已經扎根國外,開拓著海外市場,他們是中國的新富階層、知識精英等高端群體,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以及專業的技術技能。這些移民對居住地的文化差異開始慢慢適應,許多消極的心態也逐漸淡化。
1.“雄性化”海外移民形象的塑造
早期中國熒屏中的海外移民大多身份低微,如保姆、搬運工、小偷、工匠等,他們總是唯唯諾諾、低聲下氣,這種“陰性化”的移民形象定位顯然迎合了西方對中國的一種想象。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電視劇逐漸開始注重塑造具有中國男性氣質的“雄性化”海外移民形象,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男人的看法。在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王啟明是一個明顯帶有個人英雄氣息的中國海外華人男性,更是一個通過自己的努力拼搏能在紐約取得成功的少數海外華人。就是在白人大衛面前,王啟明也依然顯得桀驁不馴、放蕩不羈,他敢于在紐約鬧市區用中文大肆詆毀白種人,敢于不順眼就出手打架,敢于在曼哈頓渡口放肆喝酒,渾身上下散發著男性荷爾蒙的味道。在加油站求職時,王啟明因為不能忍受老板的侮辱而與之發生沖突,并大打出手,這種行為正如大衛所嘲諷的,王啟明這位中國人就是太野蠻、太粗魯、缺乏文明素養。
在電視劇《窮爸爸和富爸爸》《摩登家庭》《危險旅程》以及《迷失洛杉磯》中,中國部分移民不再顯得那么猥瑣、自私、狹隘,相反,他們盛氣凌人、出手闊綽、咄咄逼人,甚至能輕易俘獲白種女性的喜愛,這種行為就是白種男人也不得不為此折服。在演員選擇上,電視劇《夢斷天國》選用作風硬朗又不失霸氣的張豐毅,電視劇《窮爸爸和富爸爸》選用沉穩而又厚重的陳寶國、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選用體型高大而又威猛的姜文,熒幕上這些堅毅與陽剛的移民男性形象,全身上下無不體現出中國的雄性氣概。
2.海外移民從邊緣融入主流社會
中國大陸早期移民似乎總是與貧窮、不公平、饑荒等相隨相成,人物形象大多集中為保姆、小偷、偷渡客等。《危險旅程》的“女蛇頭”林姐竟然用犧牲別人的幸福積累起巨額財產,過去是白人賣黑人,荒唐的是現在黃種人倒賣黃種人;《夢斷天國》的偷渡客為了獲得外國的居住權,竟然出賣婚姻,不顧尊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推進,被想象成中國代表的新富階層逐漸走進西方主流社會。這些人群有著豐厚的個人財產、特立獨行的自由個性、全球化的思維眼光、深邃的思想遠見以及敏捷的市場意識,他們大多也從事著體面的工作,比如前衛時裝設計、高雅的藝術創作以及前沿的IT行業等。作為電視劇的一種參照,電影《中國合伙人》以“新東方”創業故事的外殼,講述著中國式的海外成功故事,進而尋找強烈的認同感。故事中的成東青、孟曉駿、王陽三個青年從白手起家到百萬富翁的奮斗故事與“民族”話語結合起來彌合了不同階層的民族認同。“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中,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提高,美國想象和美國夢也經歷了多層次的嬗變。現在的文學作品里面對美國的想象,跟大眾文化接觸的不太一樣。作家筆下的中國人去美國,不再是一定要融入美國社會,反而會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性,強調中國人在美國創業,改變美國的規則。”(13)
在電視連續劇《紐約麗人》中,學習時裝設計的湯潘、離婚的凌風以及大學教師何小藕因各自的心愿來到美國紐約。最終,湯潘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著名時裝設計師,并開創自己的服裝品牌“曖色系列”;何小藕終于拿到了博士學位;凌風的陳氏機構順利收購了藍詩波公司并成為紐約世界的名牌;凌姐找到真愛克里斯。“美國”似乎不再是異鄉的代名詞,而是成了她們夢想的載體。
3.海外移民從故國回望過渡到民族自信
在強勢地位的異質文化環境中,中國海外移民深刻地體會到人情的冷漠,生活的艱辛、社會的無助以及地位上的不平等,他們常常面對東方,遙望祖國,借此慰藉心靈,擺脫內心的空虛。因此,文藝創作較為集中地表現中國移民與異域社會的交往及由此引發出的一系列心理震蕩、文化沖突及其無根感和荒原感。新世紀移民題材電視劇不再僅僅沉溺于異域悲情與“他者”身份,更多是從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尤其是一些制度建設以及民族自信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展示。“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后大量涌入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以及近年的華裔移民,赴美國的原因除了向往富裕的物質生活、求學深造之外,尋求民主的社會制度、輕松的人文環境,以及自由寬廣的個人空間,應該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14)
在36集電視連續劇《溫州一家人》中,1981年至2004年期間“溫州商人”的經歷和命運都與中國經濟的每一次變化有關。“溫州女兒”周阿雨是一個堅強而又能自理的女性,很小就被送到國外意大利。然而,周阿雨和溫州同鄉們最終用踏實的行動從打工者奮斗為餐館老板,以中國式的誠信成為中國在意大利普拉托溫州商人的代表。《溫州一家人》將異國元素與中國溫州人的堅持不懈、倔強勇敢的拼搏精神融為一體,讓觀眾體會浙江商人的內在精神特質,也讓觀眾了解到這三十年間“中國人確已改變了世界”的事實。同樣,由尹大為執導的30集電視連續劇《溫州人在巴黎》講述了幾代溫州人離開家鄉,遠赴海外艱苦創業的故事。能吃苦耐勞的溫州人李中堅為擺脫溫州貧窮落后局面,竭盡全力將溫州符號產業“打火機”行業沖入歐洲市場。面對歐洲市場的重重阻攔以及歐盟“反傾銷”的競爭環境,李中堅沉著應對,一方面聯合眾多法國溫州企業家努力適應市場競爭法則,另一方面積極拓寬產品銷售渠道,最終為中國小商品行業贏得了“反傾銷”的勝利,同時獲得了國際市場的認可。面對著中西文化和市場規則的迥異,勤勞而聰慧的溫州人依靠那粗大有力的雙手、充滿智慧的頭腦以及海外溫州人團結協作的精神,改變了溫州家鄉一窮二白的面貌,成為令中國人民感到驕傲的民族代表。
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到《別了,溫哥華》《下南洋》《錢學森》和《溫州一家人》等,越來越多的移民題材電視劇進入大眾視野,并以不同視角和藝術手法立體化地展示出海外移民的生存發展狀況以及與祖國千絲萬縷的聯系。從最初對出國移民抱有的憧憬和新鮮感,到從海外移民與西方主流文化的沖撞中陷入煩惱而難以自拔,到移民在異質文化中探尋傳統文化與西方主流文化的共融,再到移民的文化自信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增強,當代熒屏再現了中國海外移民在他者身份以及異質文化的合力下,其自我身份認同的演變過程,這種過程反映出中國海外移民自身綜合實力對中國本土影響力的上升。移民將來自不同地方的文化帶到一起,在沖撞、融合后保存下來,他們既對移出地的文化有強烈的認同感,又潛移默化地接受了異域文化的精神取向。因此,中國海外移民需要在不同的文化價值系統中相互尊重、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這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文明自我完善、延續發展的要求。
注釋:
①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載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頁。
②(11) 曹桂林:《北京人在紐約》,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8、157頁。
③ [美]愛德華·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8頁。
④ 司馬云杰:《文化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頁。
⑤ 胡勇:《文化的鄉愁——美國華裔文學的文化同》,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⑥ 何與懷:《“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試談澳華小說的認同關切》,《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1年第1期。
⑦ 張翎:《金山》,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頁。
⑧ 葉凱蒂:《藍土地,遠行者》,《小說界》,1996年第1期。
⑨ 李其榮、姚照豐:《美國華人新移民第二代及其身份認同》,《世界民族》,2012第1期。
⑩ [英]安東尼·吉資斯等:《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生活巾的政治、傳統與美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75頁。
(12) 李明歡:《20世紀西方國際移民理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13) 張平:《中國夢無需照搬美國夢》,《中國文藝報》,2013年7月3日。
(14) 張抗抗:《強心錄—中國當代文學中所描述的美國華族》,《小說界》,2001年第3期。
(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編輯:張國濤】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大眾傳媒在文化建設中的功能和作用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2JZD02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