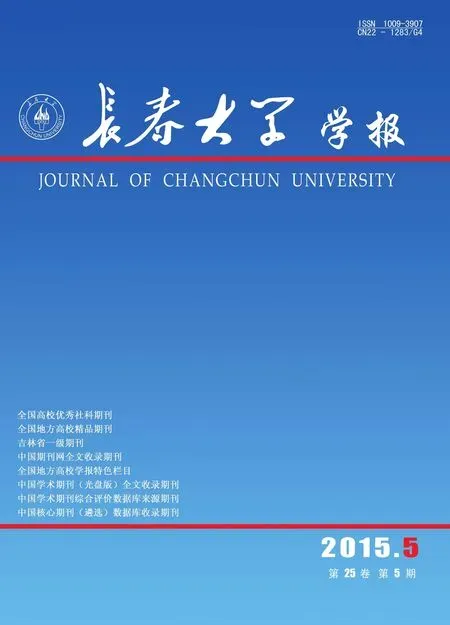日美關系在日本二戰歷史觀中扮演的角色
劉發為,魯 迪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2)
日本,在二戰中與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相互勾結,給整個世界帶來了一場空前的浩劫。在二戰過程中,以美、蘇、中、英為首的反法西斯國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最終換來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二戰結束后,戰敗國應當正視歷史,為戰后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但是,日本卻始終試圖掩蓋侵略戰爭這一歷史事實。究其原因,參考之前文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戰勝國對日本的清算不夠徹底,中國陷入內戰和朝鮮戰爭的泥淖,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1];第二,戰后日本的政權仍然是建立在戰前的體制之上;第三,冷戰的發生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第四,日本國家的歷史文化因素,國民普遍信奉神道教,缺乏懺悔意識,盲目效忠天皇[2]。
而本文打破之前的文獻研究的定勢框架,選取日美關系在日本對待二戰的態度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一角度進行初步分析和研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從之前的文獻研究來看,日本掩蓋二戰事實的原因當中,多半都伴隨有美國的影響;第二,之前的文獻對日本為何不承擔二戰責任和德日兩國在對待二戰態度上的不同以及原因做了較為詳細系統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尚無文獻單獨將戰后日美關系與日本拒絕承擔二戰責任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第三,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能夠從另一個側面來了解完善對戰后日美關系的認知,從而更好地理解當前的日美關系以及對當前日本所做出的行為舉動進行剖析。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總結回顧日本對待二戰的態度;第二部分,回顧二戰后日美關系的發展階段;第三部分,將前兩部分的內容結合進行分析,總結日美關系在日本對二戰反思態度中所扮演的角色;第四部分,探索這一視角研究對當今國際關系的啟示。
1 日本對待二戰的態度
二戰結束之后,受害國對日本對待二戰的態度表示了強烈不滿。總體上說,日本并未真正承認戰爭的錯誤,相反,日本在很多方面苦下功夫掩蓋二戰的侵略事實。
1.1 修改憲法
二戰結束之后,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重新壯大,美國在麥克·阿瑟將軍的主持下,對大日本帝國憲法進行了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修正是第9條:“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也正是因為這一條修正,戰后日本的憲法被稱為和平憲法,被認為是日本總結戰爭教訓之后向世界做出的“公約”。和平憲法在維護戰后日本和平與發展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從和平憲法生效之日起,日本的右翼勢力就從未停止過修憲的步伐。最初,在朝鮮戰爭爆發后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修改之時,日本右翼勢力均掀起了修憲的高潮,但均未得逞。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日本國內要求政治大國地位的呼聲越來越強大,許多政治家加緊修憲的活動。在他們的煽動之下,越來越多的日本國民也加入了支持修憲的行列[3]242-248。進入新世紀,日本憲法面臨的已經不是修不修改的問題,而是何時修改的問題。
正如上述所言,和平憲法被看作是日本對世界做出的“公約”,但是日本卻一直在試圖修改憲法,這樣的行徑無疑是要掩蓋二戰的歷史。從這一側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對待二戰的態度。
1.2 靖國神社問題
靖國神社問題始終是日本與亞洲國家間關系的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
二戰期間,“軍國主義分子利用靖國神社煽動崇拜天皇、刺激軍國主義情緒起到了特殊的作用”[3]220。戰后,右翼勢力不僅沒有停止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行徑,而且推動天皇、首相及閣僚以官方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更為甚者,靖國神社供奉二戰甲級戰犯,這意味著它否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站在肯定的立場之上為戰犯翻案。
從1980年的鈴木善幸首相開始,日本首相開始了至今為止尚未停止的參拜靖國神社甲級戰犯的活動。在新世紀,這種參拜更有愈演愈烈之勢。
日本首相作為國家的官方立場代表,他的這種行為無疑是對二戰過錯的藐視,是對當年受傷國的再一次傷害。從這一側面,日本對待二戰反省的消極態度表露無遺[4]212-215。
1.3 歷史教科書問題
日本在戰后不僅試圖抹殺戰爭責任①“戰爭責任”,是指發動侵略戰爭的一方對戰爭受害的國家與國民應負的責任。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概念專指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發動侵華戰爭及亞洲太平洋戰爭的責任。,而且試圖推卸戰后責任②“戰后責任”,是指發動侵略戰爭的一方的后代也要對戰爭受害的國家與國民應負的責任。有關“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參見[5]。[5]。這一點在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篡改歷史事實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
日本教科書審定制度是保守勢力篡改歷史真相的工具。二戰后,主要有三次教科書修改浪潮。第一次發生在1958年,并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在岸信介內閣主持下,對歷史教科書做了重大修改。“新書不僅不再寫明中日甲午戰爭的侵略性質及其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反而稱贊甲午中日戰爭‘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6]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經濟起步、追求政治大國的情況下,加緊推動教科書修改,將之前教科書中的“侵略”字眼改為“進入”,掩蓋南京大屠殺真相,欲求徹底否定歷史。第三次發生在新世紀初,此次修改范圍更為廣泛,程度更為深入,而且姿態更為強硬,得到了右翼保守勢力的有力支持;同時,修改教科書與修改憲法二者結合到一起。
教科書是一個國家對歷史的再現與認知,日本不斷修改教科書、篡改二戰歷史的行徑,清楚地表明了其試圖掩蓋二戰真相、拒絕承擔歷史責任的事實。
總之,日本在對待二戰的態度上十分消極,自二戰結束以來至今,一直在通過各種手段試圖抹殺二戰的侵略事實。
2 二戰后日美關系的發展階段
二戰結束以后,日美關系經歷了戲劇性的轉變。按照不同階段的特點,筆者將二戰后的日美關系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二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這一大的階段又可分為三個小的階段。
第一,占領階段。日本在二戰中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因此,在二戰后期及戰后初期,美國開始準備對日本的占領政策,其中最早的對日占領政策早在1945年6月就已制定出來[7]。通過1945年8月12日頒布的SWNCC150/2號修改稿③該文件是對美國1945年6月11日頒布的題為《投降后初期美國對日政策》的SWNCC150號文件的修改稿。及之后的“投降后初期基本政策”,美國基本形成了戰后初期對日占領及管理政策的整體框架,在這當中,美國強調對日占領的主導權。而且,強調對日實行嚴格的懲罰與改造。
第二,單獨媾和。隨著中國戰場國民黨江河日下,美蘇之間矛盾不斷加劇,世界進入冷戰前時期。因此,在東京審判當中,美國與其他國家聯合忽視亞洲的受侵略國,打著“文明”審批的旗號將眾多受害亞洲國家排除在外[4]21。同時,美國開始調整對日政策方向,準備實施新一輪的對日政策。在實施新的政策之前,美國首先要完成的是對日媾和。而為了讓自己能在媾和中占據更大的主動權,美國采取了單獨媾和的方式,整個媾和過程幾乎完全由美國來主導。美國制定的是一項寬大的媾和和約,更重要的是,美國與日本還單獨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及《日美行政協定》,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美同盟已經被鋪平了道路。
第三,扶植階段。經過上述的單獨媾和以及日美安保條約的簽訂,日美關系從戰后初期的占領改造逐步演變為扶植幫助。而朝鮮戰爭的發生則進一步加強了美國對日本的扶植。自衛隊在朝鮮戰爭期間建立起來,美國對日的戰爭“特需”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戰后日本百廢待興的經濟。
第二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經濟伙伴的建立。
經過美國十年的扶植,日本的經濟已經有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同時,美國也希望能夠通過日本自己經濟的發展來減少自己扶植日本的開支,希望日本能夠為美國分擔外援的壓力。因此,在1960年修改的《日美安全條約》第二條中規定“兩國將設法消除它們在國際經濟政策中的矛盾,并且將鼓勵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8]從此開始,日美逐漸成為親密的經濟伙伴。
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政治伙伴的建立。
經過數十年的恢復和發展,日本在經濟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因此,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謀求政治大國地位,這一點需要美國的大力支持。而美國也需要日本分擔其全球戰略中的經濟外援,為其減輕壓力;同時,也通過削減日本的實力來減緩其崛起的速度。因此,二者在政治上的合作日漸頻繁。
從長遠來看,日美建立政治伙伴關系具有過渡性質。日本的政治大國化是其經濟大國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其走向政治大國化的重要前提[9]。
第四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軍事伙伴的建立。
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上的蕭條令日本難以在經濟上支持美國,轉而從軍事上給予美國支持,而美國在地區戰爭中的表現也需要日本在軍事上給予美國支持。
但是日本的再軍事化有一個重要的限制,便是和平憲法第9條。因此,美國便在修改憲法問題上對日本國內施壓,以求消除對日本的軍事力量的憲法限制,進一步發展二者的軍事同盟關系。
第五階段,21世紀初至今。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日美關系不斷調整,追求全面伙伴關系。
經過了幾十年的同盟關系,日美關系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在這樣的伙伴關系中,日本或多或少處于被美國支配的地位。因此,日本更多地開始尋求獨立發展的大國道路。但同時,在朝鮮問題、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等諸多問題上,雙方又有著廣泛的合作基礎。
因此,日美關系開始不斷調整,但是整體上,日美關系并沒有減弱。
3 日美關系影響下的日本戰后歷史觀
在前文中,已經提到過之前的研究對于日本對待二戰不認罪的原因的分析,在這里就不再贅述。本文主要從日美關系的角度,分析日美關系在日本對待二戰態度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3.1 戰爭賠償
同樣的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因其罪行向受害國賠償了大量的損失,而同為戰敗國的日本,卻逃脫了巨額的戰爭賠償。而在這里面,美國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可想而知,一個國家犯下了如此滔天的罪行,卻被免除追究賠償責任,這在很大程度上會縱容日本國內對二戰的認罪和負責任的態度。而日本恰恰很好地利用了與美國的關系,從此開始走上扭曲二戰罪行之路。
3.2 東京審判
懲治戰犯,不僅是對戰爭受害國的撫慰,也是對國際和平環境的一種保障。然而,二戰后的東京審判,卻只是有名無實,成為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追求自身國家利益的一種工具。
在審判中,只有少數幾名戰犯得到了懲治,在這其中,大都是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直接與美國對抗的軍隊的首領。而日本在中國、越南等其他戰場的軍隊首領卻都逃掉了被懲治的命運。為了主導東京審判,美國以“文明”審判將很多亞洲受害國家排除在審判之外。許多戰犯的逃脫再次助長了日本不認罪的氣焰。
3.3 舊金山和約與媾和
在為日本爭取到了減少賠償和從輕審判戰犯之后,隨著東亞共產主義勢力的不斷發展,美國逐漸提升日本在其東亞戰略中的地位。為了能夠更好地發揮日本在東亞的鉗制作用,美國首先需要與日本解決戰爭媾和問題。
在媾和問題上美國依然采取之前的方式,從開始到舊金山和約的簽署,美國一直處于主導地位,不給其他戰勝國以機會。而既然媾和是為了讓日本更好地服務美國的東亞戰略,那么,美國在舊金山和約中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就會少之又少。經過媾和,日本與美國擺脫戰爭狀態。而且,日本利用和約中并未提及戰爭責任的機會,更加不愿承擔二戰的歷史責任。
3.4 日美安保條約
在舊金山和約簽訂的同時,美國開始考慮與日本同盟關系的構建。最初的日美安保條約雖然不是軍事同盟的條約,但是已經有了軍事同盟的雛形,為之后的軍事同盟打下了基礎。在日美安保條約的保障之下,日本的安全有了保障,在這種情況之下,日本更不可能對二戰抱有認罪的態度了。
3.5 軍國主義
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爆發,占用了美國在亞洲的大量武力。而借此機會,美國不想讓他國染指日本,因此縱容日本自衛隊的建立和壯大。戰爭剛剛結束不久,日本的軍國主義實力便開始抬頭。發動戰爭的那些軍國主義分子,在戰后幾年內就得到恢復,更不可能去正視二戰的罪行。
此后,美國為了其地區性戰爭和反恐的需要,積極支持日本自衛隊的發展。但是由于和平憲法第9條的存在,日本的自衛隊建設始終面臨很大的限制。因此,美國開始推動日本國內修改憲法的進程,試圖以此來建立與日本的真正合法的軍事同盟關系。
這樣的日美關系,顯然只會讓日本離直面二戰的歷史越來越遠。
3.6 經濟恢復與政治大國地位
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特需”,給日本戰后的經濟注入了催化劑。美國為了其全球戰略需要及減少對日本援助的負擔,鼓勵日本經濟的發展,建立起經濟伙伴關系,使日本經濟在戰后20年便已達到相當的高度。
經濟上得到恢復發展的日本,開始謀求政治大國地位。而二戰歷史問題始終是日本被世界多國所看重的焦點問題,但是日本仍然采取逃避二戰責任的態度,而美國為了自己經濟和全球戰略的需要,在二戰遺留問題上仍然支持日本。在美國與日本的伙伴關系之下,將二戰責任予以推卸。
總而言之,戰后的日美關系,恰恰是助長了日本逃避戰爭責任、不認罪的囂張氣焰。不僅從經濟上幫助其恢復和發展,而且在軍事上與其結成同盟,使日本軍國主義早早復蘇,也喚醒了日本的右翼保守勢力。
戰后的日美關系,應當在很大程度上為日本不認罪的態度負有責任。
4 結語
戰后的日美關系,實質是日美兩國關于利益的交換。但是,在這組關系中,日本或多或少處于被美國支配的地位。進入新世紀,日本開始尋求獨立的大國地位。想要成為真正的大國,僅僅依靠美國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真正的大國,應當是敢于擔當的國家。
因此,日本應當重新審視日美關系。二戰歷史不容顛覆,如果日本想在國際社會中走得更遠,終有一日需要正視二戰的歷史。既然歷史上的日美關系在這一問題上犯過錯誤,那么,在關于二戰責任的歷史問題上,日美關系也應當為正面這段歷史、還受害國以公道而做出相應的努力。
[1]石涵月,肖花.德日對二戰反省的差異及其原因[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1):117.
[2]扈明麗.德國和日本對二戰的不同歷史態度評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120.
[3]彭玉龍.謝罪與翻案:德國和日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罪行反省的差異及其根源[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
[4]大沼保昭.東京審判?戰爭責任?戰后責任[M].宋志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5]高橋哲哉.戰后責任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6]蘇智良.日本歷史教科書風波的真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3.
[7]于群.美國對日政策研究[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32.
[8]鹿島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1卷[M].東京:原書房,1983:961.
[9]劉世龍.戰后日美伙伴關系的三個發展階段[J].日本學刊,20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