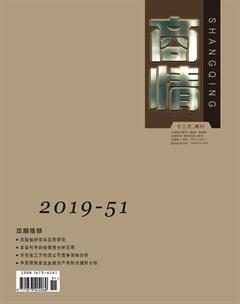基于崗位能力培養導向的酒店管理教學創新
熊彬
【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崗位能力培養導向進行酒店管理專業教學創新的意義,從以職業崗位群人才需求為導向確定人才培養目標,實現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的緊密結合,創建學生、學校、企業深入合作的育人模式,加強酒店管理課程體系建設四方面分析了基于崗位能力培養的酒店管理教學創新策略,對于高素養酒店管理人才的培養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崗位能力培養;導向;酒店管理教育;創新
隨和酒店行業經營服務范圍的不斷拓展,其服務功能也實現了多元化的發展。酒店行業的發展及創造力財富也為人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質量不斷提升。在新形勢下,酒店行業的服務與管理實現了專業化的發展,這對從業者的專業化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酒店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工作需要結合行業發展所需,以崗位能力培養為導向進行教育創新,這樣,才能為酒店行業的發展培養更多優秀的酒店管理專業人才。
一、基于崗位能力培養導向進行酒店管理專業教學創新的意義
為了更好地適應酒店行業發展的人才需求狀況,對酒店管理專業教育進行改革是時代所需。創新酒店管理專業教工作,是優秀酒店管理類人才培養的保障,這種創新能夠顯著提升學生的崗位能力,促進學生能夠實現職業化的有效發展。酒店行業服務內容和方式發生了變化,對相關從業者的需求標準也發生了變化,基于崗位能力培養,進行酒店管理教學創新,需要研究酒店行業人才需求趨勢及行業發展趨勢,基于此進行人才培養方法策略的調整,這樣,所培養的人才就能夠滿足行業發展的需要。目前,高校由于擴招,所培養的畢業生數量龐大,這樣學生的就業壓力就很大。而基于崗位能力培養進行酒店管理教學創新,學校在人才培養中就會突出酒店管理實踐教學部分,也會不斷強化學生崗位能力的培養,這樣就能夠提升學生崗位能力和就業素養,使學生能夠在激烈的人才競爭具有優勢,使學生能夠憑借自己的崗位能力與素養贏得就業的機會,這對于學生發展而言意義重大。
二、基于崗位能力培養的酒店管理教學創新策略
(一)以職業崗位群人才需求為導向確定人才培養目標
近年來,酒店行業發展迅速,除了傳統崗位服務外,很多企業還與一些旅游企業合作,開拓了很多新的經營管理崗位,設置了一些休閑產業相關的崗位。基于崗位能力培養為導向進行酒店管理教育創新,首先需要能夠認真分析酒店行業的職業崗位群人才需求情況,能夠做好市場調研工作。在人才培養中,教育者要認識到酒店職業崗位群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單一崗位,人才培養目標要能夠基于崗位群需要進行設置。要認真研究酒店行業崗位群人才需求特征,就目前而言,酒店行業需要的人才必須要具有較強的服務操作能力和基層管理能力,在人才培養目標設置中,相關核心能力要有所體現。酒店管理專業人才還需要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能夠具有較強的服務能力,能夠勝任酒店行業相關崗位群的基層管理工作,在人才培養目標設置中,相關內容都要考慮到。
(二)實現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的緊密結合
基于崗位能力培養導向的酒店管理教學創新,必須要實現理論與實踐教育的融合發展。在人才培養中要能夠建立課內與課外有效聯通的教育機制。學生在課堂上學到的主要是一些酒店管理專業的理論知識及技能,而這些技能需要通過學習交流得以有效的消耗、吸收,之后,要通過實踐活動使學生能夠對相關知識及技能進行個體化的操作應用,實現知識技能的有效掌握。培養學生的崗位能力,更多地需要依靠實踐活動實現,傳統課堂很難對學生動手能力、實踐素養進行培養。因此,設置實驗實踐環節很重要。教育者要重視對課堂拓展,結合課堂教育開展創業實踐活動,設置第二課堂課外實踐環節,將課內所學的知識和實驗融入到實踐活動設計中去,實現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的融合發展,實現學生動腦動手的有機統一,這樣才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實踐素養和崗位能力。
(三)創建學生、學校、企業深入合作的育人模式
傳統的酒店管理專業教育主要要是通過理論知識學習及案例分析法開展育人工作,雖然教師在課堂上也會通過一些案例使學生感知酒店管理的日常活動事務,但這種教育模式畢竟與現實工作場景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不利于學生崗位能力的有效培養。基于崗位能力培養導向的酒店管理教育創新,就需要改革傳統酒店管理育人模式,能夠創建學生、學校、企業深入合作的育人體制。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和直接受益人決定了學習實踐的成效,也是學生把學校與企業聯系了起來。學校作為教育活動開展的主體,其教育方式手段對學生學習效率的高低有著直接的影響,學校育人工作的成效對于企業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企業的發展狀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學校育人成效,也是評價學校育人質量高低的重要參考。企業主要承擔實踐育人任務,對于學生崗位能力培養能夠產生積極的作用。要保障酒店管理專業育人質量的不斷提升,需要學校,企業與學生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學校與企業合作,為人才培養提供良好的崗位環境,這對于發展學生的酒店管理專業知識水平,提升學生的崗位能力是極為有利的。
(四)加強酒店管理課程體系建設
要實現學生崗位能力的有效培養,就需要能夠加強酒店管理課程體系創新工作。實現酒店管理課程體系的創新,需要以崗位能力培養為核心,進行課程體系的模塊化設計。可以將酒店管理專業課程設置為專業基礎課程模塊、專業核心課程模塊和職業拓展課程模塊。專業基礎課程模塊設置中要做好公共必修課程與專業通用課程的設置,使二者能夠有機結合發揮育人作用。在專業核心課程模塊設置中要能夠實現酒店管理專業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的結合,并要與職業資格認證結合起來,要能夠設置好服務技能類課程與管理技能類課程,保障相關內容的實用性和前瞻性。職業拓展課程模塊可以基于崗位需要進行內容設置,主要設置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拓展課程的設置要重點關注學生的職業潛能的挖掘,同時還需要考慮學生的職業愛好及選擇情況,設置一些個性化的課程內容。
總之,酒店管理專業要能夠基于崗位能力培養為導向進行教育創新,這樣,才能保障所培養的人才具有較強的崗位實踐能力,保障所培養的人才能夠滿足酒店行業發展的需要。在教學創新中,要能夠制定科學的人才培養目標,重視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的結合,重視課程體系的建設,要能夠通過多種策略,推動酒店管理專業教育的發展,實現高素養實踐性酒店管理人才的成功培育。
參考文獻:
[1]楊娟娟,張來陽.酒店管理專業學生職業能力培養探析[J].湖南城市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3).
[2]姜華.酒店管理專業核心職業能力的培養[J].商場現代化,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