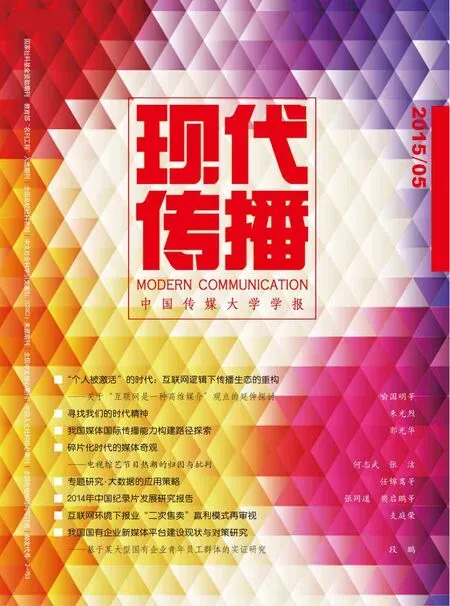尋找我們的時代精神
■朱光烈
尋找我們的時代精神
■朱光烈
進入后現代以來,文明進步的觀念被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所消解,而大量的事實和數據顯示文明確實是在不斷地進步。進步是曲折迂回的,利弊互見的。看文明是否進步,需要辯證地分析,需要算總賬。舊的進化論強調的是叢林法則,它反映的是原始資本積累時代崇尚殘酷競爭的時代精神。現代進化論強調集體進化,反映著信息社會對于合作與道德提升的需求,文明進步是人類整體進步的觀念,顯示著信息社會新的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對于當前較為順利地度過文明大危機極為重要。
多元主義;叢林法則;合作;向善;集體進步
21世紀初,明媚陽光被一片陰霾所覆蓋
2000年8月4日,筆者在北京《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新經濟:生產方式的革命》的文章,其中寫道:
1999年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發表《新經濟指標——了解美國的經濟變革》的研究報告,將“新經濟”定義為:“新經濟是以知識和思想為基礎的經濟”。根據各種關于新經濟的報道,筆者認為所謂新經濟的構成要素是:第一,以技術為主要推動力,特別是電腦網絡技術,在技術層面組織和整合其他技術構成了強大的經濟發展動力;第二,以人的智慧(思想、主意和決斷能力)統領技術,構成新經濟的靈魂和關鍵;第三,以和諧的關系整合發展是新經濟的生存環境。這三個要素是相互聯系的,但是不是平行的關系,而是由第一經由第二到第三遞進的發展關系,第三個要素是最具有意義的。這方面的發展從信息社會到來之時就開始了,內容十分豐富,諸如企業內部以人為本的管理原則,對員工從物質到人格的尊重,員工普遍地持股,企業外部對消費者的尊重和真誠服務,企業間的廣泛合作,以及普遍進行公益事業,道德成為競爭的源泉,等等。新經濟新在什么地方?不應當把新經濟僅僅理解為網絡經濟,或者是電子商務經濟,在我看來,新經濟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的主產方式就表現以上三個方面,而主要是體現在第三個要素方面。不僅新的網絡經營在遵循著這種新的生產方式,而且傳統的制造業也在奮起構成這種新的生產方式。
……在我看來,美國以及西方發達國家的道德回升,是新經濟的生產方式革命帶來道德革命。它與舊的道德有著繼承性質,但是它更是一種革命。世界正在進行一場空前的生產方式的大革命和道德的大革命。新經濟的三個要素,特別是第三個要素,反映著這種革命,而且已經顯示出了未來文化社會(文化主義文明)的端倪。新經濟正在把人類帶入一場有史以來最深刻、最偉大的革命之中,人類正面臨著有史以來最根本的轉折,我們必須作好充分的準備。①
從1999年冬天開始我一直在寫一本書,當時恰逢“新經濟”的爆發。“新經濟”以雷霆萬鈞的勢頭沖擊著那個年代,文明呈現出巨大進步的勢頭,而這種勢頭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的。在這樣的沖擊下本書的寫作首先是從“新經濟”問題入手的。當時我看到的是“新經濟”所帶來的一片明媚的陽光,企業是“以人為本”地進行管理,以客戶為中心,并開始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道德水平也有明顯的提升。關于道德水平的提升的分析,我當時使用了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等四五位美國學者、記者的文章里提供的大量資料、數據和分析。我把寫完的這部分稿件(約4萬字)寄給了中國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看,看后他在電話里對我說,這篇東西很有價值,他看過后對人類前途的信心增強了。他還囑咐我這些研究成果一定要發表,不發表太可惜。
這一年我把這部分稿件改寫成了三篇文章,分別在北京、廣州兩家刊物和一家報紙上發表,其中之一就是以上節選的那篇文章,還有兩篇:一篇是《新經濟鼓起道德“重建”之風》,其中包含著的小標題有:《西方道德:從混亂到“重建”》《道德“重建”與新經濟同時到來》《新經濟建構了企業內部生態關系》《企業與社會之間生態關系的建構》《生活方式革命和價值觀念革命》等;一篇是《企業與社會之間生態關系的建構——新經濟推動下的生產方式革命與道德革命的分析描述之一》,其中包含著的小標題有:《企業間的合作迅速發展》《客戶成為中心》《社會責任的承擔和道德成了競爭的源泉》等。這兩篇文章都是作為封面文章發表的,其中《新經濟鼓起道德“重建”之風》的標題還是經由編者加工的。這里回顧當年李慎之先生的肯定和各家報刊的重視,是想根據我的親歷讓讀者看到那時人們都感受到了“新經濟”所帶來的文明的一片明媚陽光。在我看來這是新文明的曙光。
但是這片曙光還主要是技術和知識制造的希望之光,隨著2000年3月底納斯達克股市的突然崩盤,這片曙光迅速被一片陰霾所覆蓋。再過七年便爆發了本次金融危機。新世紀的最初十多年還爆發了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更有氣候變暖嚴重加劇,已經六七年了,整個世界至今仍未爬出金融危機的陷阱,而且世界上的紛爭在加劇,環境危機在加劇,天空變得越來越黑暗。對于大多數人直接影響最大的要算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說:“階級斗爭持續了20年,我所在的階級取得了勝利。”樂施會總干事戈德林說:“這不僅是平等的問題。世上有人餓死或無法獲得醫療照顧。這個問題已經成為生死議題。”②資本主義把它自己開創出來的那片曙光封閉在它的牢籠里。
十五年來差不多每一天我都坐在我的書房里為寫這本書敲打著鍵盤,或讀著與寫作有關的書、報刊。在這個斗室里我常常感受到好像坐在“過山車”上,有乾坤顛倒的震撼。本書基本上是在“過山車”上寫的。大概從2001年開始,我寫的文章也從某些報刊較為歡迎的稿件一下子滑落成為“棄兒”,即使預約的稿件也一樣。只是那片“新經濟”的曙光和春風并沒有從我們心頭上消失,我相信一切讓人不愉快的事情只是道路的曲折與迂回而已,文明是不斷進步的,在信息社會里文明的進步已經加速。
一部關于文明和道德進步確定性論述的大書
2013年春天,當我第一次把書稿交給一家出版社之后,老同學蔣迅先生給我郵寄了錢永祥的一篇題為《今天我們更進步了嗎?——“道德進步”:一本書與一種歷史觀》③的文章。文章寫道,當代社會對于歷史和道德是否走向進步的問題一直諱莫如深,愿意正面肯定和追求道德進步的人還是少數,不過自由主義歷史觀認為歷史和道德是進步的。美國紐約大學教授斯蒂芬·平克就是持這種歷史觀的,最近他出版了一部新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何以暴力在降低》,系統地闡述了這種歷史觀。
錢文與該書指出,粗略地看歷史進步觀,歷史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前后階段相比較可以看出生活品質和文明程度都有了進步,求其原因在于“求生方式(生產方式)的不同。亞當·斯密、馬克思、維柯、孟德斯鳩、休謨、弗格森都持有這種觀念。
平克的論據主要是暴力隨著歷史的延長線的延伸在不斷地減弱,關于這個問題平克提供了大量的、系統的數據。在沒有國家組織的遠古時代里,暴力沖突導致人口死亡的比例占到15%,20世紀的戰爭看起來空前慘烈,但是造成死亡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3%。隨著歷史的延伸,每一個人的暴力相向情況也在降低,從歐洲的中世紀到今天的中歐社會,兇殺事件的比例從每10萬人每年超過100件降到了0.8件;殘酷的酷刑和死刑都在顯著減少。古代人類設計了各種各樣酷刑方法和刑具,各種以人獻祭的習俗和獵殺女巫、殘害宗教異端等行為曾經盛行了幾個世紀,如今都不復存在。至于死刑,在英國亨利8世的時候每周超過了10次,亨利的6個妻子有兩個處以死刑。1822年英國法律列出的死罪有222項,而到了1861年只剩下6項,到了20世紀中葉英國完全廢除了死刑。這種趨勢在大多數國家都可以看到。
在以往文明里,像《水滸傳》里的英雄好漢可以隨意把人殺死的現象,曾經大行于世,有人甚至把殺人當成取樂的游戲。中國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就有以殺人為樂的癖好:張獻忠軍每屠殺一個地方,都詳細記錄所殺人數,其中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等記載。他打下麻城后,把婦女的小腳砍下來堆成山,帶著他最心愛的一個小妾去參觀。小妾笑著說:“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也不過了。”張獻忠笑咪咪地說:“你的腳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腳剁下來放到“山尖”上。張獻忠說:“不亦快哉!”④
所有這些,還有各種觸目驚心的酷刑,如凌遲、點天燈,在信息社會里已經成為難以置信的傳說,很多國家甚至廢除了死刑,即使保留死刑的國家,處死犯人也會使用無痛苦的和體面的方法。迫害人的極端現象只是偶爾發生。
政治斗爭也越來越顯得文明起來。在歷史上為了奪取政權,兄弟之間相互殘殺屢見不鮮,一般的政變更是家常便飯。中國領導人林彪在1966年5月曾經作過一次關于政變的講話,他說,從1960年到他講話的時候的六年里,據不完全統計,僅僅在亞非拉地區,發生過61次政變,平均每年有11次,其中有8個首腦人物被殺死。才過去不到半個世紀,這樣的政變目前已經很少見了,筆者雖無統計,但是回憶起來,這些年來在全球往往一年都沒有一次。
2010年8月5日,智利33名礦工被困在700米的礦井下面,全國總動員,甚至總統現場指揮救援,世界各國都來支持。10月13日所有33名礦工終于全部被救了上來。救援活動驚動了全世界,大約有10億人收看了電視轉播。救援成功使智利全國陷入無與倫比的歡騰之中,一位參加救援活動的中國工程師在自己的微博里寫道,看著救援情況,“我被深深感動了,全球人類是一家,我這么對自己說。”
最近十來年發生的印度洋大海嘯、“卡特里娜”颶風、恐怖主義襲擊和中國汶川大地震這些巨大的災難事件,以及2011年3月日本發生的引發大海嘯和核事故的大地震,都引起過各國政府和廣大志愿者的忘我支持。在這些救援過程中,博愛精神得到了從未有過的大發揚。日本救援隊員每當挖出一具汶川大地震遇難者尸體都會向他默哀。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
本書還把向善的源頭延伸到生物的源頭,表示相信人類文明是以向善為主導的。
平克還指出,20世紀后半葉的民權(少數種族的權力)、女權、兒童權力、同性戀權力都有很大的改善。在過去的歷史中,動物權力只有在某種宗教里得到尊重,極少在全社會里受到保護;在20世紀后半葉,動物的權力也受到了越來越有力的保護。
錢文還介紹了平克關于暴力不斷減少的原因的分析。從沒有政府到政府的出現是暴力減少的重大原因,司法力量的提升,經濟和貿易的發展都促進了暴力的不斷減少。平克還指出文化力量的發展壯大對于人道主義革命的巨大意義,他認為印刷技術的發達、讀書人的大量增加和書籍報刊的普及是人道主義不斷提升的主要動力。閱讀幫助人們設想到他人的經驗和感受,也可以理解到他人不一定是邪惡的威脅,從而減少了參與虐殺的意愿。本書收錄的資料顯示,全世界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從1950年的3年,提高到了2010年的8年,即使在發展中國家,成年人人均接受教育的年限也從2年增加到了7年。⑤他還認為,人性中有一些動機會促使人向惡,但是也有一些動機會促使為善,至于實際上哪些動機會發生作用,則往往取決于環境的觸發。
我們從錢文里可以看到,平克認為文明是一條不斷走向減少暴力的道路,那么這是否就是一條和諧、善良和更加道德的道路呢?當然,文明發展史中還有許多重大的事件值得關注,它們自有它們的價值,衡量文明是否進步有許多尺度,但是暴力所制造的痛苦是一種極度負面的價值,消除它的存在有很高的甚至絕對的必要,隨著歷史的延伸,減少暴力、減少痛苦不僅已經構成了一種趨勢,而且在人們的道德意識中也已取得了越來越核心的地位。
平克還指出,18世紀以來人類的價值觀念有了顛覆性的改變,認為謀求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減少身心所承受的痛苦,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不亞于蒙神賜福或者成圣成賢。這種心態逐步擴大道德關懷的范圍,導致了對他人同情的產生,進而產生平等的意識,兼愛的范圍逐漸延伸,特別是在以前遭受到排斥的異己也落實到了兼愛的圈子里面。另一方面,關心日常生活利害苦樂可以稱之為“道德的日常化”,這種趨勢轉移了道德關懷的焦點,道德關懷不再是彼岸,像以往宗教所要求的那樣,也不再是向往精英式的道德成就,而是日常現實生活,現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一樣受到道德的關注,甚至成為最為迫切的道德關懷所在。這樣一來就把道德拉回了現世,拉向弱者、受苦者和無力出聲者身上。很顯然,這種道德提升正是中世紀末啟蒙運動、人文主義的主旨。
平克強調,暴力的不斷減少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平克在描述了暴力隨著文明歷史的延伸而不斷減少之后發問: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還要追問這算不算“道德進步”,只能說是不知道道德為何物。
這種道德的日常化還表現在壽命的延長。根據2013年的報道,從25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一直到19世紀初,人類的平均預期壽命一直停止在大約35歲的水平上。之后便迅速提升。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2014年8月27日的文章報道,目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人的預期壽命已經達到了80歲上下,即使全世界也達到了70歲(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人口司和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人均預期壽命的大幅增長是人類生存狀況的不斷改善和衛生醫療條件的不斷提升帶來的。⑤
多元主義對進步的否定很難成立
錢文寫道,今天的讀者在多元主義、相對主義、自然主義中浸潤已久,他們不承認道德或者文明是進步的。根據錢文的介紹,平克歸納了三種不承認的理由:第一,衡量各種不同的文明是否進步不應當有一個統一的尺度。歷史誠然有變化,但是變化的前后狀態何以就能說是改善或者進步呢?一方面,改善或者進步預設了某種評價的尺度,這是違背價值多元觀念的。如果文明之間要作比較,所預設的比較尺度必然外在于、超越了個別文明,但是由于任何文明都是完整獨立的整體,不應該受制于某種外加的普世價值,文明之間焉能有發展先后高下可言?第二,承認歷史的進步是一種無法令人接受的歷史決定論,它就意味著歷史朝著某個終極的文明狀態前進,這種歷史目的論預設了某種決定在先的目的狀態,歷史所發生的事情,仿佛都是準備階段,其意義在于促成以目的狀態的生長成熟、獲得實現。今天的專業歷史學者們很難接受這里所包含的輝煌史觀暗流的觀念。第三,在所謂進步的同時卻帶來了大災難,進步是一種欺騙。20世紀以來技術帶來巨大變革的同時,也帶來了對人的侵略、壓迫和戰爭,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不斷破壞。這樣一來,在許多人眼里進步就變成了一個帶有欺騙性的理想了。從這種悲觀的歷史觀看去,20世紀的歷史不僅沒有進步,還反而只是惡勢力的發展精進罷了。今不如昔。于是今天人們對進步產生了強烈的反感,甚至把它看成偽善,所謂啟蒙運動也受到了質疑和批判。
所有這些理由我們經常可以在當前的學術話語里看到,如果我沒有理解錯,大致可以說它們就是當代流行的后現代主義的觀念。我以為這些理由難以成立。
關于第一個問題,衡量各種不同的文明是否進步應不應該有一個統一的尺度?多元論者認為不應該。不管是在本文的討論還是在平克大著里的討論里,從整個人類文明歷史的發展趨勢上都不難發現,這個統一的尺度是存在的,即人富裕的物質生活,人性得到保障和尊重,向著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趨勢。我們無論如何設想,也不能得出這樣的認識,挨餓、被奴役、被壓抑以至于被屠殺是人們所喜歡的,相反正常的人總是希望過得富裕一些、自由一些,能夠得到社會的尊重,社會能夠更和諧一些,除非是一個由于長期被奴役、被壓迫到精神已經不正常的人,任何人都需要這樣的生活。這種人類的普遍需求就應當是衡量各種不同文明是否進步的統一尺度,這一點是不能否定的。而正是在這個維度上文明是不斷進步的。
關于第二個問題,所謂歷史決定論或者對于它的否定都不過是一種觀念,而實際的情況是:歷史確實一直在不斷進步的道路上前進,雖然期間不乏曲折和迂回。多元論者把進步觀念說成是預設了的歷史決定論,那么按著這種邏輯是不是也可以說,否定文明進步的理論也是一種先驗論?問題在于科學是建立在事實和邏輯這兩個基礎上的,見解只要是建立在這兩個基礎之上,就不必考慮是否符合流行的觀念了。
關于第三個問題是,由于進步的同時帶來了災難于是進步論成為一個大欺騙的問題。持這種觀點的人忘記了生物界的進化甚至宇宙的演化,總是會帶來某些磨難、某些優勢的退化,甚至還會帶來某些災難。所謂“甘蔗沒有兩頭甜”,因為這種情況而否定進步,甚至把進步當成退步,這是對進步機制的不了解所致。當然并不是一切變化都是進步,有些確實是退步。在生物進化中我們可以發現,當一種新的功能出現之后,原有的某種功能會隨之消失。當動物生長出肺臟,大幅度提高吸收氧氣(從空氣中)的功能之后,原來的用于從水中吸收氧氣的腮卻消失了,在水里呼吸的優勢也就消失了。文明進步也有類似情況: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信息社會,人類不像以前悠閑了,自然環境也不像以前那樣清潔了,但是人類物質生活水平卻有了大幅度提高,人類的自由程度,得到社會尊重的程度,社會的和諧程度都大幅度提高,人類的壽命也大幅度地提高。而且在信息生活里,人類的勞動強度開始下降,環境惡化問題正在開始解決。現在世界上仍然存在著前工業文明,處于信息文明中的人類有幾個愿意重返前工業文明?衡量文明是不是進步需要辯證地分析,需要算總賬,把進步伴隨著各種磨難一起看成無所謂進步甚至是退步的觀念,是不是把進步看成純粹地獲得好處的事情?是不是恰恰違反了否定進步的人所強烈主張的多元化思維?反之承認進步所帶來的各種不同的后果而又從總體上觀察是否進步的思維方式是不是更符合多元論思想?
在不同的維度上看文明的進步
文明是可以從不同維度上觀察的。首先,在當前的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的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儒教文明等等。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沖突”所指就是這種維度上的文明。這是文明在空間維度上的分布。但是文明還存在于時間維度上,在這個維度上學者們把世界上各個不同民族的文明作為一個整體在歷史進程的長河里加以觀察,發現了不同的依次遞進的文明形式。馬克思主義和當前的未來學家都是在這個維度上來觀察文明的。
空間維度上分布的不同文明之間的價值觀是不同的,在實際生活之中不同的人對于它們之間的價值觀的評價也是不同的。西方人會把“伊斯蘭國”的價值觀看得非常低下和惡劣,“伊斯蘭國”會把西方的價值觀看成是罪惡。這似乎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平克的著作對文明的分析是在時間維度上進行的。在我看來,空間維度上的文明實際上也是時間維度上的文明,從整個人類文明演變的歷史來看,像目前的“伊斯蘭國”或塔利班和目前非洲的某些民族的文明,都還處在文明的比較初期的發展階段,歷史經驗表明,它們也是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如果我們把整個人類作為一個文明整體在時間維度上加以觀察,很容易發現文明是在不斷進步的,也可以區分在目前空間維度上分布的不同文明什么才是先進的,什么才是落后的。進行這樣的區分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標尺,亦如上所述。這個標尺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所展現出來的,是被人們所普遍選擇的,不是什么人強加給歷史的。
從工業社會開始,人類進入全球化的發展階段,到了信息社會全球化發展突然提速,各個國家和各個民族越來越緊密地捆綁在一起而無法分開。把整個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應當成為全球化時代的觀念,而到了今天文明面臨著氣候變暖等許多對于人類文明有極大威脅的問題的時候,把人類文明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意義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重大。
或許真的像霍金預測的那樣,文明會在不遠的未來毀滅殆盡,但是文明曾經不斷地進步過仍然是一個歷史事實。
從混沌中找出簡單的表述
按照錢文的表述,今天的讀者在多元主義、相對主義、自然主義中浸潤已久,在這種浸潤里,似乎一切都說不清了,確定性認識遭到質疑,所謂歷史進步、道德進步的觀念遭到質疑。我想這種思潮的崛起可能是現代社會發展越來越復雜、越來越混亂的一種思想上的反應。文明發展到今天有兩個維度越來越清晰,一個是信息社會帶來的空前的進步,一個是當代資本主義帶來的種種危機,特別是環境的空前大危機。一喜一憂,兩個維度相互交織,相互影響,難解難分。雖然本書作者也注意到了現代社會的復雜混亂,但是卻不贊成以多元主義、相對主義、自然主義統領我們的思想。在我們的時代里,科學技術和各類學術活動正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繼續發展著,這一切都是以某種確定性認識為前提的。
學術研究應當避免簡單化、直線化,使我們時刻不要忘記會有各種可能性。但是這種“浸潤”卻是一種破壞力量。受到這種“浸潤”的人們,往往把混沌學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似乎混沌學認為一切都是混沌的,世界不具有確定性,但是混沌學的創始者E·N·洛倫茲在《混沌的本質》一書里卻說:
混沌現象“表面上看似隨機的,不可預測的,而事實上卻是按照嚴格的且經常是易于表述的規則運行著”。⑥
只是這種規則過于復雜、曲折、交叉和隱秘,不易發現,以我們目前的研究能力還不能搞清楚而已。但是學者不可沉迷于混沌之中,這樣你好像很深沉但是卻放棄了話語權。學者應當是混沌的穿越者,既要沉入其中又要跳出其外,站在外面發現它尚可“表述”的簡單邏輯。我們需要從復雜中找出簡單。只是沉醉于“混沌”,好像是深刻,但是什么也沒有做。
錢文告訴我們,斯蒂芬·平克被認為是當代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現在他站了出來,寫了一本八百多頁的大書,用大量的數據和分析,“說明道德進步確有其事,人類的歷史,的確是一部道德進步的歷史,并且指出這種進步部分要歸功于啟蒙運動、歸功于廣泛的現代性所包含的普遍主義原則。”
科學技術的發展甚至于文明的進步從來沒有走過筆直的道路,曲折、迂回、出岔、甚至蝴蝶效應,退一步進兩步是發展和進步的常態。在信息社會里,這種情況越來越凸顯,但是我們依然應當相信文明是不斷進步的,而且在我正在寫的書稿里,主要描述了人類文明正面臨著一次空前的、根本的大革命,人類將由物質主義文明跨上文化主義文明的發展軌道,建立一個空前和諧的文明。
或許完全傾向于不確定性的認識也是可以確立的,在某些宗教哲學那里是存在的,比如在古印度吠檀多哲學和佛教哲學那里。但是迄今為止的文明主要不是在這種哲學指導下演化的,而是反映著世俗的意識形態,如果人類都是以吠檀多哲學和佛教哲學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很可能的是文明還停留在漁獵階段,而不會有今天我們討論文明進步的事情發生。吠檀多哲學和佛教哲學充滿著震撼人心的大智慧,未來文明是不是會吸收和發揚這種哲學,這樣的問題我是無力討論的。本書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當下的文明狀況,而非未來文明的詳細情景。于是本書只能在世俗的眼界里進行討論,從世俗的眼界看去,文明的進步是確實存在的。
在今天,我們一方面面對著環境破壞的威脅卻又可能走向空前和諧輝煌的時刻,我們不應當被不可知的悲情所控制,以利于找出對未來的信心和出路。
任何確定性的認識和任何不確定性的認識,都可能走上片面性和絕對化,學術研究需要使兩者互補,相結合。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是極為困難的。這是因為,影響認識的因素太多,我們無法完全發現和把握它們,因此我們充其量可以指出一種基本的傾向,學術研究說到底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建立一個相對的、開放的框架。
未來的大智慧來自于智力大交流、大合作的“社會腦”
17世紀的英國人去咖啡館不僅僅是去喝咖啡,而且是去讀書和探討最新的小冊子、小報上的傳聞。有些咖啡館還專門討論特定的話題,如科學、政治、文學和航運等。隨著顧客的轉移,信息還在多個咖啡館里流傳。在咖啡館里人們不再理會各自的社會地位,顧客們被鼓勵與來自不同行業的人們交流。詩人薩繆爾·巴特勒說:“紳士、修理工、貴族和流氓混雜在一起,大家融為一體。”當時很多人指責咖啡館奪走了人們的正規學習時間,這種情況很像是目前人們對電腦網絡的指責。但是正是咖啡館成為了創造力的源泉。英國開創性的科學協會——皇家學會的成員們經常到咖啡館里繼續他們的討論,甚至還在那里進行實驗,發表演說。
正是咖啡館里的這種爭論促使伊薩克·牛頓寫出了現代科學的奠基著作之一《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商人們把咖啡館作為會議室,這促使了新公司和新商業模式的興起。甚至于證券交易所的雛形也是誕生在咖啡館里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是在咖啡館里創作他的《富國論》的大部分章節的,他把最初的書稿拿給那里的人們傳閱和討論。今天是過去的延續和發展,當前的網絡所提供的交流力量是遠非當年咖啡館所能比擬的。
Brothers L1990年提出了“社會腦”理論假設,認為人類(甚至整個靈長類動物)的大腦里存在著一種機制,可以在交往中處理與他人相互作用的各種信息,從而推動對于環境的適應和人類的進化,因此一種所謂的“社會腦”應當是存在的。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13年6月26日的報道,牛津大學托馬什·戴維-巴雷特等人的一項研究成果表明,“社會腦”假設研究得到了計算機模型的支持。相關論文發表在《皇家學會生物學分會學報》上。⑦
根據2009年6月的報道,倫敦大學的一項研究通過基因分析發現,南非地區和歐洲、中東地區初次出現現代人行為的時候,它們的人口密度非常接近。而南部非洲人類現代行為暫時消失的時候,其人口密度可能是由于氣候原因出現了下降。這項研究證實了人類碩果累累的創新、發現更多地是依靠群體內部不斷地相互交流,而不是個體的智力。現代人的行為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密度的提高,而不是大腦功能的進化。⑧
以上的歷史經驗和研究發現不僅可以使我們相信,一方面文明的進步有賴于人與人之間大規模的交流、合作,一方面也使我們可以猜想:技術的發展正在形成新的包括每一個人的大腦以及無數的計算機的“大腦”的超級“社會腦”,將極大地推動社會的交流與合作,極大地提高人類的智力水平和創新能力,很可能對未來文明的發展起到目前我們還無法預測的偉大作用。
“一切智慧與黎明同盟”
很幸運,我的書稿里關于進步的觀念與斯蒂芬·平克是一致的,而且與平克一樣,暴力不斷減少成為我的最重要的根據。
我的書稿提供了很多數據表明二戰之后戰爭發生的頻率和烈度不斷下降,在信息社會里戰爭向著和平征服的方向轉化,全球化的發展是遏制戰爭的強大力量,非物質化趨勢使戰爭的必要性下降,龐大的戰爭機器似乎患上了肌無力癥。
本書還整理了一些資料表明,古代人們把使用暴力殘害同類不當回事,隨著文明不斷延伸,人類的行為越來越向善良、合作方向轉化。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長期以來勞動者的真正身份是奴隸或奴農,直到20世紀初風行于歐美的“科學管理”還把員工當成自私的、愚蠢的和必須加以管制的奴隸。信息社會的企業管理追求“以人為本”,尊重員工的本性。“以人為本”管理模式取代了“科學管理”管理模式。本書還專設一節討論了人的獨立、自由程度隨著文明歷史的延伸而不斷提升,到了信息社會提升的速度突然加快。在信息時代里,“以人為本”觀念大幅彰顯,全社會的福利制度普遍建立,人類之間的相互救援演繹了一出出激動人心的話劇。關于這種進步形成的原因,本書引用的解釋是一位名叫斯蒂芬·平克的說法:隨著生活的富裕人們對生命的評價得到了提高,對生命尊重程度得到了提高,并懂得了博弈的互惠理論,雙方合作能使大家都獲益,于是對別人使用暴力的行為也就減少了。我猜測本書引用的斯蒂芬·平克就是錢文介紹的斯蒂芬·平克。
我的書稿用大幅篇幅討論到,經濟的不斷發展,人類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是歷史和道德進步的根源。本書還從系統論角度來解釋歷史和道德的進步,認為文明系統的不斷復雜化必然要求文明不斷地走向合作與和諧。
根據眾多的研究成果,本書相信人類文明發展歷史就是一條不斷向善的發展歷史,人性也是在不斷地表達出合作與善良的一面,而且這種進步到了信息社會突然加快了步伐。
在我的書稿里還專門討論了人類文明向善的發展規律源于生物進化的問題。
著名靈長類動物行為專家、美國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的弗蘭斯·德瓦爾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一個猴子得到了食物,另一個猴子沒有得到,后者表現得十分壓抑。在另一段錄像里一只老鼠為了幫助另一只老鼠逃出陷阱,主動放棄了巧克力。德瓦爾解釋說,這一實驗表明,動物之間存在“對等、公平、同情、安慰”的社會友好傾向。⑨
在由生物組成的各種各樣的系統中,存在著兩種生存法則,一種是自私,它的極端行為是弱肉強食;一種是合作。最近的報道寫道,同胞的小象大的照顧小的,同胞的裸鼴鼠大的給小的讓路。合作的最高行為是以自殺維護集體的生存發展,譬如南美有一種螞蟻,在遇到火災的時候,可以抱成一團向火場外面滾去,外層的螞蟻被燒死了,而整體卻存活了下來。還有的科學家發現,細菌在遇到病毒攻擊時會自殺,以保護群體的安全。雖然動物中存在著叢林法則,但是合作、向善才是生物進化的主導力量,不然我們就無法解釋生物的持續進化。
人類中有一種慷慨行為,在可能沒有回報的情況下,花費財力、物力讓他人受益。以往的生物學家認為這種行為不利于適者生存原則,經濟學家也認為這是不理性的。但是根據合眾社2011年7月26日報道,美國科學家馬克斯·克拉斯諾在《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發表研究成果指出,如果經濟學家的這種理論是正確的,那么慷慨行為早就在世界上消失了,但是研究人員在仔細衡量人們的選擇后發現,不管在全球哪個地方,人們的表現都比以往的看法要慷慨得多。即使他們的交往只是一次性的,他們也往往表現得十分慷慨。慷慨不僅是社會壓力的結果,可能還是人類的天性。⑩(中國人現在有一種說法,“幫助別人,快樂自己。”)
弗蘭斯·德瓦爾2012年在一次大型國際研討會上也指出,19世紀的托馬斯·亨利·赫胥黎認為,道德不存在于人類的本性里,道德只是后天養成的,它只是人的薄薄的一層外衣。這種“人之初,性本惡”的觀念一直統治到了12年前。而目前的研究表明,有關人類本性殘忍,喜好競爭和攻擊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他說,人類之間具有大量社會友好傾向。⑨
文明是在合作與競爭的相互交織中進步的,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合作是處在主導地位的。過去的進化論過于看重相互競爭在推動生物進化中的意義,而新的發現更看重相互合作的意義。合作、向善、和諧與道德不斷的提升不僅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具有更加根本的意義,它的源頭來自于生物界相互關系的本性。如果人類和生物界的相互關系不是以合作為主導的,而是以競爭為主導的,那么他們早就會在相互死掐中走向毀滅。
人們曾經把赫胥黎的發現與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崇尚殘酷競爭聯系了起來。科學發現(解釋)有時候也反映著時代精神。如果此輪正確,或許可以說,當代科學家這類發現,顯示著信息社會新的時代精神:對于合作的需求。科學基本上是對于客觀世界的描述,但是有時候也反映著人類自己的需要,這種需要引導著科學家研究的方向。
現代進化論不同于傳統的進化理論,這是一種綜合進化理論、集體進化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物種形成和生物進化的基本單位不是個體,而是群體。生物進化是以合作為主導的。進化不可能是個體單獨進化,而是群體的集體進化。
錢文指出,平克在解釋幾千年來暴力之所以減少的原因時,完全不訴諸于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內在因素,而是尋求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幾種社會、經濟、制度性的外在推力。關于文明的進步在我寫的書稿里也在強調人類生存環境改變的巨大意義,但是我的書稿指出,從我所收集到的這些生物進化的資料看來,文明和道德的進步不僅有著人類生存環境改變方面的根據,而且還有生物學的根據。人性是多元的,人類不僅從動物那里繼承了相互競爭的行為,而且還繼承了合作和向善的行為,而且后者更為根本。沒有合作生物就不能存在,更不可能進化。
在許靖華著的《大滅絕》一書的封底印著這樣一段以介紹那本書的主要觀念的話:
我們該探究的是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律可能并沒有意義。……如果大多數生物的滅絕是由災變引起的,那么決定生物生死存亡的將是機遇而不是優越性。我判斷的結果發現天擇說決非科學,只不過是一種社會偏見,而且是非常邪惡的偏見。它已經嚴重地干擾了人類清醒地領悟生命歷史的能力。(11)
許靖華的話是在20世紀80年代寫的,而愛因斯坦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經這樣寫道:
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同它有關的選擇的理論,被很多人引證來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根據。有些人還以這樣的辦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競爭這種破壞性經濟的必要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個過著社會生活的的動物。正像一個螞蟻窩里的個別螞蟻之間的交戰說不上什么是為生存所必須的,人類社會各個成員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12)
根據著名宇宙學家、《時間簡史》的作者斯蒂芬·霍金等少數科學家的預測,由于氣候變化以及其他可能爆發的大災難,人類將從地球上消失。而我的書稿試圖論證,今后幾十年里人類將爆發一次空前的文明大革命,物質主義文明將被文化主義文明所取代,文明和諧程度將大幅提高,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人類面臨著極大的風險,甚至毀滅的風險。或者走上空前和諧的文明,或者走向毀滅,我們必須進行選擇。當然還會有中間道路,但是那一定也是非常艱難、必須付出巨大犧牲的道路。對于我們來說,沒有什么比選擇一條相對安全的文明大革命的道路更為重大的任務了。為此我們需要厘清當前的文明狀況,尋找它的歷史方位,尋找我們這個時代的發展趨勢。文明和道德是在曲折紛亂之中不斷進步的,這是文明發展歷史的一般規律,信息時代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強勁地走向合作和道德提升。舊的進化論強調的是叢林法則,反映的是原始資本積累時代崇尚殘酷競爭的時代精神。現代進化論強調集體進化,反映著信息社會對于合作與道德提升的需求,顯示著信息社會新的時代精神。
目前我們正面臨著一個矛盾日益叢生、十分紛亂的世界,很可能這種情況還會發展,在文明大革命過程中人類的合作和道德提升一定會受到嚴重干擾,這是文明大革命題中應有之意。但是我們不應因此而悲觀,應當堅信我們時代的發展趨勢,堅信我們的時代精神。這樣可以使我們頭腦清醒,建立信心,有利于我們盡量避免付出太多的犧牲,走向空前和諧的文化主義文明的明天。
美國哲學家、散文作家、隱士亨利·大衛·梭羅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做《瓦爾登湖》,讀起來總是讓人如醉如癡。它寫道:“我們整個的生命是驚人地具有道德性的。……在整個世界中顫動著的豎琴的樂聲,正是因為它強調善才使我們為之激動。……雖然青年人最終變得冷漠,宇宙規律卻不是冷漠的,而且永遠站在最為敏感的人的一邊。”它還寫了這樣一段話:
《吠陀經》說,“一切智慧與黎明同盟。”詩歌和藝術,以及人類最美好最值得記憶的行為,都始于這樣的時刻。我們必須學會重新醒來并保持清醒,不是通過機械的方式,而是通過對黎明的無限期待,即使在最沉睡的時刻它也不會拋棄我們。(13)
〔本文系作者根據正在書寫的《文明大革命即將爆發》(暫名)一書的《跋》改寫的〕
注釋:
① 朱光烈:《新經濟:生產方式的革命》,《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8月4日。
② 見《樂施會呼吁給億萬富翁加稅》,《參考消息》,2014年11月9日第六版。
③ 錢文載于《南方周末》2013年3月29日。
④ 劉亞洲:《甲申再祭》,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sE7OyBYmmGoc_ekiv0ESc3HDFkeXi2nuRL68-cYP8FkWdFnSexcKt PMkrkEEhbt_dxhbZumxsV5yov_5kXcqzlVG3CVdGg0-YqKAJXxugy,百度文庫,2006-08-23。
⑤ 見美報文章《世界正變得更加平等》,《參考消息》,2014年9月4日第10版。
⑥ [美]E.N.洛倫茲:《混沌的本質》,劉式達等譯,氣象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頁。
⑦ 見湯姆·斯坦戴奇:《17世紀的社交網絡》,原載2013年6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網站。見《17世紀“新媒體”咖啡館證明社交網絡是創造力源泉》,《參考消息》,2013年7月4日第12版。
⑧ 見《人口密度決定文明程度》,《參考消息》,2009年6月9日第7版。
⑨ 見《“人之初,性本惡”站不住腳》,《參考消息》,2012年2月27日第7版。
⑩ Max M.Krasnow:《研究發現:“慷慨“可能是人類天性》,http://news.cntv.cn/20110802/115818.shtml,2011年8月2日。
(11) 許靖華著:《大滅絕》,三聯書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封底。
(12) [美]愛因斯坦著:《愛因斯坦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13) [美]亨利·大衛·梭羅:《瓦爾登湖》,王家湘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61頁。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高級編輯)
【責任編輯:張國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