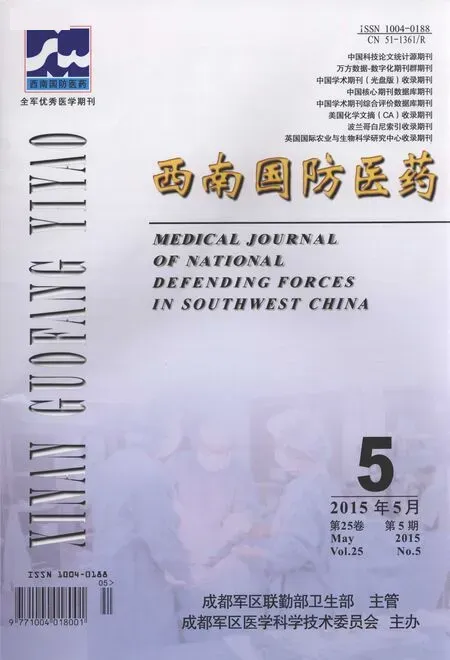腦深部電刺激術治療帕金森病患者的護理
李 莉,王 霞,陳茂君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種常見的中老年神經系統變性疾病,臨床表現為運動遲緩、肌強直、姿勢步態障礙、靜止性震顫等。 目前歐美國家60 歲以上人群發病率為2%。 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呈顯著上升趨勢,發病率為44.3∕10 萬[1]。 左旋多巴雖然能夠顯著改善帕金森病癥狀,但隨著疾病進展,其療效逐漸減退,副作用日益增加。 腦深部電刺激術(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是近幾年來最新開展的PD 外科治療的有效手段。由于該項技術類似心臟應用的人工心臟起搏器, 故又俗稱為"腦起搏器",是一種微創、不破壞腦內神經核團,具有可逆性、可調節性、并發癥少等優點,被稱為是繼左旋多巴后PD 治療的第2 個里程碑, 至今全球有75 000 例患者植入了DBS,但我國大陸僅有3100 例患者植入DBS[2]。2011 年7 月~2013 年6 月我院共73 例PD 患者進行了丘腦底核DBS 手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資料 本組73 例PD 患者中, 男性38 例,女性35 例。 年齡36~75(60.00±0.48)歲;臨床表現:單側肢體震顫9 例,肢體僵硬及震顫64 例。以步僵、開步及轉身困難為主要癥狀異動癥3 例;病史3~16 年,平均9.6 年;單側DBS 植入7 例,雙側DBS 植入66 例。深部電極植入的靶點皆是丘腦底核。
1.2 DBS 適應證 入選的患者符合原發性PD 診斷標準[3],Hoehn-Yahr 分級疾病處于Ⅱ~Ⅳ期,經正規內科治療,藥物療效減退或出現無法耐受的副作用, 已經影響正常生活和工作,智力和精神狀態正常,能配合者才能手術。
1.3 電極植入方法 在局麻下安裝Leksell 立體定位頭架,采用MRI 三維掃描來確定靶點坐標;經額部進行顱骨鉆孔,先植入測試電極于丘腦底核,進行術中測試,了解PD 癥狀控制情況,并進行副作用評估。 然后植入并固定DBS 電極;在全麻下通過頸部的皮下隧道植入延伸導線, 并于胸壁鎖骨下區皮下植入刺激發生器(Kinetra/Soletra, Medtronic Inc.)。
1.4 治療方法 一般于術后4 w、 手術的微毀損效應基本消失后,開始打開刺激發生器,進行持續電刺激,終身使用。 采用醫用DBS 程控儀(N8840,Medtronic,INC.),由醫師在體外調節刺激參數:刺激電壓1.2~4.1 V,脈寬60~90 μm,頻率130~185 Hz。以最小能耗及副反應、最大效果為程控原則,調整刺激參數,使患者最大獲益。 術后半年內每月電話隨訪1 次, 半年后每3 個月電話隨訪1次;若患者病情變化,及時門診隨訪,根據患者實際病情調整治療參數及藥物。 刺激器電池使用年限5~10 年,密切注意刺激器電量變化,如發現電量不足,及時手術更換新的刺激發生器。
1.5 療效 73 例PD 患者中,1 例術后出現顱內血腫,急診行血腫清除術,術后未再植入DBS 設備;另有1 例術后經多次程控儀治療,PD 癥狀改善不明顯。其余71 例在開始接受持續電刺激后, 帕金森癥狀明顯改善。 術后隨訪1~2 年,平均1.2 年,至最后一次隨訪,脈沖發生器開啟時,患者震顫、強直、運動遲緩、步態、姿勢穩定性明顯改善。 本組病例術前不服藥狀態下,UPDRS 運動評分(48.7±8.9)分;術后不服藥刺激器打開狀態下,UPDRS 運動評分為(17.8±6.8)分,與術前比較顯著降低(P < 0.05)。
手術并發癥:電極外露1 例,皮下積液1 例,顱內血腫1 例。 不良反應:術后短期神志錯亂1 例,肢體異動加重3 例,情緒改變2 例,記憶力下降3 例。 以上不良反應經調整刺激參數后明顯減輕或消失。
2 圍手術期護理
2.1 術前護理
2.1.1 心理護理 PD 患者因病程長,癥狀逐漸加重,藥效作用波動,患者深受疾病折磨,加之手術費用高,部分患者出現情緒低落、抑郁、孤僻、敏感等心理問題,抑郁在PD 患者中較為常見,約有一半的患者受此困擾[5]。研究表明, 心理治療和支持治療對減輕帕金森患者情緒障礙有肯定療效,并能加快緩解原發病的軀體癥狀[6]。 生病求醫是患者的主動行為, 但如何去控制帕金森病患者的心理狀態,卻是護士和家人的主動行為,心理護理應根據患者不同年齡、職業、文化水平、心理需求因人施護,為患者創造一個良好的治療康復環境。 多關心、理解患者,尊重患者的生活習慣, 講解疾病的特點, 幫助患者走出心理誤區,增強戰勝疾病的正性心理效應。
2.1.2 術前準備 術前12 h 停服抗帕金森藥物, 由于DBS 手術需全麻,手術前需禁食禁飲6 h 以上。DBS 術中需要做CT 或MRI 定位,因此,術前應按CT 或MRI 檢查前護理常規行術前準備, 不帶金屬物品。 教會患者根據自身的感覺,術中如何配合醫生做相應的動作,從而進行電極位置和電刺激的測試。
2.2 術后護理
2.2.1 并發癥的觀察及護理 (1)術后要警惕腦內出血的發生,密切觀察意識、瞳孔、生命體征、神經系統體征的變化,注意患者有無頭痛、嘔吐等臨床表現。 腦出血是DBS 手術最大的風險,Binder 等[7]報道,DBS 手術患者 無癥狀腦出血發生率是2.1%, 癥狀性腦出血率是1.2%。 本組1 例術后出現顱內血腫,于急診行血腫清除術,術后未再植入DBS 設備。 (2)防止電極斷裂、移位,忌暴力碰撞、牽拉等。 植入第1 w,囑患者脈沖發生器植入側手臂不要高舉過頭或劇烈運動,可在小范圍內活動,以防止血栓形成;植入后3 個月內,手臂不做劇烈運動,之后應避免用該側手臂負重。 本組患者中未出現電極斷裂及移位等情況。(3)密切觀察植入部位皮膚,忌揉搓植入部位皮膚,觀察局部有無紅腫、滲血、破損等。 Voges 等[8]報道,脈沖發生器植入處皮下出血率為1.2%, 皮膚感染率為5.7%。 本組患者術后發生皮下積液1 例,通過穿刺抽液、加壓包扎后消除。 發生電極外露1 例,手術取出電極,2 個月后再次植入,患者無不良反應,跟蹤隨訪,效果良好。
2.2.2 肢體康復訓練 患者因疾病影響,肌張力增高、肢體僵硬,運動減少。 患者的肢體訓練應根據各自狀況,決定運動量的大小,注意循序漸進。術后當日即可進行床上肢體訓練,如翻身、屈肘、轉腕、轉踝、肌肉舒縮、抓物等,幫助患者進行四肢的被動活動。術后1~2 d 鼓勵患者進行生活自理能力、自主行走鍛煉。 因PD 可致患者步幅過小,又缺乏平衡感,患者活動時容易摔倒,因此,應在醫護人員及家屬的扶持下進行,患者鞋子盡量采用防滑鞋底,走路時盡量跨大步伐,腳跟著地后再邁出另一步,雙臂自然擺動,轉身時盡量是身體跟著移動,弧線前進,以保持身體平衡。
2.2.3 藥物調整 DBS 術后繼續遵醫囑服用抗帕金森藥物,術后早期不減劑量,療效穩定后,再根據患者情況逐漸減量。 因此,DBS 術后患者全麻清醒后,能吞咽者應盡早服用左旋多巴,減輕戒斷效應[9]。 本組患者于術后3 個月內逐漸減少抗PD 藥物用量,以配合刺激參數的調節,跟蹤隨訪半年,有40 例藥物最終減量1/3~1/2。 31 例患者藥物減至原來的1/5,生活自理能力明顯提高。
2.2.4 術后刺激參數程控 DBS 術后首次開機時間一般是術后1 個月, 這時手術對神經核團的微毀損效應基本消失, 可以調節至最佳參數。 調控時不同的癥狀改善時間也不同,如肌張力障礙、僵直、運動遲緩等癥狀改善相對較快,短至數秒可見效果;異動癥改善較慢,需數天至數月。 DBS 術后可能需要數次程控,調節刺激參數,才能達到最佳療效。 本組病例中術后1 年調控次數在5~6次,31 例在術后1 年參數調節均達到理想水平。
3 討論
DBS具有可調節性,可逆性,微創,不破壞腦內神經核團,患者基底節系統的完整得到保留,從而還有在未來接受進一步治療的可能。 DBS 治療涉及到神經外科、精神科、神經內科、電生理以及影像學等多學科,其中以神經內科尤為密切[2]。 另外,患者及其家屬對手術要有現實的期望值,患者居住地與術后隨訪、DBS 參數調控中心的距離及患者術后情緒和心理方面的支持等因素應考慮在內[4]。 本組采用神經內外科結合來對患者進行正確的選擇。 DBS 是一種特殊治療方法, 需要對患者進行終生隨訪和維護,加之刺激器價格昂貴,在發展中國家還有很多患者難以承受[10]。 還有大部分PD 患者對DBS 還很陌生,相關臨床科室的同行對DBS 重視程度不夠[11],而且目前DBS 治療PD 病還沒有一個系統、 完整的護理程序。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 我們將在未來的工作中進一步完善護理程序, 加大宣傳力度, 加強與社會保險的聯系,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治療,提高生活質量。
[1] 張錦輝, 崔雷.帕金森病研究熱點的聚類分析[J]. 遼東學院學報,2012,19(2):115-118.
[2] 胡小吾, 梁晉川.積極穩妥開展帕金森病的外科治療[J]. 醫藥專論,2011,32(6):329-332.
[3] 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帕金森病及運動障礙學組. 中國帕金森病治療指南( 第二版)[J]. 中華神經科雜志,2009,42(5):352-355.
[4] Hariz MI, Johansson F.Hard ware failure in Parkinsonia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ubthalamic nucleus stimulation is a medical emergency[J].Mov Disord,2001,16:166-168.
[5] McDonald WM, Richard IH, DeLong MR. Prevalence, etiology,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J].Biol Psychiatry,2003,54(3): 363-375.
[6] 李留芝. 帕金森患者的心理問題分析及對策[J]. 現代護理,2002,8(2):107.
[7] Binder DK, Rau GM, Starr PA. Risk factors for hemorrhage during micro electro de-guided deep brain stimulator implantation for movement disorders [J].Neurosurgery,2005,56(4):722-728.
[8] Voges J, Waerzeggers Y, Maarouf M, et al. Deep-brains timulation: implications caused by hardware and surgery-experiences from a single center [J].J Neurol Neurosurg Psyehiatry, 2006,77:868-872.
[9] 李菊花, 任興珍.腦深部電刺激術治療帕金森病患者的圍手術期護理[J].護士進修雜志,2013,28(2):150-151.
[10] 張元鵬, 李新鋼.腦深部刺激治療帕金森病的研究進展[J].立體定向和功能性神經外科雜志,2004,17(3):183-186.
[11] 王軍, 張旺明.腦深部電刺激術治療帕金森病患者及手術靶點的選擇[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11,37(6):379-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