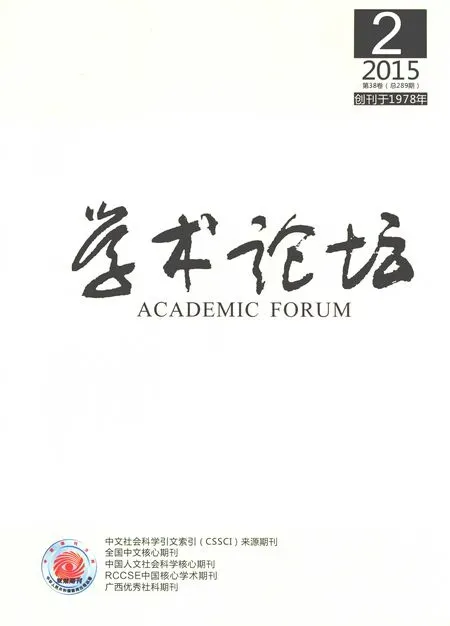何謂語境——對語境本質(zhì)的批判性考察
徐 杰
“語境”無處不在地被使用,但一問“語境是什么”時,我們竟然變得茫然了。 而我們又不得不正視這個看似簡單卻又艱深的問題,因為“要想對于一個理論以及這一理論有關的所有概念作出可靠的解釋,就必須先從解決一個中心問題入手,即先從確立一個關鍵概念的確切含義入手”[1](P3)。 所以對語境的探討必須要從“語境”這個關鍵概念的確切含義開始。 但是,每當我們試圖對一個概念或者范疇進行正面界定時,總是陷入一種無力把握的狀態(tài)。 對于語境定義的無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語境對于我們來說過于熟悉,“語境性知識是我們滿以為知曉任何事情但卻一無所知的東西”[2](P45);另一方面, 語境的具體應用和實踐多于其哲學反思,正如沙夫斯坦恩認為較之理論中的語境,我們過多地關注實踐中語境[3](P3)。 因此,沙夫斯坦恩得出令人望而卻步的結(jié)論:“語境問題對于哲學家或其他任何人都是很難解決的。 ”[3](P4)于是,有人以后現(xiàn)代對形而上學的解構(gòu)作為借口選擇放棄對對象本質(zhì)的追問;有人選擇從另一個角度來反向解釋,即將“什么是”轉(zhuǎn)換為“什么不是”;對于“什么是語境”這個令人茫然的問題,更是鮮有人對其進行清晰而深入的探討。
一、不同維度審視下的語境內(nèi)涵
語境的定義是語境理論的基石, 因為缺少對對象嚴肅的正視, 肯定會導致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理論大廈搖搖欲墜。 要為語境給出恰當?shù)亩x并非易事, 這是由于一方面語境具有復雜而特殊的性質(zhì), 另一面很多學者直接或者間接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語境概念。
對于語境定義的討論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率先拋出一個定義, 然后對這個定義的各項義素進行逐一分析; 第二種是從對象包含的基本定義所蘊含的問題出發(fā), 沿著問題的分析路徑考察無數(shù)的可能性,最后形成一個能被接受的定義。 第一種方式長處在于其明晰性, 預先提出的定義為之后的分析提供了一個確定的坐標, 但是這種方式讓人感覺語境定義產(chǎn)生自初步直覺的感受和具有一種不可改變的樣態(tài)。 第二種方式將定義過程的曲折性和復雜性通過一步步的追問和探討展示出來,以逼近相對確定的定義。 它的優(yōu)勢在于讓人意識到其結(jié)論并不是一個確定無疑之物, 而是暫時的和可以修正的, 但這種方式的途徑會讓人覺得麻煩和困惑。 筆者試圖將兩種方法結(jié)合起來,既追求理論探討過程中的明晰性, 又讓結(jié)論具有一種拓展的可能性,而非確定的教條。 也就是說,從語境已有的無數(shù)研究中總結(jié)出一個暫時的定義,然后對定義的內(nèi)涵和外延進行審視和分析。
語境,顧名思義就是語言使用的環(huán)境,比如韓禮德(Halliday)就將語境定義為“文本在其中展開的整個環(huán)境”[4](P5)。 學者們對于語境的定義主要是從三個維度來進行的。
第一個維度偏重于將語境視為對象存在的環(huán)境, 認為語境是圍繞我們所要理解的現(xiàn)象和為它的適當闡釋提供方法的框架[5](P49)。 斯格認為“語境是能被用于描述一個實體的情景特征的任何信息。 這個實體可以是一個人,地方或是物體”[6](P31)。霍弗德(Hurford)和赫斯勒(Heasley)認為“一個言說的語境是由說者和聽者共享的話語宇宙的一個小的組成部分, 并且包涵著使言說得以發(fā)生的會話主題的事實, 也包涵著會話發(fā)生時所處的情境的事實”[7](P1)。 沙夫斯坦因(Scharfstein)將語境定義為圍繞感興趣的對象并靠其相關物幫助解釋對象的東西[3](P1)。 這些學者的分析都偏向于將語境視為一種客觀現(xiàn)實的環(huán)境, 或者語言所指對象構(gòu)成的情境。 他們的論述涉及到了語境內(nèi)涵之中的客觀性維度。
第二個維度偏向于關注語境與對象意義產(chǎn)生的關系性, 個人敘述學派 (The Personal Narrative Group)認為“語境的字面意思是編織、纏繞、連結(jié)在一起。 這種內(nèi)部關聯(lián)創(chuàng)造了在人類行為中的意義網(wǎng)絡。 個體通過社會群體,結(jié)構(gòu)關系和身份加入到世界之中”[8](P19)。 這種語境定義特別強調(diào)語境的關系性或者網(wǎng)絡性,也屬于語境內(nèi)涵的應有之義。
第三個維度將語境視為主體建構(gòu)之物。 (1)純粹心理建構(gòu)物。 萊昂斯認為:“語境……是一種理論建構(gòu)之物,語言學家通過假設,對現(xiàn)實情境進行抽象并建立語境的所有因素, 通過這些因素對語言事件的參與者的影響,系統(tǒng)地決定形式,合適性或者言說的意義。 ”[9](P572)斯柏波和威爾遜更為直接地說,語境就是一個心理建構(gòu)之物,是聽者對世界假設的集成[10](P15-16)。 (2)語境在海姆斯這里并非僅僅是心理建構(gòu)物, 更像是一種社會-心理建構(gòu)物(socio-psychological)[11](P43)。無論是主體個人的心理建構(gòu)還是社會-心理的建構(gòu),他們對語境定義的出發(fā)點都是一種主觀認知角度。 雖說個別學者會提出激進的語境理論,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話語語境理論中,建構(gòu)確實也是其關鍵內(nèi)涵。
語境內(nèi)涵的三個維度在語言學語境研究之中有著更加典型的論述。 在語言學界主要存在三種語境觀:其一,認為語境是既定的、客觀存在的場景,如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弗斯(Firth)開辟的情景語境與薩丕爾、沃爾夫(Sapir-wolf)的文化語境。 其二,認為語境是一種認知和心理的產(chǎn)物,像維歐利(Violi)的“標準”語境、蘭蓋克(Langacker) 的“激活”語境、費爾默(Fillmore)的框架理論、羅杰·夏克和羅伯特·阿貝爾森(Roger Schank and Robert Abelson)的草案理論等等。 其三,認為語境是主體在交際中主觀交互建構(gòu)的背景, 即動態(tài)生成的語境。 語境的動態(tài)建構(gòu)主要從J.J.甘柏茲和C.甘柏茲(J.J.Gumperz and Cook-Gumperz)的“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理論之中體現(xiàn)出來。
無論是人文社科學者在普遍意義上對語境內(nèi)涵的歸納, 還是單純從語言學 (語境范疇的發(fā)源地)理論角度對語境含義的考察,語境的整體感都被支離開來。 于是學者們嘗試將幾個維度綜合起來,如阿南(Allan)把語境分為三個范疇:物理語境或叫場景,包括時空因素;話語世界,存在于話語當中,它可以是虛構(gòu)的、想象的或真實的;原文的環(huán)境,即上下文語境[12](P36)。 瑞伍也含混地說:“語境是一個具有廣闊范疇的概念。 它可以是語言的、物理的、認知的(包括個體對物理或語言的認知),也可以是社會的或心理的。 ”[13](P248)然而,我們必須看到,這種貌似百科全書式的雜糅定義,也只是將語境內(nèi)涵的幾個方面簡單粗暴地羅列在一起, 并沒有形成一種有機合理的語境界定。
由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對語境的定義五花八門,難怪布洛克威說,語境“有時被認為是確定言外之力的任何必須物,有時被認為是一套特征,有時被認為是一個情境,有時被認為是物理環(huán)境,有時被認為是文化或社會環(huán)境, 有時被認為是鄰近的文本或話語。 由于缺乏一個主要的定義,好像語境幾乎是任何事物”[14](P57-58)。 語境作為一種技術觀念具有無窮的力量, 然而語境這個觀念在使用時卻常常不能充分發(fā)揮其效果。 究其原因在于語境的普遍性 (ubiquity)、 抽象性(abstractness) 和易變性(changeability),因此只能通過對語境進行界定和假設才能使之明晰[15](P69)。 我們必須清楚,林林總總的語境內(nèi)涵概述是對語境本質(zhì)缺乏宏觀和深入分析的表現(xiàn),而語境的這種普遍性、抽象性和易變性也只是語境所呈現(xiàn)出來的表層現(xiàn)象。 那么,到底什么是語境的最本質(zhì)內(nèi)涵? 又應該從哪些角度去整體性地認識語境?
二、作為實在性、關聯(lián)性與生成性的語境內(nèi)涵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無論語境的定義有多少, 語境關注的最基本問題是文本自主性和對語境的依賴性[16](P15)。 也就是說,語境的概念包含著兩個基本的實體:焦點事件(focal event)和包含事件的行動場域[17](P3)。 同時,語境的目的是為了理解和解釋文本,以便獲取意義,正如帕克·羅蒂斯(Parker-Rhodes)所說,語境和意義是不能分離的, 二者要么一定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部分或不同屬性,要么它們是同一事情的不同名稱[18](P35)。 因此,“語境—意義—文本” 就成為語境定義中核心的核心。 在這一種情形下,筆者給語境初步下了一個定義: 語境是圍繞在文本周圍的建構(gòu)的關聯(lián)性實在,并以文本為中心動態(tài)地連續(xù)地生成。 語境以網(wǎng)絡體系的方式與文本相關卻不是此文本的組成部分, 它普遍性地存在著并具有必然性地賦予文本某種具體特定的意義。
第一, 從質(zhì)上來講, 語境是一種關系性的實在。 語境是與意義同時存在的,但它不是一種物理存在,而是一種個體和社會共同建構(gòu)之物,語境的現(xiàn)實狀態(tài)是一種實在,而不是一種實體。 它不一定是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客觀之物, 但它實實在在地存在著,并本體性地影響著文本的意義。 語境在這方面有點類似于德斯帕納(dEspagnat)的“虛實在”(Veiled Reality)、玻姆(David Bohm)的“隱序”(implicate order)和海森堡(Heisenberg)的“潛勢”(Potentia)。 所以, 即使語境因素只是個體才具有的,不可否認,它存在著并發(fā)揮著作用,因此我們不能將其歸結(jié)為無。 就像弗雷格所說,我們混淆了實在和存在,“我把我所稱的客觀的東西與可觸摸的東西、空間的東西或現(xiàn)實的東西區(qū)別開。 地軸是客觀的,同樣太陽系的質(zhì)心也是客觀的,但是我不想把它們像地球自身那樣稱為現(xiàn)實的。 我們常常把赤道叫作一條想象的線; 但如果把它叫作一條臆想的線就錯了;它不是思維生成物,不是一種心理過程的產(chǎn)物,而僅僅是通過思維被認識到,被把握的”[19](P42)。 語境的這種實在存在狀態(tài)內(nèi)含語境建構(gòu)性。 “語境建構(gòu)論”包含著兩個層面:第一層是激進的認知語境論, 認為語境及語境要素都是通過主體內(nèi)化為一種前見或背景, 從而對對象進行理解。第二層是本體論層面的語境建構(gòu)論。按照康德的《純粹判斷力》來理解,我們并不能真正觸及物理的世界, 因為主體現(xiàn)世之初就先驗地具有了十二對認知范疇,像時間和空間范疇,因而世界任何之物從這個角度上說都被內(nèi)化了,更不用說語境。“本質(zhì)上‘語境’也是主體所構(gòu)造的,為達到人類交流的現(xiàn)實目的而自然存在的一種認知方式或認知結(jié)構(gòu)。 ”[20](P251)范戴克(Van Dijk)也認為“語境就在你頭腦里”(context is right in your mind)[21](P115)。 但是,這種激進的建構(gòu)思想將客觀世界全盤主觀化,否認了存在著任意一種自在的可以被認知的 “現(xiàn)實”。 而這種可知的現(xiàn)實是承載語境實在性的基礎。瑪麗娜(Marina)認為語境具有客觀性,“如果一個語境不是由交際者的意圖狀態(tài)來確定的, 而是由周圍世界發(fā)生事物的相關狀態(tài)來確定的(這些事物甚至也許交際者本人也沒意識到), 這樣語境在某種意義上就具有客觀性”[22]。即使如此,筆者仍然認為這種語境客觀性仍然屬于實在的范疇, 而不能歸結(jié)于絕對客觀。
同時,我們必須看到,語境的實在性絕非一個孤立的實在,它是一種關聯(lián)性的實在。 無論是語境與對象還是語境要素之間, 甚至不同層面的語境之間都是動態(tài)地關聯(lián)著的。 語境本質(zhì)上是一種實在和關系的意向性指定。 語境既可以是一種實在性的存在,也可以是一種關系性的存在。 但是,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概念, 正如 “波粒二象性”的存在狀態(tài)一樣。 語境作為一種實在一定是和對象以及語境要素以網(wǎng)絡狀態(tài)存在著的。 萊欣巴哈就說過,實體的存在是在相互關聯(lián)中表達的。
第二,從量上看,語境是以最大普遍性到最小普遍性的方式地存在著的,具有無限性。 語境的最大普遍性(maximal universality)即我們可以從本體論上將語境作為本體來認識,它是意義的“最高約定”;語境還貫穿于人類語言歷史的一切話語意義解釋行為之中; 同時語境可以作為現(xiàn)時生活世界的表層意義性表征, 它可以將社會語境、 文化語境、 科學語境……等無數(shù)大大小小的語境囊括于自身的極度抽象性之中。 最小普遍性(minimal universality)可以換種說法為語境的具體性,但這種具體性并不意味著完全的獨特性, 而是一次或者短時言語行為中的語境規(guī)則顯現(xiàn)。 從時間維度上說,語境伴隨著整個言語行為;從空間維度上講,語境可以從具體言語行為的當下情景無限擴展到整個社會文化環(huán)境。 沒有無語境或者超語境的、具有獨立意義的文本或者語言[23](P27)。 “任何人推出一個沒有意義的句子, 聽者一般都會想象出一個事實上能夠具有意義的語境來,通過將句子置入某一框架,他們自可使它顯示出意義……移植一個序列于某一改變了它的功能的語境之中。 ”[24](P106)因此,無論在最大還是最小的維度上, 不可能存在沒有語境的句子。 即使確實存在,主體也會立即為其賦予一個合適的語境。
第三,從關系上來說,語境天生具有意向性并為文本賦予意義。 也就是說,語境生成的過程伴隨著意義的生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語境始終是指向文本的,即使文本是動態(tài)地變化著的。 語境依附于文本或語言; 同時文本或語言對語境又具有協(xié)商性和適應性。 語境與文本之間的有機紐帶是意義,即文本的意義由語境決定,至少部分決定。 我們認為語境決定著意義, 但是存在著兩種反對的聲音: 一是字面意義捍衛(wèi)者認為意義與語境沒有關系。 如卡茨(Katz)在《命題的結(jié)構(gòu)和以言行事的力量》書中設想了一種情景——對匿名信中的句子的理解,這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下的情況。 在這種匿名信場景情況下,就是無語境的理想狀態(tài)[25](P15)。 二是解構(gòu)主義者認為,語境并不能決定文本的意義,因為語境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和非限制性。 因而,文本應從其自身來被理解, 而不是被置于語境之中來進行理解[26](P9)。字面意義論者試圖將語境對意義的影響控制到最小的程度,認為存在著最簡命題,而最簡命題是可以賦予語義的。 如“李白是人”這個最簡命題完全可以為語句帶來真值。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果將這個語句置于“向懵懂的小孩解釋李白”與“同少數(shù)將李白視為神的極端學者之間的論辯”兩個不同場景之下,“李白是人”這個短句的意義截然不同。 解構(gòu)主義從語境的非確定性和無限定性來消解語境對文本意義的作用, 其問題在于語境的無處不在雖說為文本意義解釋帶來許多不確定性, 但這并不成為否認語境對意義具有關鍵的賦義行動。 反過來,我們同樣不贊同極端語境決定論者的觀點:一切句子都對語境敏感[27](P6)。句子本身并不能賦予語言真值內(nèi)容, 處于語境之中的言語行為才是真值的歸屬[28](P2)。當一切意義生成都被歸結(jié)于語境之后,文本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同時, 極端語境主義者也并不能解釋為何語境性因素為句子賦予意義時卻依然受到句法的限制。
筆者認為, 字面意義派和語境決定者之間的分歧可以被統(tǒng)一到語境理論之中來, 因為當他們在討論意義是由最簡命題決定還是由語境決定時,粗暴地將句子和語境分開了。 其實就句子層面甚至更小語法層面的關系而言, 其組合關系依然可以形成語境, 只是此語境并非我們所謂的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的語境,而是文本語境。 這就能解釋為什么主體在純粹思考時可以天馬行空, 但當這些想法被客觀化為語言文字之后, 他自己對寫出的文字都會難以置信, 因為語句和篇章結(jié)構(gòu)形成的內(nèi)部語境必然束縛主體思維, 甚至引導主體思維前進。所以卡勒說:“意義是由語境決定的。因為語境包括語言規(guī)則、作者和讀者的背景,以及任何其他能想象得出的相關的東西。 ”[29](P71)這種語境觀就與我們的觀點極為接近, 涵蓋所有對意義產(chǎn)生影響的因素。
第四,與語境相對的范疇是什么? 我們可以說是“語言”,也可以說是“文本”,還可以說是“符號”、“現(xiàn)象”、“對象”等等。 比如韓彩英就將語境定義為“語言發(fā)生發(fā)展、存在與變化的條件”[30]。 也就是說,在她看來,受語境影響和決定的是“語言”。Context 被翻譯為“語境”,自然地,我們會將語境視為語言的環(huán)境。 然而,context 是由con 與text 組合形成的,text 是由texere 演變而來,指的是編織、編排,而不是指語言(language)。 也就是說語境針對的對象是“文本”更為貼切。 但是我們又不能將語言徹底地從語境的內(nèi)涵中排除出去。 “文本”和“語言”還有著復雜的關系,使得不同情況下,語境適用的對象或者是文本或者是語言。
文本和語言很容易混淆, 因為二者本身就有很多交叉混溶之處。 (1)文本和語言都是由符號和支配這些符號的關系和排列的規(guī)則組成, 語言包含這些規(guī)則,文本則不包含。 (2)語言可以離開文本而存在,事實上它也離開文本而存在[31](P78)。 文本的存在以語言的部分為前提, 即使文本成為可能的那些符號和規(guī)則。 (3)文本是作者為著某個目的組合而成,語言是形成這個文本的工具[31](P78)。 所以,文本結(jié)構(gòu)比較固定難以改變,而語言則可以根據(jù)需要而改變,雖然語言擁有的符號和規(guī)則有限,但是其組合方式可以無限, 從而創(chuàng)造出期望的文本[32](P7-8)。 文本的作者一般是少數(shù)個體,易于確證;而語言的作者一般是一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社會,難于追溯。 之所以對文本和語言進行區(qū)別,因為如果將文本與語言混同的話, 那么我們很可能像解構(gòu)主義者那樣認為文本沒有限定性和確證性,可以像語言一樣多變,甚至可以獨立于作者和讀者。
三、作為外延區(qū)隔凸顯的語境
語境的定義為語境提供了精確的內(nèi)涵, 僅從純粹內(nèi)涵角度的研究并不足以窮究語境的所有含義。 但凡一個范疇的明晰過程都是一個與其他范疇相區(qū)別的過程。 研究與語境有緊密關系又經(jīng)常發(fā)生混淆的范疇, 可以使語境的范疇輪廓更加明晰。 將語境(Context)區(qū)隔開來的這些范疇包括“共文”(co-text)、“互文”(intertext)和“生活世界”。
第一,語境與“共文”。 context 與co-text 之間相差一個字母,但內(nèi)涵卻有很大的不同。 辛克萊爾就認為“‘語境’通常比文本環(huán)境(共文)擁有更加寬泛的意義”[33](P34)。 二者的差異不僅僅局限于包含范圍的寬窄,根本性的不同在于“共文關注的是文本(text),而語境關注的是話語(discourse)”[11](P58),這正如語言學中“句子”(sentence)和“言語”(utterence)之間的關系。 斯溫伍德認為“話語是其具體的現(xiàn)存的總體性中的語言, 這種現(xiàn)存的總體性就存在于主體間有效的交往關系之中。 話語的對象并不是抽象的語言系統(tǒng), 而是一些元語言的交往實踐。 語言只存在于使用它的主體之中,因此,話語具有對話特征和社會學特征, 它蘊含著社會的歷史意義”[34](P135)。 而巴瑞認為二者之間的差異表現(xiàn)在:“共文性”(co-textuality) 是由同一個作者的具有同源性質(zhì)的一組作品形成的。 這并不是說典故或者引文,而更應該被描繪為一個情景,像葉芝的“和自我爭論”,不是在獨立的詩歌里,而是在一組不同的詩歌里。 共文意識到文本的邊界是流動的,并且文本并不隨著最后的結(jié)束而終止。 相反,“互文性”語境可以被界定為“存在于其他文本之中的文本”,或者,更嚴格地說,可以界定為“其他文本之中的一個文本的語詞”。 互文性語境更多的是指由不同作者創(chuàng)作的文本之間的相互引用。[35](P5)
第二,語境與“互文”。 首先,從克里斯蒂瓦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e)到巴爾特和德里達的解構(gòu)性延伸,互文(intertext)較之語境(context)明顯具有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特點:無中心、無等級、平面化。 互文性強調(diào)文本之間的互相吸收、轉(zhuǎn)換、改寫、引用、戲仿、合并、粘貼和擴展等,“文本是一種文本置換,是一種互文性在一個文本的空間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種陳述相互交叉, 相互中和”[36](P12)。這種文本之間的互相內(nèi)含的關系并不以某個文本為中心,而是無限開放的動態(tài)網(wǎng)絡。 在這種關聯(lián)網(wǎng)絡之中,文本之間是平等的;而語境一定是以某個對象作為中心點,進行賦義的行動。 沒有對象或者文本,語境也不存在。 互文本之間沒有主與從、根與源的關系,所有文本都處于同一平面之中;而語境相對于文本來說則是其意義的根源。 互文更像是一個平面,語境則像一個立體空間。 其次,語境相對于互文來說更具有一種實在性, 因為語境與文本是相互依存的存在。 語境無論屬于什么性質(zhì),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它處于文本的另一端;而互文強調(diào)得更多的是文本之間的關系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二者又像同一對象的不同角度,即對象和關系。 最后,二者最根本的差異還在于語境是人本主義的,而互文則是反人本主義傾向。 也就是說在互文性之中,主體的地位被取消掉了,剩下的只有文本之間的關系; 而語境之中一定要有主體的參與,無論是言說者還是聽話者,在對話中,都一直不停地建構(gòu)著主體之間的語境。 克里斯蒂瓦在提出互文性之初就指出了這一點,“任何文本的構(gòu)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 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zhuǎn)換。 互文性概念占據(jù)了互主體性概念的位置”[37](P146)。 “互文性(文本間性)排擠主體間性;互文性是來自其他文本的話語的交匯;互文性把先前的或同時代的話語轉(zhuǎn)換到交流話語中; 多聲部文本; 多種代碼處在相互否定的關系中”[38](P378)。 在互文性之中,文本的源頭是另一些時間中存在過的或者空間里正存在的與其發(fā)生作用的文本;而在語境之中,語境的對象——文本或語言是對話主體產(chǎn)生的,并且嚴格受到主體的控制。總的來說, 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是從介紹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時提出的,但走向去主體化,背離了巴赫金的本意。 從這層意義上說,語境理論更接近巴赫金的對話理論。
第三,語境與“生活世界”。 迪萊認為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與語境的某些解釋更為接近[5](P20)。 國內(nèi)學者韓冰和婁奇更為直接地說“語境就是人的生活世界”[39]。 胡塞爾、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哈貝馬斯都提出過生活世界的問題。 總的來說,生活世界是個人直接的環(huán)境,日常生活和個人經(jīng)驗領域的世界。 生活世界是交際的語境,交際反過來創(chuàng)作新語境或者重新界定生活世界。 這樣看來語境與生活世界極為相近, 它們都為意義提供了存在的場域,為主體的交往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是二者之間有著諸多不同:首先,生活世界是一個先在的世界,“生活世界永遠是事先給予的,永遠事先存在的世界”[40](P1087-1088)。 而語境不是預先存在的, 而是在交際過程中由主體動態(tài)地建構(gòu)起來的,并隨著時間、空間和對象的轉(zhuǎn)移而發(fā)生變化。其次,生活世界帶有一種直覺性、前科學性、直觀性;生活世界不能被“對象化”,不能將其作為科研對象來進行思考。 “生活世界總是作為不成問題的、非對象化的和前理論的整體,作為每天想當然的領域和常識的領域而讓我們大家直覺地感知到。 ”[41](P37)語境中世界是作為被意識到的要素,而被納入文本的闡釋之中的。 再次,生活世界可以作為終極語境或者理想語境存在, 但語境這個概念本身就帶有具體性和當下性, 如果有終極語境的話,也只能是實驗室中抽象出來的理論之物。 生活世界帶有一種總體性,它包羅整個原初世界;而語境從抽象層面上也帶有總體性, 但它更多意義上是針對具體文本而言的具有邊界的 “小語境”,因此帶有個體性和具體性。 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作為語境的底層, 托顯著情景和語境,“生活世界的背景知識具有不同的表現(xiàn)條件, 不能通過意向而表現(xiàn)出來;它是一種深層的非主題知識,是一直都處于表層的視界知識和語境知識的基礎”[41](P77)。最后,生活世界是作為其自身而存在,它并沒有一種目的的意向性,相反是“每一種目的都是以它為前提; 即使是在科學的真理中認識這樣一種普遍的目的, 也是以它為前提, 并且已經(jīng)是以它為前提;而且在科學工作的進展當中,總是重新以它為前提,作為一個按其自己的方式存在著的,而且是剛好存在著的世界”[42](P558)。 而語境以文本為中心,具有一種意向性。 語境的存在一定是以文本為出發(fā)點,同時也是以文本為最終的歸屬。
四、余 論
從瀝青語境的純粹性內(nèi)涵和外延性區(qū)隔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語境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思考問題和認知對象的關系模式, 具有一種本體論屬性[43],因而必不可少帶有絕對性、宏大性、體系性和抽象性。 但是,語境同時又具有當下性、時代性和地域性, 并且語境的具體性總是在理論建構(gòu)上起著反噬作用。 為什么語境理論會產(chǎn)生這種自我矛盾呢? 伽達默爾說過,雖然任何話語的存在其意義都具有語境性, 但是話語對語境的依賴本身卻不是語境性的[44](P90)。 語境作為一種理論框架與沒有固定內(nèi)容的代詞“這”或“那”完全不同:代詞可以作為空形式被植入任何內(nèi)容, 而話語卻不能以純邏輯結(jié)構(gòu)形式而存在, 因為話語的誕生就是在語境之下的。 因此,語境理論之中所具有的一種非語境性支撐著自我理論的建構(gòu), 否則語境就會陷入一種語境性和普遍性的理論悖論或者自反性之中。 總之,對語境本質(zhì)的批判性考察所得出的抽象性理論并不會與其自身的具體性屬性產(chǎn)生沖突,相反可以將語境的理論基石建立得更牢固。
[1] 蘇珊·朗格. 藝術問題[M].滕守堯,朱疆源,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2] Lakatos,I. Proofs and Refutations: 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3] Ben-Ami Scharfstein. The Dilemma of Context[M].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9.
[4]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1978.
[5] Roy Dilley. The Problem of Context[ M ].New York:Berghahn Books,1999.
[6] Stephan Sigg. Development of a Novel Context Prediction Algorithm and Analysis of Context Prediction Schemes[M].Kassel: Kassel University Press,2008.
[7] Hurford,J.R..and Heasley ,B. Semantics: A Course Book[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8] Joy Webster Barbre,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Interpret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Theory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
[9] Lyons,J.. Semantics[ M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10] Sperber,D.and D.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1995.
[11] H.G.Widdowson. Text,Context, Pretext: Critical Issues in Discourse Analysis[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12] Allan,K. Linguistic Meaning[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6.
[13] River W. Concepts, Context and Meaning: Learning to Learn Vocabulary[M]. Oxford: Blackwell, 1992.
[14] Brockway.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B.V,1979.
[15] Graham McGregor and R.S. White. Reception&Respons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0.
[16] Anita Fetzer, Etsuko Oishi. Context and Contexts: Parts Meet Whole? [M].John Birmingham Publishing Company,2011.
[17] Alessandro Duranti, Charles Goodwin.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8] Parker-Rhodes,A.F. . Inferential Semantics[M].Hassocks and Sussex: Harvester Press,1978.
[19] Michael Dummett. Fre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Evanston, San Francisco, London: Harper&Row, Publishers,1993.
[20] 殷杰,郭貴春.哲學對話的新平臺[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21] 熊學亮.認知語用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22] Marina,Sbisa. Speech Acts in Context[ J ]. Language&Communication,2002,(10).
[23] Leplin,J. A Novel Defense of Scientific Re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4] 喬納森·卡勒. 論解構(gòu)——結(jié)構(gòu)主義之后的理論與批評[M].陸揚,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5] Jerrold J. Katz. Propositional Structure and Illocutionary Force: A Study of the Contribution of Sentence Meaning to Speech Acts[M]. London: Harvester,1980.
[26] Jacoues Derrida. Limitied Inc[M].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7.
[27] Cappelen,H.&E.Lepore.Insensitive Semantics[ M ].Blackwell: Oxford,2005.
[28] Fran?ois Récanati. Literal Meaning[ M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9] 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M].李平,譯.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30] 韓彩英.語境本質(zhì)論[ J].自然辯證法通訊,2004,(5).
[31] Paul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ssays in Hermeneutics[M]. London: Continuum,2004.
[32] Noam Chomsky.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s Theory[M].The Hague: Mouton,1964.
[33] Sinclair,J.M. Corpus Evidence in Language Description[M].London: Longman,1997.
[34] Swingewood,A.. Sociological Poetics and Aesthetic Theory[M]. London: Macmillan,1986.
[35] Peter Barry. Literature in Contexts [ M ]. Manchester&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
[36] Julia Kristeva. Le Texte du roman —— approche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M]. La Haye:Mouton,1970.
[37] Julia Kristeva. Bakthine,le mot,lle dialogue et le roman,Sèméi?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M].Paris:Seuil,1969.
[38] Julia Kristeva. Sèméi?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M]. Paris: Seuil,1969.
[39] 韓冰,婁奇. 語境與生活世界: 語用學發(fā)展新探[ J].外語學刊,2011,(1).
[40] 胡塞爾. 胡塞爾選集[C].上海:三聯(lián)書店, 1997.
[41] 哈貝馬斯. 后形而上學思想[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42] 胡塞爾. 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論的現(xiàn)象學[M].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43] 徐杰.哲學中的“語境”——語境發(fā)展的三條路徑及層面性分析[ J].東北大學學報,2011,(6).
[44]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哲學解釋學[M].夏鎮(zhèn)平,宋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