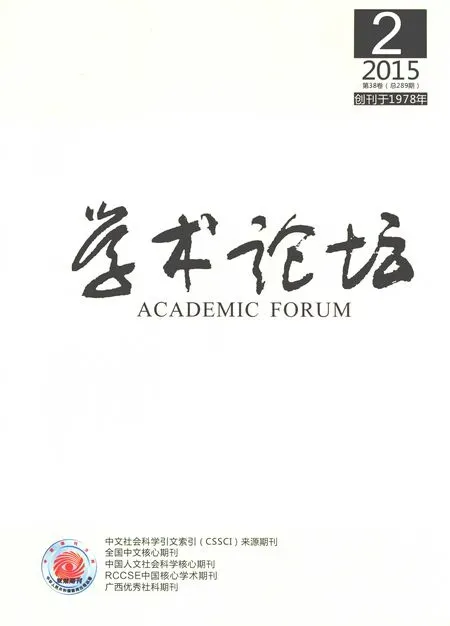符號(hào)、符號(hào)暴力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quán)的重構(gòu)
黎海燕,張忠江
一、符號(hào)與教育
(一)人的符號(hào)化。 人的本質(zhì)是什么? 這歷來是哲學(xué)家們關(guān)注的重要話題。綜觀數(shù)千年關(guān)于人的問題的各種哲學(xué)理論發(fā)現(xiàn),要想給人下一個(gè)完美的定義是非常困難的, 在科學(xué)技術(shù)水平日新月異的當(dāng)代,人的問題不但沒有取得明確的定義,相反卻更加處于深刻的危機(jī)之中。 在德國哲學(xué)家卡西爾看來,以往關(guān)于人的定義多從“人與物質(zhì)世界的關(guān)系”出發(fā),以“構(gòu)成人的形而上學(xué)本質(zhì)的內(nèi)在原則”或“靠經(jīng)驗(yàn)的觀察來確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對人加以定義, 這些關(guān)于人的定義多是一種功能性的定義,而不是一種實(shí)體性的定義。他進(jìn)而指出,人的與眾不同的突出特征在于“人的勞作”,勞動(dòng)——這種特殊的人類活動(dòng)規(guī)定了人性的圓周, 由此將語言、神話、宗教、藝術(shù)、科學(xué)、歷史等都劃入人性圓周之內(nèi),成為其圓周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一種“人的哲學(xué)”一定是這樣一種哲學(xué):“它能使我們洞見這些人類活動(dòng)各自的基本結(jié)構(gòu),同時(shí)又能使我們把這些活動(dòng)理解為一個(gè)有機(jī)整體。 ”[1](P87)由此,他從人的功能性、創(chuàng)造性出發(fā),把人定義為“符號(hào)的動(dòng)物”。
作為人類生命存在形式, 符號(hào)在主客體之間營造了一個(gè)屬人的文化意義世界, 架起人與文化之間的橋梁。 也就是說,人創(chuàng)造各種符號(hào)形式的活動(dòng), 將活動(dòng)主體—人與活動(dòng)對象—文化三者連接起來,而諸如神話、宗教、語言、藝術(shù)、科學(xué)等各種符號(hào)形式,則反映了人與文化關(guān)系的不同階段。 總之,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不僅限于物質(zhì)交換的關(guān)系,還是一種符號(hào)化的關(guān)系。 無論人以哲學(xué)的、宗教的抑或是科學(xué)的等不同方式認(rèn)識(shí)世界, 人都有一種世界圖景,且這種世界圖景作為一種建構(gòu),既適用于生物知識(shí),也適用于人類的意識(shí)過程。 其中,這個(gè)世界圖景就是人給自然建構(gòu)的網(wǎng)絡(luò), 自然也因?yàn)檫@個(gè)網(wǎng)絡(luò)而成為世界,這個(gè)網(wǎng)絡(luò)就是符號(hào)的網(wǎng)絡(luò),人通過符號(hào)與世界打交道。 從這個(gè)意義上說,人類總是通過符號(hào)感知周圍的世界, 而不是直接認(rèn)識(shí)世界[2]。 因此,人的生活世界不再是單純的物理宇宙,而是一個(gè)豐富的符號(hào)宇宙,語言、神話、藝術(shù)和宗教等都是這個(gè)符號(hào)宇宙的組成部分, 它們構(gòu)成人類符號(hào)世界的不同絲線,是人類經(jīng)驗(yàn)交織網(wǎng),且人類在思想和經(jīng)驗(yàn)方面所取得的每一點(diǎn)進(jìn)步都使人類的符號(hào)之網(wǎng)更加精致、更加牢固。 因此,“人的符號(hào)活動(dòng)能力進(jìn)展多少, 物理世界似乎就相應(yīng)地退卻多少。 在某種意義上說,人是在不斷地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yīng)付事物本身”[3](P33)。 人類被包圍在各種符號(hào)體系之中, 離開符號(hào),“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rèn)識(shí)任何東西”[3](P33)。
(二)教育的符號(hào)化。 符號(hào)化的思維和行為是人類在社會(huì)化過程中慢慢習(xí)得的,“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3](P34-35),其中,最專業(yè)、最系統(tǒng)的符號(hào)化思維和行為來自學(xué)校教育, 教育被深深打上了符號(hào)的痕跡。(1)交往過程的符號(hào)化。“符號(hào)的意義就是符號(hào)的使用, 符號(hào)除了使用于表達(dá)意義別無它用。 ”[4](P176)使用符號(hào)最典型的方式是交往,符號(hào)在交往中產(chǎn)生,交往在符號(hào)中實(shí)現(xiàn)。 哈貝馬斯在其交往行為理論研究中指出, 人的符號(hào)化經(jīng)過水平Ⅰ、水平Ⅱ和水平Ⅲ三個(gè)遞升的階段,隨著個(gè)體由自然人向社會(huì)人轉(zhuǎn)變的完成, 符號(hào)化交往便得以實(shí)現(xiàn),其中,學(xué)校是實(shí)現(xiàn)這一轉(zhuǎn)變的最重要場所, 學(xué)校教育必須通過符號(hào)化途徑才能擔(dān)負(fù)培養(yǎng)學(xué)生交往能力的重任。 首先,因?yàn)槿祟惖慕煌鶎?shí)質(zhì)上是一種符號(hào)的交往。 正如哈貝馬斯所闡釋的,交往活動(dòng)就是一種“以符號(hào)為媒介的相互作 用”[5](P4)。 人類交往最重要的符號(hào)媒介自然是語言,此外,服飾、姿勢、行為等其他符號(hào),都傳達(dá)著與語言符號(hào)相近或相反的意思, 交往的符號(hào)化過程是多種符號(hào)媒介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這一點(diǎn)是教育工作者在施教過程中必須注意的。 其次,由于交往是以符號(hào)為媒介的, 所以在交往正式開始之前可以加以預(yù)想和設(shè)計(jì), 在交往過程之中可以進(jìn)行控制和調(diào)整。 學(xué)校教育同樣如此,一方面可以讓學(xué)生在交往(如討論、辯論等)開始之前進(jìn)行模擬或預(yù)言, 進(jìn)而選擇最佳交往方式, 從而提高教學(xué)效果;同時(shí),在具體的交往過程中又可以通過符號(hào)形成的一些規(guī)則使師生交往或?qū)W生之間的交往符合約定俗成的原則, 最大限度地避免交往過程中的沖突。(2)思維能力的符號(hào)化。在卡西爾看來,人類文化是人運(yùn)用符號(hào)而加以創(chuàng)造的結(jié)果, 從這個(gè)意義來說, 符號(hào)及其運(yùn)用為人類帶來一個(gè)五彩繽紛的文化世界, 人類也正是由于符號(hào)世界才創(chuàng)造出燦爛的人類文化, 創(chuàng)造出人類所特有的精神文化世界,從而超越“動(dòng)物也生存于其中的物理世界”,“達(dá)到人的自由和理想的境界”[6]。 通過成千上萬年的積累,人類運(yùn)用符號(hào)創(chuàng)造了豐富燦爛的文化,學(xué)校教育的重要職責(zé)便是傳承人類文化, 將人類文化財(cái)富傳授給學(xué)生,因此,培養(yǎng)學(xué)生的符號(hào)思維便是教育之首要任務(wù)。 首先,學(xué)校教育培養(yǎng)學(xué)生基本的符號(hào)思維。 “人類的知識(shí)按其本性而言就是符號(hào)化的知識(shí)”[3](P72), 不同的文化知識(shí)均以符號(hào)形式呈現(xiàn),因此,學(xué)校教育的基本任務(wù)便是教會(huì)學(xué)生掌握不同的符號(hào)樣式并按這些符號(hào)樣式去思維, 如用數(shù)學(xué)符號(hào)去推演、計(jì)算,用色彩、線條符號(hào)去繪畫等。 其次,學(xué)校教育培養(yǎng)學(xué)生創(chuàng)新的符號(hào)思維。 符號(hào)使人類得以超越有限的物理世界而創(chuàng)造一個(gè)觀念的世界,這個(gè)世界可以是“真實(shí)的”、“存在的”或“具體的”,也可以是“想象出來的”、“不存在的”或“抽象的”[7], 由此人類獲得認(rèn)識(shí)上的無限可能性,符號(hào)的出現(xiàn)便是人類創(chuàng)造性的表現(xiàn)。 因此,學(xué)校教育不僅應(yīng)注重學(xué)生對抽象的、實(shí)用的知識(shí)的學(xué)習(xí),更應(yīng)注重對學(xué)生想象力的培養(yǎng), 培養(yǎng)學(xué)生創(chuàng)新的符號(hào)思維, 使學(xué)生借助符號(hào)達(dá)到精神和思想上最大限度的自由。
(三)教育的合理演變:從文化傳遞到符號(hào)暴力。 在德國著名教育學(xué)家斯普朗格看來,教育是一種文化活動(dòng), 它指向不斷發(fā)展的個(gè)體個(gè)性生命的完成,其最終目的在于“把既有的客觀精神(文化)的真正富有價(jià)值的內(nèi)涵分娩于主體之中”[8](P110)。 教育是一種文化傳承活動(dòng), 人類文明史上積累的價(jià)值觀念、 行為模式等正是通過教育才得以代代相傳。 此外, 教育還為文化的發(fā)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社會(huì)個(gè)體在學(xué)習(xí)吸收原有文化的基礎(chǔ)上積極發(fā)揮想象力,創(chuàng)造出更加豐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從而使人類文化不斷繁榮、不斷向前發(fā)展。
在社會(huì)學(xué)家、語言學(xué)家布迪厄看來,文化資本是人類社會(huì)三種最基本的資本類型之一(經(jīng)濟(jì)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huì)資本),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動(dòng)而得以傳遞的文化物品。 教育行動(dòng)是一種文化再生產(chǎn),是使其傳遞的文化專斷得以再生產(chǎn),通過文化的再生產(chǎn)實(shí)現(xiàn)權(quán)力關(guān)系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再生產(chǎn)。 而傳統(tǒng)的教育理論認(rèn)為教育系統(tǒng)僅僅是一種文化傳承機(jī)制,其功能在于“保證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文化一代一代傳下去”[9], 將教育的文化再生產(chǎn)從社會(huì)再生產(chǎn)功能中分離出去, 忽略了符號(hào)關(guān)系在權(quán)力關(guān)系再生產(chǎn)中的作用。 符號(hào)暴力“就是這樣一種權(quán)力,即在一特定的‘民族’內(nèi)(也就是在一定的領(lǐng)土疆界中)確立和強(qiáng)加一套無人能夠幸免的強(qiáng)烈性規(guī)范, 并將其視之為普遍一致和普遍適用的”[10](P153)。事實(shí)上,“所有的教育行動(dòng)客觀上都是一種符號(hào)暴力”,具有雙重專斷性,“是由一種專斷權(quán)力所強(qiáng)加的一種文化專斷”[11](P13)。 首先,從形式上來看,相對于以軍事、經(jīng)濟(jì)等強(qiáng)制手段為主的赤裸裸的強(qiáng)硬暴力而言,教育是一種軟性暴力,具有一定的隱匿性。 教育體制是文化資本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社會(huì)等級結(jié)構(gòu)的制度基礎(chǔ), 因?yàn)閺?qiáng)勢社會(huì)地位的人在教育場域和權(quán)力場域中可以利用其文化資源,尤其是知識(shí)分類、招生過程等維護(hù)其強(qiáng)勢社會(huì)地位。 教育的功能就在于再生產(chǎn)這種統(tǒng)治階級的文化, 通過這種運(yùn)作掩蓋森嚴(yán)的社會(huì)等級制度并維護(hù)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 其次,從性質(zhì)上來說,教育通過構(gòu)建現(xiàn)實(shí)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而建立符號(hào)秩序, 以此向人們昭示各類事物的法定意義。 通過學(xué)業(yè)資格,教育制度運(yùn)用具體的教學(xué)實(shí)踐和各類價(jià)值無涉的神話, 為統(tǒng)治階級提供一個(gè)特權(quán)階級來分配及確定社會(huì)特權(quán), 社會(huì)成員在接受教育的公正和民主神話的過程中, 教育制度的正直形象也被成功地植入人們頭腦之中。 就其本質(zhì)而言,教育一開始就是一種權(quán)力再生產(chǎn)過程, 著力于分配特定符號(hào)資本,學(xué)校也因此充當(dāng)社會(huì)秩序的捍衛(wèi)者,鞏固社會(huì)中文化資本的原有分配, 而并非對社會(huì)中不平等的文化資本進(jìn)行重新分配。
二、“符號(hào)暴力”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雙重屈從
語言是一種在各方面都符合符號(hào)本質(zhì)規(guī)定的“純粹符號(hào)”,“是人類發(fā)明的最驚人的符號(hào)體系”[12](P40),是最具典型意義的符號(hào)體系,人的符號(hào)化特性主要體現(xiàn)在其語言之中,“語言的問題主要是符號(hào)學(xué)的問題”[13](P39)。 布迪厄認(rèn)為,語言關(guān)系實(shí)質(zhì)上體現(xiàn)了一種符號(hào)權(quán)力關(guān)系, 言說者與他所屬的各集團(tuán)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便通過這種語言關(guān)系得以體現(xiàn)。即使是最簡單的語言交流也不可能是純粹的溝通行為, 總是置身于一定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網(wǎng)之中,體現(xiàn)了擁有特定社會(huì)權(quán)威的言說者與認(rèn)可這一權(quán)威的聽眾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 從這個(gè)意義來說,語言是社會(huì)性的而非中性的, 其中蘊(yùn)含了各種權(quán)力與權(quán)威,言說時(shí)應(yīng)遵循特定的不成文的言語規(guī)則,即維特根斯坦所謂的語言游戲, 且這種規(guī)則總是明確或不明確地表現(xiàn)為游戲者之間的一種默契[14](P18)。因此,語言不僅是一種溝通工具,還體現(xiàn)一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充當(dāng)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工具和媒介,它也能構(gòu)成一種“溫和的暴力”。福柯也認(rèn)為“話語是一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它意味著誰有發(fā)言權(quán),誰無發(fā)言權(quán)”[15](P62-65),這一具有無形威懾力的“真實(shí)的權(quán)力”被福柯稱之為“話語權(quán)”,蘊(yùn)含于制度、知識(shí)和理性之中。
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世界, 主要有決策者的權(quán)勢話語、 專家的理性話語和教師的個(gè)人話語和受教育者的話語等四類話語系統(tǒng)。 其中,決策者的權(quán)勢話語由官方的行政管理層發(fā)出, 傳達(dá)社會(huì)和國家層面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與規(guī)定; 專家的理性話語主要由研究工作者掌控,傳達(dá)一種“邏輯的權(quán)力”,主要以科學(xué)的范式和實(shí)證的方法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與規(guī)定等加以解釋和說明; 教師的個(gè)人話語是教師基于個(gè)人的教學(xué)實(shí)踐詮釋個(gè)體思想政治教育生活經(jīng)驗(yàn),更多地表現(xiàn)為一種“隱喻的權(quán)力”;受教育者的話語是接受教育的主體——學(xué)生所發(fā)出的個(gè)人話語, 表達(dá)受教育者個(gè)體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經(jīng)驗(yàn)。
從社會(huì)學(xué)角度來說, 話語表達(dá)是一種社會(huì)行為,受局部情景各因素所確定的“客觀結(jié)構(gòu)”之規(guī)約,“社會(huì)行動(dòng)的客觀結(jié)構(gòu)是情景確定的”[16](P56-57),情景中各因素構(gòu)成的客觀結(jié)構(gòu)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包括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言說及其言說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所構(gòu)成的客觀結(jié)構(gòu),對主體(包括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形成一種“情景逼迫”和“柔性的暴力”,由此導(dǎo)致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喪失話語權(quán)。 福柯認(rèn)為,一種技術(shù)策略建構(gòu)一種角色之間的關(guān)系, 當(dāng)一定技術(shù)策略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被采取時(shí), 就會(huì)顯現(xiàn)出隱藏于其中的“柔性的暴力”,同時(shí)構(gòu)建一種屈從性關(guān)系。 因此,從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過程中的符號(hào)暴力所帶來的屈從性角色關(guān)系角度審視,我們發(fā)現(xiàn)其中既有受教育者面臨的各種話語屈從,也包括教育者自身面臨的話語屈從。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教育者)的話語屈從。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場域, 權(quán)勢話語通過自上而下的層階性管理模式運(yùn)行, 即話語權(quán)源自決策者的權(quán)勢話語和專家的理性話語, 思想政治教育者無權(quán)參與教育決策和管理, 僅僅作為政策的執(zhí)行者、秩序的維護(hù)者、課程的實(shí)施者及方法的消費(fèi)者而居于整個(g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quán)力塔的最底層,其話語屈從于決策者的權(quán)勢話語和專家的理性話語。 (1)“國家的在場”導(dǎo)致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教育者)的話語屈從。 在《意識(shí)形態(tài)與意識(shí)形態(tài)國家機(jī)器》一書中,阿爾都塞認(rèn)為教育屬于意識(shí)形態(tài)國家機(jī)器并居于核心地位, 菲利普·韋克斯勒也認(rèn)為學(xué)校是“‘加工知識(shí)’的機(jī)構(gòu)”,是“服務(wù)意識(shí)形 態(tài) 功 能 的 機(jī) 構(gòu)”[17](P12),因 此,教育 系 統(tǒng) 中所涉及的理論、 政策及實(shí)踐等問題在本質(zhì)上屬于倫理性、政治性的問題,而不是技術(shù)性問題[17](P15)。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國家和社會(huì)要求, 傳播統(tǒng)治階級意識(shí)形態(tài)、主流價(jià)值觀念、政治準(zhǔn)則、倫理道德規(guī)范等的實(shí)踐性教育活動(dòng), 思想政治教育者是國家和社會(huì)在思想教育領(lǐng)域的代言人。 這種內(nèi)在的身份規(guī)定性,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必須嚴(yán)格按照國家和社會(huì)的要求來言說規(guī)定好了的話語內(nèi)容。 因此,國家和統(tǒng)治階級意識(shí)形態(tài)的在場成為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面臨的重要情景之一, 自然而然產(chǎn)生一種逼迫的力量,即“柔性的暴力”。 在這種符號(hào)暴力的情景逼迫之下, 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為了規(guī)避各種話語風(fēng)險(xiǎn),以“客體”的身份進(jìn)入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場,充當(dāng)權(quán)勢話語的傳聲筒,從而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一種屈從性關(guān)系得以建構(gòu)。 在這種屈從性關(guān)系中,由于缺乏應(yīng)有的參與權(quán),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矮化成“雇工”,從事非創(chuàng)造性勞動(dòng);僵化成“傳聲筒”,灌輸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shí)形態(tài);愚化成“思想附庸”,使其自身靈魂受到貶損;墮化成“文化保安”,維護(hù)錯(cuò)誤觀點(diǎn)[18]。 這種類似“雇工”、“傳聲筒”、“思想附庸”和“文化保安” 思想政治教育者沒有理解、質(zhì)疑和批判,他們欲言又止,成為一種隨聲附和的“單向度的人”,思想政治教育活動(dòng)由此演變?yōu)橐环N單面化的教育, 其話語權(quán)的流失自然在所難免。 (2)“專家的在場”導(dǎo)致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教育者)的話語屈從。 長期以來,研究被視為專家學(xué)者特定的工作和專有領(lǐng)域, 研究者們在其研究“自留地”里提出教育問題并開展研究,進(jìn)而創(chuàng)造各種話語,再向普通教師宣傳推廣,形成了“研究-開發(fā)-傳播-運(yùn)用”的話語生產(chǎn)模式[19]。 這種理性話語生產(chǎn)系統(tǒng)導(dǎo)致教育話語場域的層級化, 一種類似社會(huì)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控制與被控制的關(guān)系在從事理論研究的專家學(xué)者與從事實(shí)踐教學(xué)的教師之間形成。 “如果研究者試圖嚴(yán)格地控制教師”,強(qiáng)制地劃定其職責(zé)范圍,將極有可能在“一開始就把教師拒于理論思考的大門之外”[20](P554)。 由此,理應(yīng)是教育世界生活者和建構(gòu)者的教師,卻成為教育研究的旁觀者,個(gè)人話語權(quán)再次被剝奪。 對此,Houser 和Cather 明確指出,長期以來,研究者和教師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教師往往被視為“科學(xué)控制的一般對象”,這種身份地位的差別導(dǎo)致教育體系的層級化現(xiàn)象。在這種層級化教育體系中,教師處于最底層,沒有任何權(quán)力,只能被動(dòng)地聽從諸如管理者、課程論專家、教材編撰者等各路研究者的指導(dǎo),“自身的形象毫無專業(yè)意義”[20](P554)。
具體就思想政治教育領(lǐng)域而言, 專家學(xué)者們擁有強(qiáng)大的話語權(quán),他們基于“理性至上”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其在社會(huì)文化資源分配中(如科研院所、大學(xué)講壇、出版社等)的優(yōu)勢地位,不斷制造各種話語, 使得研究領(lǐng)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各種理性話語喧嘩的地方。 一般而言,理性話語主要通過有形和無形兩種方式實(shí)現(xiàn)其話語權(quán)。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領(lǐng)域的各類專家學(xué)者們利用其有形的且社會(huì)公認(rèn)的特殊身份,如研究者、教師培訓(xùn)者、書籍報(bào)刊雜志審稿人、主編等,擁有對社會(huì)上各種話語生殺予奪的大權(quán), 他人的話語必須獲得其認(rèn)可方能上市流通;另一方面,由于崇尚理性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傳統(tǒng)和專家學(xué)者們在現(xiàn)實(shí)文化資源分配中的特殊地位, 他們的話語毫無爭議地成為時(shí)代和社會(huì)的主流話語。 面對“專家的在場”這一重要情景,思想政治教育的實(shí)踐者——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個(gè)人話語難以面世,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xué)必須在各類專家學(xué)者們設(shè)計(jì)好的規(guī)定性動(dòng)作中展開。面對此情此景, 思想政治教育者為了規(guī)避各種話語風(fēng)險(xiǎn), 他們采取一種放棄自身話語權(quán)的技術(shù)策略,成為理性話語的盲從者,進(jìn)而一種對專家學(xué)者的屈從性關(guān)系被建構(gòu)起來。 在這種屈從性關(guān)系的支配下,思想政治教育者由于沒有參與研究過程,他們往往沒有自主的思考,“只是在別人通過他們并不了解的實(shí)驗(yàn)向他們提供某種方法的時(shí)候向人道謝”[21]。 在這種不斷重復(fù)與自身真實(shí)世界格格不入的理性話語的過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者們迷失在專家學(xué)者們或曰研究者們所追逐的概念游戲之中,逐漸成為被研究、被規(guī)定的對象,日益成為自身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他者”,其話語權(quán)的消解也在所難免。
(二)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受教育者)的話語屈從。 (1)傳統(tǒng)文化的規(guī)訓(xùn)導(dǎo)致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受教育者)的話語屈從。 眾所周知,“天地君親師”是中華大地廣泛供奉和祭祀的牌位, 是傳統(tǒng)文化中重要的精神信仰和符號(hào)象征, 作為儒家倫理道德秩序世俗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價(jià)值依據(jù), 安頓著炎黃子孫的世俗生活。 數(shù)千年來,“師”被冠以“圣賢”的稱謂,作為“神圣”、“崇高”、“德性”的代言人,承載著“傳道、授業(yè)、解惑”的重大社會(huì)責(zé)任。“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中華民族形成了尊師重教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 教師形象故而也被嵌入到崇高美學(xué)的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之中。 受傳統(tǒng)文化的這種熏陶,國人眼中的教師首先不是一種謀生的職業(yè),而是“道”的人格化,是終極價(jià)值(大道)的代言人、闡釋者和傳播者,“師”因“道”而尊,“師”被神圣化為理想道德人格的象征。 如前所述,所有的教育行動(dòng)客觀上都是一種符號(hào)暴力,是一種專斷權(quán)力所強(qiáng)加的一種文化專斷,這種文化專斷是一種藏而不露的隱性力量,通過布迪厄所謂的文化資本的生產(chǎn)與再生產(chǎn),有效的將支配與被支配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轉(zhuǎn)換為社會(huì)成員心甘情愿接受的自然現(xiàn)狀”[22](P138),并且現(xiàn)代社會(huì)“更仰賴于文化的符號(hào)權(quán)力這種軟性暴力來維護(hù)統(tǒng)治和支配的合法性”[23](P190)。傳統(tǒng)文化中對教師的無限尊崇自然衍生出學(xué)生對老師的無條件服從, 而將教師推向一種專斷和話語霸權(quán)的地位, 教師擁有對學(xué)生的絕對的道德權(quán)威,即所謂的“師道尊嚴(yán)”。 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淀,傳統(tǒng)文化中對“師者”的定位和評價(jià)已經(jīng)內(nèi)化于人們的民族心理和情感之中, 其影響持久且深遠(yuǎn)。 傳統(tǒng)文化的這種規(guī)訓(xùn)成為受教育者必須面臨的重要情景, 不可避免地對其帶來一種“符號(hào)暴力”,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受教育者同樣受其規(guī)訓(xùn)。 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受“尊師重教”、“師道尊嚴(yán)”等傳統(tǒng)文化的規(guī)訓(xùn),受教育者為了避免遭受傳統(tǒng)文化“制裁”,選擇采取放棄自身應(yīng)然話語權(quán)的技術(shù)策略,“欲說還‘羞’”,長此以往, 一種穩(wěn)定的持久的屈從性關(guān)系被建構(gòu)起來。(2)教育系統(tǒng)的規(guī)制導(dǎo)致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受教育者)的話語屈從。 作為正式組織的學(xué)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著天衣無縫的規(guī)制系統(tǒng), 福柯甚至將學(xué)校喻為監(jiān)獄, 認(rèn)為學(xué)校是一個(gè)重要的規(guī)訓(xùn)場所。 一般而言,教育系統(tǒng)主要通過顯、隱兩種方式對受教育者進(jìn)行規(guī)訓(xùn),即一方面通過文本、制度等顯性方式規(guī)制受教育者的話語權(quán), 如學(xué)校的各類規(guī)章制度、章程等文本規(guī)范中都有諸如“必須……”、“不能……”、“不得以任何理由……否則……”等字眼,無條件要求受教育者對教育系統(tǒng)話語權(quán)的服從, 實(shí)際上就是對受教育者話語權(quán)的一種剝奪。 另一方面,教育系統(tǒng)中各類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還通過隱性的資源控制來對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受教育者)進(jìn)行規(guī)制。 當(dāng)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規(guī)制主要從行政體系和教學(xué)體系兩方面進(jìn)行,在行政體系方面,從學(xué)校黨委、學(xué)生工作部門(如學(xué)生處、學(xué)工部等)再到各二級單位部門學(xué)生工作的分管領(lǐng)導(dǎo)(如副書記等)最后到輔導(dǎo)員、班主任等,都對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受教育者)進(jìn)行規(guī)制和教育;同時(shí),在教學(xué)體系方面,各級各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通過課堂教學(xué)對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受教育者)進(jìn)行規(guī)制和教育。 如果受教育者對行政體系話語表現(xiàn)出質(zhì)疑或者反對, 教育者則可以利用手中行政資源使受教育者無緣各類評先評優(yōu)或獎(jiǎng)勵(lì)、榮譽(yù)等;如果受教育者在課堂上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言說或話語嗤之以鼻, 則可能招致嘲諷、批評、恐嚇甚至直接影響期末考評成績。 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這些來自教育系統(tǒng)的顯性和隱性規(guī)制體系, 是受教育者不得不面對的重要情景,受這些情景的逼迫,學(xué)生被迫養(yǎng)成“識(shí)時(shí)務(wù)”的“俊杰”思維,采取放棄自身應(yīng)然話語的技術(shù)策略,從而導(dǎo)致一種屈從性關(guān)系的被建構(gòu)。 在這種屈從性關(guān)系的支配下,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受教育者)欲說不能,依附于教育者的話語控制之中。
三、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屈從性關(guān)系的解構(gòu)與話語權(quán)的重構(gòu)
(一)增強(qiáng)主體意識(shí),主動(dòng)爭取話語權(quán)。 由于主體與客體的雙重失語, 導(dǎo)致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缺乏來自實(shí)踐的生動(dòng)鮮活的真實(shí)聲音, 使得整個(gè)教育過程刻板化、機(jī)械化、枯燥化。 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理想效果, 需要整個(gè)教育場域的所有在場者(既包括教育者,也包括受教育者)都能放聲陳說,他們自主的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并且這種聲音也是最真實(shí)的聲音,因?yàn)椤八从诓煌那榫常碜钫鎸?shí)的問題與需要,是最需要被傾聽的聲音”[24]。在這種對話與理解關(guān)系中, 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雙方都被當(dāng)作“與自己交談的‘你’”,“雙方親臨現(xiàn)場,在精神深處被卷入了”[25](P138),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在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智慧等方面獲得共享,達(dá)成共識(shí),理想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得以實(shí)現(xiàn)。
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 唯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具有強(qiáng)烈的主體意識(shí), 方能自覺自主地發(fā)出最真實(shí)的聲音,上述教育場景也才可能成為現(xiàn)實(shí)。因此, 首先必須增強(qiáng)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體意識(shí), 使其意識(shí)到自身在整個(g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場域中獨(dú)一無二的地位與作用, 能主動(dòng)參與建構(gòu)的過程,積極主動(dòng)爭取話語權(quán)。 思想政治教育者應(yīng)增強(qiáng)主體意識(shí)。 在實(shí)際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往往居于主導(dǎo)地位,是整個(gè)教育過程的引導(dǎo)者,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者更應(yīng)充分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dòng)性, 在為學(xué)生提供指導(dǎo)的同時(shí)積極建構(gòu)自己的生命精神家園。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也應(yīng)增強(qiáng)主體意識(shí)。 無論是教育者還是受教育者,都應(yīng)反思傳統(tǒng)的依附于權(quán)力和權(quán)威的話語定位,使其因自己的思考和言說而存在, 以自己的方式證實(shí)自身特性的存在。 正如巴赫金所言,“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復(fù)的方式參與存在, 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據(jù)著唯一的、不可重復(fù)的、不可替代的、他人無法進(jìn)入的位置”[26](P41),而“唯有承認(rèn)我自己唯一的位置出發(fā)而獨(dú)一無二地參與存在, 才能有產(chǎn)生行為的真正中心”[26](P44)。 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場域,受教育者的話語地位同樣是無可替代的, 也是不容忽視的,因此,他們自身首先必須對此有充分認(rèn)識(shí),必須意識(shí)到他們“自己的每一個(gè)思想連同其內(nèi)容”都是“自己個(gè)人自覺負(fù)責(zé)的一種行為”[26](P4)。
(二)消解符號(hào)暴力,實(shí)現(xiàn)話語權(quán)回歸。首先,應(yīng)修正“國家”與“專家”等情景因素所帶來的符號(hào)暴力,使思想政治教育者話語權(quán)的回歸得以實(shí)現(xiàn)。 如前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場域中,教育者的話語權(quán)處于整個(gè)權(quán)力塔的最底層,而決策者的權(quán)勢話語(或曰官方行政話語)則處于權(quán)力塔的最頂端,對教育者形成一種逼迫性力量和符號(hào)暴力。 作為一種特殊的教育實(shí)踐活動(dòng), 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地帶有強(qiáng)烈的政治性與意識(shí)形態(tài)性, 但這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特性, 其最終目的仍在于促進(jì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 其過程自然應(yīng)當(dāng)是生動(dòng)鮮活的。 因此,決策者的權(quán)勢話語或官方行政話語應(yīng)適度地讓渡于教育者的個(gè)人話語, 使教育者能夠在規(guī)定動(dòng)作之外,根據(jù)個(gè)人的經(jīng)歷、思考、理解和感悟,以實(shí)踐者、生活者甚至創(chuàng)造者的身份來運(yùn)用各種豐富生動(dòng)的素材實(shí)施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者個(gè)體話語權(quán)的回歸除了需要決策者的權(quán)勢話語的適度讓渡之外, 還需要專家的理性話語的適度讓渡。 應(yīng)提倡專家的理性話語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個(gè)體話語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對話, 鼓勵(lì)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參與科學(xué)研究, 通過研究使自己獲得應(yīng)有的學(xué)術(shù)聲譽(yù)和專業(yè)地位,“以研究作為解放教師的武器”, 使其從各種歷史性壓抑——“否認(rèn)教師個(gè)人的尊嚴(yán)”、“迷信外部的權(quán)威的教育制度”——中解放出來[27](P133),使整個(g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既是科學(xué)的又是生動(dòng)的學(xué)問。 其次,應(yīng)修正傳統(tǒng)文化與教育系統(tǒng)等情景因素的符號(hào)暴力, 使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話語權(quán)的回歸得以實(shí)現(xiàn)。 一方面,應(yīng)當(dāng)改變觀念,樹立現(xiàn)代化的教育理念,倡導(dǎo)新型的師生平等的關(guān)系, 使傳統(tǒng)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那種被異化的師生關(guān)系得以改進(jìn), 教師與學(xué)生在有效溝通的基礎(chǔ)上保持理性交往, 由此消解傳統(tǒng)文化的規(guī)訓(xùn)所帶來的符號(hào)暴力, 使師生關(guān)系得以還原,受教育者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主動(dòng)性等得以充分發(fā)揮。 另一方面,還應(yīng)修正教育系統(tǒng)對受教育者產(chǎn)生的情景逼迫, 在顯性的文本制度等方面,除了文本制度的具體內(nèi)容應(yīng)以人為本,充分尊重受教育的正當(dāng)話語權(quán)力之外, 也應(yīng)注意話語的修辭表達(dá), 避免由于使用生硬冰冷的詞匯而造成情景逼迫和符號(hào)暴力;在隱性的資源控制方面,應(yīng)轉(zhuǎn)變思維, 創(chuàng)新教學(xué)考核體系和學(xué)生綜合評價(jià)體系,最大限度地接受受教育者的對話與申訴,消解資源控制所帶來的逼迫和威脅,解構(gòu)屈從性關(guān)系。
[1] 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2] 汪堂家.記號(hào)、符號(hào)及其效力——從哲學(xué)與符號(hào)學(xué)的觀點(diǎn)看[ J].復(fù)旦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4,(3).
[3] 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4] 趙毅衡.符號(hào)學(xué)原理與推演[M].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
[5]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shí)形態(tài)”的技術(shù)與科學(xué)[M].李黎,等,譯.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1999.
[6] 劉珂珂,張梅.人·符號(hào)·文化[ J].江蘇社會(huì)科學(xué),2012,(5).
[7] 蘇曉軍.認(rèn)知符號(hào)學(xué)視域中的體驗(yàn)性[ J].外語學(xué)刊,2009,(6).
[8] 石中英.教育哲學(xué)導(dǎo)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
[9] 袁春紅.布迪厄符號(hào)暴力教育理論[ J].云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4,(1).
[10] 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shí)踐與反思——反思社會(huì)學(xué)引論[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
[11] Pierre Bourdieu.The Question of the Sociology [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2]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M].劉大基,等,譯.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6.
[13] 費(fèi)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xué)教程[M].高名凱, 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0.
[14]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 后現(xiàn)代課程——關(guān)于知識(shí)的報(bào)告[M].車槿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
[15] 鄭樂平.超越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論新的社會(huì)理論空間之建構(gòu)[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6] 楊善華.當(dāng)代西方社會(huì)學(xué)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7] 麥克爾·阿普爾.意識(shí)形態(tài)與課程[M].黃忠敬,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1.
[18] 吳康寧.教師是社會(huì)代表者嗎[J].教育研究與實(shí)驗(yàn),2002,(2).
[19] 寧虹.“教師成為研究者”的理解與可行途徑[ J].比較教育研究,2002,(1).
[20] 迪爾登.教育理論中的理論與實(shí)踐[A].瞿葆奎.教育學(xué)文集.教育與教育學(xu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1] Shulamn, L.(1986).Those Who Understand: Knowledge Growth in Teaching[ J].Educational Researcher,15(2) .
[22] 張意.文化與符號(hào)權(quán)力[M].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5.
[23] 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24] 程少波.論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教育話語[ J].教育評論,2000,(3).
[25] 金生鈜.理解與教育:走向哲學(xué)解釋學(xué)的教育哲學(xué)導(dǎo)論[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1997.
[26] 巴赫金全集:第1 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27] Duckworth,E.The Having of Wonderful Ideas [M].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