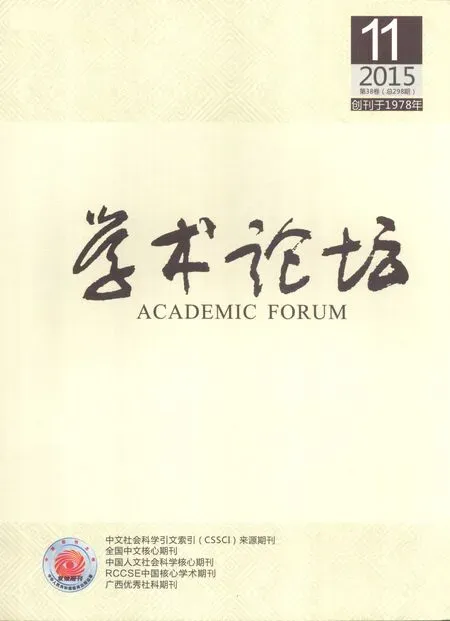《莊子》論“怨”
李建中,袁 勁
詩家有莊、屈合論之例,并于“興觀群怨”之中分別拈出“莊生善群”與“屈子可怨”的評價①明人黃汝亨《〈楚辭章句〉序》有言:“參于《莊》,可以群;參于《騷》,可以怨”;又,清人錢澄之《莊屈合詁自序》亦有“《詩》可以群,可以怨,屈子其善于怨,莊子其善于群”之論。。 相較于 《離騷》 的 “蓋自怨生”(司馬遷語),《莊子》之“怨”多為“逍遙”與“齊物”的曠達印象所沖淡。 然而,正如清人胡文英所嘆:“莊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閭之哀怨,而不知漆園吏之哀怨有甚于三閭也。蓋三閭之哀怨在一國,而漆園之哀怨在天下;三閭之哀怨在一時, 而漆園之哀怨在萬世。 ”[1](P6-7)《莊子》論“怨”是本于生命體驗的言說,所付筆墨不多,卻也別開生面。 惜于前人論述未詳,本文特擷取《莊子》論“怨”片語并綴連相關情境,以求彰顯莊子獨特的“診怨”慧識與“療怨”哲思。
一、“跪跽受命”:“怨”的字義隱喻與《人間世》的情境再現
對于軸心期華夏民族的情感體驗,《左傳·召公二十五年》概括為好、惡、喜、怒、哀、樂之“六情”,《禮記·禮運》亦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之說,加之后出《白虎通義·性情》所歸納的“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其言說范疇大抵不出此類。“怨”的情感濃度與表達方式即介于“哀”“怒”之間。實際上, 作為個人心態與世風民情的一種經驗表述,“怨”很早便引發了諸子百家的廣泛關注,并成為描述世情與闡發哲思的高頻詞匯。 所謂“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左傳·成公十六年》),在禮崩樂壞與“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先秦,儒、道、墨、法諸家紛紛提出各自的“止怨”主張: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論語·述而》)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 是以圣人執左契,不責于人。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七十九章》)
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 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墨子·尚賢上》)
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 民怨則國危。
(《韓非子·難一》)
以上四條為諸家論“怨”之中的經典言說。 儒家訴“止怨”于仁義理想,道家藉“天道”以消“余怨”,墨家“舉公義”而“辟私怨”,法家納“民怨”于“法”觀之。 防患“怨聲載道”是諸家立論的同一旨歸,而作為藥方的“止怨之道”則言說各異。 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詩大序》),個人心態之“怨”往往會上升并匯聚成世風民情的表征,進而成為關乎社稷興衰的晴雨表。 作為一種聚焦于內心的情感體驗,“怨”本源于人己關系的感知與咀嚼,并擴散至“個人—家—國—天下”的關系格局。當儒、墨、法各家乃至同屬道家的老子紛紛選擇“國”與“天下”的宏大視野時,似乎只有莊子在向個體生命體驗的回歸中,重新拾得“怨”的字義根柢。
倘若將“怨”字的構形由形聲還原為會意,便會在《人間世》中邂逅這種“跪跽受命”的情境。 自《說文解字》“怨,恚也,從心夗聲”[2](P511)始,“怨”多被看作形聲字。 就理據而言,“從心夗聲”的構造大體可通,考慮到段玉裁在“夗”字下“凡夗聲,宛聲字皆取委曲意”[2](P315)的發明,“怨”字似以“轉臥”之身形表“委曲”之心意,即所謂“輾轉反側”是也。 然而,段注“此篆體蓋有誤”[2](P511)與朱駿聲“古文從心從令”[3](P717)的推測和古文舉例,還隱約透露出另一種解字的可能。 “怨”的甲骨文與金文今已無從考證,但“心”與“令”的會意可為字義還原提供線索。先看“令”字。 盡管各家對于“令”字的上半部分解釋各異,如李孝定先生認為亼象倒口,洪家義先生指出亼為舍之省文可表廬舍; 但對于下半部分為跪跽之人的理解則相對一致[4](P364-366)。 于眾說之中,徐中舒先生對“令”字的拆解頗為形象:木鐸之形在上,而跪跽之人在下,即“古人振鐸以發號令,從卩乃以跪跽之人表受命之意”[5](P1000)。 卩擬跪拜姿態, 木鐸之形象征上級權威, 而加以心符則指向“跪跽受命”者的心理狀態。 與許慎“令,發號也”的施動者視角不同,“跪跽” 之說更關注受命者的屈服姿態。 正如張舜徽先生所言:“怨之言冤也,謂有屈在中不得申也。凡抱屈不申則怨。”[6](P55)亦如同源字“冤”的敘事情境為“兔在冂下不得走”[2](P472)一般,加上“心”后的“怨”側重于身陷困境后的心生委曲。 在《莊子·人間世》中,“跪跽受命”與“抱屈不申”的定格畫面被生動地演繹為“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和“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的兩難處境: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 吾甚慄之。 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若成若不成而后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 我其內熱與!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是兩也,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①本文凡引《莊子》原文者,均據郭慶藩撰《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12 年版,下不另注。
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 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 其德天殺。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若然者,吾奈之何? ”
如果說“令”代表社會等級自上而下的施加,那么“怨”便是弱者的承受與隱忍。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莊子借孔子之口闡明為人臣子者(即“跪跽”之人)唯令是從的“大戒”。 不辱使命固然理想,但“令”也多會帶來“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抑或”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式的左右為難。 此時,“受命”者的心態便會隨之改變。 莊子只言“令”之棘手而未言“怨”之發生,但是,葉公子高“甚慄”“內熱”之憂慮與顏闔“吾奈之何”的無助,皆已蘊藏著“怨”的可能。 這一困而生怨的正常情感走勢可舉《周易》與《論語》加以佐證。 《周易·系辭》“《困》以寡怨”理想訴求的背面,正是“困而多怨”的現實,而《困》卦六三借三條爻線隱喻“困于石,據于蒺藜”的進退維谷②依黃壽祺與張善文先生的注釋,“石”喻九四,“蒺藜”喻九二,蓋六三陰柔失正,求九四不得猶困于石下而難入;凌九二不得如錯足蒺藜而難踐。 見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275-276 頁。,正與莊子筆下的“是兩也”異曲同工。 《論語·憲問》稱“貧而無怨難”,固然是對君子“無怨”人格的褒獎,其潛臺詞同樣是“貧而怨”的普遍乃至情有可原。 于此,莊子雖未著一“怨”字,卻已偶合字義敘事的原始情境。
必須承認, 盡管文中的葉公子高和顏闔已是“跪跽受命”,但敘事者莊子卻一直按住“怨”字引而不發。 一般認為,《人間世》主旨為“能隨所適而不荷其累”[7](P137)(郭象注)。 從莊子的行文來看,兩處引文也并非有意論“怨”。 “怨”的字義隱喻在《人間世》中的情境再現確乎偶然,然而從字義演變中細加推求卻也不失其必然。 考慮到“令”與“命”初為一字,從“令”從“心”的“怨”在“葉公子高將使于齊”的寓言中其實已化妝為“命”“心”會意的勸解路線。 在這一過程中,“命”的指涉不斷滑變,而相關的“心”也漸趨解脫。 先是“朝受命而夕飲冰”的臣之“怨”,經“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的子之“怨”,最終落實于“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的“莫若為致命”。 這一看似由國至家再到個人的層層后退,實則步步關“心”。 先秦諸家皆不乏論“怨”之語①按照徐中舒先生的解釋,“怨”的最初會意與號令有關,但頗為吊詭的是,早期兵家(如《孫子兵法》)卻鮮有論“怨”之語。 這固然與從古文到小篆的形體演變有關,但就其根本而言還是關注點的不同導致原初釋義情境的丟失。 相較于儒、墨、法,兵家更側重于國與國之間的軍事斗爭。 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之“怨”需讓位于焦點矛盾,而國家之“怨”又可直接訴諸武力而不需屈服隱忍。 至于《六韜》中“興怨”之說,則是刻意煽動敵我對立,利用“怨”來戰前動員與提升戰力。,與其說獨有《莊子》偶然間再現了“怨”的原初隱喻情境, 倒不如說是獨有莊子從事功的家國天下語境中超越,在回歸自然的“逍遙游”中以道觀之,不經意間透視了“怨”的人己關系困境,也由此開出了不同于別家的“療怨”藥方。
二、“天怨”與“怨天”:《莊子》論“怨”的新維度
莊子似是無意間的“診怨”卻切中了人己關系中“困以生怨”的病灶,那么,在莊子眼中,又該如何療救這種普遍性的怨毒呢? 由于《人間世》乃至整個內七篇體系均未明確使用“怨”字,我們不妨借助外、雜篇與內篇的對讀來尋求答案。 據筆者統計,“怨”字在《天道》《天運》《刻意》《達生》《徐無鬼》《列御寇》等六篇中凡七現,其內容不可謂多,而思想卻堪稱精妙。
整體而言,《莊子》一書對“怨”的看法是頗為辯證的。 一方面,莊子及其后學承認“怨”的負面價值,并將其作為批評的對象或諷刺的素材。 在《刻意》篇中,“高論怨誹”緣自陷入“為亢”之名的“山谷之士”,這種表現與仁義、功名、江海、道引四類皆非“養神”“貴精”之舉,故可作為“圣人之德”的反襯。 《徐無鬼》中的楚人“未始離于岑而足以造于怨”,這種“無因而造怨”更成為針對惠施與儒墨楊秉“是者之是,莫得其所以是;非者之非,莫得其所以非”[7](P836)的尖銳抨擊。 另一方面,《天運》篇所載老子對孔子求道的回應中,“怨”與“恩取予諫教生殺”又可作為“正之器”,以供“循大變無所湮者”所選用。 如同《論語》中孔子處處主張“不怨”“遠怨”,卻又留下“詩可以怨”的例外一樣,《莊子》對“怨”的理解也頗為立體而未陷入凝滯。 具體到言說特色與思維貢獻而言,《莊子》論“怨”在“個人—家—國—天下”的傳統框架內引入了自然“天”的維度,先是標舉“天怨”來補充并超越儒、墨、法諸家的入世視角,進而借助“無天怨”與“勿怨天”的施受同體來建構“以道觀之”的論“怨”體系。 以下分述之。
儒、墨、法諸家論“怨”多囿于家國天下的語境,如孔子“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的理想訴求便包含:君臣關系中的上級應“不使大臣怨”(《論語·微子》),父子維度內的下級當“勞而不怨”(《論語·里仁》),而同級交際亦不可“匿怨而友其人”(《論語·公冶長》)。 從論述框架上看,《莊子》一書通過引入上位概念“天怨”,突破了“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及其背后的“個人—家—國—天下”秩序。 《天道》有言:“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 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刻意》篇中亦有相似的論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后應,迫而后動,不得已而后起。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 ”依照兩篇重章結構的詞語對位關系,《天道》所謂“天怨”應與《刻意》中的“天災”同義,即上天對普通人的懲罰。 那么,這種“天怨”或者“天災”具體為何? 是降下的自然災害,還是別有所指? 論者于此多以“上天的怨恨”[8](P203)“上天的災禍”[8](P242)等一筆帶過,但若是聯系“知天樂者”(或曰“圣人”)“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的描述反推,便可發現此處的“天怨”應與《人間世》中的“陰陽之患”相關。 所謂“人大喜邪? 毗于陽;大怒邪? 毗于陰。 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在宥》),又所謂“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訓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夫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列御寇》),“陰陽之患” 的病理是“陰陽之氣激蕩而致失調患病”[9](P123)。 借由“陰陽”的串聯,將“知天樂者,無天怨”與《人間世》對讀,即可理出隱藏的內在線索:如果說“人道之患”是家國之“怨”,那么,“陰陽之患”便是“天怨”;相較于君主刑罰所代表的“人為的禍患”[9](P123),后者的傷害要來得更為急切:“事若成, 則必有陰陽之患”,“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人間世》)。 通過“天怨”(即“陰陽之患”)的引入,莊子意在喚起世人對“人道”之上“天道”的重視。 當然,除了“是兩也”這一主體與生存境遇之間的緊張,“人道之患”與“陰陽之患”非此即彼的關系,還構成了主體內心的撕裂與緊張。 《人間世》中,莊子借助仲尼之口,指出“孝之至”與“忠之盛”之上,還存在一個更高的“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德之至”;而“知天樂者,無天怨”亦是在“與人和者,謂之人樂”基礎上提出“與天和者,謂之天樂”作為消解“天怨”的途徑。 如成玄英所論“德合于天,故無天怨”[7](P468),《莊子》于世俗之“怨”的普遍認知基礎上,提出所謂的“天怨”概念,不但突破了世俗之“怨”的束縛,而且將其置于家國層面之上。這是對傳統論“怨"模式的改造,即在”個人—家—國—天下“的社會遞進體系之外搭設起新的“人—天”維度。
作為一種情感體驗及其表達的“怨”,其實包含著“己怨人”與“人怨己”兩個面向。 如《論語·里仁》“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句便有“招致很多的怨恨”[10](P38)與“我心對外將不免多所怨”[11](P95)兩種理解。 由“怨”的施受同體性所引發的釋義糾纏同樣存在于“天怨”的理解之中。 《天道》中“知天樂者,無天怨”強調受動之人對“天怨”的規避①當然,學界對此亦有不同觀點,如陳鼓應先生便將“知天樂者,無天怨”譯作“體會天樂的人,不怨天”。 見《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44 頁。;《達生》中 “何暇乎天之怨” 則主張施動之人的不去 “怨天”。 《達生》載孫休向扁慶子訴說困惑:自己注重修身且勇敢,卻躬耕不獲豐年,事君不遇盛世,又被周圍人所驅趕,是命該如此嗎? 扁子的勸說策略是先標榜至人之忘,進而批評孫休之不忘,最后通過“怨”情比較來強調孫休的不必怨天:“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于聾盲跛蹇而比于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如同《逍遙游》的“小大之辨”,“何暇乎天之怨”的勸說理路指向形而上的“忘”,卻又借助形而下的價值比較:相較于“中道夭于聾盲跛蹇”者的“大怨”,躬耕不獲豐年、事君不遇盛世等只是“小怨”,因而也就沒有必要再去怨天。 通過比較,孫休的“怨天”算是暫時止住了,不過倘若據此繼續推導,是不是處于價值底端的“中道夭于聾盲跛蹇”者就有了“怨天”的理由呢? 顯然不是,《德充符》早就以“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和“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鐘泰先生曾言:“此文與篇首‘達命之情’義相應,蓋惟忘命而后能安命,若知其為命而猶有所未忘,則是未能達命,即宜其不安,如孫休者是也。”[12](P433)又所謂“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德充符》),在“何暇乎怨天”的形而上言說中,其實蘊含著“忘”的訴求而絕非簡單的大小之辨。 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孫休走后扁子長嘆的精彩補筆——面對 “款啟寡聞之民”,扁子試圖言說“至人之德”,卻最終意識到此舉無異于“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 其實,《莊子》真正標榜的“何暇乎怨天”者并不是孫休之輩,而是“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的兀者王駘,是“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的申徒嘉,是“猶有尊足者存”的叔山無趾等形殘而德全之人。 如此說來,《莊子》對舉“無天怨”與“勿怨天”恰成一體之兩面,不僅針對“怨”的施受同體特性進行全面防治,而且“無天怨”者的“與天和”,與“何暇乎怨天”者的“忘其肝膽,遺其耳目”皆超越了家國忠孝與居鄉修勇的社會層面。 那么,與其說《莊子》論述“天怨”與“怨天”是在“個人—家—國—天下”體系外另辟“人—天”模式,倒不如說是超越家國天下的中介而實現人與天的自然對接。
三、“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作為一劑瀉藥的《莊子》“療怨”
在“己不怨天”與“天不怨己”的雙向協調下,《莊子》提出了獨具特色的“怨”情消解策略。 以“天怨”和“怨天”審視世間的“己之怨人”和“人之怨己”,自有大鵬一般高屋建瓴的宏觀把握,而這一藥方背后其實還隱藏著更為宏大的“圖南”訴求。涂光社先生指出,“莊子迥別于孟子、荀子、韓非子的是強調超越世俗的精神自主性,所以多用‘自’的組合。 尚自然的他以天為自然,以‘天’組合的概念詞匯更是特別多”[13](P333)。《莊子》創設的“天怨”概念連同對“怨天”的新疏解即隸屬于“天”論范疇及其概念系列。 “療怨”即救世,莊子眼中的人天對接暗含著對儒墨諸家的批評, 而對接過程中所竭力批判、 所力圖超越的家國天下等社會性存在則成為《莊子》“療怨”所要根治的對象。
《達生》有則“圣人任獨無心”的寓言這樣寫道:“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 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忤物而不慴。 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 是故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 復仇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 故無功戰之亂,無殺戮之行者,由此道也。 ”此中“飄瓦”之喻與“醉者墜車雖疾不死”和“復仇者不折鏌干”構成博喻,強調無心后的無害。 “夫干將鏌鎁,雖與仇為用,然報仇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 ……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7](P635-636)—依據郭象的解釋,這是一種推至極端的說理。 “復仇者”與“忮心者”本就情感易發,因而“飄瓦”與“鏌干”得以保全便愈發難得。 站在受動者立場,“飄瓦”不招致怨恨也可理解為一種處世理想。 緊隨其后的《山木》便有一則近似的寓言:“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于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 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面對“虛船”,還只是人與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人與天)的關系;而舟上有人,便構成人與人的對立了。 前一情境中的“飄瓦中人”與“虛船來觸”可歸于自然,后者卻涉及恩怨情仇等人際利益沖突。 歸根結底,“飄瓦”與“虛舟”正是“圣人藏于天”與“人能虛己以游世”的形象化言說。
其實,所謂“無心”與“虛己”的怨情根治,采用的是斬斷世俗利益瓜葛的 “釜底抽薪”, 這與儒、墨、法諸家的“止怨”策略有很大不同。 且看儒道兩家關于如何報怨與射箭不中的兩種言說。 《道德經》五千言,“怨”字共出現三次,分布于第六十三章和第七十九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六十三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
是以圣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七十九章)①陳鼓應先生據陳柱、嚴靈峰之說,認為“報怨以德”為錯簡,當移入“必有余怨”和“安可以為善”之間。 這種調換相當于讓老子自己否定了“報怨以德”的妥善性。 見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中華書局2009 年版,第340-341 頁。
就后世影響來看,老子高揚的“報怨以德”似乎成為孔子批駁的靶子:“或問:‘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朱熹《論語集注》有言:“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 ‘德’謂‘恩德’也。 ”[14](P147)論者多以此解,謂孔子將老子虛無縹緲的美好理想落在實處,而“以直報怨”要比老子“以德報怨”的逆來順受高明一步。 然而,所謂“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老子》二十一章),“‘德’為‘道’的具體運用,并非恩惠之意。報怨以德, 即按自然之道對待怨”[15](P156)。 老子論“怨”的貢獻是認清了“調解深重的怨恨,必然還有余留的怨恨”[16](P342)的實質,而《莊子》論“怨”亦是本于“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一句的“接著說”。 在老子看來,消解“怨”情的終極策略是“圣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式的自為,而非“用稅收來榨取百姓,用刑政來鉗制大眾”[16](P342)之類的“司徹”。置此語境,方可更好理解《莊子·列御寇》中“智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的排比,即勇動、仁義多代表的有為同時也是一種“繩墨”“桎梏”“天刑”,唯有“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方可“縣解”(《養生主》《德充符》)。
在如何化解“得時失順”的問題上,孔子與莊子的策略亦有不同。 孔子有“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禮記·中庸》)的類比。 孟子為之增添了“不怨”的情感因素:“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公孫丑上》)這是著眼于人際關系的調和,即以“反求諸己”的仁者標榜,克制“怨”的外向型歸因。 《莊子·德充符》中申徒嘉面對子產“索我于形骸之外”的責難亦有近似的譬喻:“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對讀射箭不中之喻的兩種言說,可見分歧有三:就語境而論,孔孟立言著眼人與人的交接,而莊子設喻則推至人與天的維度,此其一;就策略而言,儒家是主動求諸己的內向型引導, 而莊子則是被迫歸于命的外向型消解,此其二;就效果來看,孔孟樹立君子修養,莊子則高舉有德者的超脫,此其三。 有論者指出,“如果說儒家通過道德標榜, 使利益失衡的弱勢群體認識到自己作為君子 ‘不應該’去怨,更多地側重‘德’的標榜,那么道家則通過道德標榜促使弱勢群體認識到自己作為不足的一方‘沒必要’去怨,更多地側重‘道’的標榜”[17](P66)。 “不應該”與“沒必要”的概括可謂恰切。 其實不唯儒家,墨家“舉公義”而“辟私怨”,法家納“民怨”于“法”觀之等等皆秉持“不應該”乃至“不允許”的態度。 儒家的“不應該”指向“仁”這一君子人格,墨、法兩家的“不允許”則緣于“義”與“法”的至高訴求。 莊子將“沒必要”歸為“命”(這種“命”已非君父之命令),并強調能安于命而成“有德者”,即《德充符》所謂“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顯然,“沒必要”正是對“不應該”的超越,后者將“止怨”納入仁義框架,用《莊子》的話說,是“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于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天地》);用魯迅的話說,便是將怨情訴諸社會中“一級一級的制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 ’(《左傳》昭公七年)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 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 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 如此連環, 各得其所, 有敢非議者, 其罪名曰不安分! ”[18](P179)由此觀之,《莊子》的高明在于看透了仁義禮法制度約束的局限性。
針對“怨”,如果說儒家是以禮節之,是“禮崩樂壞”后的“克己復禮”,那么,莊子便是以天合天,是“自事其心”而絕不“毀道德以仁義”。 所謂“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馬蹄》),又所謂“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 摒棄仁義桎梏,由社會人回歸自然人是《莊子》所力圖實現的目標。 因而,在“診怨”過程中,《莊子》會著重提出“天怨”概念;在“療怨”方法上,也在“無心”“虛己”與“合天”的論證中貫穿著對仁義的批駁。 清代胡文英曾言,“要知戰國是什么樣時勢風俗? 譬如治傷寒病的一般, 熱藥下不得,補藥下不得,大寒涼藥下不得,先要將他那一團邪氣消歸烏有,方可調理。 這是莊叟對病發藥手段,看作沒要緊者,此病便不可醫”[1](P5-6)。 《莊子》為“療怨”開出的正是一劑瀉藥,瀉去社會層面“有為而累”的仁義刑法桎梏,以求回歸“無為而尊”的人天對接。 當然,《莊子》釜底抽薪的構想美則美矣,可人畢竟離不開社會,就連莊子自己也會遭遇楚王征相與妻子去世事件。 就后世影響而言,《莊子》論“怨”的貢獻其實并不只是理想大廈的構建,還為歷代“處江湖之遠”者提供了精神的原鄉與庇護。鐘嶸《詩品序》有言“離群托詩以怨”,“離群者”如嵇康、阮籍、陶淵明、李白、蘇軾等,皆在莊子的“游世”與“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中尋得情感的共鳴與心靈的解脫。
“只道真情易寫,那知怨句難工。 ”(陸游《臨江仙·離果州作》)“怨” 本是蘊藉心中而不易言說的生命體驗,可《莊子》不經意間的論“怨”卻能別開生面:引入“天怨”概念突破世俗之“怨”的束縛,進而喚起人與天的對接,此乃傳統論“怨”框架上的超越;借助“何暇乎天之怨”的價值比較與“忘”的道德標榜,為“怨”的施受一體者提供心靈消解之道,此即釋“怨”路向上的開拓;“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的利益斬斷連及“虛己以游世”的生存智慧,為社會人到自然人的回歸指明方向,是為止“怨”策略上的創新。 通過心性錘煉的體驗與表達,《莊子》一書在說服自己面對人間寒熱煎熬而“不怨”的同時,也為華夏民族留下了軸心期中不同于儒、墨、法諸家的另一類“怨”感言說。 所謂“掃蕩現實人生, 以求達到理想人生的狀態”[19](P30),《莊子》中針對“怨”的心性錘煉與境界修養,是形而上的藝術化生存,也是形而下的生存性智慧。
[1] 胡文英.莊子獨見[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M].北京:中華書局,1984.
[4]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M].北京:中華書局,1996.
[5]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
[6]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M].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
[7] 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2.
[8] 楊柳橋.莊子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1] 錢穆.論語新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12] 鐘泰.莊子發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 涂光社.莊子范疇心解[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5] 顧易生,蔣凡.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先秦兩漢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6] 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7] 張磊.先秦諸子怨恨觀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2.
[18] 魯迅.墳·燈下漫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19]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