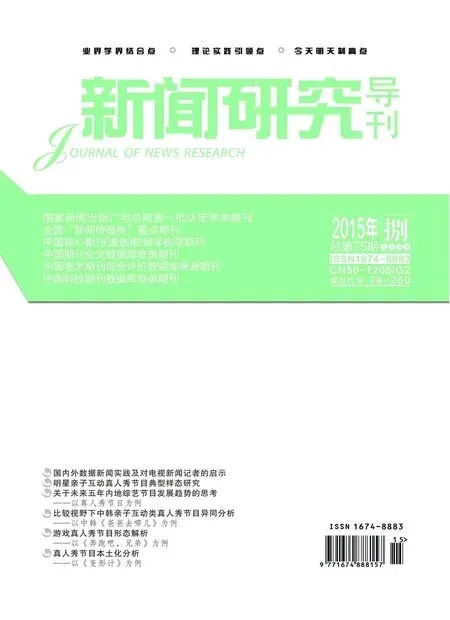上海踩踏事件媒介報道引發的新聞傳播倫理與法規思考
韓誼君
(重慶大學 新聞學院,重慶 401331)
一、外灘踩踏事件媒介行為梳理
事件緣起《新京報》與《南方周末》1月1日各自發表的一篇關于遇難者的人物報道。《新京報》以“復旦20歲‘才女’外灘踩踏事故中遇難”為標題,引用個人社交平臺上的信息以及采訪相關同學,對這位逝者的情況進行了報道,包括姓名、年齡、專業、生平喜好等。而《南方周末》則以“遇難者×××”為題,力圖還原外灘踩踏事故發生的現場。兩篇報道一出,立即引發了復旦與媒體人之間的論戰。
2015年1月1日晚上八點半,網易新聞轉載了新京報報道,并配以遇難者的真實頭像。而這也成為復旦抗議輿論的引爆點,遇難的復旦學子所在的“復旦大學燕曦漢服協會”立即在微博上發表博文,呼吁不要拿遇難者當作新聞熱點來炒作,避免對家屬的二次傷害。2015年1月1日晚22點55分,復旦大學官方微博發帖呼吁保護遇難者隱私。當日晚,復旦大學官方微信平臺又發布一則消息,指出“復旦一學生在外灘踩踏事件中傷重不治,望媒體尊重逝者隱私”。1月2日,復旦學子撰文《今夜無眠|復旦學生致部分媒體的公開信》。
就在公開信發表后不久,微信公共號“微觀者說”1月3日以授權轉發的形式轉發了一篇題為《媒體人就外灘踩踏事件致復旦學生公開信:別太矯情了》的文章。該文章認為:“網絡時代人們對個人信息極為敏感,但往往忽略很多信息是由當事人主動公開的,并不具有隱私性質。如人人網、微博、QQ空間,推特,只要當事人主動發布,這些信息不僅是對媒體的公開,而且是對每一個能聯上網的人類的公開。在現今這個公開范圍約為60億,其非隱私性也不以當事人生死而變更,媒體引用無礙。”
二、爭論焦點與筆者思考
(一)隱私權與知情權的矛盾
媒介具有向受眾傳遞真實的信息的功能,這也是新聞工作者的本職工作。依據拉斯韋爾的“5W”理論,記者在報道一件事情時,采訪到的人物或機構越多,信息越詳盡,其報道的真實度和感染力也就越強。而新聞中涉及的某些信息,可能和受憲法保護的公眾隱私權相矛盾。尤其是在尋找信息和發布信息的過程中,記者的有些行為可能是與公眾的隱私權相互矛盾的。
對《新京報》的記者而言,他們或許是想通過對活著的杜宜駿的描述,來引發人們對那消逝的36個同樣美好的生命的同情與反思;不加處理地使用從網絡上獲取受害者杜宜駿的照片在滿足感官需求的同時或許會讓人們對這個美好生命的消逝更加惋惜。從法律角度看,他們從網絡上獲取并使用死者的個人信息和刊登照片的行為并沒有違法。但是,在對災難事件的報道過程中,在獲取社會效益的同時,人文關懷也是我們需要考慮到的一個尤為重要的因素。顯然,《新京報》上刊登的這片標題為“復旦20歲‘才女’外灘踩踏事故中遇難”的報道并沒有做到人文關懷,里面對受害者杜宜駿的描述會給其親屬帶來嚴重的二次傷害。新聞報道應該追求公共價值的最大化,這片報道并沒有帶來人們對災情的更多重視與反思,反而引來了輿論的一片嘩然。在很大程度上,公眾的注意力都被轉移到對新聞從業者職業道德素養的討論上來了,媒介的社會功能被大大削弱。
(二)媒介出版自由與公共利益的矛盾
出版自由是指公民享有通過以印刷或其他復制手段制成的出版物公開表達和傳播意見、思想、感情、信息、知識等的自由。1644年在彌爾頓向國會發表的演說《論出版自由》中,抨擊英國教制阻礙科學和教育發展,以及對印刷業實行許可證制度的《出版管制法》,他呼吁“讓我有自由來認識、抒發己見,并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隨著新聞出版業在我國的飛速發展,我國也頒布了一系列保護出版自由的法律法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出版自由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利。
眾傳媒必須承擔社會責任,是全世界傳媒行業的基本準則。客觀報道和傳播新聞事實,是媒體的重要責任之一。記者是社會的守望者,公共利益的守望人。新聞媒體又是“社會民眾的教師”。從歷史看,新聞傳媒是文化的傳承物,記者是人類文化的傳播者與保存者。從功能看,記者是精神文明的傳播者。新聞媒介是課堂,記者是其中的教師。新聞傳播者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報道事實是記者的職能。因此,我們很難從法律上來界定媒體報道中對受害者杜宜駿個人信息的披露是否構成侵權行為。
(三)新聞消費主義
新聞消費主義指的是傳媒極力向受眾提供具有消費特質的文化信息,或向受眾宣揚符號化的生活方式的傾向。從這篇報道的標題中含有“復旦”、“20歲”、“才女”三個詞中,可以剝離出一個2014年很火的一個詞——女大學生。在過去的一年里,經過接連發生的“女大學生失聯事件”和傳媒對“女大學生失聯事件”的序列化報道,受眾對“女大學生”這個詞非常敏感。女性,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很容易被消費的角色。《新京報》的這篇報道中對受害人杜宜駿的描述:未經任何處理的照片、個人基本信息、愛好以及對男友的話的引用更多的是為了滿足受眾的窺私欲。面對災難事件,傳媒要做的不應該是煽情,挑起悲傷情緒,而是提供準確的信息。我們需要遵循新聞職業道德,客觀、真實、全面報道才是立身之本。《新京報》這篇報道的行文,訴求的是渲染悲情,滿足的是消費者的需求而不是廣大受眾的需求,與新聞業的職責遠了去了。
當災難發生后,受眾希望通過媒體了解災難發生的原因、過程及其造成的危害后果,從而對災難做出相對的反應或行動。法國結構主義批評家熱奈特把敘事視角分為內視角、外視角、全知視角。外視角指的是故事敘述者和故事本身沒有任何關系,觀察位置處于故事之外。《新京報》的這篇報道屬于外視角,卻失去了外視角新聞的嚴謹,并沒有做到就事論事的新聞報道。該報道對杜宜駿熱愛漢文化、請同學帶假條等事實的描述早已脫離了災難事件本身,失去了本應該追求的公共價值。
(四)筆者反思
近幾年,國內發生了多起踩踏事故,大多發生在校園。2009年12月7日,湘鄉市育才學校晚自習下課,學生們在下樓梯的過程中,因一人跌倒,導致擁擠,引發踩踏事件,造成8人死亡、26人受傷;2010年11月29日,新疆阿克蘇市杭州大道阿克蘇第五小學發生踩踏事件,導致41傷7人重傷;2014年9月26日下午,昆明市盤龍區北京路明通小學因海綿墊發生一起踩踏事故,造成學生6人死亡、26人受傷。經過多次災難的教訓,我們已經越來越注重校園人群聚集處的秩序與安全問題了。臺北市自90年代中期開始舉辦跨年晚會以來,雖然參與人數規模不斷擴大,但安全狀況迄今大致平穩。而大陸每年跨年,每個市區都有那么一兩個地方會聚集大量人群,但是也沒發生過大規模的踩踏事件。那么這次發生踩踏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和臺北市相比我們有哪些不足?需要有哪些措施?這才是我們媒體需要追問和思考的。
面對一個事件,媒介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可以報道什么,從哪個角度切入效果更好。以前報道災難新聞,媒介的重點都放在當前嚴峻的形勢上面,用一個個具體的數字來表明事件的發展,聚焦到個體上面的很少。隨著傳媒的發展,在對災難事件的報道中,對逝者的關注以及對其親屬的深度報道成了記者偏愛的手法。而事實也證明,那一篇篇戲劇性很強的故事和一段段煽情的文字確實比冰冷的數字更具有吸引力。但是,從個體為切入點對災難事件進行報道,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讓受眾了解整個災難事件,引發讀者對受災者的同情和對災難的深層次的思考,甚至采取措施。
[1]胡勇.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2]陳力丹.新聞理論十講[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3]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04).
[4]章靜怡.從上海踩踏事件看公民新聞的利弊[J].新聞傳播,2015.
[5]馬歇爾·麥克盧漢(加).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譯林出版社,2011.
[6]陳絢.新聞傳播倫理與法規教程[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