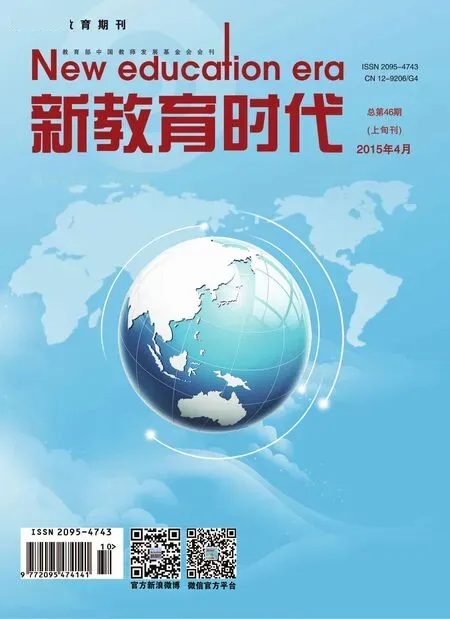淺談翻譯中的兩對矛盾
李杰
(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甘肅蘭州 730000)
淺談翻譯中的兩對矛盾
李杰
(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甘肅蘭州 730000)
翻譯是一項極其復雜的語言工作,是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翻譯是否可行,直譯與意譯,都是不容忽視的。正確處理好這些矛盾,有利于譯者進一步完善譯文,使譯文讀者更好地理解原作。
矛盾 可行性 直譯與意譯
一、引言
翻譯過程是復雜的、動態的,影響翻譯的因素很多。翻譯過程涉及的諸多因素構成了翻譯的種種矛盾,使得翻譯實踐困難重重。目前為止,有不少翻譯家研究翻譯中的矛盾。上世紀70年代,許淵沖在《翻譯中的幾對矛盾》中提出并詳細分析了翻譯過程中的三對矛盾,即理解與表達、忠實與通順以及直譯與意譯之間的矛盾(羅新璋,1984:793-802)。本文將從翻譯是否可行,直譯與意譯兩個方面來探討翻譯的矛盾。
二、翻譯之可行與不可行
哲學家賀麟認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翻譯的哲學基礎。人類的思維具有共性,翻譯是用不同的語言符號來表達同樣的意義,因此是可行的。而洪堡學派則否認了翻譯的可行性。在了解了兩種觀點的分歧之后,筆者認為翻譯可行卻又不可行,譯者可以盡可能地降低翻譯的不可行程度。
首先,翻譯必定是可行的。許鈞認為,翻譯活動的基礎就是具有全人類性的思維(許鈞:1989)。人類認知具有共性,不同語言只是同一意義的不同表達。例如,英語中的“tree”和漢語中的“樹”都是表達同一事物,這兩種語言符號之間的互換對原義沒有任何影響,可見兩者之間的互譯是可行的。奈達認為,翻譯就是翻譯意義。因此,筆者認為只要能準確表達原作意思,翻譯就是可行的。
其次,翻譯在某些方面來說也是不可行的。翻譯實踐中,譯者不僅要譯出原文的字面意義,還要再現原文的文化和思想,即實現海德格爾所謂的“思想的‘轉渡’”。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不同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語言各不相同。第一,簡單地從詞的層面上講,差異很明顯。例如,漢語中的“龍”寓意著權勢、高貴、尊榮乃至成功,而英語中的“dragon”卻指“a large fierce animal 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that can breathe out fire”(陳宏薇、李亞丹,2010:34)。這種詞匯在翻譯時就存在一定的不可譯性。此外,某些詞語是某種特殊民族文化的產物,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時,就不存在詞義對等的詞語,即詞義空缺。例如,漢語中的“文房四寶”,是中華文化特有的,英語中沒有對應的詞語,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翻譯的不可行性。第二,針對翻譯的標準,嚴復提出了“信”、“達”、“雅”。許鈞也認為好的翻譯應實現“意美”、“音美”和“形美”。但有些文體是很難達到這個標準的。例如,詩歌翻譯就很難再現原文的美感。王以鑄在《論詩之不可譯》中認為,“詩歌的神韻、意境或說得通俗些,它的味道,即詩之所以為詩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有機地溶化在詩人寫詩時使用的語言之中,這是無法通過另一種語言(或方言)來表達的”。因此,詩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譯的(羅新璋,1984:874)。
最后,譯者可以降低翻譯的不可行程度。例如,在詞義空缺時,譯者可用增添解釋的辦法來降低不可譯度。如上文提到的“文房四寶”,便可譯成“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writing brush,ink stick,inkstand and paper)”。這樣既可譯出原詞的意思,又可使目標語讀者清楚了解原詞的文化內涵。而至于詩歌的翻譯,譯者在無法完全再現原作的美感時,便可使譯作達到“信”和“達”之后,盡量趨近于“雅”。
筆者認為翻譯既可行又不可行,但譯者可以充分發揮譯者的主體作用,降低不可行的程度。
三、直譯與意譯
直譯和意譯之爭由來已久,從東漢延續到今天。早在第一篇談翻譯的文字—《法句經序》中,支謙就主張“因循本旨,不加文飾”的直譯說。后來,傅雷提出“神似說”,錢鐘書提出“化境說”,直譯、意譯之爭一直存在。有人認為在某種程度上認為直譯優于意譯,但有時單純的意譯也可能是行不通的。
英語和漢語屬于不同的語言,在語言本身的語法、句法等層面上存在差異,更有文化背景和譯者的表達方式差異以及翻譯文本的多樣性等因素影響,翻譯策略豐富多樣。直譯與意譯不是絕對的對立,更無孰優孰劣之分,目的都是準確表達原作意思。筆者認為不同的文本是決定譯者采取直譯和意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直譯的效果是不可否定的。在一些文本的翻譯中不僅能再現原文的“意”,還能傳達原文的“神”。直譯常用于一些成語的翻譯,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直譯為“一石二鳥”。此譯文英漢語字面意思完美對應,文化內涵也實現了對等。而如法律文本,若譯者采用意譯,就可能歪曲原文意思,造成嚴重的后果。
其次,直譯有時效果極佳,但有時它也不能表達原文的意境。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與其說譯者在翻譯,不如說譯者在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實現再創造。比如將中文詩詞譯成英文時,直譯效果就欠佳。例如,南宋女詞人李清照的《聲聲慢》前兩句: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
有人譯為:
Seek,seek;search,search;
Cold,cold;bare,bare;
Grief,grief;cruel,cruel grief.
而許淵沖先生譯為: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so drear,
So lonely,without cheer.(呂俊、侯向群,2001:47)
在兩種譯文中,讀者不難看出,直譯表達了原詞的字面意思,但丟失原文神韻。許淵沖先生的譯文同時實現了“意合”和“神似”。
關于直譯、意譯之爭,王佐良先生的觀點是,一部好的譯作總是既有直譯又有意譯的:凡能直譯處堅持直譯,必須意譯處放手意譯(羅新璋,1984:834)。筆者認為直譯和意譯并不完全矛盾,而是一種互補的關系,二者的合理運用才會實現翻譯的“信”、“達”、“雅”。
[1]陳宏薇 李亞丹:《新編漢英翻譯教程》。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
[2]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3]呂俊侯向群:《英漢翻譯教程》。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4]許鈞:“論翻譯的層次”,《現代外語》。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李杰,女,漢族,生于1992年12月,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筆譯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