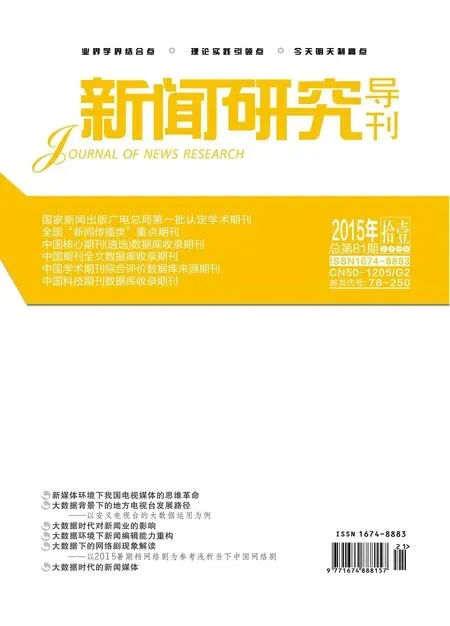從李普曼的輿論觀看理性公眾輿論形成的限制因素
劉夢瑤
(西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從李普曼的輿論觀看理性公眾輿論形成的限制因素
劉夢瑤
(西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沃爾特·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是在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一本著作。本書的主要思想是,社會公眾與真實世界相隔,公眾無法獲得真實,也無法產生理性的公眾輿論。然而,李普曼在書中對于理性的公眾輿論的限制因素做了很多分析,整本書充斥著李普曼對于理性的公眾輿論難以形成的悲觀主義色彩。本文將分析李普曼筆下的理性公眾輿論產生的限制因素,并結合互聯網時代的今天,討論輿論的力量及理性公眾輿論產生的限制因素,旨在獲得理性公眾輿論形成的途徑。
公眾輿論;李普曼;理性;限制因素
一、理性公眾輿論形成的條件
李普曼對輿論的解釋為“對輿論分析的起點,應當是認識活動的舞臺、舞臺形象和人對那個活動舞臺上自行產生的形象做出的反應之間的三角關系。”[1]李普曼將“活動的舞臺”看作“真實環境”;“舞臺形象”看作楔入在人與真實環境之間的擬態環境。他認為在公眾與真實環境中間,楔入了一種脫離現實的“虛假環境”。“人的反應”即公眾對擬態環境所做的評價和判斷。由此得出,輿論的形成需要這三方面因素的支撐。理性的輿論形成的條件首先需要公眾透過“舞臺形象”獲得“活動的舞臺”,也就是公眾接收到真實環境,滿足這樣的客觀條件之后公眾還需要用理智對此做出“反應”。
理性的公眾輿論形成條件包括客觀“真實環境”和主觀“人的反應”兩個方面。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理性的公眾輿論形成應具備兩個條件,獲得真實環境和公眾對真實環境的理性分析。
二、各條件的限制因素
自17世紀“報刊的自由主義理論”被提出并推崇之后,公眾言論自由,民間輿論場活躍起來。然而在復雜的輿論環境中,理性的公眾輿論難以產生,根據上文分析的理性公眾輿論形成的條件,下文將逐一分析各個條件的限制因素。
(一)客觀因素——交流的媒介
在復雜的世界中,中介是我們獲得信息、感知世界的一個重要手段。“看不見的環境是通過詞語報告給我們的。”[1]“同一個詞語在記者與讀者頭腦中能否喚起同一個想象,這誰都沒有把握。”[1]然而詞語所依靠的載體——交流的語言,新技術手段支撐下的電報、廣播等都屬于交流的中介。李普曼以電報在戰爭中匯報戰況為例,分析其傳播特點。電報由于條件和成本的限制,往往需要用最簡略的幾個關鍵詞傳達行動、思想、感情和結果。議員需要對電報解碼再編碼,這個過程無疑加入議員的個人因素以及個人的成見、興趣等。信息通過媒介的“加工”和客觀條件的限制,傳遞給受眾,形成逐漸脫離真實環境的“擬態環境”。
關于交流的媒介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作家彼得斯在其著作《交流的無奈》中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語詞只有充足的效能去提醒我們,以便我們看見事物,但是語詞不能向我們展示事物,以便讓我們對其有所了解。”[2]我們常常會承受內心思想和外在詞語分裂的痛苦,文字語言作為一種中介,楔入我們與真實世界之間,它不能完全真實地表達傳播者的思想,更不能完全真實地還原真實環境。公眾生活在被文字、電報、廣播擬化之后的虛假環境中,輿論的主題和意見方向在公眾眼里是模糊的、變形的。由于人們獲知世界的手段和條件有限,理性的公眾輿論難以產生。
(二)主觀因素——受眾的“刻板成見”
所謂“刻板成見”指的是人們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隨著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刻板成見可以為人們認識事物提供簡便的參考標準,但也阻礙著對事物的接受。[1]公眾對主觀環境的建構大多依靠的是“刻板成見”。公眾的刻板成見是一種固定的難以改變的,猶如“澆筑的鉛板”一樣一成不變并形成一套觀念模式,公眾在接受信息的時候,習慣于用自己已有的經驗和固定的成見分析、建構。因此,形成了有別于真實環境的主觀環境。
也就是說,當公眾之間傳播信息時,除了以上提到的文字媒介以及電子媒介所帶來的無法避免的對真實信息的偏差,人們在主觀接受信息時,也會加入自己的觀念進行分析。對于新的信息,我們往往先想象他們,然后才去經歷他們。這一觀念與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霍頓·庫利在其著作《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中提出的“鏡中我”想象性交往具有相關性。庫利的觀點是人們通過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和態度從而想象出自己的定位,然而李普曼所謂的刻板成見的想象恰好是一個相反的過程,是自我對外部世界的一個先入為主的想象,從而影響了自己對外部世界更理性更客觀的評價。
例如,當公眾看到“日本人”一詞時,就會依照自己固有的經驗和成見,想象出一群“面無表情的斜角眼黃種人”,當時的公眾如果提到“新媒介”一定會想到廣播、電報這些電子媒介,然而他們不會想到今天如此發達的互聯網技術。這些都是人們由于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及思想活動所形成的“刻板成見”,而人們因為本能的惰性,往往順理成章地使用自己的刻板成見去分析問題,在這種由刻板成見構成的主觀環境中,公眾輿論往往變得感性而極端。
三、互聯網時代下的公眾輿論
在傳播思想史的脈絡中,公眾輿論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關注。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分析了當時的輿論環境。然而,在21世紀新媒體時代的今天,復雜的傳播環境給其關于公眾輿論的觀點賦予了新的內涵,理性的公眾輿論形成的限制因素也有所不同。
(一)碎片化信息肢解事實真相
網絡時代,我們對公共事務的獲取渠道多樣且便捷。互聯網技術使每一個公眾都可以在第一時間獲取信息,但碎片化的信息使理性輿論難以形成。在2015年發生的“成都暴力駕駛”[3]事件中表現尤為明顯。此事件發生后,女司機在網絡上爆出自己被打視頻,引起公眾的憤怒,一致譴責男司機不道德的暴力行為。隨后,男司機爆出事件發生之前,女司機多次強行變道導致男司機差點發生嚴重交通事故的視頻,公眾輿論發生了一次徹底性逆轉,矛頭指向被打女司機。公眾輿論的發展情況隨著公眾對事件的某個角度的認知而發生著改變。
互聯網使公眾較之前更為直接地接觸第一手信息資源,從媒介這一影響因素分析,或許橫在我們與真實之間的擬態環境變得單薄了,但理性的公眾輿論仍然沒有產生。公眾變得感性,碎片化的信息使公眾暴露出人的本能——惰性,公眾更愿意用自己已有的經驗聯系碎片的信息,盲從大多數公眾的輿論產生“一邊倒”的現象。就此事件分析,新技術手段使公眾可以輕易獲得豐富的信息,然而碎片化的信息肢解了事實真相,公眾難以獲得完整的真實信息成了理性輿論產生的另一限制因素。
(二)封閉的社交圈子使輿論導向單一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社交圈子中,這個圈子里的人和我們總會在某個層面具有相似度,比如知識水平、社會地位、經濟水平、性格興趣。然而,如果我們只關注圈子內的信息,而忽略圈子邊緣與其他社交圈子所形成的結點,那么我們將自己封閉在一個信息來源、輿論導向單一的圈子中,而這種情形會蒙蔽我們看到真相的雙眼,阻隔了我們發現真實的觸角。
正如今天的微信朋友圈,也可以叫熟人圈。因為我們的微信朋友圈中大多數都是和我們在某些層面極為類似的人,我們甚至看不到朋友的朋友所發表的言論。在這個只與我們具有直接聯系的朋友所建立的社交圈中,信息和觀點是極其封閉的,并且由于個體之間較高的熟悉程度和相似度,往往會產生盲目的信任及相似的觀點。微信朋友圈中的輿論,往往是極端的、片面的。而微博相反,微博是一個開放度很高的社交圈子,公眾可以在微博中看到所有用戶發布的信息、觀點,在這里,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是比較全面的,信息來源是所有的微博用戶而非僅僅與我們有直接聯系的熟人。公眾對真實世界認知的觸角可以伸得很遠。獲得全面的信息和觀點,是公眾產生理性輿論的前提。通過微博和微信的對比,可以看出開放度越高的社交圈子越容易獲得理性的公眾輿論。
(三)理性的公眾輿論的形成途徑
公眾輿論存在于我們的生活各處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新聞媒體具有引導輿論對政府和公眾進行監督的職能。我們的社會追求平等、民主、自由,然而這些都需要通過輿論去實現,理性的公眾輿論對于社會的發展會有積極影響。在新媒體技術的支撐下,我們的傳播環境變得更加開放和多元,民間輿論場也相對于之前更加活躍。結合李普曼分析的輿論的特點并結合今天的互聯網環境,在獲得理性輿論的限制因素之后,應該使輿論趨于理性。
關于事實真相的獲得,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機會直接觀察,減少傳播的中介對真實環境的扭曲。積極利用新技術手段核實真相內容,同時不能過分依賴發達的媒介傳遞事實、想象事實,而忽略身體力行地去經歷事實。公眾應該在特定公共事務面前,保持頭腦清醒,克服惰性。面對大量的碎片化信息,應該盡量搜集各方信息,在掌握事實全貌的基礎上再進行傳遞或評論,避免盲從和言論極端而產生的消極后果。同時,無論是在網絡還是現實生活中,公眾應盡可能打開自己的社交圈子,積極融入更多的社交群體。獲取信息的渠道不能過分依賴網絡、手機等新媒體,信息源多元化是獲取真實信息的基礎。
在獲取真實信息的基礎上,公眾對真實環境的反應過程應保持理性,克服固有的刻板成見,不為個人或小集體的利益所影響,更大限度地形成理性公眾輿論。
[1] 沃爾特·李普曼(美).公眾輿論[M].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4,52,54.
[2] 彼得斯(美).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M].何道寬,譯.華夏出版社,2004:62.
[3] 蘇揚.成都暴力駕駛事件回放——瘋狂馬路上的鋼鐵俠[J].齊魯周刊,2015(19):A11.
[4] 李艷.“擬態環境”與“刻板成見”——《公眾輿論》的閱讀札記[J].東南傳播,2010(5).
[5] 查爾斯·霍頓·庫利(美).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M].包凡一,譯.華夏出版社,1989.
[6] 約翰·杜威(美).人的問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 黃建新,常園園.論杜威和李普曼對“報刊的自由主義理論”之顛覆[J]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
[8] 卿立新.突發公共事件網絡輿論及其應對研究[D].湖南:湖南師范大學,2012.
[9] 羅納德·斯蒂爾(美).李普曼傳[M].中信出版社,2008.
[10] 郭晶.網絡非理性輿論中的網民心理探析[J].河南工業大學學報,2011(4).
[11] 張爽.淺析突發事件中網絡輿論的理性化引導[J].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4).
[12] 夏冰,于嵩昕,曾薇,江娟,葉沖.從“人”出發的傳播學研究——對傳播學研究維度的再思考[J].新聞記者,2015(07).
G206
A
1674-8883(2015)21-0166-02
劉夢瑤,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學術型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