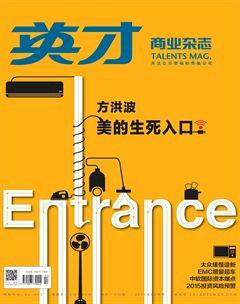央行的貨幣政策難題
高連奎
自2011年就出現了貨幣“超調”的現象,但這一問題一直沒解決。高利貸崩盤潮,企業家跳樓潮,美國量化寬松退出等都是中國解決“超調”的好時機,但是都沒有抓住。只是在2014年才真正重視這一問題,才采取了諸如定向寬松,加大合意貸款、信貸便利等措施,但效果不佳。
這是因為沒有重視貨幣“超調”問題,即使朦朧中有這方面的意識,卻始終沒有變成堅定的信念,所以問題就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而學術界也一直沒有提供相應的支持。
對于貨幣政策“回調”問題,也要具體分析,貨幣從緊變松的“回調”是最難的,而從松到緊的“回調”還相對容易些,因為央行完全可以“防通脹”為說辭進行緊縮,畢竟老百姓更擔心通脹而不是經濟增長。如果從緊到松,就會有通脹恐懼癥作怪,而央行還要面臨來自市場的一系列指責。
筆者認為這些問題必須要解決,民眾在經過幾個回合的教育之后,也會慢慢接受這些新概念,不這樣經濟就會一直在兩個極端之間循環。
貨幣政策一直沒有貨幣主義者所相信的那么靈驗,相反用貨幣政策治理經濟問題往往會出現“超調”的問題,不及時進行“回調”,那么就必然會釀成新的經濟問題。“超調”與“回調”一直沒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
在現實經濟治理中,政策的滯后性是指貨幣政策經常會放的過寬,或是提的過緊,因為判斷貨幣政策是否得當,主要看宏觀經濟指標。而貨幣政策傳導到宏觀經濟指標上需要大概三四個月的時間,甚至更長,總之這中間有個過程。但貨幣當局為了平復某種經濟現象往往等不及這么長時間,因此容易過度調節貨幣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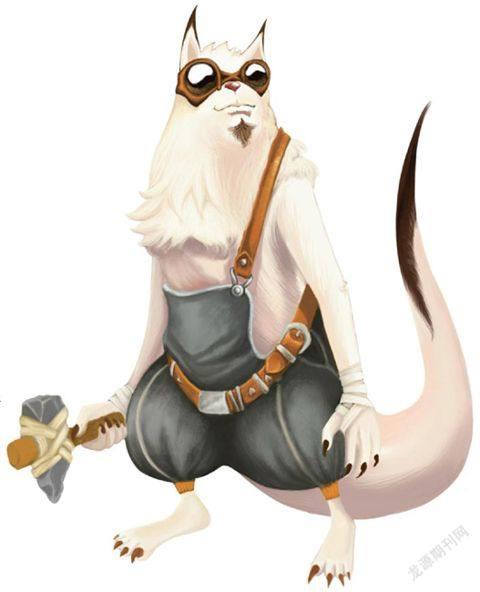
貨幣當局需要平復的經濟現象主要是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而這兩者如果用貨幣政策進行調整,本身也都需要大劑量。
貨幣政策本身也有限性,這也會導致貨幣政策“超調”。貨幣政策并沒有那些貨幣主義者宣稱的那么有用,經濟危機的解決或者通脹的治理往往需要多種政策的配合,如果其他政策配合不到位,單一依靠貨幣政策,就必然導致被過度使用。貨幣政策不僅與自然經濟周期斗爭,還與人心做斗爭,當調節不到位時,人們就會說你“空調”,甚至說你越調越壞事。
人心也是導致貨幣政策一旦“超調”就比較難挽回的原因,比如通脹剛剛控制住的時候,通脹恐懼癥仍然存在,這時央行即使知道貨幣政策處于“超調”狀態,也不敢“回調”,因為如果“回調”必然遭受人們的誤解,遭到輿論的批判。比如通脹剛剛平復時,如果放松貨幣,人們肯定會說,剛剛治了通脹,馬上又放松貨幣,老百姓可不懂什么貨幣滯后性,也不管你“超調”不“超調”。老百姓是思維非常簡單的,而輿論往往扮演煽風點火的角色。
由于貨幣政策的滯后性和有限性,不“超調”幾乎不可能,只要一動用貨幣政策就必然出現“超調”問題,觀察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政策,幾乎每次都出現“超調”問題。一旦出現了“超調”問題,就必須解決“回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