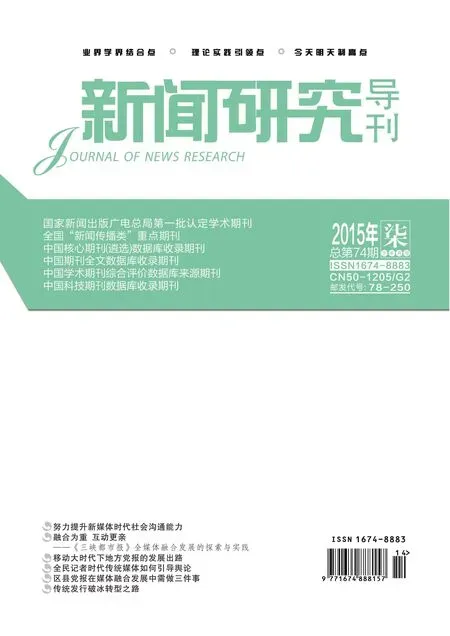關于網絡傳媒時代下文學境遇的思考
李奐緲
(山西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6)
關于網絡傳媒時代下文學境遇的思考
李奐緲
(山西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6)
瀏覽文學發展的歷史長廊,我們可以發現文學的發展是純文學與雜文學不斷更迭的過程。到了20世紀90年代,文學趨向了雜文學時代,純文學被放逐,日趨邊緣化。本文主要對網絡傳媒時代下的文學現狀及熱點爭論做了一些思考。
網絡傳媒時代;文學現狀;特點;“文學終結”說
一、當前文學現狀
何為人文現象?劉勰《文心雕龍·原道》中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劉勰強調了要從宇宙和人類的寬闊視野來理解文學,天玄地黃、天圓地方、山河煥然都是大自然的文采。而人為萬物之靈秀,天地之心靈,人的心靈產生了,言辭也就產生了,言辭確立了,文章也就昌明了。總之,他指出文章由人心所生,由人語言所生,人及其語言是文學的根本。《左傳》的“三不朽”觀點指出:“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不朽。”曹丕的《典論·論文》中說“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長久以來,文學曾承載著如此這般重要的意義。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網絡媒體迅速發展,并且直接深入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們由過去的讀文時代轉變為現在的讀圖時代。網絡圖像傳輸的便捷、直觀、無所不在,一躍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具現代性特征的事物和最具操縱人們思想情感的策源,以至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被名之為“圖像時代”。那么在“圖像時代”下的文學是什么現狀呢?文學趨向了雜文學時代,純文學被放逐,日趨邊緣化、圖像化。眼球經濟、感官刺激、欲望滿足、“快餐式”短平快的文化沖擊著大眾的視覺審美。文學受到了網絡媒介的擠壓。使之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文學的市場化、時尚化
文學的市場化即可以理解為文學作品日益商品化,以消費讀者為上帝以迎合大眾口味。作品從創作到出版都被納入市場化進程。因此,文學的價值觀念和作家的創作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
時尚化即是說文學作品緊密結合社會當下的流行趣味,與網絡傳媒關系密切。例如,許多作家筆下所創造出的文學時尚人物,他們的生活環境被設定在一個物質、信息、交通都十分發達并且文化多元的時代。他們充分享受豐富的物質生活所帶來的享樂和滿足,同時為這個時代帶來了各種新的生活與文化時尚。
(二)文學的圖像化
傳統文學的主要媒介是語言文字,文學閱讀是對語言文字的閱讀與理解;網絡傳媒時代的文學作品發生了變化,作品由傳統的“文配圖”向“圖配文”轉變,越來越多地借助圖像來表情達意,文字所具有的表達功能逐漸邊緣化,大量的文學名著有了圖說本,乃至多個不同的電視劇或電影版本。讀者的閱讀圖像化趨勢逐漸明顯,忽略了傳統文本中最主要的文字,依賴于各種圖像和影像。傳統文本閱讀中,讀者接觸的是語言文字,閱讀方式首先表現出的是文字化的解讀,而傳媒時代的閱讀方式首先呈現出的是圖像化的瀏覽,“純文學”也就越發邊緣化。
(三)文學的“去深度化”
隨著“純文學”的日益邊緣化,大眾文學也在“去深度化”。這種“去深度化”說到底還是在迎合大眾口味,作家的創作心態在與社會市場的抗爭融合中最終選擇“去深度化”,名利雙收。而這種“去深度化”文學也導致了文學創作的偶像化、明星化。閱讀動機由崇高轉向娛樂。
(四)文學的生活化、游戲化
相對“純文學”的嚴肅性,當下文學已十分生活化、日常化甚至游戲化。我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改編版四大名著、林語堂的《京華煙云》,甚至看到《Q版三國》的動漫。還有些十分不雅的游戲文學現象,如“杜甫很忙”、“元芳你怎么看”等等。
二、關于“文學終結”說的論爭
美國耶魯大學的約瑟夫·希利斯·米勒先生在《文學批評論》2001年第一期發表的論文《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中提出了一個引起中國學者廣泛討論的結論:“新的電信時代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終結。”并引用了雅克·德里達《明信片》中的一段話:“……在特定的電信技術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因素放在其次)。哲學、心理分析學也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幸免……”隨后他又在《論文學的權威性》一文中說道:“越來越少的人真正花大量的時間閱讀被稱為經典作家的作品,像喬臾,莎士比亞,彌爾頓等,至少在歐洲和美國是這個樣子……。收音機、電視、電影、流行音樂,還有現在的因特網,在塑造人們的信仰和價值觀以及用虛幻的世界填補人們的心靈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年來,正是這些虛擬的現實在誘導人們的情感、行為和價值判斷方面發揮著最大的述行效能,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世界。”對此,關于“文學終結”說的論爭出現了兩派聲音:
第一,認為文學的黃昏已然來臨,認為“文學終結”是后現代條件下文學的基本狀態;認為“終結論”者的每一次宣判都可能指出活著的文學不曾意識到的其已經壞死的部分,文學總在“終結”著。
第二,認為信息時代及“圖像世界”并未也不可能取代語言藝術;并沒有文學終結的問題;其他各類藝術離不開文學的肩膀和支撐。
基于這個論爭,筆者的個人看法是:圖形藝術等審美形式的興盛對傳統的文學審美形式的確有很強的沖擊,文學正在邊緣化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文學審美形勢依然存在生命力、審美價值及需求量。我并不認同“文學終結”說,或者只能說“文學終結”說只有在局部的特定意義上是成立的,但在嚴格的理性意義上并不成立。至少從目前及未來可見的社會發展狀況上來說,文學并不會終結。
[1] 侯文宜.當代文學觀念與批評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2] 約瑟夫·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J].文學評論,2001(1).
[3] 約瑟夫·希利斯·米勒.論文學的權威性[J].文化研究,2003.
[4] 邢建昌,秦志敏.文學終結的論爭與啟示[J].理論與創作,2006(3).
I206
A
1674-8883(2015)14-0326-01
李奐緲(1993—),女,山西大學本科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