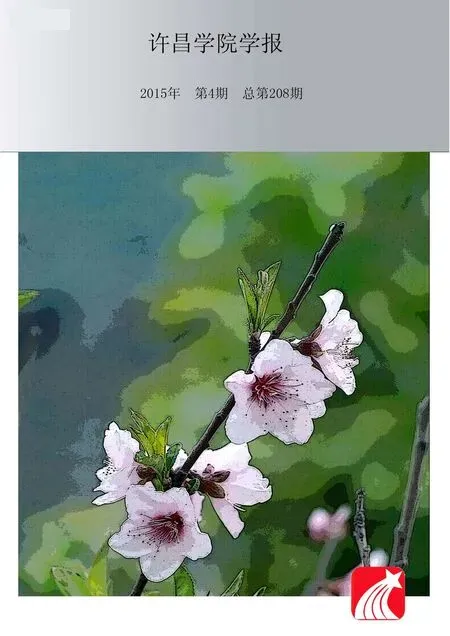經濟困難與百團大戰
——關于組織“百團大戰”的經濟因素分析
高 心 湛
(許昌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經濟困難與百團大戰
——關于組織“百團大戰”的經濟因素分析
高 心 湛
(許昌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中日兩國的經濟現狀與環境,決定了中日戰爭中雙方的戰略、戰術和戰爭的基本進程,并在戰爭中彰顯出越來越重要乃至決定性的作用;中共領導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在經濟上所具有的“三隔”、“三農”特性,決定了經濟問題從一開始便成為生死攸關的戰略問題和根本的政治問題;組織百團大戰的直接動因是軍事問題,更是經濟問題。
八路軍;百團大戰;發起原因;經濟困難
對于嚴格奉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方針,在戰略上而非戰役上給予正面戰場以配合的華北八路軍而言,影響全國戰局,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只是舉行規模反擊作戰的外因。舉百團之力大規模反擊作戰的原因,除其戰略考量外,是必還有其它強烈的內驅力;而經濟困難這一貫穿中日戰爭始終的難題,則是其中最具根本性的因素。
一、經濟問題始終是中日戰爭的核心問題
中日戰爭期間,經濟始終是影響雙方戰略、戰爭進程及國內政治的主因。
(一)中日戰爭的特點首先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
1938年5月,毛澤東在著名的《論持久戰》中指出,中日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一總特點決定了中日雙方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即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寡助我多助。這四個基本特點的存在及其在戰爭中各依其本性發生的變化,決定了中日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不能速勝,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不會亡。而其中的“強弱”與“大小”無不與經濟直接相關。在毛澤東看來,“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即是說,經濟狀況是并將繼續是中日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1]448
抗戰爆發前后,國民黨政府同樣主要基于對中日“強弱”、“大小”的分析而得出中國要取得對日戰爭的勝利,就必須“長期打”、“全面打”的結論。1938年3月30日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相關決議案明確提出:“中國以產業落后之國家”,必須做到 “源可開、流可節,敵雖圖以封鎖困我,我仍有自給自足之長策,自可與敵寇為長期之周旋而無所懼也。”[2]493
中日戰爭自始至終都是一場非對稱性戰爭。一方是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方則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一方要速勝,一方要持久;一方要步步為營,一方要全面作戰;一方要打殲滅戰,一方要打消耗戰;日方強調軍事,中方突出經濟。所有這些不對稱性,歸根結底,是由中日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在中日戰爭過程中,任何具有一定規模的戰役都將與經濟因素直接相關,一切忽視經濟因素在戰役中的重要作用的看法,都將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二)戰爭的持久性使經濟問題成為解決戰爭問題的首要問題
深入研究中日戰爭的過程,特別是中國方面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實際,我們都不難發現,困擾抗日前后方持續時間最長、影響范圍最廣、解決難度最大的問題,既不是戰略戰術問題,也不是內政外交問題,而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的方針、對策及其解決本身,是抗日戰爭的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中日戰爭的進程和狀態,其實是由經濟狀態決定的。
抗日戰爭之初,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即在其《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一文中指出:“中華民族能否從持久的抗日戰爭中,求得自己的獨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為爭取抗戰勝利而進行頑強的、不疲倦的斗爭。”[3]14他認為,中日兩國的經濟特征決定了“戰爭愈持久,敵人愈困難。而我反能在持久戰中,發展民族的經濟,建立國家的經濟基礎,以至于完全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3]5所以說,“中國抗戰的勝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戰中來解決的。”“消耗戰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耗敵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戰局的變化,改變敵我的形勢。”[3]8
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的抗戰使日本遭到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損耗,日軍在無力繼續軍事進攻的情況下,不得不改變其侵華方針,即由速戰速決,改為“以戰養戰”,對中國發起瘋狂而又全面的經濟戰。“日寇利用其占有中國的大城市與交通要道的便利條件,無論在工業農業商業上,金融貨幣上,以至稅收上,無不是以野蠻的原始的掠奪與獨占政策,摧毀民族經濟,奴役中國人民,使中國國民經濟,遭受大的摧殘,使中國在抗戰中的財政經濟,遭受巨大的困難”。日寇“對中國經濟的野蠻的掠奪、破壞,以至開發東北華北,拓植華中華南,無非是想達到其‘以戰養戰’而至中日‘滿’的經濟一體。”[4]
在相持階段,經濟問題由戰爭第一階段的隱性問題,一躍成為顯性問題。經濟不僅僅是在影響著戰爭,更是中日戰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經濟成為戰爭得以繼續的重要原因和內容。
(三)抗日戰爭的民族性使經濟問題同時成為政治問題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包括工農商學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海外僑胞參加的全民族抗戰。”[5]在所有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因素中,發展和鞏固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條件。
要發展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必須首先處理好三大問題。
第一,如何加強團結。其核心問題是如何在統一戰線內部,破解日本侵略者“不斷的以經濟誘降,經濟封鎖,與軍事進攻相配合”,以“威迫利誘中國的大資產階級,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達到殖民地化中國的目的。”[4]1938年12月3日,日本內閣召開御前會議通過的《調整日華新關系的方針》的核心,即所謂“日、滿、華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其中將 “經濟提攜”作為基礎。至少在日方看來,經濟手段對解決中日戰爭最為重要。這一手段的實施,也確實使中國時局出現了以下明顯的變化:“在敵我戰略相持階段中,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方向與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的抗戰方向兩方面展開日益明顯日益嚴重的斗爭。”[6](1087)在此情況下,經濟問題就上升為維護和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團結的核心問題。
第二,如何廣泛發動民眾。全面深入地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投身到抗日戰爭的洪流之中,是中國取得“抗戰團結進步”的根本保證。“經驗已經證明,哪個地方群眾的生活改善了一些,群眾就更加積極了,群眾團體就更加有組織了。如果哪個地方沒有注意改善民生,或者雖有改善民生的法令,但實際上沒有實現,群眾就照舊起不來。”“地方黨部如果不關心群眾的生活,不為群眾的切身利益而斗爭,置群眾的痛癢于不顧,而要開展群眾運動,要群眾熱烈起來與黨與政府與軍隊一道艱苦奮斗,這是不可能的事。” 一句話,“改善群眾生活才能發動群眾”。[7]97-99
第三,如何維系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為組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果斷地中止了最初土地革命的方針路線,轉而實施減租減息減稅的政策;不再沒收大地主的財產,而改為沒收敵偽和漢奸的財產。這些經濟措施,既動員了民眾,又團結了地富階層。但這樣做的直接負面影響卻是邊區政府收入的減少和經濟形勢日益嚴峻,群眾負擔快速增加,黨群關系和軍民關系也日益緊張。事實上,從1938年起,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便一直受到經濟保障不足的嚴重困擾。能否有效地解決經濟保障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的生存和發展。
所以,在抗日戰爭中,經濟問題一直是一個關系“強固抗日進步勢力,抵抗投降倒退勢力,力爭時局好轉,克服時局逆轉”[6]1087的大問題,是一個關系到能否實現民眾抗戰和自我生存與發展的大問題,經濟問題解決的如何,決定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廢,是最大的政治問題。
二、敵后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的基本特征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將游擊戰爭提升到戰略的高度,使中共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成為與正面戰場相呼應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游擊隊大多處于嚴重的環境,這就是無后方作戰的狀態,敵強我弱的狀態,……不統一的狀態等等”。[1]411這種“嚴重的環境”,也是根據地及其財政經濟的大環境。
(一)“三隔”是根據地宏觀經濟環境的一般狀態
處在四面或三面被敵包圍的中間,要建立長期支持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最首要的條件便是必須有游擊隊回旋的空間,要有盡可能廣大的地區。這個“廣大”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個是自然環境本身,也就是便于開展游擊戰而不利于敵軍作戰或敵軍兵力難以到達或顧及的地區;另一個是敵人力量所及,即日軍能夠相對穩固地占領和控制的地區。換言之,當地形出現明顯利于日軍或是有日軍必須確保其安全暢通的重要交通線的地方,即是游擊戰的邊沿。這種自然與人為因素的組合,便決定了各個敵后抗日根據地不論其規模大小,在客觀上必然處于一個孤軍作戰、獨立支撐的境地,根據地之間相互“隔斷”,較少甚至沒有交流與配合。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規律是,在根據地和敵占區之間往往有這樣一塊區域,“在那里,敵人極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穩固的偽政權,游擊戰爭也極力發展,但無法達到建立抗日政權的目的”,游擊隊到時屬于游擊隊,游擊隊走了又屬于偽政權,此即所謂的“游擊區”。游擊區的邊沿主要由三個因素決定,即重要的交通線如鐵路等、大多數的平原地區、大城市的附近。日軍則往往用強大的力量控制著“大城市、火車站和某些平原地帶,游擊戰爭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1]422因此,與城市相“隔離”便也成為必然。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為正確處理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兩個重大選擇:一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動搖,直至抗日戰爭全面勝利;二是到淪陷區去、到敵占區去、到敵人后方去,放手發動人民群眾,獨立自主的開展游擊戰爭。正是這兩個選擇,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不僅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在抗日戰爭中得以保存和發展自己;而且也為處理民族斗爭中的階級斗爭問題選擇了正確的行動方向,最大可能地減少和避免了國共之間的摩擦與沖突。同樣也是因為這兩個選擇,隨著中日戰爭進程的推進,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與抗戰前期的南京、武漢和以后的云貴川西南大后方、甘青新西北大后方越來越遠,形成“隔絕”狀態。
各根據地的“三隔”狀態,使其在完成財政經濟的嚴重任務時,有其特別的困難。一方面,由于“處于與敵人犬牙交錯的殘酷戰爭環境中,敵人的一切軍事行動,及其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措施,都即時的影響到根據地之內”。[4]另一方面,經濟上經常處于敵人的競爭、封鎖、破壞甚至毀滅的威脅之中。要解決經濟問題,既不能寄希望于其它根據地的援助,又難以通過攻打大城市獲得補充,更不可能從大后方獲得供應和補給,一切經濟問題只能靠自己解決。
所以,各根據地“如果要長期堅持敵后的抗戰,不能不更警惕的,更細密的,更靈活具體的,一方面與敵人作多樣的經濟斗爭,一方面不能不以愛護與鞏固根據地,作為財政經濟設施的出發點,注意在經濟戰線上,鞏固統一戰線的社會基礎。”[4]
(二)“三農”是根據地財政經濟的基本要素
面對擁有近代化裝備并控制著先進交通工具和交通主干線的日本侵略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必須并且只能選擇偏僻的、落后的地區特別是山區,作為保存和發展自己、發動民眾、戰勝敵人的根據地。所以,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實質上是中共領導的武裝對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堅持和在民族革命斗爭新前提下的再次嘗試。由此便決定了農村、農業、農民成為根據地的三個基本要素。
第一,農村是根據地的基本陣地。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1]418在敵強我弱的狀態下,毫無疑問,根據地一定不是建設在交通要道旁,更不應該是建設在城市。
第二,農業是根據地的基本產業。由于根據地在地理上的偏僻和社會發展水平上的落后,在根據地內基本沒有近代工業和服務業,以家庭手工業和傳統商業為補充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傳統農業在社會產業布局中仍然扮演著絕對的主角。
第三,農民是根據地的主要社會基礎。由于近代工商業的滯后,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所特有的土地買賣制度,使中國的農村較諸莊園制下的西方農村和現代制度下的城市,都具有超強的人口吸附能力,使廣大的鄉村分布著大量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階層,他們和雇農一起,構成了中國農村人口的絕大多數,也造成了農村人口眾多的局面。
具有“三農”特性的抗日根據地在為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提供廣闊的發展腹地、充足的兵源和利于游擊作戰的環境的同時,也使根據地在經濟上面臨自身始終難以根本解決的三大問題和困難。
其一,經濟結構單一,經濟獨立性差。單純的農業經濟不僅無法解決根據地建設以及對敵斗爭亟需的工業產品和商業產品的供應問題,而且容易在敵人的經濟封鎖、武裝走私、套購搶購物資以及貨幣戰等經濟進攻中處于被動應付的地位,使根據地的經濟困難雪上加霜。
其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弱,經濟穩定性差。自然經濟狀態下的農業經濟的本質特征是其自然性,即在生產環節中,自然環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風調雨順和自然災害及其程度,決定了“豐年”還是“歉年”、“災年”,也決定了根據地的財政收支甚至社會大局的穩定與否。
其三,生產力低下,經濟保障能力差。以家庭手工業和傳統商業為補充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保證了超穩定狀態下農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但在戰爭環境下,尤其是隨著根據地內軍事斗爭的出現和日益頻繁,軍政人員持續的大量、快速增加的時候,其低下的生產力,要保證經濟供應,就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
(三)“特區”是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抗日戰爭中的陜甘寧邊區,既是一個政治特區,也是一個軍事特區,還是一個經濟特區。隨著抗日戰爭進程的演進,中共領導的其它各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根據地內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推進,各根據地也都和陜甘寧邊區一樣,成為了一個個的“特區”。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經濟政策問題。1938年5月,在各抗日根據地草創之初,毛澤東便尖銳地指出,經濟政策問題“對于建立根據地是帶著嚴重性的”。他認為,“游擊戰爭根據地的經濟政策,必須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即合理負擔和保護商業,當地政權和游擊隊決不能破壞這種原則,否則將影響于根據地的建立和游擊戰爭的支持”;合理負責即實行“有錢者出錢”的政策,但農民也要供給一定限度的糧食給游擊隊;保護商業應表現于游擊隊嚴格的紀律上面,除了有真憑實據的漢奸之外,決不準亂沒收一家商店。毛澤東強調指出,執行這樣的經濟政策“是困難的事,但這是必須執行的確定的政策。”[1]425
中國共產黨認為,根據地的經濟“就是以農業為本的經濟,因此發展農業生產,繁榮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調劑農村各階級的經濟關系,使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自然條件,轉變為堅持抗戰的革命的社會生產力,是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政策的第一等任務,是發展整個經濟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農村能夠自給自足,包圍城市,孤立城市,以至配合全國,最后戰勝城市的基礎。”[4]
中國共產黨認為,發展邊區經濟建設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首先,邊區是全國模范的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邊區就應當在堅持自力更生,執行抗日國策的問題上,成為全國的模范,來推動全國的經濟建設”;“其次,建設陜甘寧邊區,就是鞏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后方,以及加強對于前方的接濟,后方的建設愈發展,前方的戰斗力也愈強。最后,發展邊區的經濟建設,也就是奠定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經濟基礎。”[8]
正是站在這樣的戰略高度上,在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在“特區”所特有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制定并實施了完全不同于國民黨的財政經濟政策,在農業、工業及財政金融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設。
但是,由于根據地與生俱來的地理環境上的“三隔”和經濟背景上的“三農”特性,決定了根據地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困難問題,經濟建設“遠未達到應有的成績”。[8]
三、華北地區的經濟困難與百團大戰的發動
經濟問題在中日戰爭中所處的戰略地位,敵后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的一般特征,決定了地處抗日前線的各華北抗日根據地的軍事行動必然受到經濟問題的直接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常常很直接地表現為有飯吃、有衣穿,而“軍隊給養問題對作戰的方向和形式,對戰區和交通線的選擇是有普遍的影響的。”[9]450
(一)經濟困難從華北各根據地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嚴重地存在著
與中共領導的其它敵后抗日根據地相比,華北地區特別是晉察冀根據地在經濟上遇到的困難最大。這主要是因為,其一,該根據地處于敵偽軍的四面包圍之中,外援很少;其二,自身建設和發展迅速,根據地面積和部隊人數都得到了快速發展,經濟需求也隨之迅速增長;其三,地處太行山區,崇山峻嶺、交通閉塞的自然環境,造成了該地區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其四,處于抗日戰爭的最前線,戰爭消耗量大。
193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致彭真、聶榮臻并朱德、彭德懷的指示中指出:晉察冀根據地政府,“主要的工作除廣泛組織訓練自衛軍外,就是籌給經費與糧食,解決部隊給養。籌款方法除經常的稅收捐款外,要注意向漢奸籌款。可組織特別的隊伍到鐵路車站及城市附近去沒收與逮捕漢奸。我們沒有可能大批幫助你們的經費。”[10]306該指示反映出了晉察冀經濟困難的嚴峻形勢,同時也表明中央和陜甘寧邊區的無能為力與愛莫能助。
事實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困難問題從其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著。早在1938年,由于經費不足,軍隊便不得不開始了生產運動,借以改善戰士們的生活。“一九三九年國民黨頒布《防治異黨活動辦法》,國共間的關系不如從前了。邊區的機關學校也增多,雖有外來的一點經費補助,已經分配不過來,我們處在財政供給問題的嚴重威脅下。由于這個原因,迫使我們不得不想到全體動員從事經濟自給的運動。”[11]460
經濟困難已經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以至于在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毛澤東用不容置辯的口氣講道: “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
(二)中共解決經濟困難的各項舉措并未使華北根據地財政供給困難的狀況得到明顯改善
1939年6月22日,中央軍委在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指示中強調指出,“在軍隊的物質方面,應有艱苦的準備工作。一方面進行深入的節省運動,……另方面進行征集資材的工作,進行生產運動及合作社運動,幫助地方政權開發資源,調集一批干部,加以訓練,以加強財政經濟方面的工作,保證我軍物質供給之自給而不依靠他人。”[10]311-312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更進一步強調,“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須發展人民的與機關部隊學校的農業、工業、合作社運動,用自己動手的方法解決吃飯、穿衣、住房、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難,以利抗戰。”[11](224)也就是說,到1939年,生產運動已不僅是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決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動員的范圍也不限于軍隊,而是所有部隊、機關、學校一律進行生產。
種種事實表明,至遲在1940年以前,經濟困難已經波及到敵后根據地的全部;大生產已經不再是權宜之計,而是各根據地政府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盡管華北各根據地為解決經濟困難采取發展農業和工商業的種種舉措,使根據地的財政經濟規模得到迅速擴大,經濟建設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但是,1939年全年,財政供給困難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變,其中尤以晉察冀最為嚴重。
按照中共晉察冀分局的綜合分析,1939年經濟困難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自然災害接連不斷。春季旱災,夏季水災,秋季蟲災,冬季敵寇的掃蕩進攻和“三光政策”,直接造成糧食菜蔬棗果損失在十余萬石以上,導致“邊區糧食生產量與存糧絕對的減少了”。二是“敵寇以其占領的某些據點,施行其破壞邊區經濟的陰謀,封鎖與隔斷邊區內部的糧食交通,引起購糧與運糧的困難,致若干地區的糧食供給來源也減少了”。三是“邊區內部有些縣區采取了糧食本位主義的錯誤政策,違反了邊區內部有無相通的自由貿易的原則,而奸商復乘機囤積糧食,操縱居奇,高抬糧價,……加以敵寇有計劃之破壞,利用奸商以少數糧食向邊區內部不等價的交換其它物品,激漲糧食之價格”。[12]
(三)1940年春夏晉察冀根據地的經濟困難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1940年伊始,晉察冀根據地經濟形勢的惡化,便以大規模的“災民”和“春荒”形式兇猛地表現出來,成為整個華北抗日根據地經濟形勢的縮影。
首先,日寇在1939年的冬季掃蕩“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給全邊區以更多的困難,他企圖用燒殺的辦法,增加我們的經濟困難,以動搖全邊區人民的抗日決心,削弱邊區抗日的物質力量,挑撥邊區人民與政府軍隊之親密關系等,因此救濟被燒殺地區災民的工作,成為當前的重要工作之一。”為此,邊區政府公布了救濟辦法并撥出巨款進行急賑。但是,由于“災情嚴重”和“對敵人的燒殺所造成的困難估計不足”等原因,救濟工作并“沒有收到應有的成績”。[13]
無獨有偶,救災工作尚未取得完全成效,更為猛烈的“春荒”又接踵而至。由于1939年“糧食生產量與存糧絕對的減少”,到1940年初春,多數農民缺少3個月的口糧,饑餓迫使老百姓在這樣一個青黃不接的季節里,選擇了“逃亡”——“到口外去,準備明年春天再回來”。1940年2月12日《抗敵報》報道:“現在有許多地方發現了老百姓的逃亡。如在唐縣曲陽阜平淶源等縣都有這種現象。在唐縣二區黃石口村,有一百一十多家,逃亡的就有三十多家。”[14]
這則報導有三點應該特別重視:一是逃亡的范圍是“有許多地方”,即逃亡是一個普遍的而非個別的現象;二是逃亡的比例竟然達到總戶數的四分之一以上,即使這一比例是最高比例,也仍然顯得過高;三是報道的時間為農歷正月初五,也就是說春節還沒有過完,大批的農民即走上了背井離鄉的逃荒之路,甚至其中有一部分人的春節就是在逃荒的路上度過的。
據晉察冀邊區“群眾團體聯合會”的分析,老百姓逃跑的原因有三個:一是“有些地方經過了水災又經過了敵人的燒殺,一些認識不夠的群眾,感覺沒有辦法”;二是“頑固分子漢奸的造謠破壞”;三是“有些老百姓沒有地種,生活沒有著落”。[14]毫無疑問,老百姓“感覺沒有辦法”、“生活沒有著落”是導致逃亡的最直接的原因。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春節前后大量的人口逃亡現象并不意味著逃亡的結束,反而恰恰是更大規模逃亡的開始。如果不能盡快解決老百姓“沒有辦法”、“沒有著落”的問題,“逃亡”將會在春節過后迅速傳導到整個邊區,而大量人口的出走,必將影響到即將到來的“春耕”,造成更多土地的“撂荒”,造成“春荒”的深度蔓延——夏糧的大幅減少,從而引發根據地更大的經濟困難并最終演進成經濟災難。
(四)“搶收”是普遍開展交通戰的主要原因
為解決“春荒”、“逃亡”問題,晉察冀根據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廣泛宣傳,建立合作社,組織起來,互相幫助,募集借貸,興修水利,打擊頑固分子,減少抗戰服務與自衛隊的集訓時間,適當的解決沒土地種的農民的生活問題并設法租給土地等等,[14]經過前后五個月的努力,逐漸解決了“逃亡”問題,基本完成了救災運動,終于艱難地看到了走出“春荒”的希望。
救災運動剛剛結束,“搶糧”與“反搶糧”的斗爭便如期而至。1940年上半年,敵我雙方都遭遇到嚴重的“糧荒”,即將到來的麥收無疑也成為敵我雙方最為關注的事情。所以“爭奪麥收的斗爭,已成為敵我在冀中冀西當前斗爭的中心”。5月22日《抗敵報》在頭版發表社論指出:“目前邊區人民的中心任務,除了繼續進行廣大的從軍運動,完成武裝動員計劃外,便是粉碎敵人對冀中平原的‘掃蕩’,并加緊保衛麥收的戰斗動員,隨時準備迎接和粉碎敵寇在麥收時繼續及可能的進攻與掠奪”。
為奪取“爭奪麥收”斗爭的勝利,邊區軍民采取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積極主動地襲擊、擾亂、迷惑和疲困敵人;實行臨時戒嚴、清查戶口,防止漢奸敵探的破壞活動;集中人力、物力,“快收、快打、快藏”,“分割、分曬、分打、分藏”,“隨割、隨曬、隨打、隨藏”,迅速完成麥收,縮短麥收時間等,其中最為關鍵,也是最有效的一個環節,便是“有計劃地大量地破壞敵人的交通及一切運輸工具”。
1940年5月26日,晉察冀邊區政府進一步發出了“武裝保衛麥收,勝利完成麥收”的號召,明確提出 “我們必須保護麥收,不為日寇漢奸掠奪焚燒,才能渡過麥秋之間的糧食難關”,“護麥是當前堅持抗戰的緊急任務”。[15]
自5月下旬開始,華北各根據地普遍掀起了交通戰的熱潮。“華北各地一致動員,交通戰普遍展開,太北動員以破路為主要工作之一,平漢路沿線我邊區軍民破路活躍……”。“我邊區軍政民密切配合,一面攻襲敵寇據點,同時各地加緊破壞交通,……”。 “自白晉北段鐵路為我軍民徹底破壞后,晉南敵寇后路全部斷絕”。[15]諸如此類的報道,屢屢見諸報端。
正是大規模的、全面的交通戰,為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遲滯日軍進攻,創造有利的麥收空間和時間提供了條件,也為奪取麥收斗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五)“百團大戰”是交通戰的繼續
麥收斗爭的勝利,只是解決了燃眉之急。隨著日軍掃蕩頻次的增加和“三光”政策的普遍實施,“我抗日根據地愈見縮小,部隊給養供應困難。日軍又封鎖與隔絕我各抗日根據地之聯系” ,“從一九四0年三月前后至七月,華北抗日根據地大片地迅速變為游擊區。大破襲戰之前,只剩下兩個縣城,即太行山的平順和晉西北的偏關。原來一面負擔的群眾變為兩面負擔(既對抗日政府負擔,又對偽政權負擔)。”[16]235根據地的困難更加嚴重。
自敵后根據地建設以來,抗日軍民對付日軍進攻特別是頻繁的“掃蕩”的最為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對敵人交通的破襲戰,這是我們在游擊戰爭中經常進行的,幾乎天天都在破襲”。據聶榮臻的回憶,“發動正太路破襲戰,是一九四○年的春天”,“就醞釀確定的”。[17](494)他認為,“破襲正太路,或者破襲平漢路,這是游擊戰爭中經常搞的事情,可以說,這是我們的一種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戰略問題”。[17]508也就是說,以破襲正太路和其它主要交通線為主的“交通破襲戰”,其初衷與此前破襲平漢路、白晉鐵路一樣,只是根據地軍民反擊日軍進攻的一種戰術而已,后來由于“宣傳上出了毛病”,這場“交通破襲戰役”才被人為地賦予了戰略意義。[17]508
“百團大戰”發起于8月20日,恰逢華北地區即將進入秋收時節。1940年8月24日晉察冀邊區青救會抗先隊部向全體青年發出“武裝保衛秋收”的號召,強調“保衛了秋收,不只是邊區的軍隊和人民都有了口糧的,并且還會把敵人困起來,粉碎他‘以戰養戰’的陰謀毒計。”[18]正如“保衛麥收”一樣,“保衛秋收”便成為破壞敵人交通線最直接的目的。對此,1940年8月27日《抗敵報》社論明確指出,在百團大戰中,“我邊區人民子弟兵此次全線出擊和取得勝利,特別有意義的是積極的保衛了邊區的秋收和偉大的民主運動,有力的打擊了敵人對邊區的秋收和民主選舉的武裝破壞。”[19]9月5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發出 “保衛秋收、保衛糧食——為邊區一千五百萬人的生活而斗爭”的號召,更明確提出“護秋是當前緊急的戰斗任務”,強調“糧食是我們的生命線,糧食是堅持邊區抗戰的決定條件;我們必須有足夠的糧食,保證一千五百萬人民都有飯吃,保證邊區壯大了的子弟兵,有充分的給養!”要為“保衛秋收,保衛糧食而戰!”[20]
四、結語
經濟問題如影隨形地存在于整個抗日戰爭進程之中。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是決定中日戰爭總特征的根本因素,而中日兩國各依其自身實際所制定的作戰方略,決定了中日戰爭的非對稱性;緣于這種非對稱性的得失利弊的轉換,最終決定了中日戰爭的結局;而決定這一轉換過程的速度和效率的最基本因素,便是戰爭雙方的經濟狀況。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是在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經濟環境下創建和發展的。其經濟環境與經濟特性決定了其利弊互現的兩個方面,即應付生存能力強,應對戰爭能力弱。這一強一弱,決定了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也決定了游擊戰爭的作戰方針,還決定了經濟問題往往是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基本甚至是最重要的問題。
交通破襲是游擊戰爭的基本方法和“日常工作”,其范圍和程度與日軍的進攻強度成正比例關系。1940年交通破襲戰在華北地區特別是在晉察冀地區大范圍廣泛開展,是日軍的“囚籠政策”和反復“掃蕩”所造成的根據地形勢惡化,經濟困難加劇的結果,“百團大戰”只是眾多交通破襲戰中最為突出的一次,發起該戰役最直接的目的乃是“保衛秋收”。
[1] 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3]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黨史資料(第23輯)[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4] 李富春.對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政策的意見[J].共產黨人,1941(18).
[5] 彭真.在首都各界人民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85-09-04(1).
[6] 中共中央書記處.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陳云.陳云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 朱德.論發展邊區的經濟建設[M]. 新中華報,1940-10-13.
[9] [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2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0] 中共中央書記處.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 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邊農救緊急號召加緊救災準備春耕[N].抗敵報,1940-02-18(1).
[13] 當前救災工作中的幾個問題[N].抗敵報,1940-01-05(1).
[14] 怎樣解決老百姓逃亡部下[N].抗敵報,1940-02-12(4).
[15] 武裝保衛麥收,勝利完成麥收[N].抗敵報,1940-05-26(4).
[16]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7]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18] 武裝保衛秋收[N].抗敵報,1940-09-02(4).
[19] 社論.積極動員配合八路軍百團大戰[N].抗敵報,1940-08-27(1).
[20] 保衛秋收、保衛糧食——為邊區一千五百萬人的生活而斗爭[N].抗敵報,1940-09-06(4).
責任編輯:熊 偉
2015-05-20
高心湛(1963—),男,河南長葛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政治與文化。
K265.1
A
1671-9824(2015)04-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