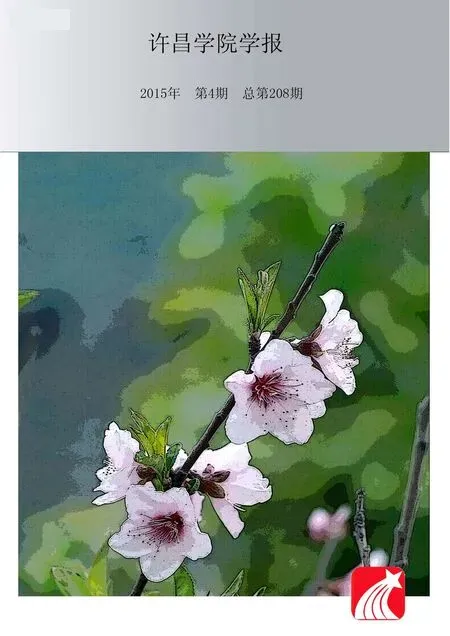論曹禺《原野》的神秘主義
肖 慶 國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0)
論曹禺《原野》的神秘主義
肖 慶 國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0)
曹禺的《原野》中充斥著許多神秘主義的元素,它們錯綜復雜,或明或暗,歷來為許多評論者所詬病。神秘主義的面紗遮住了《原野》的真實面目,也造成長久以來評論者對于人物形象等方面的誤讀。從文學觀念層面和創作方法層面著手,對劇作中的神秘主義給以詳盡的分析,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理解《原野》。
曹禺;《原野》;神秘主義;文學觀念;創作方法
正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聯所倡導的革命文學席卷文壇之時,曹禺卻創作了耐人尋味的《原野》,這似乎顯得十分不合時宜。所以自從《原野》一問世,便遭到了當時批評家們幾乎一致的指斥。而在眾多的批評聲中,有一種不能被忽視的存在,即批評《原野》充滿了神秘主義的氣質。神秘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的文藝批評標準是截然對立的,批評家們的“不接受”也就此“閹割”了曹禺的戲劇創新。從新時期以來,隨著文學時代語境的不斷開闊,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和評價《原野》的藝術成就。所以,其中的神秘主義元素也理應被重新闡釋。我們認為“神秘主義”是“一種宗教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主張人和神或超自然界之間直接交往,并能從這種交往關系中領悟到宇宙的‘秘密’。”“現代西方流行的一種文藝傾向。否認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強調表現個人難以捉摸的感受、幻象,或某種超自然的幻覺,使藝術創作服從于盲目的本能和神秘的愿望。”[1]3464-3465
實際上,《原野》的“神秘主義”是有章可循的,并且呈現為一定的整體性,本文試圖從文學觀念層面和創作方法層面來對《原野》中的“神秘主義”作出分析。
一、文學觀念的神秘性
文學觀念的不同,往往會帶來文學世界的差異性。在《原野》里,曹禺有意地選取了很多帶有神秘色彩的對象世界,比如巫術、鬼神、夢境等,這些都可以歸于宗教或民間信仰。我們認為是曹禺所選取的文學對象自身的神秘性增加了《原野》的神秘戲劇氛圍,這主要是戲劇家在其獨特的文學觀念下的刻意的選取。
《原野》中的巫術主要表現為“木人扎針害人”、“燒紙錢安神”和“喚魂”。如果我們來探討巫術的神秘性,似乎就陷入了脫離戲劇文本來獨立談巫術之神秘,這顯得沒有必要,因為巫術本身就是神秘的,“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對客體加強影響或控制的活動”[1] 4152。問題的關鍵在于,劇作家選取巫術來營造劇本的神秘氛圍,其背后究竟暗含著什么用意?
在第一、二幕的開頭詳細介紹了焦家的陳設,這里劇作家有意地營造了一個鬼神的世界:焦閻王半身像、香案、祖先牌位、菩薩等。而這一切無疑都是作者在獨特的文學觀念下“刻意的選取”對象世界進行文學表達。試想,有誰家會掛著死人的“巨闊、油漬”[2]379的半身像并且“旁邊掛著一把銹損的軍刀”?[2] 379又有誰會在家里供奉“三首六臂的”[2]379“油亮的黑臉上,顯得猙獰可怖”[2]424的菩薩?即便是寺廟里也很少有黑臉的菩薩,焦家被描繪得沒有一絲人氣,倒更像是供奉鬼神的祠堂。
焦母的一個夢境可謂是鬼氣森森,她夢見了焦閻王穿著孝衣渾身是血遠道而來,抱了小黑子不放手,眼淚不住地往下流……我們讀到這里的時候,往往會覺得有一股迎面而來的逼人的神秘感,還混雜著另一個感覺——恐懼。以往對于《原野》神秘主義的探索,并沒有將神秘與恐懼作以區分,二者常常相伴而生(如鬼神給人的感覺),但不是一個相同的概念。我們試想焦閻王活著的時候,這夢境在現實中進行,焦母只會覺得恐懼,但不會有多少的神秘感。這情景為何在《原野》里表現得如此神秘?因為這是在夢境中所發生的,夢的本身就具有神秘色彩,并且焦母將她的夢作為對現實未來的一種神秘的“指示”。
巫術、鬼神和夢境都是與焦母緊密相關聯的,因此焦母的人物形象也長期飽受著褻瀆:“焦氏幾乎成為一個充滿惡毒心機的化身,由她在那里布置全套,誘使金子和仇虎就范。”[3]132“其他的人物有焦閻王之妻焦母,是個毒如蛇蝎的瞎子。”[4]80然而細讀文本,倒并沒有一處能說明焦母參與了焦閻王對仇虎一家的禍害。老中國鄉村里丈夫在外謀事,倒并不一定與妻子事先商量好。焦母深知仇虎的出逃帶著兩家的血海深仇,會對焦家的人有血光之災,她就立刻報告了偵緝隊,并進行了一系列的布置。焦母對花金子的疑慮,在后來花金子“幫助”仇虎殺害自己的丈夫時也得到了驗證。這樣看來,焦母首先是無罪的,她的行為也就在情理之中。可是,《原野》最后終于還是將焦母的一系列的“掙扎”擊打得粉碎,我們認為巫術、鬼神和夢境自身的神秘性背后深藏著人類普遍命運的神秘性。正是焦母(一個瞎老太婆)對于自己(乃至于焦家)的命運的無法掌控,她才借助于媒介——巫術、鬼神和夢境等——來做無謂的“掙扎”,以試圖掌控神秘的命運。
二、創作方法的神秘性
《原野》的神秘主義不僅僅限于劇作家文學觀念的層面,還體現在其所努力運用的創作方法層面。《原野》曾經被譽為“中國化的瓊斯皇”,與其表現主義的創作方法是相關聯的,而象征主義卻被曹禺從《雷雨》中便保留了下來。此外,《原野》里曹禺還精心地刻畫第六感,并促成種種巧合,并調用了色彩來繪成神秘的畫面。
《原野》序幕在一開始便不惜用大量的筆墨對原野進行了一番描繪,作者主要描寫了幾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景物。我們選擇對其中的巨樹來展開詳細的論述,因為它見證了仇虎復仇的始終,也最具象征性。
巨樹外貌的高大、蒼勁,暗喻了主人公仇虎的形體特征與內在氣質。“它象征著嚴肅、險惡、反抗與幽郁,仿佛是那被禁錮的普羅米修斯,羈絆在石巖上”[2]353,巨樹又被比作被禁錮的普繞米修士,羈絆在石巖上,這與仇虎的“鐐銬”有相似之處。
《原野》中的象征意象隨處可見,比如火車、鐐銬、野塘、黑云等等,而這些撲朔迷離的意象的綜合,又統一為某種意象群,使得整個《原野》都充滿了象征意義。而象征主義的創作方法作為中國二十世紀初“文學的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它所要闡釋的是個人主觀的內心世界,用以表達令人難以捉摸的幻覺,其內容是神秘主義。
《原野》令人最感覺神秘的地方,應該是一直不斷被人闡釋的“走不出的黑森林”。在黑森林里劇作家綜合了許多的表現主義的戲劇舞臺效果,比如燈光(紅燈籠)、音樂(喚魂、鼓聲)、假面(人形)等等,終于將《原野》的神秘主義推向了極致,整部劇所展開的戲劇沖突也在這里走向了高潮。表現主義強調“閉上眼睛”來看自己的靈魂,探究個人的內部視野,表現為現實的扭曲和抽象化,尤其用來表達恐懼、神秘的內心隱秘。仇虎“走不出”的表象是“黑森林”,而其內在實質是走不出自己被命運所設的圈套。命運賦予了他復仇的責任,而焦閻王的缺席使得他的復仇失去了直接對象,終于在“父債子還”的傳統文化律令下違背著自我的良心去殺害焦大星——一個懦弱的老好人。劇作家從而將仇虎復仇的外部沖突轉化為了心靈的沖突,命運的神秘在表現主義的推波助瀾下達到了頂峰。
《原野》中有少數的幾處巧合,比如“焦花氏:(望著她)昨兒格,我夢著大星回了家。”[2]400“焦大星:(煩惡地)哭!哭!哭!今天這孩子是怎么回事,簡直是哭我的喪。”[2]425“焦大星:(低聲)——他仿佛死了似的。”[2]427等等,然后緊接著這些隨口而出的“預言”卻都變成了真實:大星回家了,焦大星喪命,小黑子死了。還有,焦大星被仇虎殺死的時候喊著“好黑!”[2]470,仇虎進入黑森林的時候無意地重復著這句話;仇虎在焦家的時候唱著《妓女告狀》來惱焦母,進了黑森林中卻被白傻子《妓女告狀》的聲音如同魔咒般糾纏。這些巧合都給《原野》獲得了神秘感。曹禺曾經在《雷雨》中構造了太多的巧合,可是《雷雨》采用的鎖閉式結構使得三十年的恩怨集中在一天里發生,強烈的戲劇沖突所產生的緊張感使得“過分的巧合”被掩蓋了。吸取了《雷雨》“太像戲”的教訓,《原野》散文式結構下的巧合便被設計得輕微不留痕跡,從而表現得似乎更加接近“真實”。這份“真實”仿佛告訴讀者,乃至劇作家自己,人的命運被冥冥之中的某種神秘的力量所主宰。
我們再來對《原野》中的顏色,作出如下譜系歸納:
黑色系列:黑黑的兩條鐵軌、白磁箍上的黑線、黑云、黑坎肩、黑森森的密云、黑香案、烏黑的香爐、黑臉的菩薩、暗黑的墻、黑緞褲、黑緞袍、菩薩油亮的黑臉、黑林子、胸前黑茸茸的、黑布褂、森林黑幽幽、黑團團的樹叢、黑色的肌肉、黑袍、烏黑的山巒、黑郁郁的樹林。
紅色系列:血湖似的云、幽暗的赭紅的云、紅紅的燈火、紅云、紅色的綢簾、紅拜墊、紅棉托、暗紅的舊式立柜、紅綢襖、紅絲線、血紅的里子、紅花、烏紅柜、紅燈籠、血紅色的緊身、半裹了紅布的手槍。
藍色系列:藍線帶、藍布褂、藍布的褲、青藍火焰的螢火蟲。
白色系列:白磁箍。
灰色系列:灰布褂。
不難看出:整部《原野》主要被黑色和紅色主宰。整部劇似乎在用一幅幅顏色艷麗、怪異的油畫,向我們傳達著神秘色彩。
“紅色可以從絕對的否定生命(侵犯、殺戮、血債血還)到絕對的肯定生命(生命力、愛情、健康)。”[5]19-20黑色似乎從來就是不祥的代表,“黑色是否定生命的顏色,對所有的積極的事物的拒絕,對發展的無條件的否定。”[5]135“黑色首先是與長年重病、衰敗和死亡同等意義的。”[5]136而除此之外,《原野》的所有矛盾沖突幾乎被安排在“黑暗”中進行。《原野》共分為三幕,總的時間是秋天,序幕是立秋后一天傍晚,第一幕是下午六時,第二幕是夜九時夜十一時,第三幕是夜一時后、夜二時后、夜三時后、夜四時后、六時后。即使第一幕是下午六時,也終究是霧太大。人類對黑暗的恐懼,似乎是與生俱來的。黑暗代表著未知和死亡,而無論是未知還是死亡,都充滿了不可言喻的神秘。
曹禺在獨特的文學觀念下,借助現代的文學創作方法,給《原野》鋪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在抗日戰爭的激流下,劇作家仍然能潛心地沿著五四探究“人”的命題而“我行我素”,創作出具有獨特美學價值的劇本,這是難能可貴的。
[1]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2] 傅光明.曹禺劇作[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1.
[3] 田本相.原野論[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1(4):122-141.
[4] 陸煒.《原野》中的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原野》新釋[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4(2):78-84.
[5] [德]哈拉爾德·布拉爾姆.色彩的魔力[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石長平
2015-02-15
肖慶國(1992—),男,江蘇盱眙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I207
A
1671-9824(2015)04-00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