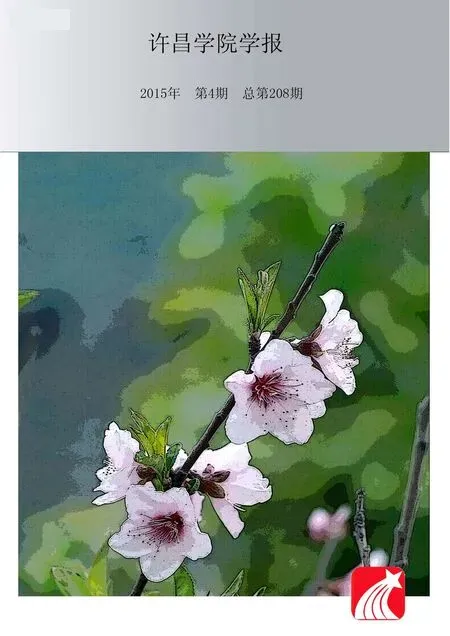知識科學與哲學中“本體”概念通約的可能性
姬 超,張 娜
(1.許昌學院 中原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河南 許昌 461000;2.許昌學院 圖書館,河南 許昌 461000)
知識科學與哲學中“本體”概念通約的可能性
姬 超1,張 娜2
(1.許昌學院 中原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河南 許昌 461000;2.許昌學院 圖書館,河南 許昌 461000)
知識科學旨在解決信息化時代信息過剩與知識匱乏并存的問題,因而代表著信息革命的又一次深化。基于本體的設計思想在知識科學領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但以智能化為特征的知識處理技術卻面臨發展瓶頸,對技術的迷戀和自負在面對異質性知識交互、共享和增值時顯得力不從心。與邊緣和交叉學科的對話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人文科學視野下重新審視了知識科學和哲學兩種話語體系中“本體”通約的可能性及可能的通約路徑:動態化、主體化和過程化,從而為知識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出路和規范框架,也為人類重新認識科學的意義和價值提供了一些參考,同時為哲學重建本體論提供了方向。
知識科學;本體;哲學;通約
知識科學旨在通過不同信息系統的集成和交互,實現知識獲取、知識共享和知識增值,這就需要首先將知識轉化為一種可以被計算機識別的語言體系,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智能計算機技術的突破,因此知識科學代表著信息化時代計算機領域進一步開發、研究和應用的重點方向。隨著本體論思想的提出,基于本體的設計思想在知識獲取、語言處理、信息識別、數據庫集成、知識共享等方面的應用日益廣泛。然而,當前基于本體論思想開發出來的技術仍然存在許多問題,由于知識的形式化深度不夠等,嚴重制約著計算機與用戶以及計算機系統之間的高效交互,從而使得知識科學一定程度上陷入發展瓶頸,本體論于是成為知識科學發展過程中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單純依靠技術手段的突破實現知識科學的發展極有可能陷入又一次類似“信息過剩”的“知識過剩”,因此在尋求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重新追溯“本體論”這一概念將是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方向。從科學發展史來看,學科之間的交流和對話對于促進科學發展意義重大,而且效果明顯,通過吸收交叉與邊緣學科的有益成果,深化學科融合日益成為推動學科發展的重要力量。在這種趨勢下,我們探究知識科學和哲學中“本體論”概念、通約的可能性及可能的通路,以此為知識科學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一、知識科學中的“本體”概念
(一) 知識科學如何實現
1.知識科學興起的背景。在信息化時代,隨著IT技術的進步和網絡的普及,信息革命在提高生產力和影響人類生產、生活方式方面釋放了巨大的能量。與此同時,信息污染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造成信息過剩和知識匱乏并存的局面,人們擁有海量信息但在面對具體問題時卻仍然缺乏準確的知識來應對。這表明了當前信息處理技術的局限性,由于大部分的信息資源都是孤立存儲于網絡媒體等介質上,不同領域之間的信息在數據格式、語言編譯、體系結構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只能適用于特定的領域并服務于特定的對象,這就限制了從信息中提取知識以及知識的共享和重用,知識在交互使用中實現增值更是無從談起,結果導致了海量信息雜亂無序地散布于網絡平臺,不但容易引起網絡堵塞,還進一步增加了用戶甄別有用信息的難度。在這種背景下,就迫切需要對信息處理技術加以擴充,增加知識處理功能,實現知識服務的智能化操作,達到高效的從信息系統中表示、獲取、利用、重用、共享并維護知識的目標。
2.知識科學如何實現。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費根鮑姆在1977年“第五屆人工智能國際會議”上首先提出“知識工程”的概念,標志著知識科學的產生。通常認為知識工程屬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分支領域,可以認為知識科學是研究通過智能計算機模擬人類活動的一門新興學科,它以知識為研究對象,根據人工智能相關原理和技術開發構造智能型知識系統。該系統“通過模擬人腦進行問題求解,相應的由一系列的支持和輔助系統共同組成,包括專家系統、知識庫系統、決策支持系統、自然語言理解、智能機器人、模式識別、自動程序識別等。”[1]模擬人腦的智能特征決定知識科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腦神經網絡研究的最新進展,這也使得知識科學的發展充滿挑戰和挫折,因而知識科學建設也是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
最初人們嘗試通過完善信息系統的管理實現知識共享,相應地開發了一些新的知識技術,包括面向知識的系統、文獻管理系統、自然語言處理、Hypertext、分布式人工智能等知識管理技術。顯然,這些技術距離知識的智能化處理還很遠,但對于知識科學體系建設卻是基礎性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隨后,“知識處理技術進一步發展到語義Web、本體論、貝葉斯分類器、自然語言處理、基本代理、虛擬協同和聯合、多語言實時自然語言處理、網格計算等復雜技術,目的在于更好地表示進而獲取知識,以及對知識內容的自動化分類、集成系統構造和知識管理,最終實現知識的高效、便捷共享。”[1]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如何將分布于不同領域、不同類型、不同存儲格式、不同分布和構造特征的信息加以提取和轉化為知識,這就需要語義Web技術的開發并賦予信息計算機可理解的語義。面對類型如此眾多的異質性信息,這項技術開發的難度可想而知,對知識的語義表征首先成為橫亙在知識工程項目開發面前的巨大障礙。在該問題得到解決的前提下,經過計算機智能識別的知識還需要傳遞給恰當的受眾,完成知識的網絡發布,這既可以通過建立文檔討論空間實現,也可以通過遠程交流技術和異步會議技術實現。但若要實現知識的更新和增值,還需要開發更加友好的支持系統以容納不同領域用戶以接近自然語言的形式對知識提出請求,這意味著知識科學還面臨滿足不同用戶多樣化需求的艱巨任務。
(二) 知識科學中本體概念的應用
根據以上描述,知識科學必須要突破專家決策和操作的局限才有可能在現實應用中獲得普及和推廣,其中關鍵的環節就在于對知識進行語義表征的技術在標準化和適應性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以滿足用戶對知識系統的互操作性和共享性。最近興起的語義Web技術為此提供了基本框架,作為構建語義Web的基礎,本體研究就成為在不同分類系統之間進行互操作的關鍵技術。[2]所謂“本體”是指不同系統共享的基礎概念的規范的、明確的形式化說明,從而為不同系統之間的互操作和共享提供了基本框架。本體由五個模塊即概念、關系、函數、公理、實例構成。[3]它們共同界定并規范了對象,“基于Web技術的工具就可以實現對本體的創建、編輯、瀏覽和使用。”[3]進而通過不同形式的本體表示機制構造更加高級的知識庫和知識系統,從而將知識工程推向新的高度。根據內容劃分,本體包括“知識表示本體、通用本體、領域本體、語言學本體、任務本體”五種類型。[3]根據不同目的,專家開發設計了不同類型的本體,開發模式根據應用需要也是類型多樣。
(三) 本體設計的發展瓶頸
作為揭示事物存在的本質,本體必須為人們提供關于某一事物的本質認識,其中不僅包括事物自身,還包括關聯事物以及事物變化的認識,更要指出事物的具體存在和抽象存在的具體聯系,只有這樣才能為知識工程的系統開發提供堅實的基礎。顯然,當前的本體開發仍然局限于分立的領域,適用范圍極其有限,內容深度和形式化程度都遠遠不夠,距離揭示事物的“本質”還有很遠的距離,也就限制了信息系統之間、人與計算機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操作,因此基于本體的設計思想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盡管語義Web技術和云計算的最新進展為此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對于知識科學能否在原有思路下實現突破性進展,我們不得不保持謹慎態度。
二、哲學中的“本體”概念
為了更深刻理解“本體”的真實含義,工程學領域的專家有必要首先了解人文科學視野下的“本體”概念,從而為自身研究尋求根源意義上的哲學指導。知識科學服務于經濟與社會發展需求的宗旨決定了在工程領域追溯本體淵源的必要性。
(一) 哲學中的本體論
本體論(ontology)的英文詞匯由希臘語ον(存在)和λγοζ(理論)組合而成,核心任務在于研究事物的本質和終極存在。盡管本體論一詞直到1613年才由德國哲學家Rudalphus Goclenius提出,并由另一位德國哲學家Christian Wolff在18世紀進行明確定義,但本體論的哲學思想古已有之。據史料記載,古希臘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Thales首次提出萬物本原問題并認為水是萬物之本,他也因此而被公認為世界第一位哲學家。隨后,中西方許多學者和思想家都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探討。很長一段時期以來本體論都被認為是哲學中最為重要的問題。
本體論研究萬物存在的本質問題,探究世界產生的終極原因。因此本體具有最抽象和最普遍的哲學屬性,具有“最高”、“最根本”、“第一”的含義,包含普遍的、一般的規定性,它不特指某一具體事物卻又不泛指萬物。可見,本體論區別于現象等經驗事實而存在,是一種“超驗”形式的存在,是一種“純粹的邏輯規定性”,是“西方哲學特有的形態”,是“與經驗世界隔絕或者先于經驗世界的理念世界、絕對精神、純粹理性的領域”。[4]于是本體就像具有某種意志一樣,“能動的生發萬物,使之統一于一個體系而具有一定秩序”。[5]在這個基礎上,本體論以及哲學的研究領域得以界定,人們也開始以另一種方式思考經驗現實,其他學科從而具備了自立的先決條件,本體論最終衍變成了終極意義上的思考。[6]這也是知識科學和哲學中兩種“本體”概念分立的原因所在,兩者之間被認為不具有實質性聯系。但是根據前文的討論,哲學中的“本體”概念顯然為知識科學中的“本體”思想提供了原始的靈感和思路,后者的“本體”實踐也為哲學中本體論的發展提供了最新的現實支撐和經驗素材。綜合考慮兩種“本體”的聯系為兩個領域的理論更新和發展都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哲學中本體論的演變
1.樸素本體論階段。最初,人們試圖從萬物中找到某種基礎物質,它可以決定其他一切事物卻又不受其他事物的影響,這種物質就稱為本體,又叫做“始基”。例如前文提到的Thales認為世界的本體是水,阿那克西米尼認為世界的本體是氣,赫拉克里特認為世界的本體是火,畢達哥拉斯認為世界的本體是“數”,德謨克里特認為世界的本體是“原子”,等等。[7]可見,盡管古人對本體的認識存在很大局限性,卻是一個不斷抽象,逐漸超越事物表面向世界深層次探索的過程,而這也恰好符合本體論的內在規定。
這一階段的本體論探討不得不提到蘇格拉底,他首倡對事物特殊屬性的理性析出而得到永恒的、絕對的概念體系。柏拉圖繼而完善了概念本體論體系,他認為事物都是變動不居的,因而依靠人們感官感知到的都是不真實的,真正實在的是獨立于事物和人心之外的概念,稱為理念。哲學的任務就是依靠邏輯思維把握理念世界的本質和內在秩序。進入到黑暗的中世紀以后,宗教神學開始壓倒一切。上帝成為哲學中的唯一本體和終極主宰者,一切教條和理論都圍繞論證這個最高本體而展開。直到文藝復興運動之后,本體論才開始肯定人的精神和尊嚴,強調人的理性和意志的重要作用。近代本體論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在繼承兩千多年來各種本體論學說的基礎上對本體論做出了最為完善的總結。在黑格爾那里,“絕對精神”以純概念的形式存在、運動和發展,每一個概念內部又充滿矛盾和對立,從而導致概念的不斷“異化”,最終達到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至此,人們也開始放棄任何進一步討論本體論的興趣,任何試圖發展本體論的努力都好像是徒勞而多余的,本體論在實際上陷入停滯。
2.主體生成的本體論階段。隨著人本主義的興起,人們逐漸開始關注人在本體當中的作用。主體之外的一切東西構成“對象”或“客體”范疇,主體成為萬物的本源和基礎。這里的主體實際上指的就是人本身,隨后主體概念進一步擴展為心智主體、語言主體和行為主體,大大豐富了主體生成本體論的內涵和外延。關于主體如何生成,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對此進行了回答:人類意識的自身活動構成自身存在的前提,主體通過自身意識和反思使自身的存在成為可能。主體的展開和自身的實現就表現為不斷外化為“自己的他物”,又同他物在更高階段實現統一。更為徹底的,馬克思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通過勞動實踐將主體和客體辯證地聯系在了一起。馬克思首先認為人最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存在于自然條件當中。人的生命過程首先體現為一個自然生物過程,與其他生物一樣需要與外界環境進行能量交換,遵循生物運動的自然規律。同時,人又絕非消極等待,完全被動依賴和受制于環境,而是主動地、有意識地、創造性地通過勞動實踐改造自然環境,從而不斷超越自然存在物。這種雙重性在使人類獲得發展的同時也使得人類與自然越來越對立,逐漸分化成二元世界。人也越來越分裂,陷入多重矛盾的困擾,人便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解放自身從而在更高層次實現統一和超越的。[8]
(三) 本體論的困境
一方面本體論為人類的存在提供終極意義上的理論訴求,也為科學等一切其他現象提供合法性依據;另一方面形而上的特征也使得傳統本體論拒絕走進“虛假”的經驗世界和現象中去,脫離實際的本體論愈發不適合科學理性和人類進步的需要,也就無法繼續為人類活動提供價值評判標準。相反,其他應用學科在科學主義和理性精神的指導下不斷獲得進步,在認識和改造世界上顯示出了巨大威力,使得本體論逐漸被排斥在經驗科學領域之外。
三、知識工程與哲學中“本體”概念的比較
(一) 兩種話語體系中本體概念通約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本體”在知識科學和哲學當中發揮的具體作用有所不同,知識科學中的“本體”更多地承載認識論和工具論范疇的功能,而哲學中的“本體”概念則構成該領域的核心內容。本體論與認識論、形而上與形而下的長期對立一定程度上表明兩個“本體”概念通約的難度,嘗試調和知識科學與哲學兩個表面看來截然不同的學科領域更是充滿挑戰和風險。然而,無論是知識科學還是哲學,它們都面臨著發展瓶頸。在哲學中根據經驗科學的最新進展重建本體論的任務已經提上日程,迫切需要知識科學以及類似知識科學的學科進步提供最新的認識論基礎,而知識科學也需要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學科的發展方向,從人文科學視角反思科學的目的和價值,扭轉那種深陷技術泥沼的局面,以更好地服務于經濟與社會發展需求。
(二) 可能的通路
1. 動態化。“本體”概念在兩種話語體系中進行通約的可能路徑之一在于動態化轉向。就哲學中的本體論而言,傳統的本體論包羅萬象,這一特征使得傳統本體論陷入長期的混亂狀態,導致本體論對于現實的解釋和指導意義有限。而其中的本體要么靜止不變,要么獨立于現實環境發生變化。在這種背景下,知識科學中的本體設計同樣顯得過于機械,要么形式單一而無法有效表征知識對象,要么過于追求某一特殊領域的適用性,兩者都使得不同信息系統之間的交互和不同知識對象的對接非常困難,從而限制知識的共享。本質上,知識區別于信息之處就在于知識的動態特征,隨著環境或應用場景的變化,知識必須得到動態的更新;隨著科學理論的發展和經驗證據的積累,基于本體設計的知識系統自身也必須得到動態的修正或再設計,即自我更新的自適應機制的實現,而這依賴于更加開放、包容的接口和界面設計,從而為不同用戶的交流和進入創造條件。同樣,本體論也需要擺脫形而上的窠臼深入到現實中去,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為科學的存在及其發展提供終極價值關懷。一方面,知識科學必須隨著經驗證據的積累而不斷更新或重構;另一方面,本體論必須伴隨認識論的變化,突破原有極限,在一個更加無限的空間和層次上為人類存在及人的解放、發展提供終極意義上的理論依據。
2. 主體化。“本體”概念在兩種話語體系中進行通約的可能路徑之二在于主體轉向。無論是本體論還是知識科學,兩者都迫切需要在主體意義上加以擴展和深化。在本體論哲學方面,主體的引入是避免以往空洞和虛無思辨的必然選擇,只有動態地考慮主體的變化和生成,本體論才有可能在終極意義上為人類提供合法性依據;在知識科學領域,本體設計也應摒棄以往見物不見人的機械思維方式。知識科學不單是要實現計算機對知識的智能化處理,還要實現計算機系統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知識交互和共享,而所有操作都由特定的主體完成,智能計算機不過是對主體之間交互的高度仿真和模擬。另外,知識科學的主旨在于滿足異質性個體的知識需求。以上表述說明,知識科學在終極意義上旨在服務不同領域、不同對象的主體,同時又在不同主體對知識的共享過程中實現知識的增值,因而本體設計需要滿足主體間性的價值訴求,摒棄以往單純依靠專家系統的決策思路。
3. 過程化。上述兩點決定了“本體”概念在兩種話語體系中的第三條通約路徑:過程轉向。無論傳統的本體論還是經驗科學,它們都經常混淆特殊和具體的關系,陷入非此即彼的簡單謬誤循環。就本體論而言,傳統的形而上學思維常常“將復雜和動態的經驗現實還原為簡單的抽象,然后又將這種抽象誤認為具體的實在”。[9]類似的,知識科學發展過程中也往往割裂不同領域知識之間的聯系,將知識片斷化和機械化。本質上,知識科學中的知識不過是行為更加復雜的信息集合,卻并不具有知識的真正特性。信息并非知識的簡單分解,因而過分簡單的用某種抽象語義規則來表征知識,達到獲取知識的目標并不可靠。知識隨著主體和場景的變化而相應發生變化:解構—重構—再解構……可見知識總是處于一個不斷再構造的體系當中。在變化過程中,主體與客體之間、主體之間、客體之間因而構成有機的關系總體,在相互聯系的事件中產生了實在,自我的存在依賴他我的存在。也正是這個過程構成了事件的本質,知識科學的進步也應轉變思路,轉變一勞永逸實現完美設計的開發策略,而致力于框架和知識規則的設計,同時將知識工程建設的任務交由不同領域、不同角色的異質性主體進行充實或更新。
四、結論
科學與實證主義的蔓延導致傳統社會崩塌和倫理價值失序,人們在面對現代社會時的焦慮感虛無感越來越強烈,日益增加的社會矛盾和個人心理問題彰顯重建本體論的迫切性和重大意義,也說明人類需要重新審視科學在整個世界的真實地位和作用,深刻反思人類理性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當中的局限性。知識科學如果繼續沿著原來的思路,沉迷于技術泥沼的自負當中,縱然云計算和大數據處理技術的進展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知識科學的發展,但終將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或者像制造信息污染一樣制造更加復雜而無序的知識擁堵,對于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毫無用處。因此,知識科學,乃至其他一切實證學科在今天都應當重新審視本學科的原始宗旨,從哲學“本體論”的角度思考科學的終極目的,在與人文科學的對話中實現本學科的包容與開放式發展。具體講,對于人類理性有必要放在整體的世界當中加以認識和理解,避免對理性的盲目自負和狂妄,避免對工具理性的自信絕對化。隨著各個應用學科在各自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人們也不能因此而自滿,而必須認識到各個分領域不過是整體世界的局部,人們必須敞開這個局部的世界,從其他領域,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和逼近整體世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本體論和知識科學的統一,才能真正接近用知識去服務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
[1] 李大玲.知識技術的發展對知識工程的影響[J].圖書情報工作,2006,(4):15-18.
[2] 魏圓圓,錢平,王儒敬等.知識工程中的知識庫、本體與專家系統[J].計算機系統應用,2012,(10):220-223.
[3] 石杰,宿彥,史曉峰.知識工程中的本體論研究[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1-3.
[4] 謝維營.本體論的“本義”與“轉義”[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1-8.
[5] 姜韋.康德本體論的特征及其對本體論發展的影響[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66-49.
[6] 倪梁康.何謂主體,如何生成——與段德智《主體生成論》相關的思考[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34-39.
[7] 謝維營.關于本體論演化的歷史考察[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130-136.
[8] 王曉紅.本體論:人之存在的理論訴求[J].社會科學輯刊,2005,(2):15-18.
[9] 閆順利,趙雅婧.過程思維與本體論遞嬗[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4):39-44.
責任編輯:師連枝
The Incommensurable Possibility of Ontology Concept between Knowledg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Science
JI Chao1, ZHANG Na2
(1.The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in Central Plains Area,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in Henan Province, Xuchang 461000, China)
Knowledge Science aims at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coexisting with the lack of knowledg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hich again represents a deepening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e application of Ontology-based design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scienc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widely, but knowled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characterized by intelligence is facing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and fascination for technology and conceit appear to be inadequate in the face of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interaction, sharing and appreciation. A dialogue with edg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which in the humanities vision re-examines the incommensurable possibility and possible paths of ontology concept between knowledg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hey are dynamic, subject and process, which provide a new way and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science, some
for humanity to re-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science and direc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ontology.
Knowledge Science; Ontology; philosophy science; Incommensurable Possibility
2015-03-16
2015年度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河南省經濟轉型的制度需求與轉型路徑研究”(2015-QN-206)。
姬超(1987-),男,河南新鄉人,許昌學院中原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原經濟區“三化”協調發展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增長與轉型,科學哲學問題;張娜(1988-),女,山東日照人,許昌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知識科學。
B016
A
1671-9824(2015)04-01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