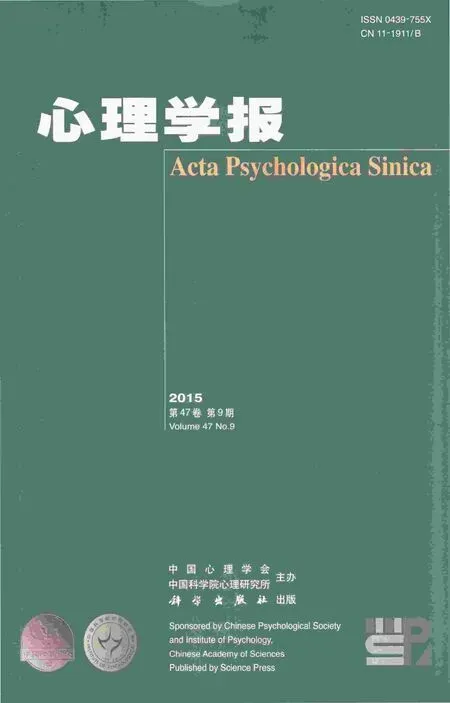領導情緒智力對團隊績效和員工態度的影響
——公平氛圍和權力距離的作用*
容 琰 隋 楊 楊百寅
(1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北京 100084) (2北京科技大學東凌經濟管理學院, 北京 100083)
1 引言
近年來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之間關系的研究已成為學術界的熱點課題, 許多研究者認為領導的情緒智力與領導風格及領導有效性密切相關(George, 2000; Vidyarthi, Anand, & Liden, 2014)。有研究表明, 高情緒智力的領導者善于自我控制和激勵下屬(余瓊, 袁登華, 2008), 易于表現出變革型領導行為(Dasborough & Ashkanasy, 2002), 還能對下屬的組織公民行為、滿意度和任務績效產生積極影響(Sy, Tram, & O’Hara, 2006; Wong & Law, 2002)。
盡管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目前只有少數研究探討了情緒智力和領導有效性之間的中介機制(Walter, Cole, & Humphrey, 2011)。如張輝華、李愛梅、凌文銓和徐波(2009)檢驗了領導能力及管理自我效能感在情緒智力和領導績效之間的傳導作用。然而現有研究尚未從公平氛圍的角度來解釋情緒智力的作用機制。公平氛圍是工作團隊作為一個整體共享的公平感, 是團隊成員公平感知的集合, 是影響團隊成員態度和行為的重要因素(Li & Cropanzano, 2009)。
團隊公平氛圍和個人公平感之間存在以下幾個不同點。第一, 兩者的研究層面不同:個人公平感是個體對組織公平性的感知, 是個人層面的構念;團隊公平氛圍是團隊成員對組織公平性的整體感知, 是團隊層面的構念(Yang, Mossholder, & Peng,2007)。第二, 兩者的形成機制不同:個人公平感源于員工自身對組織公平性的判斷; 團隊公平氛圍的形成則主要受到團隊信息分享、團隊成員“吸引?選擇?磨合”過程等組織社會化因素的影響, 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團隊成員對公平的感知逐漸趨同,從而形成團隊公平氛圍(Liao & Rupp,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