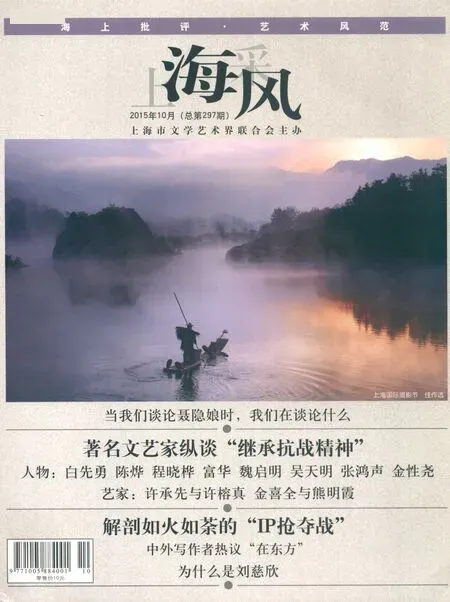任性的侯孝賢
文/黃佟佟
任性的侯孝賢
文/黃佟佟

我身邊的朋友在看完《刺客聶隱娘》之后進行了一場大清洗:原本品味一致的人展開了涇渭分明的戰斗。我還是歸之為“口味不同”。當然,那些堅決捍衛的人是真正的文青,只不過我不是。
片子當然是大師之作,但是硬傷也不少。依我看,要進入影史恐怕比較難。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我還真的和這部片子緣份非淺。最早聽到《刺客聶隱娘》大約是在2012年,在馬爾代夫香格里拉的泳池邊。身穿黑色比基尼的舒淇拿著一杯香檳,悵望遙遠的海平面,說起她最近接拍的一部電影:“一部關于唐朝俠女的片子,我不知道什么時候可以拍完,你知道侯導的電影,哈哈……但我會一直等他。”
侯孝賢對于他的合作伙伴有一種無可置疑的吸引力。《聶隱娘》的編劇謝海盟就在書里提到她身為著名小說家的姨媽朱天文對侯導無怨無悔的付出。從來狷介的大才女甘心做這個城隍廟前混大的男人的空谷和陪練,三十年如一日同他度量劇本,一日一日地討論,一遍一遍地重寫,直到有一天這個男人看完劇本抬起頭來,贊道“這個好!”他說她的劇本是給工作人員看的,最后《聶》片成片時,侯孝賢將重要場景一一剪光,朱天文一頁一頁寫傳真過去,他也不理,氣得朱天文在的士上對謝海盟說,“幸虧你寫了電影側記,不然顯得我們像傻瓜”。而他惟一的安慰是在吃飯時告訴她,“不過是一部電影”。
所以我是抱著獵奇的心態去香港書展看侯孝賢的。那天上午有一場小型的記者見面會,我進去的時候,空蕩蕩的會議室里沒幾個人,侯孝賢真人和照片并無二致,甚至更為平常。他有著客家男人典型的方頭長相,一件家常的灰色夾克,一條牛仔褲,一雙白跑鞋,一只黑色雙肩包,黑且瘦,背著包還有點勾著背,走在街上是最平常不過的精干老頭。他很少笑,對過于嚴肅的話題有著隨時消解的欲望。比如對如何拍戲這種終極話題,他就懶懶答道:“現場有什么拍什么,有什么剪什么,只有一個原則:我不喜歡的鏡頭就統統剪掉……”談到對于如何把姜文老婆周韻“勾引”過來演嘉誠公主時,他說,“就吃了一頓飯,給她講了個故事”。至于姜文有沒有反對,他訕笑起來:“姜文在旁邊干嘛呢?我又不找姜文演。”當然也偶爾會促狹地笑起來,“哎呦,查資料才發現唐朝的一品可以娶一妻十二個妾,唐朝男人可真夠累的……”也是,他生活里除了妻子,這么多年緋聞對象只有一個御用編劇朱天文,可是就算只有兩個女人,也少不了要平衡。八卦雜志爆出他和朱天文“開房新聞”的那一年,他第一次公開拉著妻子的手出席金馬獎。這多少有點以正視聽安撫原配的意思,而今年得了戛納最佳導演,公開感謝朱天文也算是有心人。
看著68歲還創作力旺盛的大導演,我感嘆不已:在亞洲男性普遍雌化的時代里,他大約是我們目力所及的東亞父權社會里最
佳大男人代表了,少言多思善聽肯忍,能擔待能成事。在社會人的那個層面,他幾乎是完美的儒家男性,忠孝仁義悌,幾乎沒有人能說他的壞話。女兒婚宴上臺灣黑白兩道全體到賀的壯觀場面,是他手面闊大結交八方的最佳證據;而作為個人的層面,“樸實,又有才華”(朱天文語);更重要的是,“沒有架子,很愛搞怪,每次叫他‘猴子叔叔’,他不但不生氣,還會撓撓頭扮猴子”(謝海盟語);到最后作為男人的層面,他又是一個私底下愛穿一身白衣,悶騷無比,自始至終擁有馬甲線的愛運動愛開玩笑的少年;他有著天然的從最底層熬出來的男性智慧,能妥協,有眼色,絕不讓人為難,又絕對能安慰人心——如果不是他告訴了舒淇這個沒有讀過太多書也沒有太多自信的野生姑娘“這世上沒有不好的演員,只有不好的導演”,可能她至今還活在三級片造成的不自信陰影里。一切人為他所用,當然,他也在努力對得起一切人。只是做他的女人比較吃虧,妻子不用說是全盤奉獻,做他的紅顏知己也很吃虧,哪怕只是請吳念真擬了幾句臺語臺詞,也堅持要把編劇的第一名頭署在朱天文前面,這在他是克己復禮的意思。
有人問朱天文為何終身未婚,她說因為她“燃點太高”。可是她也不介意提到她和侯孝賢的默契,“除了侯孝賢,很難找到頻率跟我相同的人。這么多年,我寫我的文字,他拍他的電影,兩個人一起成長,彼此之間給予養分……”這句話很高蹈,可是很明顯地,在他倆的關系里,她付出的比較多,她滋養他比較多。可是有什么辦法呢?在東亞文化里,這已然是有才華的渴望“鸞鳳合鳴”的女性找得到的最好男人了。
《聶隱娘》最深刻的映像“青鸞舞鏡”的故事——講的是鸞鳥三年不鳴,見鏡中自己,以為同類,長鳴而死的孤獨。“一個人,沒有同類”,侯孝賢如此,朱天文又何嘗不是如此。男人的孤獨可以任性地用電影說出來,女人的孤獨卻消失在無盡的天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