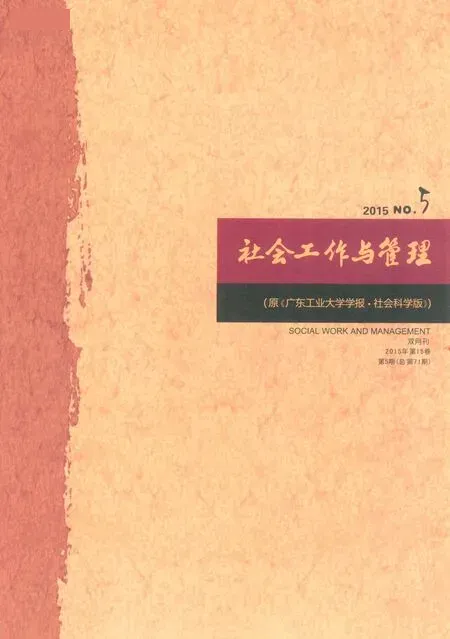廣東農村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比較研究
——基于挫折應對與獨立生活能力的分析
黃 瑋, 張茂元
(華南師范大學: 1.國際商學院, 2.政治與行政學院, 廣東 廣州, 510631)
廣東農村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比較研究
——基于挫折應對與獨立生活能力的分析
黃 瑋1, 張茂元2
(華南師范大學: 1.國際商學院, 2.政治與行政學院, 廣東 廣州, 510631)
基于廣東5市的問卷調查數據,比較分析了農村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在挫折應對和獨立生活能力上的差異。數據分析揭示,由于作為重要求助源的父母缺位,農村留守兒童在遭遇挫折時的確更加孤立無助,他們應對挫折的效果也相對較差。留守兒童應對挫折的積極性、信心和情緒調節能力也比普通兒童差,不過這些差距會隨著年齡增長、教育程度提高而逐漸消失。而在獨立生活能力上,數據和分析表明,農村留守兒童與其他普通兒童在各個指標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
留守兒童; 普通兒童; 受教育程度; 挫折應對; 獨立生活能力
一、研究背景及文獻回顧
由于地區間尤其是城鄉間經濟發展不均衡,我國存在規模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他們從農村外出到城市務工。而且,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數量也會進一步減少,這就決定了我國外出務工農民的數量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不僅不會減少,甚至還可能會持續上升。同時,由于受到戶籍等制度因素和收入低等經濟因素的限制,農民外出務工又產生了同樣規模龐大的農村留守兒童群體。近年來,農村留守兒童得到了社會各界和相關學者的廣泛關注。
一般認為,廣東省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也是我國的經濟大省,是接納外來務工人口的;殊不知,廣東省其實也是留守兒童大省。2000年,廣東省的留守兒童占全國留守兒童總量的10.13%,僅次于四川的14.19%;而且,在廣東,留守兒童也已占本省兒童總量的11.16%。[1]
段成榮等人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估算出,當年全國0~17歲的6 102.55萬個農村留守兒童中,廣東的農村留守兒童共有438萬人,占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總量的7.13%,僅次于四川、河南和安徽三地。[2]由此可見廣東省農村留守兒童的規模之大。這也決定了對廣東農村留守兒童進行深入研究是極其重要且必要的。但遺憾的是,目前對廣東省留守兒童的專門研究還極少。
目前對農村留守兒童的研究,基本上都在探討父母外出所造成的(兒童)“留守”的負面影響。而諸多實證調查也似乎都支持這種結論。
曹述蓉對湖北農村留守兒童學校適應情況的分析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的學校適應情況相對較差,具體表現為:學習適應水平較低、社交——領導行為的適應情況較差、情緒適應水平很低、自我效能感差以及容易出現焦慮和孤獨感等特征。[3]由于缺少父母的關愛和監護,在社會監護、關心和教育又缺失的情況下,留守兒童存在更嚴重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的障礙,表現出更多越軌行為。[4]
還有不少學者關注了留守兒童的負面情緒、越軌行為和挫折應對等方面。劉霞等人利用質性研究方法發現,孤獨感、委屈難過和敏感自卑是留守兒童的代表性情緒體驗,違紀、攻擊和退縮行為是留守兒童群體中的“偶爾或有時”的問題行為。[5]郝振和崔麗娟采用量表法,對農村留守兒童和普通兒童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表明:留守兒童和普通兒童在自尊、心理控制源以及社會適應性上都存在著顯著性差異。[6]范興華等人對四川、湖北、河南、安徽、河北五省2 134名農村兒童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在社會適應各指標(如自尊、生活滿意度、孤獨感、抑郁、社交焦慮和問題行為)上的表現都要比一般兒童差。[7]
也有學者區分并比較不同類型的留守兒童。葉敬忠和王伊歡通過對中西部地區的10個農村社區留守兒童的監護現狀與特點的研究發現,監護類型具有顯著影響,如隔代監護下的留守兒童出現的問題最多。[8]
不過,也有個別研究的結論發現“留守”的副作用并不明顯,甚至還可能具有某些功能。如陳欣欣等人利用2006年在陜西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小學中進行隨機抽樣調查所搜集的面板數據,采用倍差分析法分析得出:無論是父親外出、母親外出,還是父母均外出,都不會對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有負面影響。甚至還發現,父親外出的家庭,其子女的學習成績反而有所改善。[9]
綜上所述,大多數研究都指出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生活、心理方面都存在問題,最起碼要比其他普通的農村兒童要差。但之前的研究都未能明確地回答一個問題,即留守兒童在教育、生活、心理等方面的劣勢是否會一直存在,還是會隨著年齡的增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漸消失?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間的差距是越來越大還是越來越小?之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數據方面的欠缺,如缺乏歷時數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們當前對已有截面數據的挖掘還不夠深入。
本文就試圖利用在廣東省5市的實證數據,來揭示農村留守兒童與農村其他普通兒童在挫折應對和獨立生活能力方面的差異,并進而在這個基礎上揭示這種差異的歷時變化,為相關的政策制定和具體工作提供更加切實可靠的信息。本文所指的農村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外出務工而自己留在農村生活的、不滿18周歲的兒童。普通兒童,則是指父母雙方均未外出的其他農村兒童。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概況
2013年7月15~30日,課題調研小組在廣東省的廣州、肇慶、韶關、清遠和揭陽5市,對18周歲以下的初中生和小學生進行了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1 050份,其中回收1 012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6.38%。1 012個有效樣本分別來自肇慶(372人)、韶關(227人)、清遠(154人)、揭陽(134人)、廣州(125人)等五地。其中留守兒童為508人,占50.2%;普通兒童為504人,占49.8%。平均年齡、男女比例、教育程度見表1。

表1 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基本情況(%)
在留守兒童中,大多數由母親監護,共有221人,占43.5%;由父親監護的有120人,占23.6%;由外/祖父母監護的138人,占27.1%;而其他監護類型(包括同輩兄妹、其他親戚、其他寄養和單獨生活)的共有29人,占5.8%(見表2)。

表2 留守兒童的監護人分類列表(n=508)
三、 挫折應對
(一)應對挫折的態度、信心與效果
挫折是我們成長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環,留守兒童亦不外如是。不過,他們會如何看待挫折?他們應對挫折的信心、效果又如何呢?
在挫折應對方面,主要設計了6個指標,對留守兒童和普通兒童應對挫折的方式、效果等各方面進行比較全面的測量。
其中“面對挫折的積極性”和“應對挫折的孤立性”采用的是3分測量,分值范圍為1~3分,分值越高表明態度越積極、應對行為越獨立。前者對應的態度分別是:極力回避、順其自然、努力解決(挫折);后者對應的應對行為分別是:完全靠別人解決、在別人幫助下解決、完全靠自己解決(挫折)。
而“情緒調節能力”“應對挫折的信心”“求助對象的作用”和“挫折應對的效果”4個指標均采用5分測量,分值范圍為1~5分,分值越高表明相應的能力、信心越強或作用越大。
為了更好地體現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在挫折應對各方面的差異,同時根據數據屬性,我們選擇單因變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進行分析(結果見表3)。其中因變量為上述6個變量,自變量包括性別(屬性為“男”和“女”,其中“女”為參照組)、兒童類型(屬性為“留守兒童”和“普通兒童”,其中“普通兒童”為參照組)、年齡(定比數據,為協變量)。

表3 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挫折應對能力比較
注:***P<0.001,**P<0.01,*P<0.05
數據分析表明,留守兒童應對挫折的積極性要比普通兒童弱(統計檢驗顯著性P<0.05)。此外,男孩應對挫折的積極性也比女孩弱;年齡對于應對挫折的積極性也有顯著影響,是正向影響,即年齡越高,應對挫折的積極性越高。
應對挫折的孤立性方面,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留守兒童更加孤立。不過,這并不等于留守兒童獨立性更強,也不表明他們應對挫折的能力和信心更強,而是因為他們父母不在家而不知道該向誰求助。這個判斷也從留守兒童求助對象的幫助作用更小,且留守兒童應對挫折時更加消極中得到了驗證。女孩雖然表現得比男孩孤立,但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這個差異并不顯著。
此外,數據分析還顯示,留守兒童在面對挫折時的情緒調節能力更差、信心更弱、效果更差(以上差異均不同程度上統計檢驗顯著),且他們的求助對象所能起到的幫助作用也更小。

圖1 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在遇到挫折時的求助對象比較
在求助對象的選擇上,留守兒童和普通兒童都最常向“同學朋友”求助(分別是59.5%和56.1%),而“父母”則都排在第二位(分別是58.5%和49.4%)。但由于父母外出,留守兒童選擇父母作為求助對象的比例要明顯低于普通兒童,而他們選擇“父母以外的監護人”的比例則要遠高于普通兒童(20.1%∶12.7%)。
此外,就性別而言,男童除了在遇到挫折時的“情緒調節能力”得分高于女童外(但在0.05顯著性水平上統計檢驗并不顯著),在其他挫折應對方面的得分都要低于女童——其中在應對挫折的積極性和信心方面要顯著弱于女童。
年齡對這些農村兒童應對挫折的積極性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即年齡越大的兒童,在面對挫折時越積極,越不會消極回避。
(二)挫折歸因及其影響
數據分析表明(見表4),留守兒童比普通兒童更多地將挫折歸因于外界,如歸因于“運氣不好”或是“別人”;而普通兒童則更多地歸因于“自己”,同時也能夠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挫折大多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導致的”。統計檢驗結果顯示,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對于挫折的歸因存在顯著差異。控制變量“性別”和“受教育程度”后,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在挫折歸因上的區別雖有縮小,不過仍然在0.1的顯著性水平上呈顯著差異。而這種歸因差異終將影響到他們對待挫折的態度、方式甚至是挫折應對的效果。

表4 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挫折歸因比較
進一步分析表明,將挫折歸因于自己,或是能夠正確認識到挫折是“多種因素共同導致”的兒童,能夠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和行為面對挫折,他們應對挫折的效果也要更好。如表5所示,與那些將挫折歸因于“運氣不好”或是“別人”的兒童相比,將挫折歸因于“自己”或是“多種因素共同所致”的兒童,他們在“應對挫折的積極性”“應對挫折的信心”“情緒調節能力”和“應對挫折的效果”的得分都要明顯更高。而那些將挫折歸因于“運氣不好”的兒童,在“應對挫折的積極性”“應對挫折的信心”和“應對挫折的效果”三方面的得分都是最低的。

表5 挫折歸因影響應對挫折的態度
注:***P<0.001;**P<0.01;*P<0.05
(三)教育程度(年齡)的影響
總體而言,與普通兒童相比,留守兒童在應對挫折上相對消極、孤單,所能獲得的幫助更少,情緒調節能力更弱,信心也弱,應對的效果也更差。不過,留守兒童的這種弱勢是否會一直存在?還是會隨著年齡增長、教育程度提高而改變?為此,我們引入教育程度(分為小學和初中兩個屬性)作為控制變量,以進一步深入探討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之間的區別(見表6)。
控制變量“教育程度”后,留守兒童雖然仍更多地將挫折歸因于“別人”或是“運氣不好”等外界因素,但不管是在小學生還是初中生群體中,留守兒童與其他普通兒童的這種挫折歸因差異在0.05顯著性水平上都不再顯著。其中小學生群體中,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挫折歸因差異在0.1顯著性水平統計檢驗顯著。

表6 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挫折歸因比較(控制變量:教育程度)
不管在小學階段還是初中階段,留守兒童在應對挫折時都更加孤單(孤立性得分更高)、他們從求助對象那里所獲得的幫助也更小(得分低)。不過,這個差別在小學生中并不顯著;而在初中階段,這兩方面的差別都顯著存在。
在小學階段,留守兒童應對挫折的積極性、信心、情緒調節能力都要顯著弱于普通兒童;但在初中階段,留守兒童應對挫折的積極性和信心雖然仍要稍低于普通兒童,但其中已經不存在顯著差距;留守兒童在情緒調節能力方面的得分甚至還要稍高于普通兒童(不過這個差別在統計檢驗中并不顯著)(見表7)。

表7 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挫折應對能力比較(控制變量:教育程度)
注:***P<0.001,**P<0.01,*P<0.05
而從應對挫折的效果(自我評價)來看,不管是小學階段還是初中階段的農村兒童,留守兒童應對挫折的效果都要顯著低于普通兒童。
四、獨立生活能力
在我們的研究設計中,獨立生活能力主要包含四個指標,分別是:家務能力、獨立意識、到陌生環境生活的意愿和適應陌生環境的能力。對以上四個指標的測量均分成5個等級,從1~5,分值越高,表明相關能力、意識或意愿越強。
通過對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相關得分進行方差分析發現,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獨立生活能力沒有顯著差異,而且在家務能力、獨立意識、到陌生環境生活的意愿和適應陌生環境的能力四個方面均沒有顯著差異(見表8)。

表8 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獨立生活能力比較
注:***P<0.001,**P<0.01,*P<0.05
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到陌生環境生活的意愿”得分分別是2.41和2.45分,兩者不存在顯著差異(Eta=0.018,P>0.5)。
即使是在控制變量“性別”后,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在獨立生活能力的上述四個指標上仍沒有顯著差異。
而在控制變量“教育程度”后,不管是小學階段還是初中階段,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在獨立生活能力的上述四個指標上均沒有顯著差異——除了小學階段的留守兒童的家務能力要顯著弱于普通兒童外。這一點也和很多人之前的判斷不吻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由于父母外出,留守兒童會更加獨立,家務能力也會更強,但這些在我們的研究中都沒有得到驗證(見表9)。

表9 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獨立生活能力比較(控制變量:教育程度)
注:***P<0.001,**P<0.01,*P<0.05
而如果將性別和兒童類型作為固定因子,年齡作為協變量,分別以獨立生活能力的四個指標作為因變量,進行單因變量多因素方差分析(見表10),我們發現,除了如前所述,留守兒童和普通兒童在家務能力、獨立意識、到陌生環境生活的意愿和環境適應能力等四方面無顯著差異外,性別對農村兒童的家務能力有顯著影響:男童的家務能力顯著弱于女童,但男童和女童在獨立意識、到陌生環境生活的意愿和環境適應能力方面都沒有顯著差異。

表10 獨立生活能力的單因變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注:***P<0.001,**P<0.01,*P<0.05
此外,農村兒童的年齡對獨立生活能力的上述四個方面,均有顯著影響。具體表現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兒童的家務能力、獨立意識、到陌生環境生活的意愿和環境適應能力等四個方面的能力、意識和意愿均有明顯提高。
五、 結論及建議
通過對廣東省五個地區的農村留守兒童和其他普通農村兒童的比較分析發現,在挫折應對方面,留守兒童在多方面的表現都相對差些。留守兒童更經常將自己所遭受到的挫折歸因于外界因素如“別人”或是“運氣不好”,但隨著年齡和教育程度的提高,這種差異隨之顯著縮小。
與此同時,還發現,在應對挫折時,留守兒童相對消極、孤單,應對挫折的信心較小、情緒調節能力更差,他們應對挫折的實際效果也更差。而進一步的分析則讓我們更真切地看到了父母外出對留守兒童的影響。不管是在小學階段還是初中階段,留守兒童應對挫折的實際效果都要顯著弱于普通兒童;初中階段的留守兒童在面對挫折時也更加孤立,他們從求助對象那里所能獲得的幫助也更小——不過在小學階段,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在這兩方面的表現均有顯著差異。
不容忽視的是,小學階段的留守兒童在應對挫折的積極性、信心和情緒調節能力方面雖然顯著弱于普通兒童,但在初中階段,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之間在這三方面的差距都消失了。也就是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教育程度的提高,留守兒童在這三方面的表現與普通兒童基本持平,無顯著差異。
而在獨立生活能力上,留守兒童在四個指標上所體現出來的獨立生活能力和意識、意愿都不弱于其他農村兒童——即使是在控制“教育程度”后仍是如此。
與此同時,還發現,農村女童的家務能力顯著強于男童;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兒童的獨立生活能力、意識和意愿都隨之顯著提高。
總而言之,由于父母外出,農村留守兒童在面對挫折等問題時更加孤立,他們從家人那里所能獲得的幫助的確較小;但與此同時,也要看到,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留守兒童應對挫折的積極性、信心和情緒調節能力都會逐漸與農村的其他普通兒童持平。而農村兒童的獨立生活能力則主要是受年齡的影響,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之間并不存在顯著差異。
通過對數據的深入挖掘發現,農村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之間的差距并不如之前大多數研究者所擔憂的那么巨大、那么明顯。而且,即使有些許差距也不必過于擔憂,因為這種差距會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漸消失,最終留守兒童在很多指標上體現出來的挫折應對和獨立生活能力都不弱于其他普通兒童。
綜上所述,“留守”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小學階段、年齡較小的兒童身上。由于缺乏縱向數據,我們還不能確定“留守”的負面影響一定會消失;但即使這種差異會消失,父母缺位對小學階段、年齡較小兒童的不良影響仍然是值得關注的,因為這已經切切實實地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質量。
根據我們的實證分析,留守兒童的年齡是影響他們挫折應對能力的重要變量,因此,也應是父母選擇外出時間的重要參考變量。為切實維護留守兒童權益、保障他們的生活質量,我們建議,如有可能,父母應該盡量在其小孩年幼時(如小學階段及之前)能夠有更多的時間陪伴他們。另一方面,對那些小學階段及更年幼的留守兒童,地方社會和家庭也就應該給予更多關注,尤其是在挫折應對方面。
[1]段成榮,周福林.我國留守兒童狀況研究[J].人口研究,2005(1):29—36.
[2]段成榮,呂利丹,郭靜,等.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生存和發展基本狀況: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J].人口學刊,2013(3):37—49.
[3]曹述蓉.農村留守兒童學校適應的實證研究[J].青年探索,2006(3):16—19.
[4]王道春.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原因及預防對策芻議[J].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6(3):27—33.
[5]劉霞,趙景欣,申繼亮.農村留守兒童的情緒與行為適應特點[J].中國教育學刊,2007(6):6—20.
[6]郝振,崔麗娟.自尊和心理控制源對留守兒童社會適應的影響研究[J].心理科學,2007(5):1199—1207.
[7]范興華,方曉義,劉勤學,等.流動兒童、留守兒童與一般兒童社會適應比較[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33—40.
[8]葉敬忠,王伊歡.留守兒童的監護現狀和特點[J].人口學刊,2006(3):55—59.
[9]陳欣欣,張林秀,羅斯高,等.父母外出與農村留守子女的學習表現:來自陜西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調查[J].中國人口科學,2009(5):103—112.
(文字編輯:王香麗 責任校對:鄒紅)
2015-01-17
■ 基金課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農業技術應用中的技術紅利分配與農村變遷”(13YJA840034)。
黃瑋(1982—),女,漢族,助教,碩士;主要研究方向:農村金融,社會變遷。
黃瑋, 張茂元.廣東農村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比較研究——基于挫折應對與獨立生活能力的分析[J].社會工作與管理,2015,15(5):59—65.
C913
A
1671-623X(2015)05-005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