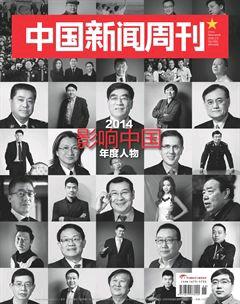北京市十一學校:發現那棵樹
楊迪

北京十一學校設有專門的“校服專賣店”。學校校服文化中心負責人表示,以前的校服就是統一的運動服,同學們不愛穿。為了滿足他們追求個性的愿望,學校決定提供40款校服供選擇。圖/CFP
提名理由
它徹底消滅了“好學生”“壞學生”的稱呼,讓每個學生都為“成為自己”而驕傲;它給予孩子們選擇的權利,與此同時也賦予了他們自由、創造與責任。在教育這個宏大的命題下,它細致入微地考量,用細水長流的韌性,為學生打造出一個造夢、追夢、圓夢的空間。它所描繪的教育,沒有功利與成敗,只有真實、寬容與創造,而貫穿其中的,是希望。
北京市十一學校高三學生安陽的課程表獨一無二。以星期一上午為例,他先要去上I級數學課,再去上II級政治課,然后是II級歷史、田徑和I級化學。
同在星期一,他的同學胡天寒的課程卻是先上數學III級,然后是物理III級,接下來是III級化學,語文B級以及田徑和英語B。當然,胡天寒的課程表也是獨一無二的。
這是十一學校自2011年開始施行課程改革的一個顯著標志:高中部4174名學生,每人都有一張自己的專屬課程表,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各學科的學習程度、興趣愛好以及未來報考大學的方向,選擇不同難度的課程。與此相配合,行政班級和班主任取消。學生走班選課,學科教師只需專注本學科的授課和教學研究即可。
如此徹底地告別傳統教學模式,北京十一學校是中國第一家。有人評價說,它“真正觸動了教育改革的核心”,但對北京十一學校來說,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觸動什么核心,僅僅是盡一切努力使學生“成為”自己。
“選擇”成為主題詞
4000余名學生,每人有一份與眾不同的課表,其背后是龐大的課程體系。
十一學校用了幾年時間,整合梳理國家和地方的課程體系,最終創建了265門校本課程,其中必修課只有17門,選修課有248門。另有30門綜合實踐課程和75門職業考察課程。即便必修學科,也分為5個不同難度。以數學為例,I級適合今后大學選擇文科的學生,II、III級針對理科高考生,IV是競賽班課程,V級則是大學先修課。課程選定也并非一成不變。學習一段時間后,如果覺得不合適,還可以重新選課。
這樣的課程安排,不只是學生,就連老師也有些羨慕。“棗林村書院”院長、歷史教師魏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上高中時,總也不明白,文科生為什么要學那么難的數學,但是在大一統的班級與教材體制下,他只好在一次次考試中正視自己在數學上的不足。“現在我的學生可比我幸運多了!”
十一學校的課間非常熱鬧。學生們抱著各自的教材,穿梭在學校的走廊里,偶而互相打個招呼,便興致勃勃奔向271間不同的學科教室(每間教室門口貼著學科名稱和教師名字),之后,仿佛船只入港,隨著上課鈴響,再次歸于安靜。“感覺學校就像個提供課程的大超市。”安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這家超市不只可以選擇課程,也可以選擇學習方式。安陽、胡天寒選擇按常規在教室上課,高二學生鄭子豪則申請數學、語文自修,理由是他未來要報考導演系,需要更多時間學習專業課程;初二學生張帆則有專門為她度身定制的“一個人的寫作課”。她酷愛寫作,已創作了一部20萬字的小說,在網上點擊率頗高。每周一下午,是她和老師一對一討論寫作方法及小說構思的時間。最近,她正以自己的經歷為原型,創作一部名為《戶口》的小說。
課余活動更不用發愁,有272個社團可供選擇。“超市”里沒有的課程,學生還可以自己“進貨”。比如,高二學生毛佳鈺喜歡建筑,但學校沒有相關社團,她便創辦了少年建筑學院,親自擔任院長,由學校出面,聘請清華大學建筑學副教授擔任指導。目前學院已招收了30多名會員,毛佳鈺本人還完成了論文《北京鐘鼓樓地區商業房屋改造研究及建議》。
甚至就寢時間也可以選擇。十一學校每周有一次“與校長共進午餐”。一次,兩名學生為就寢時間爭論了起來。一名男生抱怨學校規定的就寢時間太早,另一名女生則認為太晚。校長李希貴聽后,便責成這兩名學生拿出解決方案。兩人在全校范圍進行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4個月后,拿出了一份詳細的“分時睡覺”建議書。校方決定采納。現在,十一學校的住宿生就有了3種不同的就寢時間。
他們甚至還幫助校長選擇。每年最后一天是學校的“狂歡節”。這一天,校長要按學生的意愿進行裝扮。他已被學生安排扮演的角色有“加勒比海盜船長”“鄧布利多校長”和“大黃蜂”。
被挑戰的老師
學生獲得自由,被挑戰的卻是老師。不止一位教師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改革過程處處充滿煎熬。
事實上,這場改革可以上溯至2007年。當時,李希貴剛擔任校長不久,他發動全校教職員工要共同制定一份《北京市十一學校行動綱要》,每個人都要參與,共同歸納總結出十一學校的價值觀和普遍認可的文化傳統。
在學校工作了30余年的于振麗說:“數十年來從沒有這樣與同事們酣暢淋漓地爭論過。”據統計,制訂行動綱要過程中,共有475人參與了三輪大討論,提交各類意見和建議684條。“這個過程實際讓《行動綱要》成了大家共同的作品。”魏勇說。在爭論過程中,老師們發現了許多學校歷史中的成功基因,如“不為高考,贏得高考”“學生能做的,老師不要包辦”。在激烈的交鋒中,他們也開始接受新的理念與價值觀。
《十一學校行動綱要》第一稿在2009年下半年形成,此后兩三年,仍不斷打磨,數易其稿,最終在2011年初正式對外公布。
《行動綱要》分為15章、100條,明確了在組織結構、師生關系、教育教學等主要領域內師生員工的行為準則,其中有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樸素表述。比如,對教師的職業定位:“教師從事的是世間最復雜的腦力勞動,在學生今日之愛戴與未來之追憶中,尋找富有樂趣的教育人生”“不占用學生自主學習和休息的時間,是對學生的基本尊重”;而對課程的定義是:“課程是學校的產品,通過對課程的構建和開發,最大限度滿足不同學生的成長需求。”
此后,根據各年級的實際情況,課程改革逐步、分層展開。比如,語文和英語最初沒有參與課改,因為教師普遍認為這兩門學科不適合分層,怎么改沒想清楚,索性先不動;拆掉教室里的講臺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哪門課、哪個年級時機成熟拆哪個,全部拆光用了兩年多;最初改革成走班制時,學校帶著顧慮保留了行政班和班主任,結果造成了班主任制與學科導師制的矛盾。后來,留學回來的學生講述了歐美學校的氣氛:老師給予學生的是信任,而不是管理。校長李希貴聽后下了決心,徹底取消行政班和班主任。
配合課程改革,學校行政管理體制也開始壓縮。學校用了7年時間,陸續減少管理層級。年級學部成為課程與教師管理的核心,集教學、科研、人事、財務管理于一身;而原來的中層管理部門變為職能部門,并最終壓縮為4個:辦公室、教導處、總務處、工會。教職工的聘任由各年級學部、各部門雙向選擇,課堂教學的主導權下放到每個學科和每位教師。高一學部主任田俊說:“這里的改革沒有‘一刀切,也沒有共同模式,它是一個百花園。”
變革帶來了巨大壓力。講臺拆掉了,教師講課不再高高在上,平等對話成為常態;老師的權威不見了,有時候想找學生談話,還要看學生是否有時間;過去教師只用教師參考書備課即可,如今參考書全部公開,老師被迫另外尋找教學資料;不止一位老師被學生在課堂上直接指出:老師,你剛才講錯了。
并非沒有疑慮和擔憂。比如,改革后每個學期設計有兩個星期的“小學段”,沒有老師和作業,學生自主安排。孩子們會不會“放羊”?許多老師擔憂。但擔憂僅僅是擔憂而已。孩子們把自己安排得井井有條,有人用來讀書,有人重溫物理實驗,還有人走出校園去做義工……
漸漸地,老師們找到了成就感。當教育不再依靠權威而依靠能力時,老師們被迫不斷自我學習和成長;當學習不再依靠權威和監督時,學生們的主動性和效率都大幅提高。雖然成績不再是唯一的目標,但成績卻并未因此有所下降。2013年,首屆走班制學生參加高考,363名考生中650分以上達199人;取消班主任制,使得每位學科教師都要承擔起關注學生情緒、心理等問題的責任,教師們與學生交流更多也更加熟悉了;甚至,老師們也像學生一樣,期待每年6月的學校潑水節,水槍、水盆、水桶齊上陣,每個人都變成落湯雞。誰說快樂只對孩子重要?
“過去我們看到的都是一片森林,每一棵樹都一樣。”校長李希貴在《面向個體的教育》一書中這樣講述他眼中的學校,“但今天我們要發現那棵樹。”但對老師們而言,發現的過程是雙向的——為了發現那棵樹,他們也發現了自己這棵樹。
北京十一學校
1952年建校。從2011年起,打破班主任管理模式,構建自有的課程體系,包括265門學科課程、30門綜合實踐課程、75個職業考察課程、272個社團和60個學生管理崗位,學生依據個人能力和興趣愛好,自主選擇課程,走班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