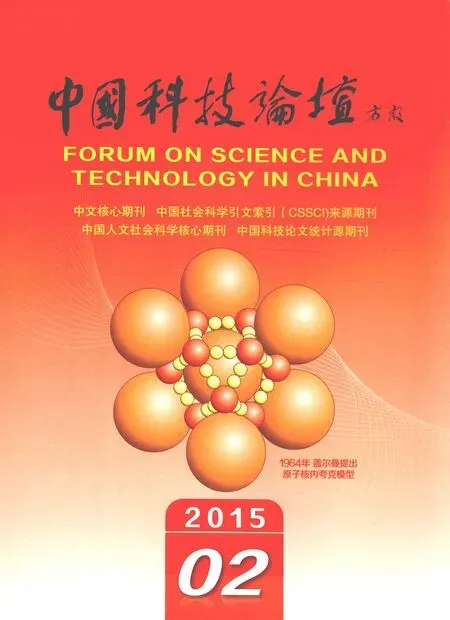人均碳排放拐點的國際比較分析
周 俊,李 賓
(湖南科技大學商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1 引言
近年來,中國人均碳排放量持續快速上升。根據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 (CDIAC)的數據,2000 年我國人均年排放0.73 噸碳,2005 年1.21噸,2010 年1.68 噸,2012 年1.94 噸。在龐大的人口背景下,如此迅猛的遞增勢頭意味著中國的碳排放規模很大。早在2006 年,中國就已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碳排放國,2012 年的排放量更是達到了美國的近2 倍、全球的27.2%。中國已成為眾多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競相施壓的對象和拒絕做出減排承諾的“擋箭牌”[1]。
本文通過觀察和分析世界各國的情況,來嘗試為中國碳排放形勢的發展尋找參照系。
2 碳排放庫茲涅茲曲線
考察碳排放的理論主軸來自于早年環境經濟學的環境庫茲涅茲假說(EKC),即: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人均污染排放量將出現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特征。大量的實證研究基本支持這樣一個假說,不過不同的物質表現出有差異的特征:固態污染物最容易出現拐點,對應的人均收入水平最低;液體污染物次之;氣體污染物的拐點較難出現,對應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最高[2]。CO2作為一種氣體排放物,其EKC 特征是最不穩健的,現有研究對它是否成立頗有爭議。出于這種爭議和氣候變化議題的日益重要,逐漸衍生出EKC 的一種專門類型:碳排放庫茲涅茲曲線CKC(Carbon Kuznets Curve)。
近年已有不少文獻在探討中國的CKC,主要是按照時間預測拐點。朱永彬等[3]、黃蕊等[4]判斷全國的碳排放峰值將出現在2040 年左右;李惠民等[5]則認為在2050 年前后;林伯強等[6]判斷碳排放拐點到2040 年都不會出現;王萱和宋德勇[7]認為中國還需要再走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的路達到碳排放拐點。不同于前文所借助的復雜技術方法,本文的思路相對簡單,就是根據各國人均碳排放的時間序列圖,直觀地判斷一國是否越過了CKC拐點。這在文獻中被稱為“脫鉤”[8]。CKC 拐點水平的高低對于判斷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形勢,可起到借鑒作用。如果各國拐點的平均值越高,那就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國際壓力可能持續得越久。
在全球約200 個國家中,值得關注的是那些已經越過了CKC 拐點的國家。我們觀察了近100 個主要國家的人均碳排放軌跡。從中,挑選出28 個國家或地區的,展示于圖1;其他未放入的,則是因為到2010 年為止仍呈現為單向上升的趨勢。雖然有文獻做了相近的工作[7,9],不過它們只是觀察了7 ~8 個國家;本文的觀察對象更為全面。
從圖1 中可觀察到這樣幾點:
(1)所列國家都邁過了或者看起來正在邁過CKC 拐點。它們大致都有歷史峰值,而且近期的人均排放量要么處在下降趨勢中,要么難以超越歷史峰值。少數國家的CKC 特征是否顯著還存在爭議,比如日本、丹麥、南非、獨聯體。這幅圖至少表明,世界上跨過CKC 拐點的國家數目比預想的要多。
(2)各國CKC 拐點發生的時間差異較大。不少國家CKC 拐點發生在1973、1979 年前后;那時對應了兩次石油危機。這表明,化石燃料價格的沖擊,可促使一國自覺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其他的拐點散布于其后的各個十年。除了獨聯體、東歐的峰值集中于20 世紀80 年代之外,其他國家的拐點時間沒有呈現出明顯的規律性。
(3)CKC 拐點的人均排放量水平分布在1.74噸(香港)到5.44 噸(美國)的寬闊區間上。多數國家的峰值在2 噸到4 噸之間,低于2 噸和高于4 噸的比較少。可見中國正在進入別國發生拐點的區間;這意味著,中國在應對國際碳減排壓力時所能列舉的理由的有效性正在變弱。
(4)CKC 曲線大多呈現出明顯的鋸齒形態,時升時降。其背后的原因還有待研究。這種形態使得CKC 的拐點不很明確。一些文獻認為我國CKC 曲線呈現為N 型、W 型等,而不是倒U 型,進而懷疑CKC 是否成立[10-11]。從圖1 看,判定拐點的發生不能只憑單一的峰值,而應從較長的歷史時期來觀察。這種形態也意味著,對那些在2000 年之后有下降表現的國家,尚不能確定CKC曲線是否還將轉而上行;即使中國達到了拐點發生的區間,也不一定很快就能真正實現下行。
3 人均碳排放拐點的定量分析
為了對拐點處的特征有更好的了解,我們找出了28 個國家或地區歷史峰值的年份和水平,以及各國在該年份的人均GDP、三次產業結構的數據,把它們列于表1 的主要觀測點部分。另外,由于CKC 曲線的鋸齒形態,表1 也列出了部分國家的附屬觀測點。他們主要是某國在其他年份的一個比較凸出的局部極值。限于數據的可得性,希臘、瑞士、波蘭缺產業結構的數據。獨聯體及南非的放在了表1 的最下方,因其近期的表現顯示出它們越過CKC 拐點的跡象較弱,所以基準情形的分析中將不包含它們。

圖1 部分國家的人均碳排放
引入三個額外變量,是基于以下考慮。在探討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的文獻中,有一種劃分角度是規模效應、技術效應、結構效應[12-13]。由于經濟規模的擴大必然帶來能源需求的增加,這往往導致化石燃料消耗量和碳排放量的上升,所以規模效應易于理解。對于技術效應,根據新古典理論,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源泉。因此,這里把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視為同一類因素,以人均GDP 水平的高低來體現。
產業結構可視為是一種資源轉換器,即通過產業間的有效運轉,把社會各種資源的總和不斷轉化為各種產品和勞務[14]。由于產業發展對化石能源有著直接或間接的依賴作用,不同產業對能源的依賴程度存在差異,產業結構的演進必然會對碳排放量和氣候變化產生影響[15]。因此,觀察CKC 拐點處的產業結構狀態,將有助于獲得更全面的理解。產業結構通常由三次產業占GDP 的比重來表達;對于定量分析而言最好只使用一個指標。有人使用二產、三產對一產的比值之和[16],鑒于第一產業所占的比例低,多在5%以下,這種方法得出的變量不僅數值大,而且對一產占比的大小會很敏感。所以,作為一種改良,我們使用三產對二產的比值作為產業結構的表達。
3.1 描述性統計
表2 列出了CKC 拐點處幾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值。對于人均碳排放,26 個觀測點的樣本均值是3.16 噸碳;總體均值的95%置信區間是從2.75噸到3.57 噸。這比圖示法給出了更精確的表達。可見,中國2012 年1.94 噸的人均量離拐點還有一段距離。各國拐點水平的中位數為2.86 噸。因低于2 噸和高于5 噸的可算作奇異點,而26 個觀測點中有多達5 個這樣的點,所以不受奇異點影響的中位數比均值能更好反映全球CKC 拐點的平均水平。均值大于中位數且偏度大于零,表明這是一個右偏分布,更多的觀測值處于數值較小的部分。峰度小于零(減3 之后),說明觀測點的數值比較分散,從而國別特性應比較重要。
當CKC 拐點發生時,人均GDP 的均值是2. 28 萬美元 (2005 年價,下同),小于中位數,表明較多的觀測值分布在高位;95% 置信區間是從1. 94 萬到2. 62 萬美元。中國當前水平還不到其下限的一半。因人均GDP 不像人均碳排放那樣漲跌頻繁,而是持續增長的,所以我國要到達CKC 拐點,確實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對于產業結構,均值1. 94、中位數2. 09 意味著在拐點處,第三產業的規模通常是第二產業的2倍以上。中國2012 年第二產業占比45. 3%,第三產業44. 6%,該比值還不到1,同樣表明CKC 拐點離中國還較遠。

表2 CKC 拐點處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3 計量回歸
3.2 回歸分析
所用的計量模型為如下的簡單線性形式:
cperi= α0+ α1× gperi+ α2× ratioi+ α3× xi+εi其中,cper 為各國拐點處的人均碳排放量,gper為對應年份的人均GDP,ratio 為第三產業對第二產業的比值,x 為其他控制變量,ε 為隨機項。
常數項α0代表一種基本拐點水平,即一國的人均排放量至少要達到α0才有可能轉而下行;α1表示,在基本拐點水平附近,給定其他控制變量不變,人均GDP 每高一萬美元,人均碳排放的拐點水平變化α1;其他系數的涵義類似于α1。對于x,考慮了兩個選項:一個是各國的緯度。另一個是使用虛擬變量來體現是否處于1973、1979 左右的年份,以觀察石油危機對拐點形成的影響。表3列出了7 組不同情形的回歸結果。其中,第1 ~3組使用表1 從美國到香港的共計23 個觀測點;第4 ~5 組則去掉了從新加坡到香港的7 個觀測點,只留下16 個成熟市場經濟體的數據;第6 ~7 組則把表1 中的輔助觀測點也當作獨立數據點,與23個主要觀測點混合,形成總計41 個觀測點的樣本。
以第1 組為基準組,結果顯示:23 個觀測點是確實發生了拐點的國家,三個系數都在1%水平上顯著;系數的大小和正負號符合直覺;R2和DW 值表現較好。常數項表明一國人均碳排放水平需達到2.08 噸才有可能轉而下降;α1>0、α2<0則表明,拐點處的平均人均GDP 越高、第二產業的占比越大,便越不容易發生拐點。中國拐點發生時的人均GDP 不好預測,以中國工業比重偏高的現狀,難以對拐點的及早出現持樂觀態度。
去掉常數項后的第2 組,產業結構的系數顯著性變弱,且R2和DW 值變化較大,但兩個主要解釋變量仍然高度顯著。第3 組加入的緯度變量并不顯著。這表明緯度的影響雖然在直覺上成立,但在數量上太弱,緯度變量不足以體現國別特性。第4 ~5 組中變量系數的估計值變化較大,顯著性有所降低,不過仍然是顯著的;加入緯度后該變量依然不顯著,而且常數項也不顯著,可見由于自由度下降較多,回歸結果變得不穩健。第6 組使用擴展到41 個觀測點的數據后的結果與基準組相近,但其數據質量不如第1 組。第7 組中加入的是否為石油危機前后的虛擬變量并不顯著。
4 結束語
借助圖形觀察、描述性統計和計量回歸這三個方法,得出平均意義上CKC 拐點大致在2.8 ~3噸之間;屆時,人均GDP 在2.3 萬~2.5 萬美元(2005 年價)之間,第三產業規模是第二產業的2 ~2.2 倍;而且,拐點的最低水平約為2.1 噸,人均碳排放在達到此水平之前難以真正進入下行階段。因中國人均GDP 只有拐點處對應水平的約四分之一,不僅提高需要時間,而且還可能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產業結構方面,工業比重居高不下,迄今為止服務業規模尚未超過第二產業的,而產業結構變化又是一個很慢的過程。根據上述分析,估計中國在一段時期內(也許20 年)還難以越過CKC 拐點。這一判斷與現有文獻中的判斷基本一致;雖然本文并沒有做這類預測工作,但本文的觀察結果,可以為已有文獻提供一個數據背景上的補充或注釋。
[1]查建平,唐方方,鄭浩生. 什么因素多大程度上影響到工業碳排放績效——來自中國(2003 -2010)省級工業面板數據的證據[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3,(1):79 -95.
[2]李賓,向國成. 從資源枯竭之憂到資源再生之慮——碳排放文獻述評[J]. 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24 -31.
[3]朱永彬,王錚,龐麗,王麗娟,鄒秀萍. 基于經濟模擬的中國能源消費與碳排放高峰預測[J]. 地理學報,2009,(8):935 -944.
[4]黃蕊,朱永彬,王錚. 上海市能源消費趨勢和碳排放高峰估計[J].上海經濟研究,2010,(10):81 -90.
[5]李惠民,齊曄. 中國2050 年碳排放情景比較[J].氣候變化研究進展,2011,7(4):271 -280.
[6]林伯強,蔣竺均. 中國二氧化碳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預測及影響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9,(4):27 -36.
[7]王萱,宋德勇. 碳排放階段劃分與國際經驗啟示[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5):46 -51.
[8]王佳,楊俊. 地區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基于脫鉤理論和CKC 的實證分析[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3,(1):8 -18.
[9]張志強,曾靜靜,曲建升. 世界主要國家碳排放強度歷史變化趨勢及相關關系研究[J]. 地球科學進展,2011,(8):859 -869.
[10]陳彩芹,鞏在武.1985 -2010 年制造業二氧化碳排放的改變點分析及周期劃分研究[J]. 中國科技論壇,2013,(5):51 -59.
[11]田超杰. 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關系的實證研究——以河南省為例[J]. 科技進步與對策,2013,(14):29 -31.
[12]賈惠婷. 規模、結構和技術效應影響碳排放的程度及交互關系——基于1997—2009 年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3,(14):34 -39.
[13]姚西龍. 技術進步、結構變動與制造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59 -66.
[14]毛健. 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優化[J].產業經濟研究,2003,(2):26 -36.
[15]張維陽,段學軍. 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碳排放相互關系研究進展[J].地理科學進展,2012,(4):442 -450.
[16]張雷. 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區域格局變化[J].地理研究,2006,(1):1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