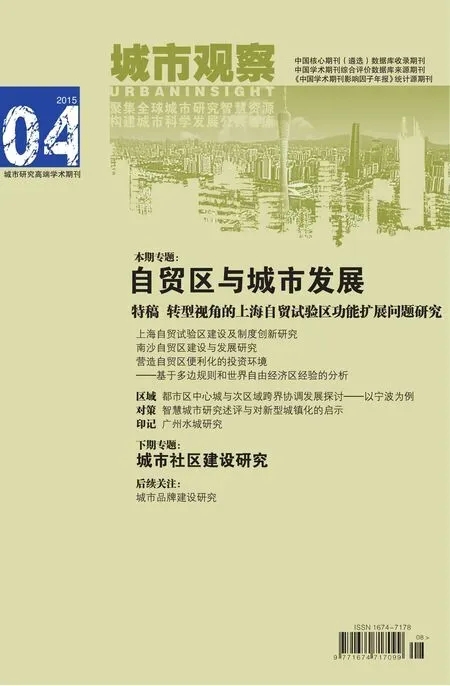符號消費邏輯下城市空間意義的轉化——空間視域下的田子坊解讀
◎蔣立業
符號消費邏輯下城市空間意義的轉化——空間視域下的田子坊解讀
◎蔣立業
摘 要:田子坊作為一個城市空間,它的再生與開發實際上不過是空間的意義再建構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創造出的文化意義,符合了當前文化消費的符號邏輯。因而,在經歷了空間意義轉化為符號消費對象之后它完成了商品化的過程。
關鍵詞:符號消費 田子坊 空間意義
城市空間在當下的城市規劃語境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與價值,眾多城市將其改造與升級同城市本身文化產業發展相聯系起來。包括北京798以及上海田子坊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在內的眾多城市空間改造都頗具各自的特色。然而城市空間的轉化與再生其背后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規律、是否能發現其本身所共有的一種城市發展的本質性的特征?這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
田子坊作為上海重要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本身便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特色。目前,該園區仍舊保持著一部分居住的空間功能,而并未像其他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一樣,以商業消費與旅游等功能完全擠占原有的空間功能。雖然對一部分居住功能的保留仍然引發了許多矛盾,不同的社會群體對該園區的空間文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認知態度,但事實上這樣的居住空間在旅游體驗的消費之下也日漸成為一種被觀賞的符號化存在了(即對于舊有上海民居以及市井生活的觀賞)。
城市發展與建設的決策者更多關注的是城市空間的轉化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提升該空間本身所能創造的經濟效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這是資本參與對城市空間的改造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但是我們更應該在城市空間的歷史文化的保留與資本對城市的改造之間保持一種良好的張力與平衡。
一、田子坊空間意義的產生與轉化
田子坊位于原盧灣區(現為黃浦區)泰康路上,原名志成坊,始建于1930年。“田子坊”是1999年畫家黃永玉為其取的
新名,以史記中記載的一位畫家田子方的諧音為名。如今田子坊早已是一派車水馬龍的熱鬧景象。擁擠的街道中,來自全球的各色人種、不同年齡段的游客,被裹挾在熙攘的人群中,在這弄堂中游蕩。弄堂兩側吸引他們的與其說是古老的具有各式風格的建筑,不如說是各式的店鋪的招牌以及臨街開放的酒吧與小店櫥窗前擺放的五顏六色的商品和廢舊的酒瓶。這就是田子坊如今給人的直觀感受,各式的消費空間所展現出的色彩風格與老舊的房屋顏色作為背景所襯托出的琳瑯滿目甚至有些致人目眩的風格是它最大的特色。然而,作為游客的人們也許不會去想田子坊作為一個空間是如何被賦予意義的。
何謂空間的意義(這里指城市空間)?現代城市中的空間大多是以其功能劃分的,無論是居住空間還是商業空間,然而在當代都市中這類空間也并非具有較為明顯的區隔。空間意義指的是空間作為功能性場所的定位所傳達出的一種觀念。假如將空間看作城市當中的一種符號,那么由建筑所構成的物理外形,必然是它的能指,而它的功能卻恰恰是它的所指。這里的“功能” 應當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即一方面是空間的實際功能,而另一方面則是空間功能所傳達出的意義,這種意義受到空間實際功能的影響關乎空間給人們的感受。通俗來說就是這個空間對我來說意味著什么?列斐伏爾在提出關于空間的“三元辯證法”之后具體探討了作為想象的空間和物理的實際的空間兩者相結合后所產生的第三種空間批判的視角。而這里我們所探討的空間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可以歸為一種對于空間的想象。
早在租界時期,田子坊所屬泰康路一帶是法租界的南端與邊緣,在這附近建有許多作坊式的小工廠,至1930年小工廠已經有30多家,基本上處于華洋混居的狀態,同時空間功能的復雜化也使得該區域內形成了不同風格的空間格局。
新中國成立后,該地區的石庫門建筑被收歸國有,進而被分配給各單位的職工,同時導致原本一戶人家居住的房子住進了五六戶的人家。①而20世紀90年代產業功能調整之后,里弄工廠效益逐漸下滑,導致整個空間原有功能的衰落,空間內基礎設施老化。在這樣的一個時期之內,田子坊空間所面臨的問題,正是后工業時代城市空間所面臨諸多問題的一個縮影,保持空間運作發展的產業結構的衰退便是空間當中生產方式變革所需要面臨的悲慘處境。而實現空間的再生所需要做的應當是為空間重新確立意義的過程,即重新表征空間存在的過程。陳逸飛、爾冬強等藝術家在1998年開始進駐田子坊,重新將老舊的廠房加以利用,從而將其變為工作室進行藝術創作與實踐。
當初陳逸飛選擇田子坊的時候,是看中了它獨具特色的建筑結構和極具生活氣息的老上海市井氛圍。然而在進駐之后他所要做的事情則是主動參與到了對于空間的改造過程中。在租下了第一個廠房之后,他又將自己的工作室空間不斷擴展。
“陳逸飛選中的老廠房面積大約有800平方米左右,在開設了自己第一個工作室后,陳逸飛又把樓上難以為繼的公共浴室也租了下來,經過裝修,變閣樓為展示室,下面則安置了瓷窯。”②
不僅如此,陳逸飛還同時參與到街道具體的改造空間內部環境與居住設施的工作中,當然這其中的過程不僅包括饒有趣
味地為了弄堂里的垃圾去居委會的投訴,同時也有頗具商業頭腦地租下更多廠房進行經營的決策。事實上最為重要的是陳逸飛等人作為藝術家參與到空間的再建構過程中去了。他們自身的藝術家身份,以及獨特的審美眼光與氣質為空間的再建構提供了更基礎的再建構方向。而這樣的一個過程也是空間意義重建的過程。
城市中最講求的是集聚效應,現代城市本身也是人口集聚的產物。在田子坊空間內部由于陳逸飛、爾冬強等著名藝術家的進駐,越來越多的畫家群體開始關注并進駐到這個空間之內,而陳逸飛本人也為這些畫家的到來提供了較好的平臺。
“在陳逸飛之后,最早來到田子坊的畫家是王劼音先生。2001年,王劼音將自己的畫室搬進了田子坊。”“田子坊畫家樓的規模并不大,五層老廠房里,其實只有下面的三層每天開啟著畫家工作室的大門……雖然同時只能容納不到百位畫家,但十年中在畫家樓里進進出出的畫家,卻有三百位畫家之多。許多畫家來過,走了,過段時間又來了。來了不走,便成為田子坊里的主人。走了的,還想回來,是希望最終仍然可以成為田子坊的主人”。③
除了畫家之外,更多的藝術家與創意工作室開始在田子坊中集聚。畫家藝術家工作方式的獨特性,以及陳逸飛本人對該空間有意地進行塑造的過程,使得田子坊逐漸變為了一個都市中頗具藝術風格的“飛地”,而在這樣的一個空間中,不僅有藝術家的創作,同時還有濃厚的民間生活氣息。在考察畫家選擇田子坊作為其創作基地或者說駐扎點的原因時,我們能夠發現其中有不少的畫家對它的都市地理位置、內部生活氣息、空間建筑特色情有獨鐘。
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包括劉偉光、楊興雅、明麗華、雷振華等人,均是從浦東的畫家村遷入到田子坊之中的,如上文所述,一方面的原因是田子坊本身的空間氣息(這其中自然包含著獨特的歷史建筑風格同時也包括一種生活氣息在內)對藝術家們的吸引,關于畫家們為何選擇田子坊,沈純道先生在《田子坊的畫家群落》一書中,有一段精確的總結:“陳逸飛崇尚唯美藝術,把視覺藝術進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現時的畫家,之所以選擇田子坊,正是認同了這樣的定位,他們沒有去莫干山50號,因為那里的藝術太當代;他們沒有去文定路,因為那里的繪畫太裝飾;他們沒有去大東方,因為那里的風格還沒有形成,誰去都可以。唯有田子坊,給每一個到達此處的人們一種現實的感覺、唯美的享受。”④
另一方面,則是與陳逸飛對這個空間的改造付出的努力分不開的。這些畫家既需要上海這個具有開放窗口的都市,同樣也需要在都市之中找到自身的容身之地。他們所希望的是在被迫離開浦東畫家村的同時將田子坊看作了一個新的藝術家烏托邦。
楊興雅曾經面對日本NHK電視臺記者的采訪時這樣表述他來上海的理由,“上海市是走向世界的窗口,我需要這樣的窗口”⑤。
早期進駐田子坊的畫家們用自身的行為以及他們的身份挽救了田子坊這個即將衰弱的空間。而田子坊作為空間的意義也開始發生了轉化,從一個瀕臨破敗的后工業時代空間景觀的遺產與具有地方特色的
市井文化的混合物到一個藝術家聚集其中并且不斷地被美化的頗具理想特色的烏托邦空間。在這一個階段之內,空間的新意義被逐漸樹立了起來。這個意義或者說此時,空間的所指就變為了一種不斷變化的烏托邦范疇,而作為一種烏托邦的范疇其最重要的特點即是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在多數情況下這種矛盾是存在于想象之中即列斐伏爾所說的第二空間之中)。田子坊空間的烏托邦范疇則由以下三個方面組成:
1.帶有互助性的有明顯的身份標示的群體與都市冷漠人際關系的對立。
2.藝術創作與世俗生活的對立。
3.現代化都市文化與內部市井鄰里文化的遺存的對立。
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規劃者們如何強調,對于空間的物理改造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事實上,假如這個空間不具備它自身的意義,那么這樣的改造終究不能挽回空間衰敗的局面。
當代城市空間的開發不同于以往,開發這個詞本身就是資本運作的方式,以當代我國城市最普遍的現象為例,城市空間被開發商購買之后,那么這個空間必然已經被當作原料買進了,而其最終結果必然是被當作商品進行分割出售,無論是樓盤還是商鋪,概莫能外。然而消費主義的邏輯關心的是對于商品在出售前符號化的表征過程,我們必須用廣告的方式對其進行推銷,而無論樓盤還是商鋪的開發,抑或是小型的消費空間例如咖啡店以及劇場,空間商品化之后它自身的功能已經退居到次要的位置。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將商品進行包裝,即對其進行符號化的過程。鮑德里亞指出:“越來越多的需求、需要欲望被帶進了意義王國,個體丟失了控制權,屈從于代碼符號潛在的重要性使社會變得井然有序,同時使個體產生一種自由和自我決策的幻覺。”⑥
我們消費商品已經不是消費商品本身而是商品被表征成為的那種符號,因而對田子坊的開發必然也具備一種商品符號化的過程,因為這是資本介入城市空間的基本邏輯。這樣的一個過程隨后在田子坊也上演了。
二、符號消費邏輯對空間意義的利用
在經歷藝術家群體自身對于空間自覺以及不自覺的改造過程之后,田子坊作為一個空間的新意義逐漸生成了,而這個新的空間意義在接下來的時間之內根據符號消費的邏輯被資本介入并重新包裝了起來,成為了一個被消費的對象。
在李摯的《自下而上的舊城更新模式研究——以上海田子坊為例》中,作者將田子坊的發展過程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總體上,田子坊的自主更新在空間上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 1998 年至 2004 年工廠區內藝術創意產業集聚區的醞釀發展階段;第二個階段是2005年之后“田子坊”概念擴展,居民區全面開放,商業蓬勃發展的成熟階段。而從入駐的產業形態變遷來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8年至2004年底左右的第一階段,以藝術圈內人士為主;2005年至2007 年第二階段,以小圈層游客進入為標志;2007年之后的第三階段,大眾知名,成為旅游之地”。⑦
從時間上來看,田子坊真正開始被推廣,同時進駐的商業開發主要是在第二階
段,由于第一階段藝術家的進駐與活動本身為空間帶來了新的意義,一種城市烏托邦氣息使得空間本身極具包裝與推廣的價值,在這個過程中空間完成了它的第一步的轉化,空間成為了商品,而空間的新意義成為了商品符號化的對象,具備消費的價值。而伴隨著這個過程的,是空間內部房租的急劇上漲。城市開發的資本邏輯被表現了出來。
在集聚效益的催生之下,城市化過程中最為核心的因素和現象就是房租的持續上漲,由于田子坊的商業區位優勢。加之其本身的由于藝術家集聚所創造的文化價值,自然比城市之中其他的空間具備了更多可被消費的可能性。然而,隨著空間的集聚導致的房租價格的不斷上漲,居民對于利潤的追求更加濃厚,使得一部分不具有市場潛力的畫家群體不得不逃離這個空間。藝術家所追求的那種超然的創作空間,以及蟄伏以期待融入市場的生存環境已經不復存在。
多元化的產業模式已經將田子坊完全變為了一個更加純粹的商業開發的空間,隨后帶來的就是不少藝術家工作室逐步的退場,將位置讓位于資本。2012年《上海青年報》發表了題為《爾冬強藝術中心難以承受租金 無奈告別田子坊》的報道。而在2012年3月20日的《常州日報》上刊登的名為《異彩奪目:田子坊的畫家群》一文中也寫到了一名叫姜昱的畫家因租金問題而無奈離開田子坊的事實。作為一種空間意義被符號化消費的結果,以上的事實給出了最直接的表達。
城市開發過程中的空間生產,開創了一種新的資本介入方式,不同于普通城市那種硬開發模式即對物理空間的改造,資本的軟介入所采取的是另外一種方式,當一個空間具備經營價值時,這個價值事實上就是空間意義本身是否具備市場化的價值,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市場化過程中的品牌效應。資本開發的重點就是將這個空間意義編碼后投入符號消費的市場之中。2006年5月30日的文匯報刊登了題為《上海創意產業集聚區進入品牌競爭 “田子坊”品牌效應日趨顯現》的報道。田子坊本身的品牌符號消費價值開始具體呈現出來。
隨著空間意義進一步被包裝入一個品牌之下,那么這個品牌便成為了一個可被消費的符號。正如我們看到的一樣,集聚開始變得更加多元化,不僅僅是創意產品的生產與經營,更多的還有高端的設計公司,以及不斷增加的餐飲與服務行業,共同構成了當前田子坊本身空間運作的產業基礎與支柱。原有的藝術家的創作空間僅剩下的是被消費的意義,同時也包括一部分能夠融入市場化運作的某種程度上成功的藝術家個體。而我們應當注意到的是,餐飲與服務業的興起事實上是針對日益增多的以體驗為目的的游客群體。如此田子坊完成了它的商業化的過程,同時也就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空間的生產。
三、符號消費邏輯下的歷史空間建構的本質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后工業社會文化消費的浪潮之下,空間已經不單純是一種生產方式以及活動的存在場所,而逐漸變為了一種加以購買和占有的商品,消費空間這樣一種行為一方面包含著對于空間意義的感知與體驗,另一方面同樣也包含著借助空間進行自我表征的過程。在
這樣的一個過程中,生產首先成為賦予空間以意義的行為,而消費則是以購買的方式對空間實施占有的過程,然而人們在對空間進行消費的過程中本身也是參與空間建構與意義傳播的過程。從田子坊的意義轉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從早期的畫家群體、藝術家群體參與對其的改造過程來說,本身是一個較為良性的并且是具有極高審美天賦與能力的人們進行的一次偉大的創作活動,這個活動本身甚至比創作巨幅的壁畫教堂裝飾的天頂更為偉大,因為他們利用自身獨特的審美能力作為在場者,參與到了對社會本身的建構以及空間的重構過程中。而這樣的一種改造正如前文所述是田子坊意義變化以及其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特殊空間而區別于周圍街區的第一次嘗試,在這之后,在城市土地開發的浪潮中,田子坊借助被藝術家群體所構筑起來的獨特文化意義,而獲得了新的開發模式,政府通過整合多方力量將田子坊打造成為創意園區。
事實上我們能夠看到,許多城市對于老城區的再生開發沒有更好地把握第一階段的實質,而往往是從類似田子坊開發的第二階段直接做起,當代城市空間的開發重要的是如何為空間尋找一個確定的意義。無論是對物理空間的硬重構還是資本的軟介入最終都離不開對于空間意義的營銷。當代對于空間的消費首先是文化消費,而文化消費的實質是商品拜物教中所傳達出的那種對于商品符號的消費與占有。而符號的表征自然也離不開對于其所指范圍的確定性。城市作為一個空間,它的推廣同樣也應當遵循這樣的邏輯。因為我們當下的世界是依靠傳媒所構筑起來的。而活躍在傳媒網絡之中的恰恰是觀念,符號作為觀念的表征形式自然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回顧田子坊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對于藝術家來說,要想在城市之中建立自己的烏托邦,已經是難上加難的事情了。因為在理性的理想國中,根本沒有前者的容身之地了。但畫家也必然要參與到市場的浪潮中去,要獲得認可,如何在空間開發的過程中既利用類似畫家群體所創造的獨特空間意義,創造商業價值從而復活一個歷史性的街區,又能夠在商業氣息與文化氣質之間保持良性的張力互動,我們仍然有很多路要走。就在不久前,《北京晚報》有一則消息,說的是南鑼鼓巷因商業氣息太過濃厚而落選歷史文化街區,這同樣值得我們反思。
注釋:
①同上。
②沈純道.田子坊的畫家群落.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5.
③沈純道.田子坊的畫家群落.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23.
④沈純道.田子坊的畫家群落.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33.
⑤沈純道.田子坊的畫家群落.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52.
⑥包亞明.現代性與都市文化理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244.
⑦李摯.自下而上的舊城更新模式研究——以上海田子坊為例,華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責任編輯:盧小文)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tial Significance under Symbolic Consumption Logic: An Interpretation of Tianzif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Vision
Jiang Liye
Abstract:As an urban space, Tianzifang’s re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virtually a proc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significance. And the process to create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s in line with the symbolic logic of current cultural consumption. Therefore, Tianzifang has accomplished the process of commercialization after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spatial significance to the object of symbolic consumption.
Keywords:Symbolic Consumption; Tianzifang; Spatial significance
作者簡介:蔣立業,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G 24 doi: 0.3969/j.issn. 674-7 78.20 5.04.0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