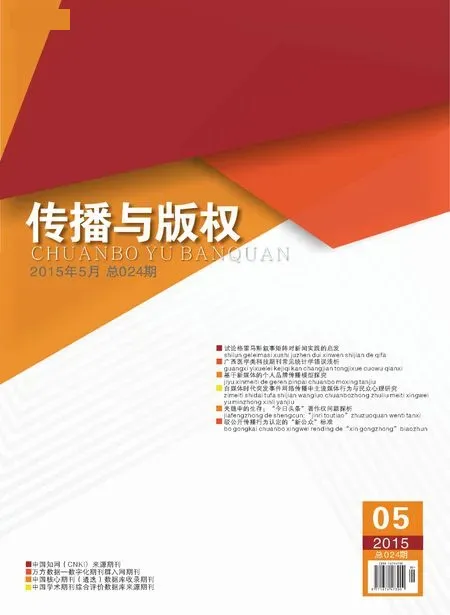網絡虛假信息的散布者研究
蔣正和
網絡虛假信息的散布者研究
蔣正和
在網絡虛假信息散布過程中,各類散布者擔負何種傳播角色?該文從傳播學角度對散布者做出理想型分類,認為在虛假信息的傳播流中共有五類散布者:早期響應者、早期意見領袖、早期跟隨者、后期意見領袖、后期跟隨者,并分析五種傳播者的社會地位、傳播動機和作用。
網絡;虛假信息;散布者
[作者]蔣正和,傳播學碩士,韓山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
一、研究對象
羅杰斯在《創新的擴散》中將大眾傳播過程分為兩塊:一是作為信息傳遞過程的“信息流”,二是作為效果或影響的產生和波及過程的“影響流”。依據創新的接受狀況和影響流向,羅杰斯把創新的采用者分作五類:創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眾多跟進者、后期眾多跟進者、滯后者。虛假信息可以看作是特殊的創新——新穎“信息”。本文只分析在網絡接受虛假信息并隨后決定傳播該信息的傳播者,不考慮那些受網下人際傳播影響而到網絡上傳播虛假信息的人,其原因一是前者居網絡虛假信息傳播者的多數;二是后者變量較多,難以分析比較。
二、虛假信息擴散中的散布者
網絡上一條虛假信息從開始露面到最后被廣泛傳播和認知,許多網民參與這個傳播流中的不同環節進行傳播和擴散,在這個傳播流中,本文把其中的傳播者分為首先響應者、早期意見領袖、早期跟隨者、后期意見領袖、后期跟隨者。在本研究中,虛假信息的捏造者不作為傳播者去分析,沒有傳播虛假信息的接受者也不作為考察對象,因其潛伏的網絡行為很難將其與其他未接受者區分開來。
(一)首先響應者
首先響應者,社會經濟地位較低,一般屬于草根階層,實際社會經驗相對較少,現實的人際圈和信息圈較窄,但花較多的時間用于網絡,對社會的許多認知和看法比較片面,對某些社會人物、事件和現象有較強烈的情緒。偏好選擇是首先響應者的最大特點。他們對虛假信息所反映的特定內容有強烈的興趣,經常瀏覽與此相關的網站、論壇,關注相關博客、微博,并參加一些話題的討論,積極評論、跟帖、轉發。在選擇性機制作用下,既有的心理偏好和認識觀點促使其選擇符合認知一致的信息,這種行為又進一步強化了他的情緒和認知,這種比較強烈的心理更易于發生投射反應。由于其社會經濟地位的限制和個人認知能力較低,存在較大的歸因偏差,以致很難主動利用客觀證據和理性思考,容易選擇性忽略網絡空間的差異信息,他們的表達更多地服從個人心理和情緒。當某一類的虛假信息開始在網絡傳播并與他們的心理切合時,他們通常會最先注意并會迅速開展傳播。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會根據個人偏執的心理和認知,夸大信息內容,使得信息增殖、極化。通過他們,虛假信息在網上微博、論壇、社會網絡(SNS)、即時信息(IM)等空間開始第一波的擴散,在每個擴散的網絡群體中,他們主要是基于投射心理傳播信息,信息的加工整合能力較弱,擴散的主要形式是復制、轉發和情緒性意見,這不一定能被所屬空間的其他人信任,但使得虛假信息被更多人關注、了解和重視,其主要在同質心理人群中傳播,總體擴散速度很慢。如經常瀏覽房地產信息的一些網民會認為高房價是當下中國人最重要和急迫的問題,大部分人買不起房,并為此焦慮不滿,一旦有某人因高房價買不起房而跳樓的小道消息,會立刻關注和傳播。
(二)早期意見領袖
早期意見領袖主要指各個網站或論壇的子版塊、IM小群體(如QQ群)等組織者或核心活躍者,以及受眾群有一定數量但整體偏小的普通自媒體人。他們通常受過較好的教育,擁有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但社會經濟地位整體不高,“在現實生活中基本都為平凡之輩”①王傳寶、李劍橋:《軍事論壇意見領袖的行為特征及培養 ——以鐵血網陸軍論壇為例》,《青年記者》,2014年第1期。,僅在所屬的網絡空間扮演著群體意見領袖的角色。他們一般處于網絡子群體的傳播中心,能夠把握該網絡空間群體的心理情緒,并擁有較多的信息渠道,同時有機會和能力獲取網絡群體之外更多的信息。
他們需要經常與群體其他成員或其粉絲互動,主要方式是網絡信息傳播。由于缺乏其他社會資源,為了保持網絡地位,獲得某網絡空間群體的認同或關注,他們需要在網上特別努力,要主動搜尋網絡最新的信息,不能錯過熱點話題,以免落在群體認知的后面。早期意見領袖多從首先響應者或其他早期意見領袖那里獲得虛假信息,若預判該信息能引起群體關注,在缺乏有力印證的情況下,可能就會匆匆傳播虛假信息。其中一些人還會將信息裁剪、添加、修飾,以迎合群體心理和偏好,吸引眼球,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如果說虛假信息在首先響應者那里主要會有朝向響應者個人情緒和心理偏向上夸張的問題,在早期意見領袖環節,則是虛假信息主要會有朝向群體情緒和心理偏向上變異的可能。
(三)早期跟隨者
早期跟隨者在現實中的社會經濟地位一般,主要是有較高網絡參與熱情的普通網民,如一上網即在某社區某版塊瀏覽信息、參與討論,或加入QQ群聊天,作為社區的積極呼應者,他們“密切關注社區的動態,對于社區發起的話題也非常積極,幾乎對于所有話題都能發表一定的回復”①宮承波、齊立穩:《試析網絡社區的角色扮演》,《新聞界》,2008年第2期。。又或上微信、微博瀏覽和發布信息,積極轉發、評論所屬網絡圈的意見領袖的信息。早期跟隨者網絡參與的動機主要是基于尋求群體認同或人際交往的心理需要,選擇的網絡空間與他的興趣或觀點基本一致,并與其保持較大黏性,是其忠實的用戶和積極的參與者。但他們缺乏主見,對話題的關注和看法易受早期意見領袖的影響。
虛假信息經由早期意見領袖的傳播,即進入所在網絡的話題議程。該網絡子空間的信息環境越封閉和同質化,早期跟隨者越缺乏差異化的信息源和理性能力去質疑,大多跟隨早期意見領袖,擴散虛假信息。
虛假信息的內容、觀點與早期跟隨者的情緒、興趣、看法越相符越一致,被擴散得越迅猛。但早期跟隨者不是一個領導者,缺乏能力和意愿去主動挑起話題,擔心得不到群體內其他成員的認同,即使有首先響應者或其他干涉者將虛假信息傳入該網絡子空間,早期跟隨者也要等到早期意見領袖的確認和傳播,才跟隨響應。隨著響應者的增多,信息流瀑機制開始發揮作用,“一旦一定量的人開始相信一則謠言,其他人也會相信”②[美]卡斯·R.桑坦斯:《謠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5頁。。這樣,早期跟隨者與早期意見領袖一起促成了虛假意見的群體氣候。
(四)后期意見領袖
隨著BBS、論壇、博客等受眾不斷減少,微博的用戶越來越多并逐漸成為后期意見領袖的主要傳播平臺,據統計,截至2014年12月,我國微博用戶規模為2.49億③中國互聯網網絡信息中心:《第3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201502/P020150203551802054676.pdf,2015-2-3。。“微博給每個人都提供了成為意見領袖的可能,但從數量和質量來看,以傳統精英為主”④王平、謝耘耕:《突發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見領袖的實證研究——以“溫州動車事故”為例》,《現代傳播》,2012年第3期。,后期意見領袖主要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社會地位高、現實影響力大,他們可以將網下的信息資源、人脈資源或物質資源轉化為網上的獨特信息內容、人氣吸引力和高信任度。與這種名人效應相伴而來的是,公眾對后期意見領袖的媒介道德也有較高的期待和要求。后期意見領袖與普通網民同樣轉發虛假信息,大家對后期意見領袖的指責遠超普通網民。與早期意見領袖不同的是,后期意見領袖的傳播對象數量大、異質化程度相對較高,彼此及其與后期意見領袖之間極少人際交往,主要黏合劑是后期意見領袖的獨特信息和人格信任。同時,后期意見領袖不存在網絡匿名性效應,網上的言行直接影響網下的生活和社會形象。微博是一個比較開放的言論空間,后期意見領袖并不能控制微博平臺,他們自己及其信息內容都處在一個激烈競爭的信息環境中,這些都對后期意見領袖的言論形成很大的壓力,促使他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開展自己的信息傳播活動。相比早期意見領袖,后期意見領袖有更多的資源去吸引粉絲,總體上不太關注信源不明、嘩眾取寵的虛假信息。在傳播信息時,一般也會先考慮微博的形象和美譽,傳播的動機主要是個人的興趣、所長。在微博使用初期,后期意見領袖的網絡媒介素養不夠是其傳播虛假信息的主要原因。
在虛假信息傳播流中,后期意見領袖扮演類似大眾媒介的角色,不管是因把關不慎還是主觀有意,虛假信息通過后期意見領袖的傳播后都將為很多社會公眾所關注,逐漸浮出輿論的水面,成為社會關注的議程。在異質化程度較高的微博空間,關注越強烈,虛假信息被質疑的可能越大,愈能引起社會各方的重視和差異信息的匯集,那些知道真相的人會立刻跟進回應。從這種角度上說,后期意見領袖的傳播一方面可能促使虛假信息在全社會的擴散;另一方面也將促成“一個均衡的信息環境”⑤[美]卡斯·R.桑坦斯:《謠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69頁。,幫助真相加快到來。
(五)后期跟隨者
跟隨在一些知名自媒體之后傳播虛假信息的即后期跟隨者,一般是微博的活躍用戶,他們積極參與微博平臺的各種互動。他們主要是基于個人興趣、認同心理和表達需要而成為后期意見領袖的跟隨者。他們傳播信息比較謹慎,比較相信后期意見領袖,認同權威,把后期意見領袖的信息看作是傳統媒體上的新聞。通過轉發、評論知名的后期意見領袖微博,傳播信息,傳遞觀點,以滿足自己的表達需求和社會參與需求,后期意見領袖對他們有較大的信息議程設置的影響力。虛假信息一般是針對具體事件的捏造、歪曲,這種“具體議題”①[美]沃納·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257頁。易于被受眾理解和感受,后期跟隨者更易受議程設置的影響。但這種影響越大,也就越快促成一個均衡的信息環境。
三、結語
在網絡虛假信息的散布過程中,信息自身特點對擴散的速度、范圍、人群都起著重要作用,網絡虛假信息的傳播擴散也離不開傳播時機、受眾特質、傳播環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本文中的五種傳播者在虛假信息傳播流中的位置不是涇渭分明的;每種傳播者的特點和內涵不是完全獨有的,存在互相交叉,如首先響應者與早期跟隨者,可能具有同樣的從眾心理,且在情感投射上也可能是相同的。這種分類是一種理想型分類,可以作為分析虛假信息傳播者的一個框架,以明晰不同傳播者的傳播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