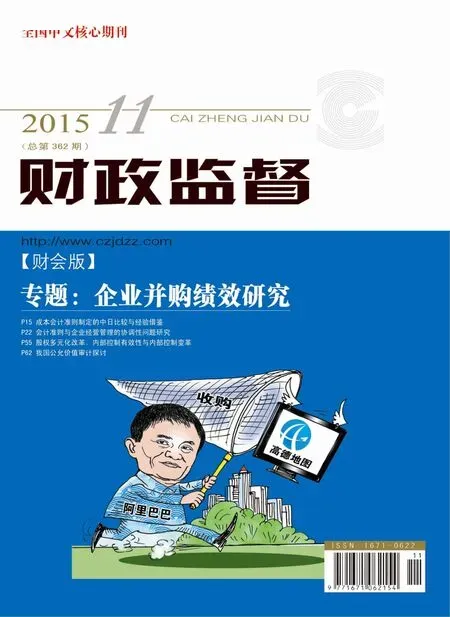論“三權并行分置”模式下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
——以解釋論展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方 琪 南昌大學法學院 胡 帥
論“三權并行分置”模式下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
——以解釋論展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方 琪 南昌大學法學院 胡 帥
“三權并行分置”模式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分化為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意在從法律賦權向法律賦能轉變。解禁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處分權能限制,需要以解釋論展開,解決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合法性問題。依法學方法論而言可有多種解釋思路,一者以價值補充的進路,將抵押解釋為“或其他方式流轉”、“等方式流轉”等兜底性條款之中。二者以反對解釋的進路,堅持 “三權并行分置”模式下的三層級權利分離體系,《物權法》第184條和《擔保法》第37條命令禁止的應是農民的承包權,而非農民經營權。
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三權并行分置 確權賦能 解釋論
一、“三權并行分置”模式
土地承包經營權系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下由家庭承包經營的一類土地權利,土地所具有的最后生存保障功能有著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市場經濟的作用力不斷深入農村經濟領域帶來的土地資本革命,農地所具有的傳統功能之涵義在不斷變化。農地權能結構由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 “兩權并行分置”向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并行分置”發展,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性權利之意義在于提高資源配置和生產經營效率,維護社會穩定。
《憲法》第10條確定土地由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二元體制,而對于農村如何發展集體經濟,《憲法》在第8條作了制度性規定亦即堅持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以此解放農村生產力,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然而隨著我國在1992年確立市場經濟以來,農村社會經濟結構也不斷融入到新型化的金融變革之中。農業是弱質產業,決定了其在參與市場競爭時不具有像工商企業般適應供求市場的適應能力,使得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效益低下。“以土地權利為核心的整個不動產權利體系都必須以滿足市場的需求為其根本使命”。1法律的價值取向在于縮小應然與實然層面之間的缺口,以權利為本位的法律應該以實現實踐需要的目標模式為追求。激活土地權利的市場價值,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水平是農村土地金融改革的重點。然而作為民事主體最基本權利規范的《民法通則》未能準確明晰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屬性,這一重擔便落在眾所期待的《物權法》肩上。
從私法的角度而言,《物權法》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界定為用益物權,一者結束了學界長期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性質的爭論;二者意在通過法律制度賦予農民更多的民事權利,以促進財產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從體系解釋來看,土地承包經營權被放在建設用地使用權等用益物權前面進行規定,從而體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在物權體系中十分關鍵和突出的地位。這是因為對于現階段的中國億萬農民而言,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僅承載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功能,也是追求財富的主要手段,因此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律關系的規范與否切實關系到國計民生。
二、“三權并行分置”模式下的賦能強權
《物權法》第127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自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生效時設立,由此規定可知農民基于集體成員之“身份”性質與村集體簽訂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即可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既然《物權法》將其確定為用益物權,那么就 “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一概念如何解釋便存在爭議。用益物權屬于他物權為廣義上物權之一,而依據“土地承包經營權”字義而言,可解釋為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等等,如此哪一種解釋屬于農民享有的物權性權利?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可見《決定》將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解釋為獨立的經營權和承包物權而允許設定抵押擔保的僅為經營權。2從靜態意義上來看,法律賦予農民承包土地以物權屬性在于讓農民享有更充分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轉等財產權利,從動態意義上而言,僅僅賦權于民尚不足夠,必須解禁處分權能之限制,實現物權之本質屬性。因為“法律賦權僅停留在法律對于弱勢人群權利的書面確認和靜態描述中,而法律賦能則在此基礎之上尋求權利和能力的動態實現,將權利上升到了實在的能力。”3
《憲法》所規定的土地二元所有制度不可突破,《物權法》賦予農民之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決定》將其分化為獨立的經營權和承包物權,“三權分離”即為集體所有權、農民承包物權、務農者的經營權。“三權并行分置”模式之建制是為修正《物權法》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所欠缺之處分權能,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從民法角度而言,實現農地利用的規范化經營是農民作為民事主體權利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護農民利益實現、維護國家穩定的應有之義。土地作為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具有資源與資本兩種資源稟賦,《物權法》的制度性規定反而使得其資本價值一直處于 “沉睡”狀態,農民作為一個市場理性“經濟人”,貨幣資本是其在市場經濟下追逐利益的最佳工具,而土地則是其重要的財產資源,也是其發揮資金融通的最重要的資本交換物,激活沉睡資本意味著要解禁處分權。
三、解釋論的展開——解釋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合法化的進路
從農村土地改革制度變遷歷史來看,誘致性制度變遷在前,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介入在后即“實踐先行、政策指導和法律兜底的‘三部曲’模式:農民基于基層實踐的制度創新獲得國家政權認可后,通過政策文件進行指導和推廣,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后交由法律文本作出最終提煉和回應。故而,相較于農民的首創行為對體制障礙的突破,法律規范呈現出明顯的滯后性”4。《物權法》第184條和《擔保法》第37條均是直接明令禁止農民耕地的抵押,《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2條未能將抵押這一流轉形式單獨予以并列形式列舉,很難明晰其立法態度,從《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5條可以看出司法實踐明確否定抵押合同的效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司法的態度決定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實踐的不可能性。
從法律角度而言,“三權并行分置”模式的構建尚且建立在黨和政府的各類政策文件之中,在眾多高位階的法律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以法律文本作出最終提煉和回應之前,具體實踐所依據的各類指導性文件和政策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效力的低質性、適用的滯后性。從基層實踐角度來看,政策精神和政策文件給予其強大支持,面對二元矛盾困境,現階段采取解釋論的立場實屬必然。
法學又稱為法解釋學或法規范學,乃以法規范為其研究對象,以確定其法意,需加闡明;不確定之法律概念,須加具體化;法規之沖突,更須加以調和也。5因此解釋論一般主張依法學方法論為指導,利用解釋現有法律規范來進行正確理解和適用,藉此破除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法律制度障礙。
(一)價值補充的進路。價值補充,介乎狹義的法律解釋與漏洞補充之間,乃系對不確定法律概念及概括條款的一種解釋方法。6以價值補充為主的思路可以將抵押解釋為“或其他方式流轉”、“等方式流轉”等兜底性條款之中。
從現有法律規定來看,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只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三項權能,而缺乏處分權。而在民法上,抵押作為擔保物權一般也是物權人利用所具有的交換價值亦即處分權能而言。《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2條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其他方式流轉。而《物權法》第128條通過“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這一轉介用語只列舉了轉包、出租、轉讓三種具體方式,以“等方式流轉”作為兜底性條款。可以看出《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均采取了列舉式和概括式相結合來規定流轉方式的立法模式,為以后解釋或修改法律留下缺口。《物權法》第128條將互換去掉,因為轉讓意味著法律權利主體之變更,從引起轉讓的法律行為來看其包括互換。并且事實上出租一詞日常所用之義與此處所謂轉包意義亦有相合之處。
民事立法向來以用語抽象,技術性強、邏輯嚴密著稱,《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所用之語顯露粗糙卻仍未將抵押列舉進來,以立法史的眼光來評析當初全國人大法工委負責起草的《民法典征求意見稿》和《物權法(草案)》,均會發現二者都曾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然而眾望所歸的《物權法》卻舍棄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的規定。考察立法者的立法說明,可知一者農地承載著社會保障功能,是農民安身立命之本,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建立之前不易放開;二者從全國范圍來看,放開抵押的條件尚未成熟。然而如今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已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基礎遠勝于前。并且市場經濟的深層次改革已然深入農村,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使土地固有的資本稟賦不斷散發。
以目的解釋或歷史解釋而言,應依社會經濟實踐就立法資料予以評估,實現立法意思的現在化及客觀化。當時法律雖沒有規定抵押,但卻以“或其他方式流轉”、“等方式流轉”作為兜底性條款等概括性規定留下一個開放缺口,從規范的意義上講,這隱含著立法者旨在條件成熟時可以放寬抵押。無論是從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來看,還是全國范圍內農村基層的抵押實踐而言,解禁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條件業已成熟。
除去事實上的處分,民法上所言處分權是指依照民事權利所有人的意志,通過一定的法律行為對財產進行處置的權利,比如轉讓、贈與等。既然法律將轉包、出租、轉讓等方式以并列方式進行列舉,從法條邏輯結構而言,其含義大致相近,均指對標的所作的法律上的處分行為。再觀之 《物權法》第133條,其規定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農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轉讓、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轉。轉讓、入股是對標的所作的法律上的處分行為固無異議,然從抵押一詞也與此二詞并列而言,以法條邏輯結構可以解釋抵押亦為與轉包、出租、轉讓、入股等流轉方式含義相近且均為一種法律處分行為。
(二)反對解釋的進路。反對解釋,系指依照法律規定之文字,推論其反對之結果,借以闡明法律之真意者而言,亦即自相異之構成要件,以推論其相異之法律效果而言。6以反對解釋的進路是在“三權并行分置”模式下對《物權法》第184條和《擔保法》第37條的解釋。
《物權法》第184條和《擔保法》第37條規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但法律規定可以抵押的除外,顯然二者的態度是直接明令禁止。從文義解釋的規范來看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是一個不可逾越的禁區,此處耕地應指通過家庭承包取得農村土地。依據“三權并行分置”模式而言,即為集體所有權、農民承包物權、務農者的經營權。從憲法的規定來看,集體所有權不能抵押是憲法的制度性規定,《物權法》第184條和《擔保法》第37條規定耕地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應理解為集體擁有所有權的土地權能之上的一種“使用權”,應當是指具有物權性質的農民承包物權。因為農民擁有該權利是以《物權法》第128條所規定的承包合同之債權方式設定的,從農村集體的角度而言就是對集體擁有所有權的土地權能之上 “使用權”的債權式讓與,而從農民角度就是取得的承包權,為法定物權。
因此在解釋《物權法》第184條和《擔保法》第37條時堅持“三權并行分置”模式下的三層級權利分離體系,就可以避其鋒芒。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前已述及,此處不得抵押只限制在具有物權性質的農民承包權,以反對解釋就不應包括務農者的經營權。而通過對《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2條、《物權法》第128條和第133條的重新解構而言,務農者的經營權可以抵押亦可以解釋為《物權法》第184條和《擔保法》第37條法律規定的例外,而納入對前面《物權法》第128條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2條的解釋之內。
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被解釋進現有法律框架之內,是對土地承包經營權處分權的解禁,有利于發揮物的最大效用,實現法律賦權向法律賦能的轉變,符合權利人的內在要求,因此解釋論的立場與《物權法》第1條之立法旨趣相符。
四、結語
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是“確權賦能”的結果,是市場經濟下實現民事權利主體由靜態權利向動態權利實現的必然選擇。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并行分置”模式不僅在于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也有利于解釋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合法性問題。依法學方法論而言可有多種解釋思路,一者以價值補充的進路,將抵押解釋為“或其他方式流轉”、“等方式流轉”等兜底性條款之中。二者以反對解釋的進路,堅持“三權并行分置”模式下的三層級權利分離體系,《物權法》第184條和《擔保法》第37條命令禁止的應是農民的承包權,而非農民經營權。■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規劃項目 “農地入股股份合作企業的法律規制”〈批準號:FX1405〉、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二五”(2015年)規劃項目“農用地抵押貸款風險控制法律制度的研究”〈批準號:15FX27〉,及2014年南昌大學創新學分科研訓練項目“農地抵押擔保法律實務研究——以江西省農地為例”〈項目批準號:1400131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孫憲忠.1997.論我國土地權利制度的發展趨勢[J].中國土地科學,6。
2.陳小君.2014.我國農村土地法律制度變革的思路與框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相關內容解讀[J].法學研究,4。
3.馮果、袁康.2012.從法律賦能到金融公平——收入分配調整與市場深化下金融法的新進路[J].法學評論,4。
4.徐勇.2012.農民改變中國[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5.王澤鑒.民法基礎理論(民法實例研習叢書第一冊)。
6.楊仁壽.2013.法學方法論(第二版)[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