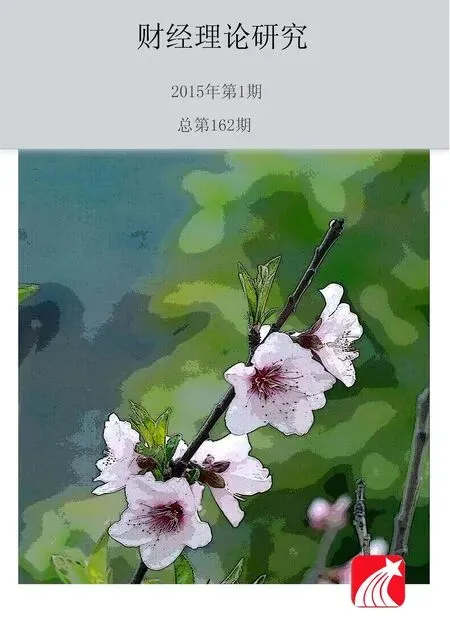我國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困境與出路——基于社會化小農的調查分析
我國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困境與出路
——基于社會化小農的調查分析
楊曉鋒
(武漢紡織大學會計學院,湖北武漢430200)
[摘要]社會化小農作為現代社會小農演進的新形式,是聯接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的橋梁,也是生態農業發展的重要主體。通過對社會化小農的調查取證,厘清了社會化小農的突出特征。立足于社會化小農這一分析進路,找出了我國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困境,并初步確立了農業科技創新、制度創新以及改造社會化小農三位一體推進生態農業發展的思路。
[關鍵詞]生態農業;社會化小農;可持續發展;農業生態環境;人力資本投資;創新
[收稿日期]2014-06-08
[作者簡介]楊曉鋒(1982-),男,湖北麻城人,武漢紡織大學會計學院講師,博士,從事農村經濟、人力資本與收入分配、產業組織與經濟發展研究.
[中圖分類號]F323.22
人們對農業的需求從傳統意義上的吃得飽向吃得安全、吃得營養、吃得健康轉變,對農產品的多樣性、農業的生態服務和文化傳承等多功能性更加關注。但是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仍十分脆弱。化肥、農藥施用強度高,流失量大,使耕地和地下水受到大面積污染[1]。全國第一次污染源普查顯示,農業源污染物排放中,COD排放量為1324.09萬噸,占全國總量的43.7%,TN、TP排放量為270.46萬噸、28.47萬噸,分別占總量的57.2%、67.4%[2]。農業生態系統既是系統外環境污染的受體也是污染物產生源頭,農業生態環境污染的直接后果必將威脅國民的飲食安全[3],加劇人們生活的危機感與挫敗感。在整個農業生態環境污染源監管客體中,最大的難點還在于星羅棋布于我國城鄉的社會化小農。社會化小農作為徐勇、鄧大才、劉金海等學者提出的針對農村發展問題的一種新的分析框架[4-6],揭示了我國農民演進的時代特征,契合并拱衛了農業家庭經營制度[7]。社會化小農是聯接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的橋梁,也是推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重要主體。通過對湖北省武漢市、黃岡市等共四個市、七個縣374戶社會化小農的調查取證,厘清了社會化小農的突出特征,立足于社會化小農這一分析框架,直擊我國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困境,并初步確立了農業科技創新、制度創新以及改造社會化小農三位一體推進生態農業發展的思路。促使占中國絕大多數農業生產形態的社會化小農自覺走生態農業發展之路,不僅能從根本上治理我國農業生態環境污染,對推進“四化”同步亦有重要意義。
一、社會化小農的特點
傳統小農經濟時代,生產活動以農業生產為主、以自給自足為目標,是一種相對獨立、靠天謀生的生產生活方式。關于傳統小農的發展演化問題的論著頻現于國外經典文獻,如孟德斯鳩的《農民的終結》、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小農的滅亡”等的論斷[8-9]。然而,時至今日,以家庭經營為主的小農農業生產模式仍表現出極強的生命活力,且遍布全球,成為推動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社會化小農作為現代社會小農演進的新形式,一度成為政策理論界關注的焦點,也讓這個搖擺于傳統小農與新市民之間的特殊群體不再邊緣化,漸入主流大農業發展學科研究者們的視野。實際上,社會化小農這一概念模式的提出,一語點破當前小農的本質特點,有效回應了農業生態化、現代化發展出路問題,也是一種全新的分析進路。從社會化小農的內涵看,社會化小農是一種被外部社會全方位、整體性影響并型塑的小農形態。通過對湖北省武漢市社會化小農的調查取證,我們發現小農與大中型農戶以及傳統小農相比,其社會化印跡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農業生產主體社會化
從調研主體基本情況看,社會化小農主體社會化主要表現為農民個體的社會化和農民身份的模糊化兩個方面。就農民個體的社會化而言,農民個體在生產組織過程中不再依靠過去的家庭單位,農民也不是低素質群體[10],約八成的農民能獨立完成農產品的生產與銷售,這也意味著社會化小農充分整合了農業技術創新成果、現代社會文明進步成果等資源,其資源配置能力大幅提升;就農民身份的模糊化而言,活躍于城市街頭、農產品集散地的小農兼有市民和農民雙重屬性,他們能利用農業區位優勢、熟練駕馭農產品市場機制,發揮小農經濟作業靈活、精確等得天獨厚之優勢,他們從事完全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專業化生產,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現代農民,是中國農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就是新型職業農民[11]。
(二)農業生產過程社會化
生產過程社會化集中體現在產前、產中和產后三個環節,較傳統意義小農作業已有根本性的轉變。湖北省武漢市社會化小農主要以蔬菜種植、家禽水產養殖等投資短、收益高的農、副產品生產為主,為便于分析其社會化表現,這里以蔬菜種植為例。調研發現,農戶蔬菜生產前的基本生產資料幾乎無一例外地源自外購,蔬菜種子外購率達到100%,其他生產工具外購達到90%以上,農家肥外購率也達到86%,這種社會化小農與自給自足傳統小農已是涇渭分明;在蔬菜種植、蔬菜管理以及蔬菜采摘環節中,也導入了現代農業科技以及其他新興技術,如在除草和防蟲過程中,農戶既可以選擇除草劑,還能選擇其他生物制劑,亦可通過農業技師傳授的蔬菜間作實現防蟲治蟲的目的;在生產后期,農戶根據農產品市場、農產品物流等信息元,統籌農產品的銷售、加工和運輸,對農產品施行及時供應、有效供應。需要指出的是,在傳統農業和過渡性農業之間,不僅農戶農業生產行為呈現出游離狀態[12],而且農戶農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也呈現出游離特征。
(三)農業生產決策社會化
生產作為實現消費的手段,其決策具有重要的工具性意義。當前,小農農業生產決策社會化的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在選擇何種生產結構方面,社會化小農更注重對農產品生產風險、農產品市場供求信息、農產品物流水平、農產品生產成本等過往信息經驗的分析,而不是根據自己的種植經驗簡單安排生產結構;二是社會化小農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貨幣,滿足社會化生活需要,這也意味著社會化小農生產決策的基本前提是貨幣最大化,也即如何在短時間、低成本條件下獲取最大化的貨幣量,儲蓄剩余貨幣而非投資或全部消費是社會化小農一種常態化的理財行為;三是社會化小農具有較強獨立做決策的特征,這表現為單一農民便能實現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運輸與銷售,并且這種多面手的發生率高達80%以上,顯著異于大中型農戶以及傳統小農農戶成員之間的分工協作。
二、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困境
生態農業是把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發展和保護環境為一體的新型綜合農業體系[13-14],與可持續農業基本目標一致,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生態農業發展的關鍵不僅取決于農業技術革新、充足的物質資本投入,更在于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農民主體的質量。社會化小農作為一種常態,仍然是我國農業基本生產單位,也是構成生態農業發展系統的細胞單元。社會化小農的生產作業方式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城鄉居民生活質量與食品安全,對我國生態農業發展也將產生深遠影響。對社會化小農的實地調研發現,當前我國生態農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困境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薄弱
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主要是指投入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各類物質資源的循環與再利用,主要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等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15]。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是生態農業發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支撐生態農業持續發展的技術基礎。調查顯示,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過程中對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意識較為薄弱,且掌握的農業可持續利用技術也較為落后。
土地作為人類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是人類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生態農業發展的基礎,其基本內容涵蓋穩定或增加土地的有效耕種面積、提高土地生產質量等方面。約八成的社會化小農認為土地可持續利用技術與傳統小農傳承的土地循環利用相同,約六成的社會化小農認為現代農業科技可以取代土地可持續利用。顯然,社會化小農在思想上淡化了對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重要性的認識,并且由于過于迷信現代農業科技,滋生出了更令人擔心的念頭:即現代農業科技不僅能顯著提升土地資源的產出率,還能大幅削減土地資源的維護成本。實際上,社會化小農對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的理解的偏差,并不完全是因為該技術的供給不足造成的,與社會化小農自身的活力不夠、能力不強有直接關系。調查統計顯示,社會化小農平均年齡46歲,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5年,平均從事農業生產年限為29年,人均耕地1.8畝。
更進一步的調研發現,由于社會化小農拋棄了傳統小農的循環耕種技術,先進的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也因缺乏有效激勵而不曾導入其中,以至于大部分社會化小農耕種的土地自然肥力下降,且有效耕種面積也在逐年縮減。社會化小農坦言,過去種植一年的蔬菜所需要的肥力要明顯小于來年的肥力,并且種植面積也因為肥力下降、水土流失、土壤板結等而逐漸縮減。值得一提的是,仍有一小部分較為年長的社會化小農不僅沿襲了傳統小農農業資源再利用技術,還創新了可持續利用技術,大幅改善了農地生態環境,也提升了土地的產出水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農業生態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特性,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缺位,這也是農戶有效耕種面積逐年縮減的重要原因。
(二)農業粗放式生產仍占主流
農業粗放式生產的本質是農業生產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和低產出,主要表現為農藥、化肥、水資源等的不合理施用,是一種投入產出率較低且不可持續的農業生產模式,與生態農業發展理念格格不入。但在兩型社會建設背景下,粗放式農業生產不僅沒有被集約型生產所替代,反而成為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的主流模式。對社會化小農進行深度訪談后發現,大部分社會化小農偏好于粗放式生產的原因為:
一是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高于非農就業。如前所述,社會化小農生產過程、生產決策高度社會化,這也使得其在選擇從事農業還是非農就業過程中充滿了博弈。成本與收益的動態關聯關系構成社會化小農選擇就業結構的基本準則。對于地處城鎮邊緣的社會化小農而言,農業區位優勢較為明顯、非農就業優勢較弱,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與非農就業之間往往是難于抉擇的,但是由于農民生活態度的轉變以及農業生產的艱苦與危險,也倒逼社會化小農盡可能選擇少投入工時于農業生產;對于地處偏遠的社會化小農而言,農產品區位劣勢較為明顯,農業生產機會成本顯著高于非農就業,大部分社會化小農選擇離鄉不離土非農就業,留守農村的社會化小農的農業勞動參與率顯著下降,人均實際耕地大幅提升,他們不得不選擇粗放式農業生產模式。
二是基于社會化小農專業化分工后“規模”生產的需要。社會化小農家庭內部的分工較傳統小農有顯著的不同,最突出的特色在于,農戶內部的每一個農業勞動力都能成為獨立的農業生產者。調查顯示,約有五成的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由一人完成,其中約有六成的是由女方獨立完成農業生產,男方則多從事勞動工資高的非農就業或者農產品物流等職業。在這種家庭專業化分工背景下,一戶擁有的土地實際由一人承包耕作,農村人地矛盾的痼疾基本得到了根治,農地“規模化”也給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經營提出了更高要求。拿蔬菜除草、防蟲、澆灌來講,單一社會化小農要管理三畝以上的土地,他們必須選用更為高效的除草劑、殺蟲劑,采用更為徹底的澆灌,而不是精耕細作。
三是現代農業技術為“農業新式粗放式”生產提供了便利。現代農業技術的興起,不僅為農業現代化提供了技術支撐,也為社會化小農選擇更為靈活的生產方式提供了可能。過去蔬菜種植無休止、繁雜的除草工作,而今只需要一袋高劑量除草劑就解決;過去面臨旱季時的人工澆灌,而今只需要一臺小功率水泵就近或就地取地下水,一頓田間式的灌溉即可;過去蟲災泛濫引致大量人工投入治蟲,而今從菜苗到蔬菜下架都有價格較低的高倍農藥,蔬菜幾乎見不到一個蟲洞。從種子選擇到菜苗孕育,再到蔬菜采摘,整個農業生產都融合了現代農業科技,一些社會化小農甚至自詡已達到農業現代化。但是,社會化小農對農藥的使用量、化肥的施用量、水資源利用等的科學合理性并沒有理性的認識,常常憑借主觀感覺,以農產品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投入產出的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顯然,這種粗放式生產與生態農業發展要求相去甚遠。這也是農業已經演變為立體交叉污染最為嚴重的產業的主要原因。
(三)農產品安全生產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協調性差
生態農業就是要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基礎上,生產出品質較高、品種多樣、產量較大的農產品。農產品安全生產是生態農業的基本要義之一,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有著內在一致性。農產品安全生產要求農業生產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同步進行,二者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共同作用于生態農業的發展。然而,社會化小農對農業生產安全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關注遠遠不及他們對整個農業生產的投入產出經濟效益。一言蔽之,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的強逐利性是造成農產品品質較低、品種單一等農業不可持續性問題的罪魁禍首,究其緣由有三:
第一,農業生產在社會化小農家庭中的經濟地位被削弱。長期以來,農業經營一直充當農戶生計中堅的角色,是家庭經濟的重要來源。社會化小農時期,非農就業機會的可得性增強,農業經營的工資性收入常常難以覆蓋其教育、醫療、娛樂等投資與消費需求,農業經營的核心經濟地位逐漸被較高工資水平的非農就業所替代,成為化解剩余勞動力、彌補農戶家庭生活消費不足、維系養老等的副業。實際上,退守農業的社會化小農多因年齡過大、技能較低、健康狀況不佳等緣由被非農產業所隔離。農業經營的弱經濟地位以及農民之間財富攀比的升級,使得社會化小農更關注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淡化了甚至無暇顧及對農產品安全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關注。
第二,農業安全生產意識淡薄,且農產品市場質量監管制度缺失。農業安全生產是農產品品質的保障,事關人們飲食健康與生命安全。然而,一些社會化小農為了一己私利,全然不顧道德良知,將存在食品安全隱患的農產品直接投放市場。訪談得知這樣的事例,有小農獲知某農產品市場價格較高,但該農產品種植還未成熟,便買催化劑強行將未熟的農產品催熟并投向市場;還有小農為了搶農產品市場價格,認為只要吃不死人就算安全,將噴過殺蟲農藥的農產品未按規定間隔期便采摘直接投放市場。由于農產品市場質量監管制度極度缺失,特別是針對那些“對手交易”游蕩在城鎮大街小巷的農產品商販缺乏必要的監管,消費者自身也因難于甄別農產品的品質而誤買問題農產品。盡管這些做法并未產生顯性惡劣的影響,但是這種慢慢侵蝕社會化小農社會良知、損害廣大消費者身心健康的行為,已然給生態農業發展敲響了警鐘。
第三,粗放式農業生產給農田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社會化小農化肥、農藥等高投入,不僅造成了農藥殘留超標、土壤板結、土地自然肥力下降等惡果,對農產品品質及多樣性、農田生態系統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特別是那些兼業家禽養殖與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小農,既沒有科學處理家禽糞便,也沒有有效掌握養殖與種植之間的循環利用技術,造成嚴重的水體污染,使得原本脆弱不堪的農田生態自然環境更加難以為繼。
三、我國生態農業發展的出路
生態農業發展離不開農業科技進步、惠農支農政策,更離不開社會化小農強力推進。社會化小農推動生態農業發展的出路在于:
(一)加強生態農業科技革新
科技創新被譽為推動生產方式轉變的引擎,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農業科技創新是實現農業生產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相統一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動生態農業全面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盡管官方權威公布顯示,我國農業科技貢獻率已達到50%[16],但是,對于社會化小農而言,除了種子的改良值得稱道外,其他農業科技成果并不為奇。生態農業發展不僅要滿足社會化小農基本的經濟利益訴求,更應注重生態農業科技的革新,這包括生態農業發展觀念革新、生態農業種植養殖技術革新以及農田生態系統保護革新三個方面,具體而言:
生態農業發展觀念革新。首先,要幫助社會化小農建立正確的農業資源觀,即要有資源的循環利用與不可再生資源保護的意識。農業資源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生物資源等,農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生態農業發展的基本物質保障。對可以循環利用的農業資源要注重其循環利用節點間的銜接,使其發揮更大地的功效;對不可再生的農業資源要適可而止、有序采用,注重對其實施保護。其次,要摒棄舍本逐末的農業生產觀。農業生產既有顯著的經濟效益,也有明顯的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對于整個農業生態環境而言,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是附加于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之上的額外收益。若社會化小農只一味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勢必會形成一種殺雞取卵的急功近利之風,也是得不償失的生產行為。最后,建立科學的生態農業生產作業模式。高投入的農業生產模式固然可以節省人工,但是卻不利于農產品品質的提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倡導集約型農業生產,借助現代農業科技成果,加強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的耦合,改善農業生產內外部環境,提升農業生產率與綜合產出效益。
生態農業種植養殖技術革新。根據社會化小農人力資本分布特點,結合農產品市場狀況,針對農田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由農業科研院所牽頭,加大對生態農業種植養殖實用技術的攻關,為社會化小農提供一批可得性強、可操性好、經濟與生態效益兼顧的技術方案。針對處于城鎮邊緣以及城中村的社會化小農而言,生態農業種植養殖技術的供給更要關注瞬息萬變的農產品市場和潛在的農產品需求信號,發揮農業區位優勢,有效利用城鎮化、信息化、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互動帶來的發展機遇,可以為社會化小農提供層次分明、品種多樣的農業種養殖技術,以及農產品物流技術、農產品儲藏技術、農產品加工技術等實用性技術;針對處于較為偏遠于城鎮的社會化小農而言,更應立足當地農田生態環境實際,發揮生態農業規模生產之優勢,準確定位其生態農業社會分工,合理布局生態農業產業,為社會化小農提供戰略性強、易學好用的生態農業發展技術,如生態旅游業相關技術、生態農業種養殖技術,著重幫助其打造特色品牌,延伸生態農業產業價值鏈。
農田生態系統保護革新。當前,我國生態農業執行的農田生態系統保護措施主要有:基本農田保護制度、退耕還林制度、保護性耕作技術體系、水土保護技術、沙漠化土地綜合治理制度、土壤污染修復制度等,基本覆蓋了農業生態環境保護范疇,但是各個制度之間的耦合性和執行力較差,難以發揮制度支撐生態農業發展的導向與保障作用。革新農田生態系統保護制度體系,就是要在農田生態保護的基礎上,加大農田的利用規劃,借助生態農業科技放大農田生態環境正外部效應,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其中最為關鍵是聯接社會化小農農業能手與農業科技人員,引導社會化小農優化農業種養結構,合理布局農產品生產規模。
(二)進一步挖掘制度“改革紅利”
進一步挖掘制度“改革紅利”是深化農村社會體制改革的內在必然要求,也是扎實推進生態農業發展、改善社會化小農生產生活環境的重要手段。要針對社會化小農的特點,從農業生產過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農產品銷售等環節進行制度創新。
農業生產過程制度創新包括產前、產中和產后三個環節。就產前而言,建立生態農業發展常態化普及宣傳制度,強化社會化小農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提升其走生態農業發展道路的自信心與自覺性。需要指出的是,建立生態農業資金扶持與獎勵制度也是產前制度安排的重要內容,各地農業主管部門以及政府相關部門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設立此制度。就產中而言,建立農業高級技師、農業實用人才與農技人才等生態農業專家指導幫扶制度,讓社會化小農從“干中學”中提升農業生產實用技能,實時解決社會化小農生態農業的技術難題,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就產后而言,建立農產品市場分析與預測制度,為社會化小農總結與交流生態農業經驗提供終端平臺,并為生產規劃提供必要依據,同時建立農田種養殖新技術發布制度,供社會化小農制定新一輪生產規劃參考。
完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制度。良好的農業生態環境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具有污染性的農業生態環境則具有顯著的負外部性,二者都將引起農業生產帕累托效率發生偏離。農業生態環境補償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消除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之間的差異,實現帕累托最優。堅持公平與可持續原則,以“誰受益、誰補償、社會收益政府補償”為基準[17],盡快建立一套相對完善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法律法規體系,對社會化小農、農業生態環境保護者以及其他主體實施資金、實物、技術、政策性以及項目補償,有效保證生物的多樣性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對于那些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肆意破壞農業生態環境、無視農業生產公德的社會化小農,應制定相應的懲罰措施,作為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典型,形成相互監督、控制的生態農業文化氛圍。
建立農產品質量認證制度和價格調控制度,有利于調動社會化小農推進生態農業積極性。農產品安全與多樣性業已成為人們對生態農業發展提出的基本要求,也為社會化小農農業收入的實現提供了契機。農產品銷售是社會化小農農業收入的重要的通道。建立靈活多樣的農產品質量認證制度,不僅有助于社會化小農提升農產品銷售績效,也是契合社會化小農農產品銷售特點的內在要求。針對社會化小農對手交易、批量銷售與攤位銷售并存的局面,可以嘗試建立與“綠色食品”、“低碳食品”、“無公害食品”認證制度相協調的屬地農產品質量認證制度,也即根據社會化小農屬地設立一種地方性、范圍性的農產品質量內部監督與認證制度,這對于社會化小農農產品品牌的構建亦有顯著的促進意義。在農產品價格調控制度方面,以保證地區生物多樣性、打造屬地農產品品牌以及尊重社會化小農勞動價值為原則,對農產品市場實施差別化的價格規制制度,以此帶動社會化小農自覺發展生態農業。
此外,還亟需探索一套由政府支持、社會化小農自組織發起的生態農業服務體系。社會化小農特別是具備相當規模的農業能手,如果缺少或者不依賴自組織的生態農業服務體系的支撐,僅靠政府輸血式的扶持,既會扭曲生態農業基本經營制度,抑制社會化小農創新創業積極性,社會化小農生態農業經營也很難得到可持續的發展。
(三)加快改造社會化小農
社會化小農作為發展生態農業的主體,其人力資本水平決定了生態農業發展的成敗。建國以來,我國農民憑借節約和勤勞的工作創造了農業生產奇跡,但是僅憑這一點不足以克服農業的落后性,也難以實現生態農業的快速發展。為了生產豐富的、高品質的農產品,必須采用激勵的方法加快社會化小農改造進程,使得這種改造成為社會化小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的途徑。根據楊曉鋒提出的人力資本結構三維分析框架[18],結合我國新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要求與生態農業發展的基本理念,社會化小農改造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在體力資本提升方面,以體魄健康為主要改造目標。首先,由村委會發起,社會化小農先進典型引領,以樹立良好的生活飲食習慣為主要目標,以茶話會、歌舞會、綜藝節目、生活廣播等為主要形式,推行健康新生活運動,為社會化小農提供可得性強、可信度高的喜聞樂見的養生“長壽秘方”。其次,完善縣—鄉鎮—村三級醫療服務體系,建立惠及面更廣、更深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障體系,同時加強家庭常見疾病防治知識的普及,切實做到體檢防病、及時治病、高效醫病,對那些困難社會化小農給予更強的物質資助和人文關懷。最后,以社會化小農生產安全與防護為前提,建立科學的生態農業作業行為示范體系,對一些體力耗損大的農業工作,應建議由機械或精壯男性完成;對一些高危農業作業,應征詢專業農技人員、農業能手的意見,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對一些反生活作息規律的農業工作,應采取交替輪換的方式,并給予及時修復方案。凡此種種,均可形成必要的行為規范。
在智能資本提升方面,以增強專門技能與綜合知識為主要改造目標。首先,建立生態農業種植養殖技能咨詢與培訓中心,不定期組織和動員社會化小農了解、學習和掌握一批生態農業專門技能和專業知識,并由中心提供專門的幫扶服務,強化對相關技能與知識的理解與運用。其次,定期發布生態農業創新創業項目,通過政府、企業與科研院所等政策、資金、科技等要素的引入,鼓勵社會化小農投身于創新創業大潮中,促進社會化小農從農業多面手向創新創業能手轉變,更好地踐行生態農業觀。再者,建立以農村留守精英為主體的“師徒化”人力資本培養模式,保證各類“絕活”、“絕學 ”永續傳承[19],也可降低社會化小農人力資本的開發成本。最后,借高等教育改革契機,針對社會化小農人力資本分布特點,積極探索高等職業技術學院、社會化小農與生態農業協調發展的辦學路子,放開一批具有農業特色、人文色彩濃郁的高等職業院校,為社會化小農提供上大學接觸了解知識、終身學習的機會和平臺。
在道德資本提升方面,以培育文化涵養高、品性信譽好、價值取向端正的新型居民為主要改造目標。超越國家法律的天然的道德準則體系與公共價值機制的存在是法治國家得以順利運轉的前提與關鍵,道德市場良性運轉離不開社會主體的道德資本投資。社會化小農脫胎于傳統小農,烙有傳統小農文化背景下的道德準則,如各掃門前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偽道德。因此,用崇高的經濟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作為改造社會化小農道德的載體,以正規教育與社會教化提升社會化小農的思想道德與科學文化素養,并且,建立不唯經濟效率上、不唯道德上,以個人、家庭、企業和其他組織為主體的層級道德考評體系與道德懲戒制度[20],促進社會化小農道德資本投資機制的良性運作。
四、結束語
生態農業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有效回應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需要。生態農業是最可能盈利的新興產業[21],也是傳統農業改造的根本出路。作為一個脫胎于傳統農業、處于快速發展中的大國,我國農業發展的物質基礎還很薄弱,農民的人力資本水平還較低,生態農業還未進入實質性發展階段,但在生態農業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重要基礎性地位日益凸顯。也正是因為我國仍然是一個處在發展中大國,我們不應該也不能將生態農業發展的出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且不說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等亟需政府全方位的支持,單就科教事業投資嚴重不足而言,當前政府在處理各事業發展的優先序上亦不可能顧及生態農業發展的方方面面。社會化小農作為一種常態化普遍存在于我國的家庭經營形式,對生態農業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個受傳統農業束縛的人,無論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產出許多食物[18]。顯然,寄希望于社會化小農自身發展,對推進生態農業發展而言將會是一種事半功倍的選擇。利用社會化小農演進規律,加快社會化小農改造進程,借助現代科技進步成果,做實、做活強農惠農政策,通過社會化小農理性投資、優化生產結構、穩步提升農業生產率來確保農產品生產與安全、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為農民增收、農業可持續、農村全面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參考文獻]
[1]韓俊,葉興慶.以改革創新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N].人民日報,2014-03-22(6).
[2]程序.中國農業與可持續發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38.
[3][日]暉峻眾三.日本農業150年[M].胡浩等譯.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11.1-2.
[4]徐勇,鄧大才.社會化小農:解釋當今農戶的一種視角[J].學術月刊,2006,38(7):5-13.
[5]鄧大才.社會化小農:一個嘗試的分析框架[J].社會科學研究,2012,(4):89-96.
[6]劉金海.“社會化小農”:含義、特征及發展趨勢[J].學術月刊,2013,45(8):12-19.
[7]黃祖輝.必須堅持農業家庭經營[J].中國合作經濟,2014,(4):4.
[8][法]H.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5.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5.
[10]林亦平,滕秀梅.關于中國傳統農業、農民、農村三個論斷的辨析[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78-82.
[11]張曉山.深化改革方能激發發展活力 中國農業和農村長久可持續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消除制約農業農村發展的體制障礙[J].中國合作經濟,2014,(1):1.
[12]胡艷麗.農戶經濟行為調控與貧困地區生態農業發展研究[J].生態經濟,2014,30(5):138-140.
[13]Infante Amate,Juan.“Sustainable de-growth” in agriculture and food: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pain’s agri-food system (year 2000)[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3,38(1):27-35.
[14]Brecking,Broder;Reuter,Hauke.Up-scaling ecological effec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in agriculture[J].Ecological Indicators,2011,11(4):935.
[15]Roger-Estade,Jean;Anger,Christel;Bertrand,Michel;Richard,Guy.Tillage and soil ecology:Partner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J].Soil and Tillage Research,2010,111(1):33-40.
[16]徐勇,林冠.論農業生產能力與農戶生產能力提高的非均衡性——以社會化小農為分析視角[J].江漢論壇,2011,(8):5-8.
[17]高尚賓等.農業可持續發展與生態補償[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1.1-2.
[18]楊曉鋒,趙宏中.人力資本分布結構、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后勁[J].軟科學,2013,(12):80-84.
[19]楊曉鋒,趙宏中.湖北省新生代農民本土就業影響因素研究[J].湖北農業科學,2012,52(13):3206-3209.
[20]楊曉鋒.論道德資本投資[J].學術論壇,2013,(2):10-13.
[21]溫鐵軍.生態安全是現階段“三農”的重要問題[J].農村工作通訊,2014,(2):45.
[22][美]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梁小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75.
[責任編輯:張曉娟]
The Plight and Way of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ocialized Famers
YANG Xiao-feng
(School of Accounting,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200,China)
Abstract:As a new form of the evolution of small-scale farmers in modern social, socialized famers is the bridge connec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a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ized famers are clarified by 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ized famer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approach of socialized famers, the paper finds out the main dilemma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itially establishes integration thought of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nnovation and change of socialized famer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Key words:ecological agriculture; socialized fame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