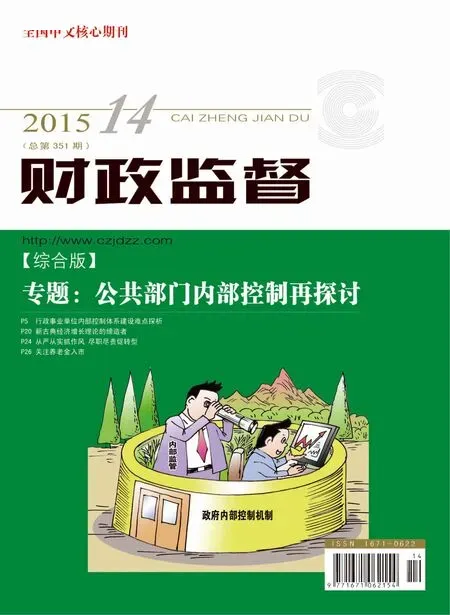以公共利益的真實(shí)化為政府治理的中間目標(biāo)
●本刊評(píng)論員
以公共利益的真實(shí)化為政府治理的中間目標(biāo)
●本刊評(píng)論員
本期發(fā)表的一組關(guān)于政府治理的論文使筆者想起馬克思曾對(duì)他置身的社會(huì)所持的一個(gè)觀點(diǎn):資本主義國(guó)家作為階級(jí)統(tǒng)治機(jī)器背景下,“公共利益才以國(guó)家的姿態(tài)而采取一種和實(shí)際利益(不論是單個(gè)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dú)立形式”。中國(guó)已經(jīng)進(jìn)入新的發(fā)展階段。目前,按最大公約數(shù)原則和擇優(yōu)排序原則,什么樣的政府治理目標(biāo)能到確認(rèn)?毫無(wú)疑問(wèn),發(fā)展好、維護(hù)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的最終目標(biāo),問(wèn)題在于選擇什么樣的中間目標(biāo)。馬克思的這一觀點(diǎn)對(duì)筆者深有啟示:作為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與資本主義本質(zhì)區(qū)別之一,應(yīng)該是兌現(xiàn)、落實(shí)公共利益,使其不再虛化。
對(duì)政府治理目標(biāo)的訴求,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在以下幾組矛盾中:一是經(jīng)濟(jì)體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快速增長(zhǎng)、龐大的國(guó)有資產(chǎn)與國(guó)民利益非均衡的矛盾;二是過(guò)高的行政成本、制度運(yùn)行成本乃至整個(gè)社會(huì)交易成本與人民實(shí)際福利增長(zhǎng)的矛盾;三是牢固的既得利益藩籬與改革需求、制度創(chuàng)新的矛盾;四是權(quán)力運(yùn)行不規(guī)范、不透明、權(quán)力濫用、尋租腐敗嚴(yán)重與政治發(fā)展潮流的矛盾。這些矛盾集中指向社會(huì)公正缺失。這一背景下,應(yīng)圍繞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公正這條主線,將公共利益的真實(shí)化、公共制度的公正化作為目前時(shí)勢(shì)下國(guó)家治理優(yōu)先排序的中間目標(biāo)。
確認(rèn)這樣的中間目標(biāo),還有出于政府治理面臨的約束條件的考量,這除了國(guó)家治理能力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的約束之外,還有基本政治框架的約束。國(guó)家治理目標(biāo)要與黨的全面領(lǐng)導(dǎo)、基本政治經(jīng)濟(jì)制度和核心價(jià)值觀、社會(huì)穩(wěn)定等相容。
我們要正視目前中國(guó)公共利益虛化傾向的存在。財(cái)政分享不公,厚體制薄社會(huì),厚官薄民,厚城輕鄉(xiāng),社會(huì)保障制度的多軌制是表現(xiàn)之一;行政成本過(guò)高、公共采購(gòu)和公共工程的浪費(fèi)嚴(yán)重,是表現(xiàn)之二;以公共利益的名義侵犯群眾利益是表現(xiàn)之三;公共利益部門(mén)化、私有化是表現(xiàn)之四;設(shè)租、尋租,利用制度漏洞、自由裁量權(quán)、不合理的審批權(quán)等形成的“合法傷害權(quán)”對(duì)公民和市場(chǎng)主體進(jìn)行抽租是表現(xiàn)之五。這些公共利益虛化的現(xiàn)象與一些帶有特惠性、歧視性色彩的制度有關(guān),也與制度越位、缺位和扭曲,制度的軟約束和自由裁量有關(guān)。
我們還應(yīng)看到生產(chǎn)和兌現(xiàn)公共利益在經(jīng)濟(jì)資源、政策資源上的特殊優(yōu)勢(shì)。中國(guó)經(jīng)歷了較長(zhǎng)時(shí)間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財(cái)政規(guī)模十分可觀,算得上很多發(fā)達(dá)國(guó)家都難以匹敵的“富政府”(從廣義政府收入占國(guó)民收入比重很高、政府大手筆投資、巨大的樓堂管所建設(shè)投入規(guī)模等可見(jiàn)端倪),加之擁有其它國(guó)家所沒(méi)有的巨額國(guó)有經(jīng)營(yíng)性收入、國(guó)有土地出讓收入,生產(chǎn)和提供公民可體驗(yàn)的、真實(shí)的公共利益的資源相對(duì)充分。通過(guò)財(cái)稅體制改革降低宏觀稅負(fù),減少財(cái)政舞弊和浪費(fèi);通過(guò)社保制度改革實(shí)現(xiàn)社保待遇并軌;通過(guò)國(guó)有資產(chǎn)收入的注入降低社保費(fèi)率;通過(guò)政府自身改革,建設(shè)儉樸政府,置換出更多財(cái)政資源用于的民生投入;通過(guò)簡(jiǎn)政放權(quán),治理腐敗,減少設(shè)租尋租空間,降低“腐敗收入黑數(shù)”和社會(huì)交易成本。這些都是當(dāng)前的可行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