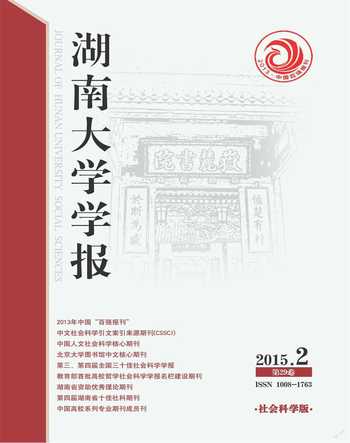南宋書院的學祠與學統
中國書院研究專輯
主持人語:
在中華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復興書院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事業的組成部分。2014年岳麓書院牽頭成立中國書院學會,其目的也是推動中國書院文化的發展。本輯的書院研究論文,涉及書院的起源、書院祭祀、書院與科舉等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是老問題,但這些文章提出了新的觀點,能夠深化對書院的認識與研究。
(朱漢民教授)
[摘 要] 宋代書院與理學的發展密切相關。理學家形成的學統及道統觀念,對書院祭祀制度的完備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南宋時期的理學家有一種強烈的建構書院學統,以確立書院在儒家道統史上的意義、地位的精神追求,他們通過創建書院學祠,開展書院祭祀活動,以完成這一文化使命與道義責任。
[關鍵詞] 書院祭祀;學祠;學統;道統;理學
[中圖分類號] K2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5)02—0005—08
Abstract:Academies of Song Dynast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The learning and Confucian orthodoxy of NeoConfucianism exerte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completion of sacrifice system of the academy. Most scholars who promoted NeoConfucianism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a strong spirit pursuit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es to establish the status of academies in Confucian orthodoxy histor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ultural mission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y created academy temple and implemented sacrifice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orthodoxy.
Key words:sacrifice of academy;temple;learning orthodoxy;Confucian orthodoxy;NeoConfucianism
中國古代書院的基本規制是由三個方面構成的,即講學、藏書、祭祀。在中國書院制度成型的北宋初年,那些著名的書院如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即具備完整的講學、藏書、祭祀的基本規制。但是,書院的規制有一個發展與成熟的歷史過程。北宋初期書院的規制基本上還只是對官學制度的模仿,以后才逐漸發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
書院祭祀制度也是如此。雖然北宋時期書院就有了專門的祭祀空間,但是書院祭祀能夠真正具有自己的特色,則是與南宋書院的學術思想、教育理念的發展密切相關,尤其南宋理學的學統觀念,對書院祭祀制度的特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 北宋書院的祭祀制度
以“書院”命名的藏書、讀書乃至教書的機構,萌芽于唐代,但是,作為真正的文化教育組織的書院成型,則是到了北宋。唐、五代時期,書院是一種偶然的、零星的、不確定的藏書、讀書或教書之所;而到了北宋初期,書院已成為一種穩定的、普遍的、制度化的文化教育機構。由于統計的文獻依據不同,學者們對北宋書院的建置數量不太一致,但是總體而言,北宋時期建置的書院具有數量多、分布廣、規模大等特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書院的講學、藏書、祭祀的規制完整。
首先,北宋書院的講學功能完備,擁有講堂、齋舍的專門設施。書院具有多種功能,而作為教育組織而言,講學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唐、五代時期民間出現那些以“書院”命名的機構,大多只是一些個人的藏書、讀書之處,而并不是一種制度化的教育機構。但是,北宋時期所創建的書院不太一樣,這些書院普遍是以教書育人為主要職能和任務。如岳麓書院初創時有講堂五間、齋舍五十二間, “有書生六十余人聽誦”[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63,《文津閣四庫全書》第0611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1頁。;應天府書院則是有戚同文者,“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63,《文津閣四庫全書》第0611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1頁。。宋初產生的著名書院,還包括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等等,均有固定的生員名額、著名的山長主持教學,在人材培養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成就。
其次,北宋時期創辦的書院,均有一定規模的藏書,有專門供藏書用的書樓,這些藏書主要是為培養人才所用。唐、五代以“書院”命名的民間書舍,主要是民間個人的藏書、讀書之所,宋初時期的書院,在藏書方面承襲前朝書院,但是其藏書的來源、規模、用途等方面,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藏書的來源不一樣,宋初書院的藏書來源大不一樣,除了保留民間個人的藏書外,尤增加了官府、朝廷所頒典籍。宋初幾所著名的書院如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均曾經授受過國子監甚至皇帝的賜書。其次,藏書的規模大大擴展,唐、五代的書院主要是供個人讀書的藏書處,而宋初書院的藏書則是為廣大生員、教職人員所需,故而藏書的規模擴大,如應天府書院“聚書千五百余卷”,而唐、五代的書院很少談到藏書規模,少談的原因應是規模太小不值得談。
其三,北宋書院基本上具備了祭祀的功能。唐、五代時期民間書院起源于讀書人個人藏書、讀書的功能需要,即使個別書院已經具有教學功能,但并不具有祭祀功能。北宋初期創建的書院已經成為功能完備的、制度化程度高的學校,故而也模仿官學的“廟學”制度,產生了祭祀的功能,并有了專門供祭祀孔子的獨立空間和設施。中國古代學校,經歷了一個由“學”到“廟學”的發展過程。從西周到兩漢,均執行“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圣、先師”的規定。東晉時期,正式在國子學西邊建立孔子廟,形成了最早的“廟學”制度。此后自唐太宗至清朝末年,“廟學”制度推廣到地方的州學、縣學,一直延續。唐代形成的地方官學的“廟學”制度,影響了北宋初期的書院制度。
唐、五代時期的書院,尚未見祭祀功能的記載。但是,宋初創建的書院,關于祭祀的設施已經十分完備,與官學的“廟學”制已無區別。如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王禹偁撰寫的《譚州岳麓山書院記》中,就有明確記載:
初,開寶中,尚書郎朱洞典長沙。左拾遺孫逢吉通理郡事。于岳麓山枹黃洞下肇啟書院,廣延學徒。二公罷歸,累政不嗣,諸生逃解,六籍散亡,弦歌絕音,俎豆無睹。公詢問黃發,盡獲故書,誘導青衿,肯構舊址。外敞門屋,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序以客次。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華兗珠旒,縫掖章甫,畢按舊制,儼然如生。[宋]王禹偁:《譚州岳麓山書院記》,《小畜集》卷17,《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090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8頁。
這次記文,記載北宋初年兩次修建岳麓書院的過程,其中均講到其完備的祭祀制度、設施,這種“供春秋之釋典”的制度與官學的“廟學”制度已無區別。除岳麓書院外,其他如白鹿洞書院,也于咸平五年重修時,“塑宣圣十哲之象”[宋]王應麟:《白鹿洞書院》,《玉海》卷167,《文津閣四庫全書》第0950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90頁。,即也是有專供祭孔用的廟學體制。
北宋書院為什么要仿廟學制,設置專供祭祀先圣先師的殿宇?其文化功能是什么呢?兩漢以后,儒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從而確立了“儒教”在國家意識形態、文化教育體制中的地位。“儒教”之“教”顯然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特點,而特別體現出對“教育”、“教化”的重視。而各級學校之所以要“釋典于先圣先師”,正體現出“崇儒重教”的文化特點。而北宋形成的書院,正是儒家士大夫所體現出的“崇儒重教”的文化追求。書院創辦者在書院內部設置專門的祭祀空間,舉行專門祭祀先圣先師的釋奠儀,正是為了彰顯書院的儒教文化特質與崇儒重教精神。二 南宋前期學祠的發展
如果說北宋書院主要是仿官學的廟學制度,而設立祭祀“先圣先師”的祭孔廟堂的話;那么南宋書院則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祠堂祭祀,以表達宋儒才獨有的學統觀念與道統意識。通過這種祠堂祭祀活動,書院開始建立起自己獨有的學術與教育理念,書院主持人希望將書院祭祀納入到書院學統與道統的建設目標與建構過程中。可見,同是書院祭祀,但學廟祭祀與學祠祭祀卻有十分明顯的區別。書院的主持者建孔廟祭祀“先圣先師”,還只是一種延續、仿效官學的廟學制行為,體現不出書院主持者獨特的文化創新與教育追求。但是,南宋書院主持者開始建造祭祀本學統人物的祠堂,以表達他們新的學術理念與精神追求,不僅體現了這一時期宋儒那種學術創新的獨立精神,而且也反映出他們制度創新的不凡氣象。
南宋書院設學祠祭祀,有一個初步創始,逐漸推廣到制度成型的歷史過程。這里重點討論南宋前期,即從宋高宗建炎、紹興年開始,到宋光宗紹熙年間為止。
南宋初年,最早由理學家創辦、主持書院講學者,應為“開湖湘學統”的胡宏。南宋紹興年間(1127-1130年),著名理學家胡安國率其子胡宏等家人隱居湖南湘潭碧泉,在此著書講學,完成了經學名著《春秋傳》。胡安國在世時的講學處并沒有稱之以“書院”,后來史著如《宋元學案·武夷學案》也僅稱其為“精舍”、“講舍”。胡安國逝世后,胡宏才在此地正式修建了“碧泉書院”,并作《碧泉書院上梁文》。于此同時他還修建了“文定書堂”,因胡安國逝世后謚“文定”,這處建筑就是碧泉書院師生為祭祀胡安國而建,胡宏在《文定書堂上梁文》中寫道:“伏愿上梁以后,庭幃樂豫,壽考康寧;中外雍和,子孫蕃衍;流光后世,受福無疆。”[宋]胡宏:《胡宏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201頁。這顯然是一個學祠兼家祠性質的祠堂,和《碧泉書院上梁文》中“襲稷下以紛芳,繼杏壇而蹌濟”的教育功能有差別。其實,南宋時期以“書堂”為學祠的例子并不少,如淳熙四年(1177年)江州太守潘慈明重建廬山的“濂溪書堂”,就是一處學祠性質的書堂,朱熹在《記》中說太守“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宋]朱熹:《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朱子全書》第2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41頁。。文定書堂其實就是一所與濂溪書堂性質一樣的奉祀之所,只是文定書堂附屬于碧泉書院而已。
在南宋初的高宗、孝宗時代,長江以南地區的學術文化一度得到發展。理學家群體逐漸形成一股較強的社會文化勢力,他們推動著理學思潮與書院教育的結合。于此同時,他們特別重視創建北宋理學家的祠堂以供祭祀,尤其是那些在江南地區出生、講學的理學家,其出生地、宦游地、講學地更是成了創建專門理學家祠堂的重要場所。至于書院與學祠的普遍性結合,就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從南宋高宗時期開始,江南地區逐漸修建了許多專門祭祀理學家的祠堂。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湖湘學派的理學家向子忞在周敦頤的老家道州,首次創建道州濂溪祠,胡銓作《道州濂溪祠記》。這所最早的濂溪祠在后來得以不斷修建,另永州州學亦建濂溪祠。除了道州與永州之外,崇敬理學的儒家士大夫紛紛于周敦頤宦游、講學之地創建祠堂專門祭祀周敦頤。如周敦頤曾在韶州做官,淳熙二年(1175年)在韶州建濂溪祠,張栻作《濂溪先生祠堂記》。他們在創建濂溪祠的同時,也修建祭祀其他理學大師的祠堂。如淳熙五年(1177年)張栻在知靜江府時,在府學明倫堂旁建“三先生祠”,祭祀周敦頤、程顥、程頤三位理學宗師。次年,張栻知袁州,又建三先生祠,請朱熹作《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守南康時創建濂溪祠,張栻作《南康軍新建濂溪祠記》。當時的道學家們,經常在地方的州學、府學、縣學及紀念地創建祭祀北宋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的祠堂。在張栻、朱熹的文集中,均留下一些祠記。如《南軒先生文集》中,另外有《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衡州石鼓山諸葛忠武侯祠記》、靜江府學的《三先生祠記》等等。而在《朱文公文集》中,亦有大量這類祠記,如《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德安府應城縣上察謝先生祠記》等等。可見,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間理學大盛時,宦游、講學各地的理學家們積極推動地方創建專門祭祀北宋理學奠基者周、程諸人的祠堂。
在這種背景下,理學家們亦進一步將這種專門祭祀先師先賢、表達學統傳承的祠祭引入到書院,前面已經講到,早在南宋紹興年間,胡五峰就在湖南碧泉書院建了祭祀胡安國的“文定書堂”。到了乾淳理學型書院興起時,理學家開始在他們創建的書院中,設置專門祭祀道學先師的祭祀儀式。這一點,在朱熹那里表現得特別突出。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軍,上任后即開始修復白鹿洞書院,次年修成后,他率生徒于書院行祭祀先圣先師的釋菜禮。可見,這時朱熹還主要是以地方官員身份,在白鹿洞書院舉行與廟學制相關的祭孔活動。但是,當朱熹的道統觀念逐漸建立起來后,他開始將這種新的道統觀念與書院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創建了滄州精舍,他同樣率生徒于書院舉行祭祀先圣先師的釋菜禮。但是,這次他有意識地將祭祀對象由孔子、顏回、孟子,進一步拓展到宋代的儒學大家周敦頤、二程等人,從而將道統理念制度化為書院的釋奠活動。據朱子門人葉賀孫記載: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師。……雞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備,就講堂行禮。宣圣像居中,兗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并紙牌子)。濂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橫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先生為獻官,命賀孫為贊,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贊,敬之掌儀。[宋]朱熹:《朱子語類》卷90,《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28頁。
應該說,朱熹早在乾道、淳熙年間,就已經形成了周敦頤、二程等北宋諸儒的道統思想,只是這種思想還沒有落實到書院制度層面。而到了紹熙年間創辦滄州精舍時,朱熹已經非常自覺地將他建構起來的道統觀念,即以北宋以來的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司馬光、張載、李桐等七子接續孔孟道統思想納入到書院祭祀活動與制度之中。特別是他將自己的老師李桐列入北宋七子之中,一方面是表明朱熹本人的學統與道統的一致性,表達他在道統脈絡中對文化使命的自覺承擔,另一方面也是將滄州精舍的學統與儒家道統承傳更緊密地結合起來。所以,朱熹在祝文中表達了他的道統理念。顯然,朱熹已經將他在《中庸章句序》等著作中不斷闡述的道統觀念,最終納入到滄州書院的釋奠儀的制度之中。
從南宋初的紹興年開始,到南宋紹熙年的一段時間,正是理學家群體逐漸興起、理學學術創造力大盛的歷史時期,也是理學家們積極創建、恢復書院非常活躍的歷史時期。他們在強烈的學統觀念與道統意識引導下,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紀念地、地方學府中大量創建祭祀周敦頤、二程等北宋理學奠基人的祠堂,通過學祠以弘揚道學、傳承學統;另一方面他們亦開始在書院、精舍開展對道學人物的祭祀活動,并開始了將道統觀念的思想建設與書院祭祀的制度建設結合起來。他們的這一制度創新的做法,到理學地位發生重大變化的“嘉定更化”以后,才得到了完全鞏固與全面推廣。三 南宋后期書院學祠的成型
“慶元黨禁”時期,南宋理學與書院均受到禁抑,理學家很難推廣這種以標榜道統為旨趣的書院祭祀制度。所以,朱熹通過滄州精舍而祭祀北宋道學家、將道統理念落實于書院制度的創舉在當時并沒有得到推廣。
直到南宋嘉定(1208-1224年)以后,特別是宋理宗(1224-1264年)當朝以后,乾淳之盛時的理學家們紛紛平反,并得到朝廷的表彰。這段時期也是書院發展的重要時期,不僅是書院建置的數量大大增加,書院制度的建設也更加完備,與道統理念相關的書院祭祀制度,到此時才完全成型。此正如袁甫的《重修白鹿書院記》所說:“伊洛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中興。南軒、晦庵、象山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更化。”[宋]袁甫:《蒙齋集》卷13,《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79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75-476頁。 北宋周濂溪、二程等人的講道,至南宋乾、淳理學中興而更顯,有關對周程等北宋諸子的學祠祭祀已經在乾、淳時形成;而南宋乾、淳理學諸君子如朱、張、陸、呂等,到“嘉定更化”以后,則與北宋諸子一道被普遍地列入到書院祭祀對象,使書院祭祀與道統理念結合起來。
南宋理宗以后的書院,比較普遍地建有專門祭祀理學人物的祠堂,從而形成了南宋書院祭祀制度的顯著特色。如果我們進一步深究即可發現,這個時期書院普遍建立供祀理學家的制度,是通過三種途徑來完成的。
第一,將南宋前期專門供祀理學家的祠堂,進一步拓展為包括祭祀、講學等多種功能的書院。
從南宋初年開始,一些崇奉、繼承理學學術的士大夫即開始在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的故居、講學地、宦游地創建專門的祠堂,以表達對理學的尊崇。到了南宋嘉定以后,這些理學家的專祠,往往拓展為書院。這些書院,一方面保持其原有的供祀理學家的祭祀功能,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培養人材的教育功能,從而形成了一種合祭祀與教學為一體的理學型書院。最著名的是湖南道州的濂溪祠、江西廬山的濂溪書堂等。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湖湘學者為推崇濂溪之學,首次在道州創濂溪祠。到了宋理宗時期,濂溪祠拓展為濂溪書院,景定三年(1262年)還獲得理宗賜額“道州濂溪書院”。道州濂溪書院開始招收士子就讀,并且確立了“蓋欲成就人才,將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楊允恭:《濂溪書院御書閣記》,《湖南通志》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81頁。的教育宗旨,濂溪書院同時保留濂溪祠,專祀周敦頤。又如江西廬山的濂溪書堂創建于淳熙四年(1177年),為奉祀周敦頤的專祠,但是到了理宗時代也發展成含講學與祭祀為一體的書院,宋理宗端平年間州守趙善璙“更治其書堂,繕修其祠墓,肄習有廬,祭薦有田”趙善璙:《濂溪書堂謚告石文》,《濂溪志八種匯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21頁。,成為一所講習理學、祭祀濂溪的書院。
于此同時,其他供祀理學家的祠堂也紛紛發展為書院。南宋淳熙初,大學士劉珙曾創建明道先生祠于建康府學官內,還請朱熹為之作記。到了南宋理宗淳祐年間,明道祠在得到不斷修復的同時,被拓展為明道書院,開始“聘名儒以為長,招志士以共學,廣齋序,增廩稍,仿白鹿洞規,以程講課,士趨者眾。”[宋]周應合:建明道書院》,《景定建康志》卷29,《文津閣四庫全書》第0488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535頁。明道書院成為一所講習理學、供祀程顥的著名書院,宋理宗還為之賜額。又如,呂祖謙曾于乾道、淳煕之時在故鄉婺州講學,“嘉定更化”時其弟子在他講學會友故地竹軒建祭祀呂祖謙的專門祠堂,到了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也拓展為東萊書院,也成為一所合講習理學、祭祀呂祖謙為一體的書院,袁甫作《東萊書院竹軒記》[宋]袁甫:《蒙齋集》卷14,《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79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848頁。,記載了呂祖謙講學于此、創建東萊祠、改建東萊書院的過程。總之,這一類祭祀理學家的專門祠堂大多創建于南宋前朝的紹興、乾道、淳熙時期,而到了南宋理宗時期后,紛紛改建、拓展為書院,具有了祭祀、教學的雙重功能。由于這些書院大多與著名理學家周敦頤、二程、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有關,故而相關的書院還得到朝廷的賜額。
第二,將以前以講學為主要功能的書院,增設與該書院學統相關人物的學祠。
北宋、南宋前期建置以講學為主的書院,雖然大多也建有專供祭祀孔子的空間如禮殿、孔子堂等,但很少有祭祀本朝學者的專門祠堂。朱熹在滄州精舍開展了祭祀本朝道學家的祭祀活動,但無資料證明朱熹創建了專門的祠堂。而到了南宋嘉定年以后,情況很快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許多辦學影響很大的書院,紛紛創設了祭祀本朝、本院學者的學祠。如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創建于北宋,比較早就建有祭祀孔子的廟堂。高明士:《書院祭祀空間的教育作用》,《中國書院》第一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3頁。到了南宋淳熙時,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并恢復祭祀孔子,但無專門祭祀本朝學人的祠堂。直到嘉定十年(1217年)書院再度重修時,才增設前賢祠,專門祭祀周程朱等前賢,朱熹弟子黃翰作《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至宋紹定年間(1228-1233年)白鹿書院又新建君子堂,祭祀宋儒周敦頤,據袁甫《白鹿書院君子堂記》,“而此堂則新創……堂瞰荷池,取濂溪愛蓮語扁以是名。”[宋]袁甫:《蒙齋集》卷13,《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79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77頁。又如岳麓書院創建于北宋初,剛建時即辟有專祀孔子的禮殿,這一格局一直延續,南宋初張栻主教時仍然如此。但是到了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知潭州,于岳麓書院創供祀推動書院建設的本朝先賢朱洞、周式、劉珙的諸賢祠堂。到了元朝,又將朱熹、張栻與上述三人合祀,稱諸賢祠。
南宋乾道、淳熙年間理學大盛,當時的理學家創辦了一些新的專門講學的書院或精舍,到了南宋理宗時代,也紛紛增設與創辦人相關的祠堂。如南宋初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建竹林精舍,后又改名滄州精舍或滄州書院。到了南宋理宗寶慶年間正式創建朱子祠,以蔡元定、黃翰、劉爚、真德秀四高第配享。至淳祐四年(1245年)獲得理宗“考亭書院”賜額。可見,朱子祠是滄州書院(考亭書院)的增設部分,這一格局一直延續到元、明、清。又如陸九淵于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在江西貴溪老家創象山精舍講學,門徒甚眾,成為“南宋四大書院”之一。南宋理宗紹定四年(1231年),象山門人袁甫請于朝而改建,新建后請理宗賜額“象山書院”,除新修講堂、齋舍、圣殿外,尤創設了祭祀陸九韶、陸九齡、陸九淵的“三先生祠”。袁甫于紹定六年(1233年)作的《象山書院記》中,記載他們“始至舍奠先圣,退謁三先生祠,竦然若親見象山先生燕坐,而與二先生相周旋也。”[宋]袁甫:《蒙齋集》卷13,《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79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71頁。應該說,宋理宗后,由于理學家受到普遍尊崇,以講理學為宗旨的書院紛紛創建增設祭祀理學家的專門學祠。
第三,創建許多將講學、祭祀功能合為一體的書院。
南宋理宗時期,理學的地位獲得大大提升,同時也出現了一個創辦新書院的熱潮。在這些新辦的書院群中,許多就是在那些著名理學家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謝良佐、楊時、李桐、朱熹、張南軒、陸九淵等人的家鄉、故居、講學地、宦游地。“嘉定更化”以來,儒家士大夫紛紛在這些地方創建書院,一方面通過書院講學,傳播理學思想,另一方面通過祠堂祭祀,表達對這些理學家的尊崇。如理宗時期新創辦了許多濂溪書院,這些都是將祭祀濂溪、講習理學合為一體的書院。如湖南地區在南宋嘉定以后先后在道州、邵州、桂陽、郴州、永興、寧遠等地建了6所濂溪書院,除了道州、邵州的濂溪書院系由原來的濂溪祠發展而來,其余幾所書院均是新建的。這些新建的濂溪書院均是將講習理學、祭祀濂溪的功能結合起來。
南宋后期這種合講堂齋舍與祠堂祭祀為一體新建書院有很多,如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陳復齋在福建南平縣創建延平書院,延平書院是專為紀念朱熹的老師李延平而建,為彰顯閩學學統,陳復齋于南山之下創建延平書院,“以為奉祀、講學之地”,后亦獲得“延平書院”的賜額。福建創建了合講學、祭祀為一體的考亭書院、延平書院后,亦有崇奉理學的士大夫推動創建紀念楊時的“龜山書院”,認為“道南一脈”始自二程的著名弟子楊龜山。故在楊時故居創建合祭祀龜山、講習理學的書院,并上奏朝廷賜額“龜山書院”。
總之,宋理宗之后,理學的價值得到了朝廷的肯定,理學家的聲譽日益高漲,和理學思潮密切聯系的書院也獲得了蓬勃的發展。無論是老書院還是新創辦的書院,大多以講理學為學術、教育主旨,故而這些書院大多已經或后來增加了祭祀理學先師的學祠,南宋書院的學祠祭祀制度就在這種彰顯學統、弘揚道統的追求中得以發展起來。四 創建學祠與建構學統
兩宋時期書院的祭祀制度有一個明顯的演變發展過程,北宋書院仿官學而建立了祭祀孔子的禮殿、孔廟等設施,而南宋書院在繼承祭祀孔子的基礎之上,又發展出了一套創建專門祠堂以祭祀理學大師的祭祀制度。這種新的祭祀制度形成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與宋學學統的興起有關。
中國學術史上所說的“學統”概念,形成并興起于宋代。從字面意義上說,“統”有兩種涵義:其一,指學術的正統,即清人熊賜履在其《學統自序》所說:“統者,即正宗之謂,亦猶所為真諦之說也”。清熊賜履:《學說》、《學統自序》,鳳凰出版社2011年6月,第17頁。其二,指學脈的授受傳承,即人們通常理解的學術傳統,如人們稱熊的《學統》一書是“明學之源流派別”,同上書,《高商序》,第14頁。就是這個意思。宋代以來,學術正統與學脈源流的觀念已結合起來,這就是所謂的“道統”。其實,宋代以來學術史盛行的“學統”觀念,是受“道統”觀念影響而產生的。今人饒宗頤就指出,“學統”是“以正統觀念灌輸于學術史”。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頁。這一學術史的正統觀念就是“道統”觀念。
宋代是中國學術發展到極盛的時期,陳寅恪先生說:“中國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科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82頁。宋代儒學的特點不僅是將傳統儒學發展到致廣大、盡精微的程度,尤有特色的是,當時的儒學還體現為一種地域化的學術形態。群星燦爛的新儒家學者分布各個不同的地域,或者是主持不同的書院,從而奠定了各自的地域性“學統”。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描述了宋慶歷“學統四起”時的盛況:
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孫復)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王開祖)經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胡瑗)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候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篳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六,《士劉諸儒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251-252頁。
慶歷是宋學初興之時,各個地域均開創了自己的學統,包括齊魯、浙東、浙西、閩、蜀、關中等地。從全祖望所描述的“慶歷之際,學統四起”,我們看到了宋代學統的地域化形態初起的狀況,這是宋代儒學學派普遍均以地域命名的緣由,這也是《宋元學案》的編撰為何總是以地域、書院命名的原因。
為什么宋代以來的學術界大興“學統”?為什么宋元明清的學統主要呈現為地域化學術形態?這顯然與宋代以來的學術創造、學術授受的方式有關。兩漢也是儒學大盛的歷史時期,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局面,是中央皇朝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設運動中產生的,五經博士的設置、太學的經學傳授是學術研究與傳播的主要方式,經學的研究、傳播依賴于那些由朝廷供養的經師們的“家法”、“師法”。而宋代儒學的大興則是儒家士大夫從民間講學開始的一種學術活動。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個人的身份,在其家鄉或寓居之地,獨立自主地從事知識創新的學術活動,同時從事知識傳播、人才培養的講學活動。所以,宋明以來,學術史上出現一個十分重要而獨特的現象,就是大量地域性學統的出現。全祖望在研究、整理宋以后的學術史時,就大量使用這種地域性學統的命名,包括“浙中學統”、“湖湘學統”、“婺中學統”、“甬上學統”、“粵中學統”、“橫渠學統”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全祖望:《鮚埼亭集》等。等等,這些學統大多是宋代奠定,并沿續到明清時期。
宋以后學術界能夠建立起學術宗旨各異的地域性學統,還與這個時期興起的書院組織密切相關。書院是萌芽于唐、大成于宋的文化教育組織,它繼承了傳統私學的自由講學、發展學術的教育傳統與學術傳統,又具有制度化的特點,還吸收了佛教禪林的一些特點,故而受到了那些希望推動民間講學的儒家士大夫的特別推崇和喜愛。兩宋時期,那些希望振興儒學、重建儒學的新儒家學者們紛紛創建、主持書院、書堂、精舍、講舍、私塾等民間性的學術—教育機構。學統的構建必須有兩個條件:其一,知識創新、獨立體系的學術思想;其二,學術傳承的學者群體。而書院正是這個學術創新、學者群體的中心。這些書院、書堂的組織成為各個地域的學術中心與教育中心,這個由具有學術創新的儒家學者與承傳學術的學者群體構成的文化社群,正是經過他們的共同努力,從而建構了書院的學統,同時也建構了地域性的學統。全祖望曾經提到“南宋四大書院”,他說:“故厚齋謂岳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并起齊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45,《答張石癡征士問四大書院帖子》。《四部叢刊》本。岳麓、白鹿、麗澤、象山是南宋時期最重要的學術中心和教育中心,由當時最負盛名的理學家的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主持,并且“四家之徙遍天下”,使他們的學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因此,南宋四大書院其實就是南宋四個重要學統的所在地,他們所建構的學統,不僅僅是對當時的學術思想、人才培養、地域學風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明清時期的學術傳播也產生久遠的歷史影響。這也是全祖望之所以反復講“學統”的原因。
其實,南宋書院增設祭祀本朝學人的專門祠堂,主要就是祭祀與本書院學統直接相關的學人,以標榜、弘揚本書院的學統,并將這一標榜學統的追求與弘揚儒家道統聯系起來。我們可以從南宋的湖湘學、閩學、江西學、婺學等幾大地域學統與書院祭祀的關系來作一分析探討。
首先看湖湘學統與書院祭祀。南宋初年最早創辦書院講學、建立理學學派的是胡安國、胡宏父子等人。南宋紹興初年胡氏家族在湖南湘潭創碧泉書院講學,創立湖湘學派。胡安國去世后,胡宏創建了專門祭祀胡安國的“文定書堂”。這是一處將胡氏家祠、書院學祠結合的祠堂建筑。胡宏在修建文定書院時,就明確將這個祠堂賦予了繼承學統、弘揚道統的意義。他在《上梁文》中寫道:
拋案上,道與天通自奮揚。當仁不愧孟軻身,禪心事業遙相望。
拋案下,明窗凈幾宣憑藉。道義相傳本一經,兒孫會見扶宗社[宋]胡宏:《胡宏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201頁。
對于胡宏及其湖湘學者而言,文定書堂是碧泉書院內一處專門祭祀胡安國的學祠,它既有繼承、堅守湖湘學統的意義,還有“道與天通自奮揚”的尊崇、弘揚道統的意義,因為對湖湘學者來說,道統與學統是一致的。
其次看閩學學統。二程之學經楊時、羅從彥、李桐而傳之朱熹,為南宋理學規模、影響最大一派。朱熹亦是有著很強的學統觀念與道統意識的學者,他很早就將這種學統與道統觀念納入到書院祭祀制度中去。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創辦滄州精舍并率諸生行釋菜禮,祭祀孔子、四配及周敦頤、二程,邵雍、司馬光、張載、李桐,他這種由自己老師上溯到北宋理學、孔孟儒學的脈絡,既是閩學學統的脈絡,更是儒家道統脈絡。朱熹在祝文中說:“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圣。……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宋]朱熹:《滄州精舍告先圣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6,《朱子全書》第2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50頁。可見,朱熹是依據一種合學統與道統為一體的意識,將祭祀先師的活動納入到書院祭祀制度中去。朱熹的這一理念,在朱子后學得到進一步弘揚。后來改名或者創建的濂溪書院、明道書院、龜山書院、延平書院、考亭書院均是強化那些閩學學統人物而建立的書院。這些書院均設有學祠祭祀,并將這種學祠與繼承學統、弘揚道統聯系起來。如俆元杰在延平書院的祭祀中,就是將周敦頤、二程、李桐、朱熹的學統納入到孔孟的道統系列之中。他在祭文中反復申明:“濂溪之教,洙泗之遺,內外交養,敬義夾持。……況以四先生之像與夫子坐列于書堂之祠,歲率二禮而申講夫仲丁之彝。”[宋]徐元杰:《延平書院仲丁祭先儒文》,《梅野集》卷11,《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85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9078頁。
象山學派也是如此。陸九淵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于江西老家創建象山精舍,他本人自稱其學是直承孟子而來,故其學統意識不是特別強。但是,他在象山精舍培養的后學,卻倡導并堅持了象山學統,并且在象山書院創建專門祠堂,祭祀陸氏三兄弟。他們在象山書院的祠堂祭祀,同樣是基于對本院學統的繼承和弘揚。袁甫是陸九淵的再傳弟子,他修復了象山書院并創三先生祠,他將這一活動的動機與目標歸之對象山學學統的繼承與弘揚。他明確“書院之建,為明道也”的宗旨,他增設祠祭的目的就是為了表明象山書院的學統是直承孔孟道統而來,他在祭祀象山先生的祭文中說:
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云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未具備,不墮一偏,萬物無蔽。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宋]袁甫:《祭陸象山先生文》,《蒙齋集》卷17,《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79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514頁。
袁甫在祭文中反復伸明象山學統的大旨在“我之本心”,同時強調這一學派宗旨來之于孟子,其實就是將象山書院的學統與儒家道統聯系起來。
總之,南宋的書院學祠建設,一直是與書院學統建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南宋時期的理學家有一種強烈的建構書院學統,以確立書院在儒家道統史上的意義、地位的精神追求,他們通過創建書院學祠、推動書院祭祀活動,以完成這一文化使命與道義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