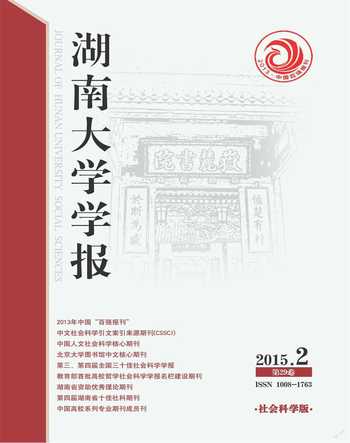抗戰時期張舜徽先生在湖南的學術成就
[摘 要] 抗戰時期任教湖南藍田國師的治學經歷對張舜徽先生的學術生涯有著重要的影響。張先生得以站在較高的學術平臺,跟眾多學者交往,獲得了同學術界廣泛對話、深化學術見解的機會。在藍田,張先生遍覽群籍,結撰名作,積累材料,制定計劃,立下了一生治學之規模。張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與該時期在湖南的治學經歷密不可分。
[關鍵詞] 張舜徽;抗戰時期;藍田國師;壯議軒
[中圖分類號] K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5)02—0100—05
Abstract: It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ZHANG Shunhui’s academic career to teach in Lantian Normal College in Hun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Subsequently,Mr. Zhang stood on a higher academic platform, and formed his academic views by having extensive dialogues with many scholars. In Lantian, Mr. Zhang read large collections of books and wrote articles hard.Meanwhile,he accumulated material and made plans for his later works. Mr. Zhang’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academic research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experiences in Lantian.
Key words:ZHANG Shunhui;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Lantian Normal College;Zhuangyi Xuan
藍田國師,創建于1938年,是設立在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的國立師范學院的簡稱。校舍是“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李燮和老家修建的府第,即李園。藍田國師環境優美,“院舍在藍田鎮北里許之光明山,岡巒起伏中,橫宇林立,前后古木參天,境極清曠。”[1](P4)雖處抗戰期間,仍有不少著名學者來這里任教。錢基博是該校招牌性的學者,學校大門和大禮堂的對聯、院歌都出自他的手筆。除錢基博外,第一批來該校的教師,還有汪德耀、任誠、鐘泰、袁哲、羅睿[2](P114-115)等著名學者。錢鐘書也曾來該校任教,《圍城》中的“三閭大學”即以藍田國師為原型。
張先生于1942年9月17日由楊家灘至藍田國師,開始了其人生至為重要的一站。張先生來該校任教與錢基博、馬宗霍二位前輩學者有密切的關系:“無錫錢子泉、衡陽馬宗霍兩先生主講國立師范學院,過采虛聲,謬加招攬,書問稠疊,令人感奮,適駱紹賓先生亦自辰溪來藍田,相與慫惥,其議乃定。余自惟拙劣,豈敢抗顏為大學師。既辭不獲已,乃強起應之。”[1]P3在藍田國師期間,張先生居第一院李園東樓,“松竹四合,蒼翠異常,”非常怡人。與張先生“洽比而居”的除錢基博先生外,還有阮樂真、曾金佛、吳忠匡等。張先生《八十自敘》中所述的“年過三十,始都講上庠”[3]P108即指藍田國師任教之始。藍田國師相對寬松的工作環境和學術氛圍,為張先生潛心學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一 友朋切磋,壯議振俗,立論學之偉愿
張先生任教藍田之始,即樹立了論學之偉愿,從其新用齋號“壯議軒”可知。1942年11月3日日記:
朝食后,收到徐紹周丈寄來所書“壯議軒”額橫幅,書法甚健,當付裝池,懸之壁間。余生于辛亥七月,去秋三十已滿,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如斯,因取《大戴記》之語,名所居曰壯議軒,以期昕夕省惕,庶幾免于無業之譏,非敢高論以忤俗也,實欲誦先正之法言,無違于正,以免俗耳。昔閻潛邱晚而篤學不衰,自扁其居曰老教堂,蓋亦有取于《大戴》之義。吾于潛邱,無間然也。今之采于斯以自勖,亦以慕大賢云。[1](P97-98)
張先生所云《大戴禮記》之語,出自《曾子·立事》:“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4]P75這段話的意思為,人生分為“諷誦”、“論議”以及“教誨”等三個階段,三十至四十歲之間正值人生之壯年,應該有所“論議”,努力成為“有業之人”。張先生認為自己已過而立之年,應該在壯年有所論議,在學術上有所作為。任教藍田是張先生在學術生涯上由“少”而“壯”,由“諷誦”而“論議”的重要轉折時期。張先生在藍田國師時期“壯議”學術,大致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友朋之間,切磋學問。張先生同前輩學人討論學術相當頻繁,其日記中留下了很多這方面的記載。如1942年10月29日,張先生午后到駱紹賓先生家,論議清代經師之利弊,及近人治學之風氣,并對其師黃君做出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黃君有為人所仰慕者三事,可以矯厲末俗者三事:
盛推其師蘄春黃君高絕不可攀望。綜其學詣,為人仰慕者三事。讀《說文》、《廣韻》爛熟,于均學尤為專門,一也;思理縝密,讀書無一字跳脫,二也;文辭雅艷,三也。黃君學術精密,誠如紹賓先生所言,不為溢美。余嘗從武昌徐氏假觀黃所批校群書,及其往還書札甚多……則其專力致精,常通夜不眠,宜非它人所能及。然余以為此猶黃君之小者,未足以盡之。吾獨得其學行之大,可以矯厲末俗者,有三焉:天性醇厚,事嫡母至孝,一也;絕頂聰明,而治學以愚自守,二也;不附和時下風氣,卓然有以自立,三也。[1](P88-89)
在藍田國師期間,張先生同錢基博先生“朝夕相見,談論歡洽”。張先生在紀念錢基博先生誕生一百周年所作的題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崇高典范》的講話中憶起其與錢基博先生的交往情況:
記得和錢子泉先生第一次通信的時候,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那時我剛三十歲,而他已五十多歲了。我在署名的上面自稱“后學”,這是應該的。但先生在回信中卻說:“后學撝謙,非所克當,獲廁友朋,為幸多矣。”我于是發現這位老學者是一個很謙和的人,容易接近。不久,我應國立師范學院之聘,到藍田任教,與先生朝夕相見,談論歡洽。時間雖只兩年,往還卻很稠密。[3](P360)
張先生日記中有多處關于與錢基博先生講論學術的記載。如在1942年9月25日的日記中,有與錢基博先生討論“北岳之學”的記載:
錢翁以為北岳之學,由義理以貫典制,推典制以歸義理,經經緯史,頗似南宋之永嘉金華學派……與余所見略同。錢翁撰《近代文學史》,未及錄北岳。自去歲余贈以《北岳遺書》,讀而好之,故能窺其微處。余談次,又力勸其補入《文學史》,以表章之也。[1](P6-7)
又如在1943年5月3日的日記中,有與錢基博先生講論《百年來湖南之學風》一書的記載。張先生認為該書“屬意可謂盛矣,”同時也從書名和著述義例兩個方面,對該書所擬錄入人物之去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知其近欲撰《百年來湖南之學風》一書,就湘賢事跡敘述之,藉以作厲士氣。所采自羅、曾、左、郭、江、劉、王、李諸公外,益以湯海秋、魏默深、王壬秋、閻季蓉及今人章行嚴共十五人,但從諸人困心衡慮時論議行事加以闡揚,以為后人處貧賤患難者之鑒。其屬意可謂盛矣。惟余以為,既以“學風”名書,則王壯武特于治戎為長,不合入錄,與不得已,附之羅山傳末可也。章行嚴至今猶存,以著述義例言,不錄見存之人,避標榜也。余舉此二者告之,不知其果能聽取否也。[1](P421-P422)
除錢基博先生外,張先生同鐘泰、馬宗霍二位學者論學亦多。在同輩學人中,張先生與董世昌、張汝舟、阮樂真、曾金佛等人亦時常講論學問。
二是品評時賢,激揚學風。對于當時人的著作,張先生亦能秉持公心,予以評述。如對于梁啟超、錢穆二家考論清代三百年學術源流之書,張先生認為梁氏書但敘清初大儒,而未及乾嘉以后;錢書晚出,較為翔實,而漏略亦甚。1942年9月27日,張先生在研讀錢穆之書后,對該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其取材廣博,采擇精當,持論平實,能見其大,指出該書成就遠在時下一般著述之上。但同時亦指出該書“可補者實多”:
自余觀之,可補者實多。梨洲之下,宜附以邵念魯,以其為章實齋史學所自出,不可忽也。顏、李之下,宜附以劉繼莊、王昆繩,以其羽翼習齋,同歸致用,兼舉并列,相得益彰。戴東原宜有惠定宇,以其開吳學之先河,足以匹敵東原,不當在東原下……章實齋之前,宜有翁覃溪,救敝之言如合符契,豈容偏廢?曾滌生之下,宜取劉霞仙與羅羅山并舉,義理之言劉氏所發尤多,實為湘學后勁,自船山以來未之有也。此特就其顯見者言之,至其它必待充實者尤多。[1](P12-13)
張先生不茍時俗,不附會時議,對于其時已經形成風氣的學術觀點,亦敢于大膽發表意見,提出不同的看法。在1943年4月13日日記中,張先生指出孔氏有維系人心、濟補刑政之功用,對廢孔之說加以駁斥:
夫孔子生于周末,去今二千四百余年,其所論說容有宜于古而不適于今者,且人事日新,文明日進,而謂吾華立國之道求之孔氏而足,是固拘虛之見也。雖然,立國于大地,必有其所以維系人心于不敝者。孔氏于既往二千年中為天下綱紀,足以濟刑政之所不及者實大且多。今欲有所革易,自必先立一新倫理之中心思想,而后可譬諸窶人之子。今漸富矣,惡夫茅茨采椽之陋,必別營峻宇彫墻而后可徙也……故言廢孔可也,廢孔而不別圖樹立倫理之中心思想不可也。[1](P370-371)
緊接著,他又指出“孝”為先民教民之本,與華夏之存亡息息相關,并以鄧禹之舉為例,對非孝之說予以駁斥:
若夫善事父母之為孝,先民以為教民之本。吾華夏歷數千年而見滅于異族者,亦賴有此耳。其與乎邦族存亡之故蓋有二焉:一曰人才之消長系于此也……二曰國民忠憤之思必基于此也……昔余讀《后漢書》,深服鄧禹初入長安,遽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其智慮為不可及。有此一舉而天下歸仁,勝于臨之以兵,施之以政萬萬也。嗚呼,此豈敢為異論高言之書生所能夢見哉
對非孝廢孔之說的駁斥,體現了張先生的真知灼見,及獨立、冷靜地思考學術、學風的理性態度。
二 遍覽群籍,如克名城,成學術之宏基
藍田國師“略無塵俗之擾”的環境給張先生潛心讀書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張先生在教學工作之余,遍覽群籍,為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張先生的讀書方法很值得我們學習,其特點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敢于讀大部頭的書,制定計劃,日有定程。張先生恪守“攻書如克名城”的古訓,對于經史要籍,立志要遍搜盡讀。張先生讀書有自己的計劃,計劃一旦制定,就會嚴格執行。以其在藍田國師時讀《宋史》和宋人、清人文集為例:
其一,以一年之力,盡心以治《宋史》。1942年10月6日日記:
今稅駕此邦,略無塵俗之擾,愛日以學,期竟前功。所宜汲汲從事者,其《宋史》乎?余近來思研尋宋學精蘊,尤非通知其史事不可,期以一年之力,盡心以治之。[1](P39)
次日,張先生即往圖書館借閱宋代史書。1942年10月21日,張先生發憤以歸熙甫之言自厲,定讀《宋史》以為日課:
自明日起,定讀《宋史》為日課,雖百忙亦不可間斷。昔歸熙甫深于此書,鉆研不替,集中有《宋史論贊》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此通人之言也。余治此書,當昕夕奉斯言以自厲。[1](P61)
據張先生晚年“至一九四四年,當吾三十三歲時,全史校畢”[16]之語,可見宋史以下諸史,正是張先生任教藍田國師時校讀完畢的,張先生嚴格地執行了自己的讀書日程。
其二,以十年涉獵,遍讀宋人、清人文集。1942年9月29日日記:
暇思清代學術,其耑悉自宋人開之……由此言之,有清一代之學莫不淵源于宋。今欲窮清儒之根株,必先明宋學之流別。余自今以往,當取宋清兩代之書縱心力讀之。期以十年涉獵,庶幾免于一孔之譏矣。計余此時已讀清名家集,不過三十余家;宋名家集,不過十數家……弇陋已甚,安可不自勉耶?”[1](P20-21)
1942年10月28日日記中亦有“宋元兩代博通之人極多,余必求其文集而遍讀之”之語。《清人文集別錄》的結撰,正是其縱心力以讀文集的最好證明。
二是善于將讀書、思考和寫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張先生的日記中,有大量的閱讀文集后所作的要點摘錄及評說的記載。如1942年11月25日日記中摘錄了魏了翁文集中的論“文”之語,并指出其“議論通達,實獲我心”:
魏鶴山論文之言曰:“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為者,皆文也……”議論通達,實獲我心。吾平昔持此論久矣,而古人已先言之。士生今日,閱覽不可不博也。[1](P162-164)
1942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張先生在讀完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外集》之后,對陸隴其之學進行了評價:
陸清獻之學,專宗朱子,排斥陸、王甚力。論學大旨,具于《學術辨》三篇(《文集》卷二)。它若《答嘉善李子喬書》、《上湯潛庵先生書》、《答同年臧介子書》、《答秦定叟書》(《文集》卷五)諸篇,亦大有關系。觀其論陽明處,未免過苛。然俌弱扶微之思,固足尚也。《四庫提要》稱其學問深醇,操履純正,此八字蓋足以盡之……吾觀清獻論太極理氣,慮猶涉乎超玄,未足以喻諸中下之資。其教誨學子,平易正直,而可循者則有在矣。[1](P66-68)
張先生日記中所作的摘錄和評說,既是材料的積累,也是其學術觀點的總結。張先生很多重要的學術著作都能從日記中找到材料或思想淵源。如《清人文集別錄》中關于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外集》的觀點與日記中所述非常相近:
為學專宗朱子,排斥陸王甚力。論學大旨,具見是集卷二《學術辨》三篇。其次若卷五《答嘉善李子喬書》、《上湯潛庵先生書》、《答同年臧介子書》、《答秦定叟書》諸篇亦大有關系……由其論學定于一尊,自不免舉一而廢百。言論所至,又不第詆斥陸王而已。[6](P54-55)
三是樂于讀書,以讀書為人生最大的樂事。張先生讀書非常勤勉,“每日凌晨三時輒醒,醒則披衣即起,不稍沾戀。行之畢生,受益至大。起床后,整頓衣被幾案,迨盥漱畢,而后伏案觀書。”[7](P216)幾十年如一日,寢饋于群籍之中,人不勝其苦,張先生但覺其樂。1943年1月12日日記中有關“勞”、“愚”的一段話頗能道出張先生讀書所達到的境界:
近來讀書甚勤,不覺疲憊,而領悟亦日進。從知以勞自養,則精神愈用愈出;以愚自處,則聰明愈用愈靈。能守此勞愚二字以終吾身,必無不成之事。勉之而已。[1](P288)
在張先生的日記中,常能體會到其讀書時得意忘言的愉悅心情。1942年11月3日日記:
如言鹿有粗義,鹿裘乃裘之粗者,非以鹿皮為裘也。鹿車乃車之粗者,非以鹿駕車也。《呂氏春秋·貴生篇》顏闔鹿布之衣,猶言粗布之衣也。此解真諦,得未曾有。一語道破,積惑頓消,快慰之至。”[1](P98)
1943年3月16日的日記中有“得此一言,冰解的破,歡欣鼓舞,得未曾有”[1](P331)之語;1943年3月18日的日記中有“偶悟及此,無任豫悅”[1](P335)之語;1942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有夢見關中大儒李颙的記載,夢境與讀書相連,與所景慕之先賢“精誠與通,亦可喜也。”[1](P87)此中真趣,實難與外人道。
三 結撰名作,廣植根基,開一代之學派
在藍田國師任教時期,張先生伏案著述,其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完成了校讎名作《廣校讎略》的寫作。《廣校讎略》是一部推衍鄭樵《校讎略》思想的著作。從其日記推測,《廣校讎略》的撰寫應始于1943年上半年,完稿當為年底。張先生在《三十五年來我是怎樣把教學和科研結合在一起的》一文中對《廣校讎略》有詳細的介紹:
當我在三十二歲(一九四三年)的時候,便開始《廣校讎略》的撰述,首先談到“校讎學”名義及封域,然后因論立題,分為古代著述體例、標題、作者姓字標題、補題作者姓字、援引古書標題、序書體例、注書流別、書籍傳布、書籍散亡、簿錄體例、部類分合諸論。這是有關介紹古書情況的部分。繼之以書籍必須校勘、校書非易事、校書方法、清代校勘家得失諸論。這是有關闡述怎樣校書的部分。再繼之以審定偽書、搜輯佚書諸論,而以漢、唐、宋、清學術論結尾,共一百篇。這是我講授校讎學的最早著作。[3](P583)
《廣校讎略》是張先生在藍田國師任教期間,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標志性成果,是張先生的開山之作。該書是他三十歲之前的治學小結,也是他一生著述的起點。1958年,他提起此書時,指出書中的某些內容,“仍不失為愚者千慮之一得”:
十五年前,我寫過一部《廣校讎略》(有壯議軒自刊本),是推廣鄭樵《通志·校讎略》的體例而寫作的。主要談到了學術流別、著述體例、以及目錄、校勘、辨偽、輯佚等多方面的問題。當時是用文言文寫的,因論立題,各相統攝,共一百篇。現在看起來,其中有些內容,仍不失為愚者千慮之一得。[8](P210)
可見張先生對《廣校讎略》一書亦是頗為重視和滿意的。作為《廣校讎略》的附錄,《毛詩故訓傳釋例》亦完成于該時期。
二是完成了《清儒粹語》等資料長編的纂輯工作。張先生在撰寫學術著作之前,很注重資料的收集和纂輯,以為其學術立論提供材料支持。如張先生欲撰《清儒通義》,并不急于動手,而是先進行材料的“博求”和“周采”工作,完成了《清儒粹語》、《清儒識大編》的編纂,并計劃另纂《清儒著述敘錄》,以為《清儒通義》的撰寫做準備。1942年12月31日日記:
余年來搜輯清儒論學之文,分令及門手錄者積百數十篇,今日付書肆,分裝成三厚冊,命之曰《清儒識大編》,此后猶當博求而周采之,以充斯篇帙也。自去秋發愿欲撰《清儒通義》,自懼才力不足以任此,姑先為長編,以俟異日寫定可也。凡吾所錄《清儒粹語》及此《識大編》,皆《通義》之底本。此外猶思纂《清儒著述敘錄》,以甄錄有清一代之書,茍能成此三種以當長編,庶幾《通義》可涉筆矣。[1](P249)
三是完成了《鄭雅》的纂輯以及《兩戴禮記札疏》、《逸周書》校釋等著述。張先生舊有寫定“九雅”的計劃,《鄭雅》為其中的一種。所謂《鄭雅》,即“纂鄭氏《禮注》、《詩箋》及佚注之輯存者”[31]而成之書。張先生在六七年前已開始了《鄭雅》的編纂,并已完成部分工作,但一直因“分心它業”而遷延未成。1942年10月30日日記:
余嘗持論以為,考辨群經名物,必以鄭氏為宗,而取賈、孔之說疏明之,浩然欲撰《鄭雅》一書。《禮注》、《詩箋》綜錄略定,既已寫為《三禮鄭注義類》、《詩箋義類》二種,臧之篋衍六七年矣。惟諸經佚注未及排比。頻歲奔走四方,恒以鄭氏佚書自隨,思乘暇隙竟此全功,率以分心它業,不克專意于斯,坐視無成,良足嘆息。[1](P90)
1943年3月17日日記中說:“余嘗發愿欲篹《鄭雅》,久而無成,近乃矢志為之。”[1](P331)這大致上是張先生集中精力纂輯《鄭雅》之始,整個《鄭雅》的定稿工作,用了約四個月的時間。《鄭雅》經過了張先生細致的剪裁,已非一般的資料匯編可比。《鄭雅》一書,后來成為張先生《鄭學叢著》中的一種,是他最為珍視的一部分。
1942年12月7日日記中有“自今日起,校《逸周書》”[1](P185)之語;1942年12月30日有“《逸周書》初校畢”[1](P247)之語。從該日日記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張先生為校釋《逸周書》所費功夫之大:“此書舊多脫誤,不可卒讀。自盧文弨、丁宗洛、王念孫、洪頤煊、莊葆琛、朱右曾、何秋濤、徐時棟、陳逢衡、朱駿聲、俞樾諸家相繼考校,殘書闕簡漸復可觀。”[1](P247)其校釋成果在四年后又重加整理,寫成《周書小箋》,于40年后,編入《舊學輯存》。收入《舊學輯存》中的《兩戴禮記札疏》亦完稿于該時期。
張先生的治學范圍非常廣闊,著述頗豐。張先生后期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清人文集別錄》、《中華人民通史》、《說文解字約注》、《清儒學記》以及《經傳諸子語選》、《周秦諸子政論類要》等,皆能從藍田時期找到其淵源。在藍田國師任教期間,張先生壯議學術,遍覽群籍,著書立說,并制定規劃,積累材料,為以后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錢基博先生曾預言張先生“異日必享盛名,足以自開學派。”[1](P729)張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在歷史文獻學學科建設上的開創性貢獻,與他任教藍田時期的治學經歷密不可分。
[參 考 文 獻]
[1] 張舜徽.張舜徽壯議軒日記[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2] 李洪巖.錢鐘書與近代學人[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3] 張舜徽.讱庵學術講論集[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4]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 點校.大戴禮記解詁[M].北京:中華書局,1983.
[5] 張舜徽.舊學輯存·敘目[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6]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7]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8]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序言[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