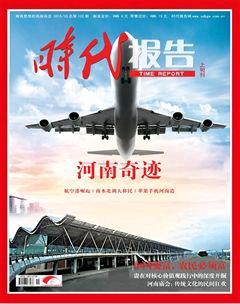A股牛市:可能是下一個危機的開始
譚保羅
新一輪的A股“牛市”,不是中國實體經濟好轉的結果,而是股市痼疾的間歇性發作。
2014年11月以來,A股在兩個月的時間里,經歷了一次意味深長的漲和跌。在這個過程中,券商扮演了“發動機”的角色。它們通過各種高風險的杠桿融資手段,裹挾萬億的資金進入A股,催漲了這個“資金市”的短暫狂飆。同時,上市券商自身的股價狂升,背后大佬紛紛套現離場。
實際上,券商們早已獲得這些高杠桿“金融創新”的許可權,那么股市爆發為何偏在此時而非彼時?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市場的早先降息預期和隨后的降息。換言之,那些有著超強政治嗅覺的資本市場“大佬”很清楚,在轉型的特殊時期,貨幣的猛虎暫時還無法回籠,資金的廉價和泛濫依舊是中國經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再環顧全球,在全球證券中介不斷去杠桿的時代,中國的同行們卻反其道而行之。尤其對于一個資產證券化程度極低的國家來說,券商過度的杠桿化的“金融創新”必然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很可能,這只是下一個危機的開始。
“杠桿炒股”游戲
在跳完廣場舞后,身強力壯的大媽們會在9點鐘準時擠進證券營業部的大門,啃著煎餅,盯著大屏,觸摸著“牛市”。
大媽群體是本輪行情的重要推動力。2014年12月的第一個星期五,證監會發言人透露,參與交易的A股賬戶數劇增至2027萬戶,比前一周增長了43%。
11月肇始的A股狂飆,不是經濟回暖的產物,而是泛濫的錢流堆出來的行情。它和上市公司盈利狀況以及國家經濟大勢關聯甚微,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資金市”。
“非官方”數據顯示,經濟基本面尚未好轉。近兩月以來,反應實體經濟狀況的匯豐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不升反降。11月,PMI降至50.0,創6個月新低。12月,較11月終值再回落0.5,7個月以來首破50.0的枯榮線。
企業不好,股市卻好,這主要受益于中國股市一個特殊的“資金放大器”,即“兩融”業務:融資和融券。“融”為“借”之意,融資是投資者向券商借入資金用于證券買賣,并在約定期限內償還本息;而融券則是投資者向券商借入證券賣出后,在約定期限,買入相同數量和品種的證券歸還券商并支付相應費用。
通俗來說,“兩融”是投資者、券商和市場的一次三方“賭博”。對投資者來說,融資是在“賭”股票會上漲,而融券則是“賭”股票會下跌,因此投資者才有利可圖。而對券商來說,除了一般經紀業務的交易傭金之外,該業務還有融資融券利息和其他費用可以收取。如果投資者因虧損無法還債,投資者要以質押資金或證券來對券商進行清償。
對幾年不振的A股而言,“兩融”業務不啻為一根救命稻草,它通過“借”的方式,重新換回了曾經用腳投票的大媽們。按照監管規定,“兩融”業務的保證金比例不得低于50%,這等于放大作用是2倍。但在實際操作中,券商可通過復雜的“技術手段”規避監管,將杠桿放大至3倍。
12月19日是2014年的倒數第二個星期五,A股的“兩融”余額一舉突破萬億,達到了1.007萬億,而A股的流通市值不過30萬億。對比2013年底,A股“兩融”余額僅為3465.27億。顯然,“兩融”對2014年年末本輪“牛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兩融”業務并非2014年才有的新鮮事物。早在2010年3月,證監會便公布了融資融券首批6家試點券商。但一直以來,該業務都做得“不慍不火”,直到2014年下半年才開始突飛猛進。2014年6月底之前,兩融余額一直徘徊在4000億元左右,僅為年底的2/5。
顯然,券商的“金融創新”踩準了時間。和所有借貸業務一樣,從事“兩融”最大的風險之一是利率風險。簡單說就是,投資者在從事融資融券交易期間,如果央行規定的同期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調高,那么券商將相應調高融資利率或融券費率,投資者將面臨融資融券成本增加的風險;反之,如果央行降息或存在降息預期,則券商可以調低利率,實現“薄利多銷”。
2014年,多家券商曾不惜以7%的利息在“兩融”市場大打價格戰。這個利率幾乎可以看作是,投資者從券商那里以和銀行貸款利率相差無幾的優惠利率“貸款炒股”。
券商之所以敢這么做,其重要原因在于對降息的預期,以及對降息必然導致牛市這個普遍規律的篤定。年底,央行的確“意外”啟動了兩年以來的首次降息,決定自2014年11月22日起全面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
2014年年中開始,券商分析師便紛紛高論“對熊市的最后一戰”,看來券商們全都“猜”對了。
券商的“牛市”
對本次央行降息,“官方解讀”是為了降低社會融資成本,而民間異議者則認為,在資金泛濫、企業投資效率低下的時點,降息等于火上澆油。獨立研究機構MFI首席研究員江勛對記者指出,降息很大程度上是中央對地方的妥協,以減輕地方債利息負擔。另有估算稱,僅一年期貸款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可減少國內企業和社會的利息負擔4000億。
地方政府吃到了肉,而券商也喝到了湯。它們通過融資融券這樣的“金融創新”充分地享用了央行降息的大禮包。享用的方式很簡單,即必須抓緊利用降息通道,調動更多資金入市,只要市場起來,傭金和利息都不在話下。
除了“兩融”業務的“放大器效應”之外,券商還通過收益互換等“創新”涉足銀行理財資金。目前,我國銀行理財資金余額已達15萬億,幾乎等于A股流通市值的一半,它們是券商眼中的“唐僧肉”。
收益互換是個比融資融券聽起來更復雜的金融工具,但其本質和融資融券相通,即用少量的錢撬動更多的錢來投資股票,其杠桿最多可加到5倍,遠超過“兩融”業務。
按照監管規定,銀行理財資金不得投資于境內二級市場公開交易的股票或與其相關的證券投資基金,但通過收益互換復雜操作,可以一定程度上將實際上的投資關系“包裝”成互換關系,從而規避監管。目前,已有超過20家券商在試點該業務,全行業的互換規模可能已經超過千億。
不論是“兩融”業務,還是收益互換,其本質都是通過杠桿把“虛擬”資金或實際資金吸引進股市,推動股市的交易,做活做大市場。如此,券商將受益多多。
事實上,中國券商太需要這樣一次絕地反擊了。在過去的熊市中,券商投行部和研究所人心惶惶,大裁員降低了費用,但改變不了行業數據的悲催。
中證協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的115家券商全年實現凈利潤440.21億元。但是,工商銀行一家在2013年便實現了2630億元的凈利潤。換言之,中國券商全行業的利潤只有工行一家的1/6左右。此外,排名靠后一些的券商,利潤只有區區數百萬元。而且由于不少券商是地方國企,一把手“政績”考核嚴格,不少利潤都來自于“財技”的運作。
熊市固然是券商“冬天”的罪魁禍首,但中國券商的根本問題在于本身的盈利模式存在巨大缺陷。目前,國內券商的主要盈利局限于證券經紀、承銷和自營三大業務,而經紀業務中的傭金收入一項就占據總利潤的50%以上。該業務具有典型的“靠天吃飯”特征,換言之,A股走熊,經紀部門就只能喝西北風。對比高盛等美國同業,后者的利潤來源結構中,經紀業務中的傭金收入約占20%,而其他收入創造的利潤才是主力。
券商的困境在于兩個原因,一是地方分割,券商都是地方國企或者央企子公司,并購整合難,市場主體分散,惡性競爭頻發。另一方面,管制嚴格也限制了券商的創新,使得非經紀業務長期裹足不前。
但遇到2008年之后的大熊市,監管也打算幫券商們一把。2010年,融資融券業務首批6家券商試點。2012年底,收益互換試點。而前不久,證監會又發布了《股票期權交易試點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期權有望于2015年年初推出。顯然,這些都是券商的大利好。
這些創新的“官方解釋”多半冠冕堂皇,但實際上,券商的生存無疑也是監管必須要考慮的因素。監管的放松,給了券商更多創新的可能,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東風是更廉價的錢,央行的降息正好送來了東風。
再做“接盤俠”
東風吹起了豬,但總會跌下來。2014年12月最初的3周,券商為首的金融板塊和部分藍籌集體上漲,滬指大盤也重上3000點。其中,18支上市的券商股多次漲停,主要券商股票累計上漲七成。
一組廣為流傳的數據顯示,以市值計算,目前世界前23大市值的證券公司名單中,15家為中國券商。其中,中信證券以563億美元的市值成為全球第四大券商,僅落后于高盛,摩根士丹利以及UBS。
繼銀行業問鼎全球榜首以來,中國證券業也開始崛起,但這種崛起似乎是在逆潮流而動。金融海嘯之后,西方投行紛紛開始“去杠桿化”時代,而中國的券商卻在不停“加杠桿”,即不斷借錢來支撐所謂的“金融創新”。Wind數據顯示,2014年以來,券商發行的短期融資券、公司債和證券公司債總規模已經達到5976億元,而目前,中國券商的總資產不過剛突破2萬億。
券商融資的相當部分都用在了“兩融”、收益互換等“金融創新”上,而這些“創新”風險極大。
在本世紀的最初5年,中國的證券公司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倒閉潮。原因在于這些證券公司挪用客戶的理財資金和結算資金去炒股,最后坐莊失敗,產生巨虧。而“兩融”業務的債務關系,本質上也是券商“深度參與”了炒股,風險不容小覷。
不過,券商總能找到“埋單者”。在中國股市,風險的最終承擔者永遠是股民。對股民而言,融資融券的杠桿效應意味著,如果投資者虧損,那么虧損也將正比例放大。例如,投資者以100萬元買入一只股票,該股票從10元/股下跌到8元/股,投資者的損失是20萬元,虧損20%;但如果以50%的保證金比例,從券商融資200萬買入該股票,則虧損40萬,虧損40%。顯然,投資者的虧損被放大了。
兩融業務還有強制平倉的風險。按照規定,證券公司為保護自身債權,對投資者信用賬戶的資產負債情況實時監控,在“一定條件”下可對投資者資產強制平倉。換言之,在股票暴跌之時,證券公司可以直接把投資者的股票“賤貨甩賣”,而不給投資者一絲“徐圖再漲”的希望。
以2013年的昌九生化爆倉“慘案”為例,其連續7天跌停停牌,股價累計下跌近60%。統計顯示,7個交易日其累計換手率還不足1%,也意味著,僅有1%不到的投資者逃出厄運,投資者數億資金深陷其中。對融資買入昌九生化的投資者來說,當跌停打開,券商必然會在第一時間平倉。最后,不少投資者發現,手中的股票沒有了,還欠券商的錢。
顯而易見,在中國的資本市場,“金融創新”永遠代替不了真正的基礎性改革,所謂“創新”,很多時候只是對股民財富進行乾坤大挪移,以挽救某些特殊利益群體的手段。在“創新”推動的混亂“牛市”中,股民不知不覺便充當了“接盤俠”的角色。A股開市20多年,這種局面從未改變。
Wind數據顯示,2014年11月的“牛市”以來,A股的19只券商股中,共14只被重要股東減持,涉及8.4億股,累計減倉參考市值116.3億元。看來,大佬們得以再次微笑離場。
中國《刑法》規定賭博是違法的,以營利為目的的聚眾賭博可處3年以下徒刑,但在資本市場,“賭博”卻是合法的。大媽、失足婦女、販夫走卒,還有處于家庭資產負債表平衡邊緣的“房奴”,全都加入其中,成為一波又一波莊家的“接盤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