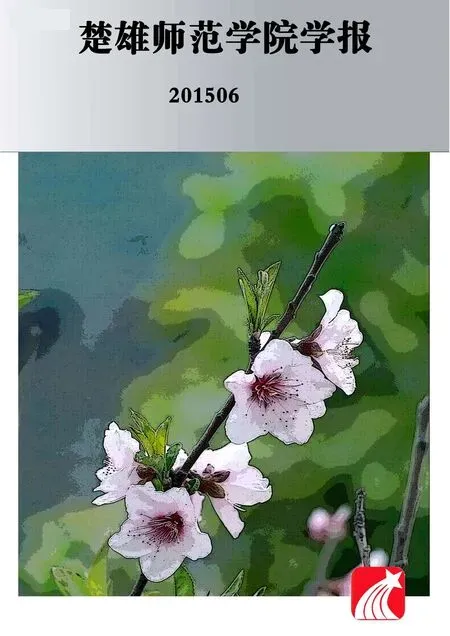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投融資策略分析*
徐曾興
(國家開發銀行,北京 100084)
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投融資策略分析*
徐曾興
(國家開發銀行,北京 100084)
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投融資所需資金可以在PPP模式下,通過中國和東盟國家政府部分出資、引入社會資本投資,以及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申請貸款解決。可以考慮由亞洲國家政府共同出資成立一個中立的第三方評級機構,建立亞洲評級體系,給予東盟國家公正的信用評級,增強東盟國家國際市場融資能力。此外,還可以考慮由亞洲國家共同出資成立一家專門支持亞洲國家基礎設施貸款的政策性信用保險機構,為包括東盟在內的亞洲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貸款提供信用保險,分散PPP模式下各參與方的投資風險。
中國-東盟;互聯互通; PPP模式;投融資
1.互聯互通概念的起源和發展
“互聯互通”起源于電信通訊行業,指在不同電信網絡之間建立有效連接。由于電信行業的特殊性,占據主導地位的運營商往往控制著大部分的電信基礎設施,其它規模較小、占據非主流地位的運營商欲進入這個市場,就不得不通過互聯互通的方式與主流電信運營商共享資源。東盟是最早將互聯互通概念推向廣義范疇的先行者,2007年簽署的《東盟憲章》里就明確提出了希望東盟國家能夠共同努力,增強東盟成員國與其它國家和地區互聯互通的戰略。2009年10月,在第15屆東盟首腦會議上,東盟國家領導人就明確提出了互聯互通的重要性,并發表了重要聲明,這是區域性組織第一次正式提出廣義互聯互通概念。[1]
國內學者認為,廣義互聯互通多強調空間概念,理論基礎主要源于經濟地理學。在實踐中涉及經濟地理學中的現代區位理論,區域經濟學中的增長極理論、點軸開發理論、回波與擴散效應、發展經濟學中的產業結構調整理論以及貿易引力理論。[2]
2. PPP概念及其定義
PPP是英文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縮寫,主要是指政府公共部門與企業私人部門通過建立伙伴關系來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或者公共服務的一種合作方式。PPP的具體定義目前還沒有公認的說法,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此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從國內來看,對英文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譯法也各不相同,既有公私伙伴關系,也有公私機構伙伴合作,還有官方與民間合作等。綜合而言,PPP包括了廣義和狹義兩種定義,其中,廣義的PPP主要指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建立的各種合作關系,主要是為了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或者公共產品,具有社會效應,是一種廣泛的合作關系,即無論在項目的何種階段、以何種形式,只要存在公私合作,都可以認為是PPP模式,這當中包括BOT(建設——經營——轉讓)、BOO(建設——擁有——運營)等融資模式。而狹義的PPP則主要指由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組成特殊目的公司,通過引入社會資本,以及共同設計、共同開發、共同承擔風險、全程合作來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一種開發和運營模式。這種模式強調的是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貫穿于項目的全過程。國外的PPP多指廣義的PPP;國內的PPP多指狹義的PPP。[3]
3.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投融資現狀分析
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投資空間巨大,但資金投入不足成為制約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因素。PPP模式是一種得到普遍認同的投融資模式,相比較單純的政府投資或者私人投資,PPP模式很好的解決了大型公共基礎設施項目投資期長、投資規模龐大、投資回報率相對較低、風險偏高、不確定性因素大等難題,同時,也妥善的處理了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公益性和盈利性問題。
4.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投融資策略分析
4.1項目可研階段費用出資來源
一般情況下,項目可研階段的費用支出往往占項目總體投資的比例較小,但是對于大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而言,尤其是公路、鐵路、港口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前期的項目可研、勘測等等往往耗費巨資,對東南亞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而言,前期費用的支出會給財政造成巨大的壓力,很多項目也因此被擱淺或者推延。在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前期可研費用的支出一部分將由中方企業或者中國政府承擔,但另一部分需要由項目所在國(東盟國家)來承擔,通常而言,商業銀行貸款往往只能覆蓋成熟項目總投資的一部分(通常情況下最高不超過項目總投資的85%),對于前期的可研費用,由于風險較高,除非東道國政府提供主權擔保或者提供其它擔保品,很難獲得銀行貸款支持。
但是,除通過政府財政支出支持和投資企業出資外,東盟國家需支付的這部分資金還可以通過申請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技術援助貸款來解決。以亞行為例,其技術援助部分可分為:項目準備階段的技術援助、咨詢技術援助和項目執行階段的援助。技術援助項目需要經過亞洲開發銀行董事會的批準,如果援助額度不超過35萬美元,亞行行長也有權力批準,但仍須通報亞行董事會。
4.2多元化籌資解決項目資本金出資問題
在PPP模式下,項目的資本金出資來源主要包括政府出資和投資企業出資,對于東道國政府而言,資本金來源包括:財政撥付、發行國債或特別債券籌集資金;對于投資企業而言,資本金來源包括:企業利潤直接投資、發行公司債籌資、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等。除此之外,在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中,還可以引入第三方投資機構參與投資,包括東盟基金、絲路基金等機構均有望參與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其中,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絲路基金將成為第三方投資機構的主力。
2014年11月8日,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將成立絲路基金,首批出資金額為400億美元。根據規劃,絲路基金今后將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能源資源開發以及產業合作等各領域提供投資及融資支持。目前,絲路基金正在積極籌建。絲路基金的出資方包括外匯儲備、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其中,由外匯儲備出資65%,由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各出資15%,剩余5%由國家開發銀行出資。絲路基金作為股權投資基金,將直接而有效的解決亞洲地區重大戰略性項目的資本金短缺等投融資難題。
此外,亞洲開發銀行也可以參與部分股權投資,向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提供部分資本金。亞洲開發銀行的股權投資是亞行對私營企業新開展的一項業務,該投資無需政府擔保。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有望為項目的資本金提供部分軟貸款,以解決項目資本金出資問題。
除上述東盟國家政府、兩國參與項目投資建設的企業、政策性投資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股權投資基金等)外,還可以引入商業投資機構參與投資。
4.3引入實物期權解決投資回報率商業化難題
4.3.1實物期權對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的適用性
實物期權適用于周期長、投資大、階段性強、波動性大的項目,屬于動態的戰略決策,對于不確定性較大、風險較高、投資收益不確定的項目比較適合引入實物期權進行開發。由于PPP項目在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項目價值不由當前現金流決定,而是由未來變化決定,其實施也具有不可逆性,在投資決策時面臨較大的風險,而實物期權則賦予了決策更多的靈活性,可以對沖未來潛在的較大風險,以較低的成本鎖定風險博取較高的收益,故實物期權在PPP項目中具有一定的適用空間。
4.3.2構建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實物期權[4]
延遲期權:對于PPP項目而言,未來經營情況的好壞較難準確預測,因此,在面臨投資不確定性風險時,決策者可以根據項目實際進展情況以及政府賦予的政策來決定是否終止項目,以避免更大損失,這就是延遲期權,但由于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規模較大,基本上由中國與東盟相關國家政府牽頭執行,項目一旦確定實施,基本上需要按照雙方商定的既定計劃執行,不存在延遲的可能性,所以,對參與該類PPP項目的企業而言,不存在延遲期權。
增長期權:在很多領域,企業需要參與某項投資以獲得其它的投資機會,這種以某種先決投資獲取未來成長機會實際上隱含了一種選擇權,這就是增長期權。對于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而言,由于很多企業根據自身的戰略規劃,有進入中國和東盟市場的計劃,但迫于現有的門檻等諸多原因尚未進入,而通過參與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獲得了市場準入權,其未來存在較大的成長空間,其實變相的相當于獲得了一種增長期權,這也是很多民間資本愿意參與PPP項目的重要原因。
放棄期權:放棄期權指的是企業管理者可以在經營狀況不佳和投資回報率低于預期的情況下選擇提前終止項目的一種期權,但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的性質決定了企業是不可能中途結束項目的建設。因此,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不存在放棄期權。
轉換期權:轉換期權指的是投資者可以根據市場變化情況獲得追加投入或轉換投資的權利。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由于其公共項目的特殊性,不具備轉換期權。
變換規模期權:投資者可以根據市場變化改變投資規模的選擇權即為變換規模期權。根據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的特點,其投資規模往往在投資決策時已經議定,不存在隨意更改規模的空間,所以變換規模期權不適用于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可能的5種實物期權中,實際上最有可能被投資者接受并采納的是增長期權。企業通過該項目的投資可以熟悉新的領域,鍛煉和培養人才,為公司在該領域贏得知名度,從而為公司在該領域或者其它領域參與投資奠定基礎,贏得潛在的成長空間。對于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PPP項目,增長期權可以使參與者獲得進入中國和東盟市場其它領域的機會,從而提高投資者參與PPP項目的積極性,同時也降低了投資風險。
由于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本身的公益性決定了其投資回報率將低于通常的商業投資項目,加上項目投資規模大、投資期長、風險高,單靠項目自身的收益,注定其對商業投資機構的吸引力不高,但是由于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主要為跨境公路、鐵路、港口等大型基建項目,政府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可以通過引入實物期權的模式,在PPP項目開發中,授予參與投資的民間資本部分商業設施開發權,諸如配套附屬商業設施開發,如鐵路運營權、公路收費權、港口運營權、商業地塊開發權、能源礦產開采權等。同時,通過實物期權模式,尤其是增長期權模式,在鎖定企業配套設施開發風險的同時,也為政府公共項目投資鎖定了收益,還給予了企業未來資產價格上升可能帶來的大額回報,增加了企業參與大型公共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的積極性,確保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吸引到足夠的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建設。
5.化解融資困局策略
5.1探討建立亞洲評級體系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信用評級往往決定了一個國家和一個企業在資本市場的話語權,可以說誰掌握了國際信用的評級權,誰就掌握了金融市場的定價權。信用評級話語權對國家核心利益的影響前所未有。在當前債權債務關系日趨全球化的時代,是否掌控信用評級話語權對于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國家影響深遠。毫無疑問,信用對現代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金融市場上,信用評級往往是一個國家和企業融資能力的風向標和準繩,是金融市場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也是國際資本市場保持公平、公正和誠信的重要基石。目前,國際市場的信用評級權長期掌控在美國公司手里,尤其是以穆迪、惠譽和標準普爾為首的國際三大評級機構,長期壟斷了國際資本市場的評級權,對全世界的資產價格予以定價,而且在不公正的現行國際金融體系下,三大評級公司的信用評級往往帶有很大的偏見,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不僅企業的信用評級被人為壓低,甚至國家的評級也被人為的降級,以此來達到干擾、影響乃至控制別國經濟的目的。
目前,東盟國家受制于較低的評級,在國際市場融資成本居高不下,而美國的三大評級機構通過主導評級標準,牢牢控制了世界各國在國家融資市場的定價權。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主要為公路、鐵路、港口等大型項目,建設周期往往跨越10-30年,注定了項目在建設周期內,需要不斷從國際市場籌集資金,而國家信用評級偏低無疑將加大項目各國的籌資成本,給各國政府和參與PPP項目的企業造成沉重的財務壓力,從而阻礙項目的順利建成。
國家評級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本國政府和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籌資成本,以債券為例,通常情況下,債券的信用評級往往決定了其流通利率,不同的評級決定了其不同的流利差。一般而言,BBB債券與AAA級債券之間的利差一般在1%以內。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同等級債券之間的利差也日趨擴大,直至超過2%。AAA級債券與AA級債券的利差到0.4%(通常情況下僅為0.1%~0.2%),AA級債券與A級債券的利差相差0.7%(通常為0.1%~0.2%),A級債券與BBB級債券之間的利差擴大到0.6%~1.0%(通常為0.3%)。因而,即便是同一等級的債券,利率水平的波動范圍也在不斷擴大。而隨著利差的擴大以及利率的提高,由評級機構給出的等級也被劃分的越來越細。與此同時,利率浮動過大使得企業的償債能力在短期內會發生很大波動,這就要求評級機構必須快速適應這些變化,適時調整等級評定,這不僅使得等級劃分更細,而且也使信息公布更為頻繁。由此可見,評級公司的評級基本上完全主導了相關國家政府和企業的融資能力和融資成本,評級公司成為了資本市場上真正的定價者。對于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企業而言,國家評級公司基本把持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融資定價權。
從長遠來看,要想解決東盟國家評級普遍偏低的問題,需要探討建立由亞洲國家主導的評級機構,可以考慮由亞洲國家政府共同出資成立一個中立的第三方評級機構,建立亞洲評級體系,破除美國評級機構壟斷局面,改變美國評級機構長期帶有一定偏見的評級標準和評級結果,奪回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亞洲國家的評級定價權,增強東盟國家國際市場融資能力。
5.2開辟多元化融資渠道
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中,作為PPP項目的各方都無法回避高額的籌資成本難題,尤其是東盟國家政府和企業。為此,在PPP項目模式中,各參與方可以考慮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跨國金融機構申請部分低息貸款。
5.2.1世行貸款介紹:世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貸款包括低息貸款和無息貸款,此外還向低收入國家提供贈款,用于推動包括農業以及環境、公共管理、教育、基礎設施、自然資源管理投資、衛生、金融和私營部門的發展。
5.2.2亞行貸款介紹
亞行的業務范圍包括技術援助、股本投資、貸款、聯合融資和擔保。亞行資金支持的主要領域有農業、交通運輸業(包括公路和鐵路、機場、港口等)、以農業為依托的工業(包括一般性農業、灌溉、森林、漁業和牲畜業和農村發展)、電力(發電、輸電、配電)、給排水和衛生發展、城市發展、能源(油、汽、煤)、通訊、健康和人口,以及金融業,旨在促進發展中成員國的銀行體制、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的管理、改革和開放。
亞行所發放的貸款按條件劃分,包括硬貸款、軟貸款以及贈款三類。由各國政府、財政部或央行“統貸”,再層層轉貸至各類政府融資平臺。其中,硬貸款期限多為10-15年(含5年寬限期),定價在6MLibor+40BP至6MLibor+60BP之間。硬貸款包含技援貸款、項目貸款、行業貸款、計劃貸款等,其中技援貸款額度較小,一般不超過2000萬美元;行業貸款政策性較強;計劃貸款等同于政策性貸款,用于支持一國財政收入;軟貸款指亞行的優惠貸款,此類貸款僅提供給人均GNI低于670美元(按1983年美元計價),且還款能力有限的會員國或地區成員,貸款期限通常為30-40年(含10年寬限期),無利息,而且每年只收取貸款總金額的1%作為承諾費。亞行的贈款屬技術援助范疇,資金由技援特別基金提供,贈款額沒有特別限制。
聯合融資和擔保:亞洲開發銀行不僅為成員國的發展提供建設資金,同時還吸引商業金融機構、多雙邊金融機構參與融資。亞行還向其它參與亞行貸款項目的機構所提供的貸款提供擔保。亞行提供的擔保服務可以為項目增信,這樣有利于降低借款國的融資成本。1989年,亞行開始做第一筆擔保業務。通常情況下,亞行會向其提供擔保的項目收取一定的費用,但數額不大。
5.2.3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貸款介紹
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在先后出訪東南亞時提出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倡議,得到多國響應。2014年10月24日,中國、新加坡、印度等21個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投行。目前,各國正在就亞投行章程等進行談判,爭取2015年底正式成立亞投行。根據設想,亞投行是一個基于政府間協定的亞洲區域內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將按照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的模式和原則來經營管理。亞投行的宗旨是為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以及其它生產性領域投資提供高效、專業的平臺服務。如果未來條件具備,亞投行也將探索適當開展區域外業務。截至2015年3月底,亞投行的意向成員國已達42個,目前各國正在開展機構成立前的各項談判工作,亞投行有望于2015年底前正式成立。
亞投行作為以中國為主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將改變和完善現有美日主導的以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為主體的亞洲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體系,更好地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向對我有利、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方向發展。
除上述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可以提供較低成本的資金支持外,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均可以提供大額、長期貸款,且貸款利率相對較為優惠,既可以解決公路、鐵路、港口等大型項目巨額投資所需資金,還可以讓PPP項目各參與方以較低的成本獲取大額資金。此外,通過組建國際銀團的模式,還可以吸納其它商業銀行參與國際項目融資。
此外,東盟各國政府和參與PPP項目的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特別項目債券來籌集項目投資所需資金,上市企業還可以通過增發股票來為項目建設募集資金。
5.3探討由亞洲國家出資成立跨國政策性保險機構
目前,除世界銀行的多邊擔保機構(MIGA)為國際銀行貸款提供擔保外,中國企業在高風險國家對外投資及開展工程承包,貸款銀行往往要求項目借款人為項目貸款購買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以下簡稱中信保)的政治險和商業險,或者是申請海外投資險。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國家風險較高,項目風險也較高,所以,以PPP模式建設這些項目,為確保風險隔離,保障投資企業的利益,無疑也需要為這些項目的貸款購買政治險和商業險。
當前,面對如此龐大的項目貸款,受限于國家承保限額,其需要投保的金額已遠遠超出中信保的承保范疇,需要尋找其它第三方政策性保險機構來承擔此類投資的保險。此外,目前的運行模式中,國內的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往往由中信保承保,銀行將風險轉嫁于中信保,中信保則以境外的項目資產為抵押物,并為項目貸款風險兜底,實際上這種模式中并未真正實現風險的完全轉移,本質上只是國內的金融機構將風險轉嫁于中信保。同時,受制于境外抵押物處置可能存在的種種障礙,實際上風險被轉移到了國內。對國家而言,這種中信保承保,國內銀行放貸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需要考慮成立一家跨國政策性保險公司來承擔部分保險責任。可以考慮參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組建模式和中信保運作模式,由亞洲國家共同出資成立一家專門支持亞洲國家基礎設施貸款的政策性信用保險機構,為亞洲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貸款提供信用保險,化解由于國家風險較高影響項目融資難題,增強國家風險較高國家的融資能力。如果能成立這樣一家跨國的政策性信用保險機構,無疑可以大大增加東盟國家的融資能力,并通過保險增信,降低融資成本。
6.總結
綜上,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投融資所需資金可以在PPP模式下,通過東盟國家政府出資、引入社會資本,以及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申請貸款等方式解決。可以考慮由亞洲國家政府共同出資成立一個中立的第三方評級機構,建立亞洲評級體系,破除美國評級機構壟斷局面,奪回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亞洲國家的評級定價權,增強東盟國家國際市場融資能力。此外,還可以考慮由亞洲國家共同出資成立一家專門支持亞洲國國家基礎設施貸款的政策性信用保險機構,為亞洲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貸款提供信用保險,分散PPP模式下各參與方的投資風險。
[1]許寧寧.解讀“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J].華人世界,2011(07).
[2]楊惠旭著.金融學原理[M].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3]王灝.PPP的定義和分類研究[J].都市快軌交通,2004
[4]楊璐.基于實物期權的PPP項目投資決策研究[D].浙江大學,2008.
(責任編輯 劉祖鑫)
An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trategies of the China-ASEAN Infrastructure PPP Project
XU Zengxing
(ChinaDevelopmentBank,Beijing, 100084)
Funds needed for the China-ASEAN infrastructure can be raised, under the PPP mode, through three ways: 1) investment from the Chinese and the ASEAN governemtns; 2) social investment; and 3) loans from the World Bank,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t is desirable that an independent third-party rating agency be founded on joint funds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the Asian countries, whose function is to give the ASEAN countries trustworthy credit ratings. This way, the financing capability of the ASEAN countries can be improved. In addition, an insurance institution can be established exclusively for the purpose of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loans to the Asian countries. This institution can be jointly financed by the Asian countries to provide credit insurance to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f the Asian countries. Thi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ilute risks of the participants under the PPP mode.
China-ASEAN,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working, PPP mod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2015 - 03 - 15
徐曾興(1984—),男,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學。
F832.48
A
1671 - 7406(2015)06 - 0069 -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