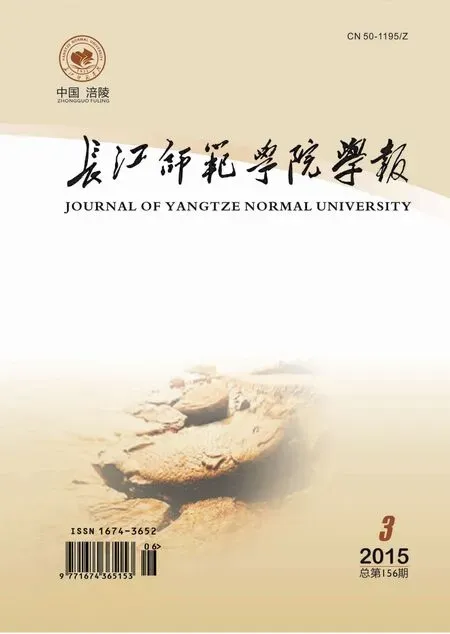國內宇文所安文學思想研究述評
李芳
國內宇文所安文學思想研究述評
李芳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70039)
北美漢學家宇文所安用他詩性的語言和西方的視野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審視中國古典詩歌及文化,先后創作了《初唐詩》《盛唐詩》《追憶》《迷樓》《他山的石頭記》和《中國文論》等一系列解讀中國古典文學的作品,對中國古代文化權力運作模式和傳統知識分子心態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比較文學的視野和可能性。他對潛藏在文學背后更隱秘和更深層的內涵有極高的敏感度,所以能還原中國古典詩歌的最初狀態,挖掘出文字深層的意蘊和話語參照。國內外很多學者都意識到了他“文本細讀”方法的運用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語境還原,所以研究他的著作也不斷出現。這里試圖從四個方面總結國內學者對宇文所安文學思想的研究現狀。
宇文所安;文學史觀念;文本細讀;非虛構傳統;翻譯
一、引言
對于一個不是在中國語境中成長的西方人來說,要還原中國古典詩歌及文化的生成語境是非常困難的,他們之間始終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由于無法脫離自身文化母題的范圍限制,就不能真正深入理解中國文學產生的背景和動機,但宇文所安天生與唐詩有一種不解的緣分,感性體驗和理性思維并重的話語思維模式使他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發現我們常人容易忽略的東西,而他對詩歌的天才感悟力,對紛繁歷史表象下內在結構敏銳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也使他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也間接影響了中西方的很多學者[1]。
最早認識到宇文研究中國詩歌新思路和新視角的當屬李珍華和王麗娜,他們分別從宇文的文學史觀念和對唐詩的翻譯入手,肯定了宇文在審視中國古典詩歌時所采取的路徑以及帶給我們的啟發。兩年后,賈晉華撰文《〈初唐詩〉評介》表示對宇文著作翻譯和引入的贊賞和支持。10年后,文敏在《不同文化的眼睛》中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歐文在所著《追憶》一書中,評介了李清照《金石錄后序》,歐文的眼睛就在李趙夫婦‘美滿生活’中發現了瑕疵。”[2]第一次發現漢學家對待中國古典文學的不同眼光。次年,何向陽撰文《重現的時光——讀斯蒂芬·歐文〈追憶〉》,驚異于西方學者新穎的視角和文化眼光。“在這部中譯本不足170頁的著作中,輕擦去蒙在石碑和箭鏃、時間和往昔之上的積塵,借了典籍、碎片和記憶,在文明延續與文化傳遞過程里,講述他所承認的‘永遠不能完整’的‘有生命’的過去。時間在兩岸呈現出奇異的光芒,其見識的銳敏、深邃,仿佛是引我們溯流而上的水。”[3]從而對《追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數年后,莫礪鋒和劉健明相繼發表書評,既承認宇文為我國古典詩歌研究所做出的貢獻,同時也指出宇文所存在的誤讀和附會,在批判中接受和吸收。自從1983年宇文的著作首次引入中國,學者們對其思想的解讀和審視就從來沒有停止。相比較而言,西方學者主要關注于宇文英譯唐詩以及對中國文論翻譯的研究,而國內學者則對宇文研究中國唐詩以及古代文學的思路和視角比較感興趣,而且由其“文本細讀”方法的運用歸納出中國古典文學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非虛構傳統”特色。多年來,國內外學者在這條路上發現了不同尋常的美。
二、文學史觀與唐詩研究
不同于以往程式化的文學史敘述,宇文以一種宏大的視野拋開現有的文學史話語模式,放棄詩歌全景式的直觀描述,也不同于詩歌史只是由一部分重大詩人寫成這一傳統認知,他將眼光放在我們常常忽略的地方,試圖找出隱藏在詩歌背后最真實、最原始的東西,重新激活文本內在的理路和思維,回到詩歌本身。他的唐詩史系列作品不僅回答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問題,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思考。
傅璇琮在《初唐詩·序》中評價說:“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這本《初唐詩》,在中國學者之先對初唐詩歌做了整體的研究,并且從唐詩產生、發育的自身環境來理解初唐詩特有的成就,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時期西方學者的學風,而且較中國學者早幾年進行了初唐詩演進規律的研求……宇文先生的貢獻還是應該受到中國同行的贊許的。”[4]4
宇文在《初唐詩》中說:“我撰寫這本書的初衷是為盛唐詩的研究鋪設背景,但是我卻發現,初唐詩比絕大多數詩歌都更適合于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研究。”[4]6由初唐到盛唐,再到中唐和晚唐,是他文學史觀念的系列體現。而首次系統地研究宇文文學史研究法的是陳引弛,他稱宇文有一種“史的觀念”,“這種史的意識,是整個對初唐詩新看法的基礎。并且這種史的觀念如前已指出的更重于以未來回顧過去,以流反溯其源。它與當代闡釋學思想暗合,與過去單面的由源至流,由過去到未來的思路有著不小的內在分歧。”[5]宇文有一種清醒的文學史意識,他在解答關于初唐的問題時也找到了研究盛唐詩的理路并發現了它們之間內在的聯系。初唐有文學團體,盛唐時期依然有,而依照此想法,宇文還將盛唐詩分成了“京城詩”和“非京城詩”兩大類,從而找到了一種文學史發展和演變的線索。
蔣才姣在《對盛唐詩歌的重新解讀——讀宇文所安的〈盛唐詩〉》中從三個方面分析了宇文在《盛唐詩》中所透露出來的文學史觀念:對唐代八世紀文學史的重寫、對盛唐詩人的重新評價和文本的重新解讀,從而對宇文研究盛唐詩的方法有了全面的理解和認識。王黎黎在其碩士論文中說:“宇文所安十分注重詩歌流變史的重新建構,著重評述不同時期唐詩發展演變的過程和前后因承關系。他將文學史視為一個過程,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匯集了各種已經發生的事實和尚未發生的可能,它是動態的,而非靜止不動的,只有流變史才是歷史的真面目。”[6]又從盛唐“京城詩”創作主體、創作內容和它與中國古代都市文學的關系三個方面闡述了宇文盛唐詩歌研究的方法。徐志嘯則在《文學史及宮廷詩、京城詩——宇文所安唐詩研究論析》中說:“作者盡可能地將文學史的發展線索在闡述詩人和詩歌作品中予以融合,特別是沒有孤立地就詩論詩、就人論人,而是努力做到了縱向詩歌發展的前后聯系關照和橫向作品的風格特點比較,這是很不容易的。”[7]韓軍從語言的角度發現宇文在書寫中國古代文學史時對內部“語言”模式的運用和突破。
宇文又將這種詩歌史意識和歷史觀貫穿于其整個唐詩史系列。成瑋專門研究宇文在其《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所體現出來的“自我”意識,中唐之不同于其他時代的突出特點在于此時期的詩人們在努力建構一種獨特的生存空間和話語體系,“宇文教授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從這種抗衡中,偏又觀察到了潛藏著的共謀關系:沒有他者也就沒有自我,自我與他者既界限分明又相需相濟……天才靈感式的寫作讓位給反思式的寫作,造成了中唐寫作觀的新變。”[8]趙瓊瓊則專門對比川合康三和宇文對中國中世紀的認識,以便理清宇文之所以如此重視所謂的“中唐”并積極探索其轉折意義思路。楊春旭則以“晚唐詩”為切入點,探索宇文在研究中國古典詩歌時所采取的斷片式分析策略。
早在2005年蔣寅就清醒地認識到了宇文研究唐詩的獨特視角而不禁發出這樣的提問: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寫唐詩史?[9]67-73楊智則從宇文的文學史觀中提煉出了文學史寫作的四個“不等號”,他說:“好的文學史應該是一種生命的過程,是人類文學智慧的動態敘述,而不僅僅記錄文學的知識,我們期望的文學史應該是融文學的靈動與優美、哲學的思辨與智慧、歷史的邏輯與使命為一體的文學史”,并認為在“重寫文學史”口號依然響亮的今天,這種新的思維方式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啟示[10]。2010年,王瑛在《歷史意識與文學史寫作——論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針對宇文的歷史研究法和文學史寫作中的歷史觀說:“文學、歷史及對前二者的闡釋,共同構建了文學史研究的顯性在場……歷史意識在更深的層次上影響了宇文所安的問題意識和方法論。”[11]他認為宇文為我們的文學史研究提供了映照,歷史意識的建構,也許是我們的文學史研究的入口和出口。宇文放棄了全景式的詩歌史視野,從而激活了單個的文學作品,重建了一種新的敘事方法。殷曉燕從宇文對懷古詩的研究發現了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互文性”的運用[12]。李佳和曲景毅也高度評價了宇文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所體現出來的文學史觀念和意識。2012年,劉璐的《宇文所安的唐詩史書寫方式研究》也從解構傳統文學史、建構唐詩史寫作邏輯和重寫唐詩史的實踐三個部分解讀了宇文唐代詩歌史寫作的方法。史冬冬則發現宇文在書寫唐詩史過程中的“破執”觀念,他認為宇文的研究法“從文學史的中觀層面,打破唐詩史的傳統敘事和歷史觀念,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范疇,如初唐的‘宮廷詩’‘對立詩論’,盛唐的‘京城詩’等,以這些普遍性的范疇貫穿唐詩史的寫作。”[13]南京大學葛紅之《多維視角的語篇分析——現代語言學視域的宇文所安唐詩史研究》更是從語言學角度,總結了宇文對隱喻、互文、詩史互證等方法的運用。宇文異域的獨特視角和對傳統文學史寫作的大膽解構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寫作范式,他對當下語境的合理想象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三、比較詩學與跨語境文論研究
除關注宇文新的文學史寫法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大膽重構外,中國學者還注意到了宇文在解讀中國文學時所運用的比較詩學研究法。他的《追憶》《迷樓》《他山的石頭記》以及《中國文論》中評論的部分都是這種比較詩學方法論的體現,他不斷發掘文本中的斷片式美學形態,用殘存的碎片整理并重構出全新的整體,從而得出中國文學“非虛構傳統”的結論。
王曉路撰文《西方漢學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述評》,總結西方學者認知中國文論的新思維和新視角,在談到宇文的比較詩學研究法時,他說:“這些內化于一種文本的基本規則以及假定是某一種傳統不斷積累而形成的,它涉及到經典的作用、文化審美的變遷以及人文傳統的慣性”“從這一角度對中西文本的解讀方式加以審視”,就可以發現中西之間的差異。但他認為虛構與非虛構的差異被宇文過分強調了,我們必須認識到,“對于異于自身傳統的不同文本的解讀,絕不可停留在其表層結構之上,而須意識到其表述方式背后所支撐的完全不同的文化架構、文學及文論傳統”“在進行文本解讀時必須注意到文本的語境和史境以及話語生成模式的內在范疇,即不能完全受制于任何現成的概念立場,而須在實際的閱讀體驗中形成構成性理解。”[14]可謂客觀合理地評述了宇文的比較詩學研究法。
2003年,胡曉明在其《遠行回家的中國經典》中說宇文的《中國文論》是“繼理雅各、華滋生、康達維之后,中國經典又一次規模盛大的西方旅行。”[15]同年,《社會科學報》也登了一篇名為《美國漢學:英譯文論“返銷”中國》的文章,來自不同高校的學者紛紛承認并贊賞宇文全新的研究視角和思路[16],給中國學界帶來了極大的轟動。
陳引弛認為宇文在《中國文論》中體現出的觀念以及因而產生的關注文本本身活動的姿態背后,蘊含著現代西方從“新批評”直至“解構主義”都一直持有的聚焦于文學文本的基本理論取向,而這一姿態不能僅僅理解為西方理論立場的產物,而是宇文對中西文學比較后所獲理論視野的結果。“一部以文本為中心構成的著作,最后可以導向與物質文化和社會史的聯通,這可謂是過去百年文學理論在‘文本’和‘歷史’的不同側重之間辯證、綜合過程的投影。緊扣文本,向歷史敞開,文學、思想與文化史、社會交光互影,相互映照”,而這一文本意識必定會對中國學者帶來啟發[17]。程亞林從中西差異入手,認識到宇文在把握中國文論時所采取的不同方法,“西方讀者雖然承認詩歌基于詩人經驗,但更尊重詩人加工改造經驗的權利,所以詩歌文本被視為一種虛構,其含義總是被理解為隱喻性的而不是史實性的。中國讀者則特別強調經驗對詩歌創作的重要性,認為詩歌必然描寫了詩人特定時空中的遭遇和心境,絕非虛構。”所以宇文也更重視作為獨立客體存在的詩歌文本的文學意蘊和內在結構,“探尋詩人認知自我的特征。”[18]黎亮則首先認識到宇文在《中國文論》中幾個關鍵術語的把握問題,接著又去探尋這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所激發的新質和超越審美的現代意義。浙江大學陳小亮也注意到了宇文對中國古典文學非虛構傳統或者情境化歷程的設想,也承認宇文在其中無法避免的文化誤讀。
趙雪梅從“偏離道家‘自然觀’、誤讀‘自然文論’和曲解‘自然’文學”三個方面闡釋了宇文對中國文論的誤讀。史冬冬則認為這一構想主要是對中國古典文學中詩歌閱讀傳統的片面性描述,它概括了古人對詩歌意義的一種理解方式和傾向。盡管不能代表對中國古代文學閱讀傳統特點與模式的整體論斷,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模式,以中西方的雙重視野,對詩歌文本進行細致的分析解讀,從中提取出諸多可供參考的抽象命題,在中西碰撞的文化語境下開辟了中國文論向現代轉型并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新途徑。沈一帆著眼于中西方對真理追求和認知的不同,得出宇文“非虛構傳統”實際上是西方傳統中一個老問題的新版本的結論,并認為要理解宇文詩學建構的實際貢獻,還要在西方漢學論述的歷史參照中尋找答案。
張萬民以比較的眼光發現了葉維廉和宇文對中國古典詩歌認識的不同,“葉維廉認為中國詩完全達到了‘無我’和‘以物觀物’的境界,宇文所安則認為中國詩記錄了詩人真實情感和真實經驗。他們一個看到的是詩中無我,一個看到的是詩中全是真實的自我。然后,他們根據自己看到的圖像拼出中國詩學的全景。”[19]沿著他的思路思考,無疑會發現兩個異域學者對待中國詩歌竟然是兩個完全相反的結論,但如果仔細推敲,會發現他們二者立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不同的,所以結論不同就不那么稀奇了。盧永和也說:“作為中西詩學最原初的理論預設,‘詩言志’與‘A poem is something made’這兩個定義的比較,寓示了中西詩學傳統在理論原點上的差異。中西詩學分別從自己的理論原點出發,沿著不同的軌轍,在文學本體規定、作者與文本之關系、批評闡釋等基礎文學觀念層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圓融自足的理論體系。循此思路展開辨析,能夠從理論源頭上梳理中西詩學之間的根本歧異。”[20]
汕頭大學倪書華說《中國文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跨文化對話的平臺,為我們打造了一條可以突破中西文論體系、在互動中通過雙向闡發而產生新思想、新建構的門徑。而張衛東則認為宇文已經由中國文論建構了一種漢語詩學的書寫體系。李清良也說,宇文從中西文化的真理觀和語言觀出發,深入考察了中西闡釋學的最初關注點和核心假定,并據此辨析了中西闡釋傳統關于作者—文本—讀者之間關系的基本觀念,值得中國學者思考和借鑒。王曉路也認為宇文這種解讀和闡釋體現了他尊重不同文化傳統本身的態度以及尊重文學研究獨有的生命體驗與理性思維并重的話語思維模式,代表了中國文學研究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宇文突破了差異話語表述的艱難和文化互釋的困境,為中國文論研究找到了新的思路。張燕從儒家和道家的角度發現中國傳統詩藝中的爭論,并認為宇文的視角給我們帶來了這樣的啟示:只有透過價值爭議語境中的詩藝存在這一維度,才能真正看清中國詩論傳統,認識到詩論的“理論性”從何而來,歸宿何在。王瑛也肯定宇文這種比較文學的視野和探究方法,雖然宇文的漢學研究不可避免地帶上西方文化傳統的視角,但他者的眼光往往能夠發現一個文化傳統之內的研究者所不能發現的意外驚喜,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就是在這種自我與他者的雙重視野下洞見的。最難能可貴的是宇文不僅認識到了這一點,還努力消除東西之間的話語背景差異。郭西安則認為宇文的研究思路調和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張力問題,也解決了歷史連續性與斷裂性的對抗問題,但他所挖掘出的隱匿在一般訴說背后的焦慮所指向的時代和詩學自身的問題,很難說是對“歷史實況”的絕對還原,而只能是另一種類型的“后設關照”,所以我們在接受海外漢學家所帶給我們的啟示的同時,也要警惕其背后值得尋味的困境。
2013年,《社會觀察》刊登了一篇樂黛云的文章,高度評價了宇文在講述中國文論時所采取的形式,即原文、譯文再加注釋的形式,這就“真正做到了從文本出發,改變了過去從文本‘抽取’觀念以至排除大量與‘觀念’不完全吻合的極其生動豐富的文學現實的錯漏,并使產生文本的語境、長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內容,甚至作者試圖彌縫的某些裂隙都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21]
四、文本分析方法論
第一次提出宇文深受西方新批評研究法影響的當屬程鐵妞,她認為由于宇文處于異于中國的西方文化傳承的背景,當他“遭遇”完全陌生的中國文學文本時,其諳熟的西方文化背景與陌生的中國文化之間便發生了劇烈的“碰撞”和“震蕩”,吸引與排斥的張力使他在對文本意義的“理解”和“詮釋”中不自覺地會運用其西學積累[22]。陳小亮曾對此評價說:程文第一次揭示宇文所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新批評方法的應用……這一批評特色在強調西方讀者出于自身文化背景“讀”的自由于中國文學傳統考據式閱讀之間,詩話的隨意性與西方文化主流的精心構筑之間構成多重張力,并最終在兩種文化碰撞中向其主體文化偏斜[23]。
張志國認為對于“文學傳統與個人才能”二者之間互動關系的描述與辨析,構成了宇文所安詩歌史敘述架構的主導邏輯,“文本家族”觀念與“對比閱讀”“文本細讀”方法的運用進而充盈了其詩歌史的“文本”肌理,所以在宇文獨具魅力的敘述結構與敘述方式背后,隱含著“新批評”的內部文學史觀。也看到了宇文對西方“新批評”方法的沿襲和運用。計美麗在其碩士論文中總結宇文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對“舉隅法”的運用,并認為“舉隅法”是對中國傳統文學中詩歌創作和閱讀習慣的描述,舉隅是通過想象、借代等表現手法,建立人與自然的多重聯系過程,宇文正是以他者的視角摒棄傳統的“先見”,用文本細讀的方法挖掘出潛藏在文本背后的一系列秘密。鄒廣勝同樣看到了宇文所獨具的后現代語境,并認為他的文章典型地體現了新批評的基本風格,通過文本細讀解構傳統觀念,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邱曉和李浩具體而細微地闡述了宇文“新批評”文學理論在其唐詩研究過程中的不斷運用,并認為這一方法不僅體現在他對中國古典詩歌史的重新建構上,還在于他對唐詩進行的語義學分析上,具體表現為他以文本細讀方式對唐詩展開的復義語言研究、反諷詩學解讀和“三部式”結構分析。作者在文中指出,盡管宇文的理論視野宏闊復雜,但西方現代形式主義文論對他的影響異常明顯,尤以“新批評”理論的影響最為突出。宇文善于發現邊緣化的個人書寫和文本內部的“自足”,不得不說這與其西學淵源有密切關系。谷鵬飛則不同意這種看法,他以宇文對《文心雕龍》的研究為例,證明這種方法論當屬于文學解釋學而非新批評,新批評只是一種工具和手段,解釋學才是最終方法論,正是運用這種解釋學的方法,才使得《文心雕龍》在一種效果歷史的辯證結構中走上了再經典化的道路,從而為探索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理論提供了可能。這種論證從不同角度考察都各有其意義,宇文在對中國古代詩歌進行解讀時確實運用了文本細讀的方法,而他對中國文論的概述又可以歸屬于闡釋學領域。
宇文自己也曾說過:“偏愛文本細讀,是對我選擇的這一特殊的人文學科的職業好不羞愧地表示敬意。”[24]因此他在具體審視中國傳統文本所帶給他的沖擊和震顫時,總是能在細微處窺探到廣闊的空間,這種微觀的視角使他不僅關注“語言”和“文字”,也關注單個自足的“人”,所以能不斷給我們帶來啟發。韓振華在《從詩意漢字到語體詩學——西方漢學家眼中的漢語詩學》中說:“借助精彩的文本細讀,宇文所安幫我們恢復了對于漢語文本語義的感覺。”[25]宇文所做的努力是解構的,但卻不是破壞的,反而為我們重構了許多新的設想。對宇文研究較多的殷曉燕從三個方面剖析宇文在解讀李清照婚姻關系時所用的文本細讀方法:從“細讀”中看出婚姻的變質、從“人稱代詞”的轉換看出夫妻關系的裂痕、從“重點字詞”推敲出李、趙婚姻的暗潮洶涌,可謂具體而細致地為我們展現了宇文究竟是如何運用西方“新批評”方法的。
作為一個域外讀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必然存在著誤讀和過度闡釋的可能,但他敢于拋卻既有的想法,打破傳統思維的禁錮,用文本細讀的方法挖掘文字背后的東西,從而為我們重新認識中國古典文學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國學者雖然認識到了這一點,但還未能用宇文這種微觀的視角去發現文本內部的自足和張力。
五、翻譯與譯介法
宇文對中國文學的嘗試首先在唐詩方面,他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種獨特文學史觀,又通過對中國文論的解讀、用比較詩學的眼光發現了中國文學的“非虛構”傳統,國外學者較多地關注宇文在英譯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以及所帶來的啟發,中國學者則較少涉及宇文在翻譯領域所做出的貢獻。
在國內,主要有孔慧怡、蔣暉等涉及到宇文的譯介工作,孔慧怡認為宇文利用文學選集來投射一個強烈的影像,一個古典文學傳統的特色視野和宏觀范疇,從而建構他心目中的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宇文所安投射出來的文學視野,一方面代表濃厚的個人觀感,另一方面卻也把古典文學傳統包覽無遺。”[26]111-127對宇文的唐詩譯介工作評介頗高。2005年,席珍彥在其碩士論文中對宇文的學術生涯以及翻譯思想和理論做了簡單的介紹,并對其語言特色進行總結,肯定其對傳播中國文化所做出的貢獻。蔣暉則認為宇文行文的整個框架和文本的選擇以及注釋都別具一格,盡可能地接近中國文論的原貌,對東西方都有極大的啟示。朱易安和馬偉主要考察宇文對唐詩意象、節奏和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探尋其翻譯手法的特點,認為宇文對西方讀者展現了中國文學史的概貌,并立足于文化交流,以文化媒介者的姿態成為中國文學傳統在異域的代言人。鄧國軍則持不同看法,他的著眼點主要在宇文對中國唐詩及古典文化的誤譯現象,并認為宇文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范疇還缺乏哲學背景的考慮,對抽象范疇的翻譯存在“硬譯”現象。最近,西南大學王震在其畢業論文中梳理了宇文的中國文學思想,考察了它在中國流傳的土壤和路徑,并客觀地評價其功與過。
六、結語
國內學者對宇文的接受和質疑也是對整個海外漢學家態度的縮影,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在引進與吸收的道路上是如何前行的。作為對中國古典詩歌以及文化研究最出色的海外漢學家之一,宇文在很早以前就已影響了中國的諸多學者。1996年,由樂黛云主編的《北美中國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就選取了宇文的3篇文章,由此打開了宇文思想真正進入中國的序幕。2008年,王曉路主編的《北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思想研究》介紹宇文中國文學思想研究的篇幅達到100頁。而徐志嘯所著的《北美學者中國古代詩學研究》對宇文的研究和論述也占據了3個章節。在接受與批判的過程中,國內學者顯示了敏銳的學理視角與理性批判精神,在近20年的宇文氏思想研究當中,大陸學界已經占據了無可替代的位置。
就宇文氏文學思想的回應情況來看,其唐詩研究與文學史研究中的問題意識無疑是回應面最廣、研究最深入的一個方面。文學史書寫需要直面歷史真實性問題、斷代文學史合理性問題以及迭代話語記憶的相互傾軋,已經成為了古典文學學界的學科共識。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就唐詩抑或文學史研究而言,宇文氏所提供的研究路徑以及相關回應尚有廣闊的發展空間。眾所周知,宇文氏中國文學史思想以問題意識以及對傳統固化觀念的重新思考為出發點。這也是大陸古典文學界探討其思想的重中之重,但是對其思考意識的過分關注卻往往帶來了對具體問題的忽視。宇文所安文學史思想非止于思路本身,而是由具體化、碎片化的待研發課題所組成。在文學史個案研究上,針對宇文氏思想的進一步闡發尚鮮有成果。學界目前將宇文氏的基本定位依舊是理論家與文學研究者,其歷史學方法引入文學史的研究范式所受關注還并不充足。乃至于宇文所安將文學與歷史、思想、環境、心理、生態等學科所進行的交匯,都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而就其比較詩學思想而言,目前學界較突出的呈現兩種不足之處。一種觀點從西學背景入手,以藝術本體化理論討論宇文所安提出的“非虛構傳統”,斷定其體系本質來自于“人本”說,這種做法將西方藝術理論命題套入宇文氏所做的具體分析與文學史書寫當中,割裂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特殊性或者說異質性。而另一種觀點則忽略了宇文氏的西學背景以及厄爾·邁納的比較詩學研究譜系,僅突出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單方面因素。這兩種研究視角都片面化突出了宇文氏的理論方法或研究對象。并未對其比較詩學思想體系——尤其是建立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這一特殊界定——作出充足的整體回應。換言之,宇文所安的比較詩學思想研究,應當建立在對比較詩學學科背景及其自身研究特殊性的尊重與了解的基礎上才能更加恰當的展開,這也是目前對宇文氏專題性研究的迫切要求之一。
作為宇文所安帶給所有文本類研究的特殊禮物,舉隅法是其學術思想當中性質特殊、地位獨特的一環。宇文氏第一次來華進行宣講的,也正是其舉隅法研究范式。目前,對這種研究方法的梳理與應用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展開,但其問題也同樣存在。在一般意義上,我們將宇文所安的研究方法論作為新批評主義文本細讀方法的衍生體。但是在這樣的西方理論學派譜系下,往往會漠視掉宇文所安對其他理論方法的接納與吸收、因研究對象特殊化而做的理論調整,以及個人學術風格的特殊表現,導致在研究當中舉隅法等方法論往往會失其全貌。另一方面,作為西語背景的中國語言文學研究者,由于語言背景的差異以及學術方法的不準確適用,常常導致宇文氏對中國古典詩歌的過度闡釋以及錯誤解讀。對此批評由來已久,但對這些闡釋訛誤的梳理以及根源探索卻較少得到展開。事實上,理論在應用中的訛誤正是分析理論本身的有效途徑。
對于宇文氏翻譯的研究在國內尚在起步階段,目前關注點還主要集中在文本準確性以及術語翻譯上。而跨語系術語比照、傳統文論譯介背后的語法規則,以及文論翻譯與文學作品翻譯的差異性等問題,受到的關注還十分有限。換言之,對宇文氏翻譯體系的研究,還亟待上升到理論高度與比較詩學整體視野當中進行討論。
整體而言,宇文所安文學思想在大陸的研究與探討,主要受到來自學科分化體制的壓力與限制。不同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并且學術關注點也不盡相同的研究者往往會攫取宇文氏研究中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而這無疑是對宇文氏思想的割裂與片面化。跨越東西文化不同語境,不同學科的整體研究當然需要很強的把握能力與學術視野,但在宇文氏思想已經得到充分傳播與討論的今天,更進一步的研究必然會要求更加深入、全面、跨學科的學術思考。母庸置疑,宇文所安文學思想在近20年間的傳播發展,已經切實改變了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現狀與看法。在我們感慨取得驕傲成績的同時,也期待著更深刻的改變發生。
[1]王曉路,史冬冬.西方漢學語境中的中國文學闡釋與話語模式[J].中外文化與文論,2008(15):56-70.
[2]文敏.不同文化的眼睛[J].讀書雜志,1993(7):153.
[3]何向陽.重現的時光[J].讀書雜志,1994(10):88-90.
[4]宇文所安.初唐詩[M].賈晉華,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5]陳引弛.詩史的構筑與方法論的自覺——宇文所安唐詩研究的啟示[J].中國比較文學,1996(1):112-123.
[6]王黎黎.宇文所安盛唐“京城詩”研究之研究[D].北京語言大學,2009.
[7]徐志嘯.文學史及宮廷詩、京城詩——宇文所安唐詩研究論析[J].中國文化研究,2009(1):202-209.
[8]成緯.推敲“自我”——讀宇文所安《中國“中世紀”的終結》[J].中外自學指導,2007(3):50-53.
[9]蔣寅.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寫唐詩史[J].讀書雜志,2005(4):67-73.
[10]楊智.文學史寫作的四個“不等號”——淺談宇文所安的《瓠落的文學史》中的文學史觀[J].當代小說,2009(7):41-42.
[11]王瑛.歷史意識與文學史寫作——論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史研究[J].當代文壇,2010(4):19-23.
[12]殷曉燕.論漢學家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互文性”運用——以宇文所安對唐代懷古詩的研究為例[J].江西社會科學,2010(2):108-112.
[13]史冬冬.在傳統中破執——論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史觀[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3):116-119.
[14]王曉路.體系的差異——西方漢學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述評[J].文藝理論研究,2000(1):40-47.
[15]胡曉明.遠行回家的中國經典[N].文匯報,2003-04-03.
[16]美國漢學:英譯文論返銷中國[N].社會科學報,2003-04-03.
[17]陳引弛,趙穎之.與“觀念史”對峙:“思想文本的本來面目”——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評[J].社會科學,2003(4):120-124.
[18]程亞林.入而能出疑而求新——簡析宇文所安研究中國古詩的四篇論文[M]//國際漢學(第11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19]張萬民.辯者有不見:當葉維廉遭遇宇文所安[J].文藝理論研究,2009(4):57-63.
[20]盧永和.“詩言志”與“詩是某種制作”——析中西詩學理論原點之異[J].學術論壇,2009(1):133-137.
[21]樂黛云.突破中西文體系的“雙向闡發”——介紹《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J].社會觀察,2013(1):44-45.
[22]程鐵妞.試論斯蒂芬·歐文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M]//漢學研究(第一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6:227-260.
[23]陳小亮.論宇文所安的唐代詩歌史與詩學研究[D].浙江大學,2009.
[24]宇文所安.他山的石頭記[M].田曉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25]韓振華.從詩意漢字到語體詩學——西方漢學家眼中的漢語詩學[J].國際漢語教育,2009(2):69-74.
[26]孔慧怡.翻譯·文學·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黃志洪]
J206
A
1674-3652(2015)03-0091-07
2014-10-26
李芳,女,河南駐馬店人。主要從事魏晉及唐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