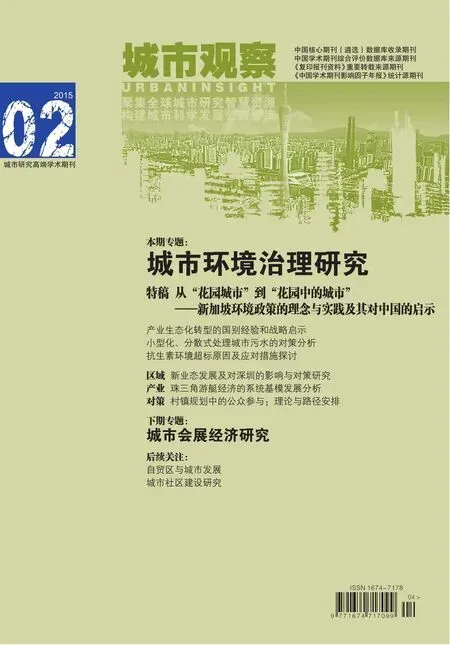從“花園城市”到“花園中的城市”——新加坡環(huán)境政策的理念與實(shí)踐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 王 君 劉 宏
新加坡2014年土地面積約718平方公里,總?cè)丝?50萬人,人口密度為7600人/平方公里。作為赤道熱帶城市島國,新加坡淡水、土地及各種自然資源匱乏,國家發(fā)展具有天然的局限。1965年獨(dú)立以來,新加坡政府一方面推動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①,從根本上改變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hù)二者競爭性目標(biāo)的關(guān)系,減輕人口和經(jīng)濟(jì)增長對自然生態(tài)的壓力;另一方面積極有效地推行城市綠化、美化計劃,將城市環(huán)境綠化和維護(hù)上升到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高度,并成為國家治理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實(shí)現(xiàn)了環(huán)境保護(hù)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雙重可持續(xù)性。
新加坡建國近五十年,實(shí)現(xiàn)了從起初貧窮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發(fā)展成如今的全球新興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和中心城市之一,以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綠色宜居吸引著全球人才、企業(yè)、商旅和投資,也為國民提供著優(yōu)良的生活品質(zhì)和美好的生活工作環(huán)境 (劉宏、王輝耀,2015)。新加坡城市國家的治理模式是學(xué)術(shù)界和政策制定者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之一,而本文所側(cè)重的城市環(huán)境綠化政策則是其實(shí)現(xiàn)“花園城市” (Garden City)和邁向“花園中的城市”(City in A Garden,CIAG)的起點(diǎn)和基礎(chǔ),是新加坡城市治理的重要戰(zhàn)略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紹新加坡從“花園城市”到邁向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花園中的城市”的政策演變,解析“花園中的城市”特點(diǎn)及其與“花園城市”的關(guān)聯(lián),隨后探討政府的綠化城市和提升環(huán)境品質(zhì)的理念、實(shí)施機(jī)制與具體個案,最后總結(jié)新加坡經(jīng)驗(yàn)對中國政府環(huán)境治理和建設(shè)的啟示。
一、新加坡城市環(huán)境:從“花園城市”(Garden City)到“花園中的城市”(City In A Garden)
“‘花園城市’新加坡”的稱謂于20世紀(jì)80年代聞名于世,這項(xiàng)成功起源于60年代獨(dú)立之初新加坡領(lǐng)導(dǎo)人李光耀的構(gòu)想。他提出把新加坡打造成具備“第一世界”城市標(biāo)準(zhǔn)的東南亞的綠洲,通過清潔、綠化的環(huán)境優(yōu)勢吸引世界投資和商旅,實(shí)現(xiàn)新加坡經(jīng)濟(jì)從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的跨越(Lee,2000)。隨著“花園城市”成為現(xiàn)實(shí),9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又提出了“花園中的城市”愿景,并且正在“花園城市”基礎(chǔ)上,注重生態(tài)自然的保護(hù)和連接城市環(huán)境的綠色空間、使其網(wǎng)絡(luò)化和系統(tǒng)化,邁向世界級“花園中的城市”。
(一)二十世紀(jì)六十至九十年代:建造“花園城市”
新加坡獨(dú)立后即進(jìn)入快速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政府著力發(fā)展經(jīng)濟(jì)、創(chuàng)造就業(yè)和實(shí)現(xiàn)“居者有其屋”,致力于改善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時,應(yīng)對人口增長和城市擴(kuò)張導(dǎo)致的自然生態(tài)收縮和退化,以及鋼筋水泥建筑和路橋設(shè)施林立的城市形貌,政府積極主動地調(diào)整價值取向,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展開城市環(huán)境的“綠化運(yùn)動”(Greening Movement)。1963年,總理李光耀發(fā)起了第一次植樹運(yùn)動,標(biāo)志著新加坡五十年來全民參與的綠化運(yùn)動的興起,此后,樹木和灌木被廣泛種植在路旁和道路隔離帶上,通過路面綠化奠定了新加坡“花園城市”的基礎(chǔ);1968年,政府在向公眾解讀“環(huán)境公共衛(wèi)生法案”時首次提出把新加坡轉(zhuǎn)變成清潔而蔥綠的“花園城市”的目標(biāo)②。城市綠化依托土地整體性使用規(guī)劃(概念規(guī)劃和總體規(guī)劃)和布局,除保留足夠的發(fā)展用地和自然保護(hù)區(qū)之外,政府嚴(yán)格規(guī)劃各類指定專門用途的土地使用的性質(zhì)和強(qiáng)度,利用商用和民用建筑的成片、集中和高層高密度設(shè)計,對留出的地面空間進(jìn)行植樹綠化。
1970-1980年,城市美化項(xiàng)目引進(jìn)多樣和色彩豐富的植物品種,是打造“花園城市”的重要一步。1973年,由政府各部委和法定機(jī)構(gòu)的高級官員組成的“花園城市行動委員會”成立,負(fù)責(zé)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政府各相關(guān)部門規(guī)劃執(zhí)行、市區(qū)重建、公屋建設(shè)和工業(yè)開發(fā)中的綠化行動,這標(biāo)志著“花園城市”已上升至國家戰(zhàn)略(Yuen,1996)。70年代的另一個主要特征是,政府開始主動規(guī)劃開發(fā)各類公園及配套設(shè)施,使休閑性開放空間成為城市的主體設(shè)計,以滿足人們生活休閑的需要。20世紀(jì)80、90年代,新加坡躋身亞洲四小龍的行列,環(huán)境方面經(jīng)過20多年的綠化美化,各類公園和開放空間用地不斷增加、娛樂設(shè)施配套升級,城市景觀蒼翠蔥郁。城市的富足使其發(fā)展規(guī)劃更注重人們生活品質(zhì)的提升。依據(jù)80年代關(guān)于開放空間的理念,即公園、綠色空間、開闊空間和閑置空間應(yīng)被視為網(wǎng)絡(luò)化、一體化的綠色系統(tǒng),既有無形和潛在的經(jīng)濟(jì)價值,又宜于滿足公眾生活品質(zhì)提升的需求(UN,1989)。由此,90年代初新加坡開始建設(shè)全島公園網(wǎng)絡(luò)連道系統(tǒng);實(shí)施“綠色和藍(lán)色規(guī)劃”連接城市綠道和水流河道,城市建設(shè)體現(xiàn)“以人為本”的理念(URA,1991)。1992年“綠色計劃”以平衡環(huán)境保護(hù)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為宗旨,同時期,300公頃各類型公園和開放空間得以興建(Johnson,2008)。
總的來說,1960-1990年新加坡“花園城市”建設(shè)采取實(shí)用主義原則,以經(jīng)濟(jì)目標(biāo)為導(dǎo)向,在技術(shù)上采用人工設(shè)計、裝飾和塑造城市環(huán)境,實(shí)現(xiàn)記錄在冊樹木140萬株,植被區(qū)10000公頃,為新加坡陸地面積的14%,這其中包括3318公頃的公園、公園連道和開放空間以及3327公頃的自然保護(hù)區(qū),全島公園綠道達(dá)200多公里,城市景觀繁茂蔥翠。
(二)新世紀(jì)以來的變遷:邁向“花園中的城市”
新加坡國家公園局(National Parks Board, NParks)是“花園城市”建設(shè)的主要負(fù)責(zé)機(jī)構(gòu)③,它隸屬于開發(fā)建設(shè)國家基礎(chǔ)設(shè)施的國家發(fā)展部(National Development Ministry)而非人們通常認(rèn)為的環(huán)境與水資源部。1996年時任國家公園局首席執(zhí)行官陳偉杰博士最早提出“花園中的城市”(A City In A Garden)概念,1998年新加坡《海峽時報》將之作為國家發(fā)展新方向予以報道,④此后市區(qū)重建局和“可持續(xù)發(fā)展部際委員會”(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⑤等重要國家機(jī)構(gòu)制定發(fā)展規(guī)劃時,如“2008總體規(guī)劃”(Master Plan 2008)(URA,2008)和2009《永續(xù)新加坡藍(lán)圖》(IMCSD,2009)都將之列為城市國家的長期戰(zhàn)略目標(biāo)。2002年,新加坡環(huán)境部出臺“2012新加坡綠色計劃”(Singapore Green Plan 2012,SGP 2012),作為十年期環(huán)境治理藍(lán)圖提出城市環(huán)境不僅應(yīng)綠化清潔,更應(yīng)面向未來、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Chua,2002),為此后新加坡“花園中的城市”提出及其建設(shè)提供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理念支持。
新加坡“花園城市”擁有優(yōu)化的布局結(jié)構(gòu)和完善的綠化體系,是政府幾十年努力積淀的“環(huán)境基礎(chǔ)設(shè)施”(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花園中的城市”是在“花園城市”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城市綠化和街景美觀,強(qiáng)化城市國家的身份特征,通過城市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保護(hù)和發(fā)展升級“花園城市”。具體來說,就是將目前矩陣式的公園綠地系統(tǒng)、綠化系統(tǒng)⑥和擴(kuò)大的水域空間相互連接,形成網(wǎng)絡(luò)化、一體化的回歸自然的生態(tài)空間。它的實(shí)現(xiàn)基于三個基本原則:一是使城市坐落于綠色無處不在的熱帶森林景觀中;二是發(fā)展生機(jī)盎然的城市生態(tài)系統(tǒng),使其在公園、花園、自然保護(hù)區(qū)和空中綠化無縫連接的綠色城市景觀中蓬勃發(fā)展、欣欣向榮;三是讓人們對高品質(zhì)的生活環(huán)境和社區(qū)有歸屬感和擁有感(Auger,2013)。
“花園中的城市”目標(biāo)最大的挑戰(zhàn)不僅是要延續(xù)“花園城市”建設(shè),通過植物綠化美化城市,柔和冷硬的城市環(huán)境,更重要的是注重自然生態(tài)遺產(chǎn)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hù),將之延續(xù)擴(kuò)展至已有自然保護(hù)區(qū)之外、融入到城市的人居生活空間——這是對環(huán)境建設(shè)范式的改變,要求城市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公園、公園連道系統(tǒng)建設(shè)和街景綠化(特別是垂直綠化和空中綠化),修復(fù)和提供適宜生物棲息的環(huán)境地貌。同時,培育公眾對社區(qū)的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使保護(hù)和回歸自然成為全體公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認(rèn)同和參與的行動。
打造“花園中的城市”是新加坡國家發(fā)展新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它是在“花園城市”基礎(chǔ)上,使城市與自然完整融為一體,讓“花園”從城市的點(diǎn)綴變?yōu)槌鞘械妮喞膶?shí)現(xiàn)將使新加坡?lián)碛歇?dú)一無二的城市國家風(fēng)貌,既服務(wù)于吸引全球投資和高端人才、建設(shè)全球中心的經(jīng)濟(jì)目標(biāo);又兼顧為人們提供良好的生活環(huán)境品質(zhì)和生態(tài)關(guān)懷,體現(xiàn)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從根本上堅持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原則。
二、新加坡政府打造“花園城市”和“花園中的城市”的理念
李光耀認(rèn)為優(yōu)質(zhì)的城市環(huán)境是對未來發(fā)展成本-收益最優(yōu)的投資,今天新加坡“花園城市”成果和“花園中的城市”愿景正是在領(lǐng)導(dǎo)人和政府的主導(dǎo)作用和基本理念指引下逐步實(shí)現(xiàn)的。
(一)城市環(huán)境優(yōu)質(zhì)和可持續(xù)發(fā)展是經(jīng)濟(jì)成功的前提和基礎(chǔ)
新加坡獨(dú)立時,政府面臨資源局限、基礎(chǔ)設(shè)施匱乏、經(jīng)濟(jì)停滯和高失業(yè)困境,引進(jìn)外資是推動經(jīng)濟(jì)的唯一辦法。為此,李光耀提出將新加坡建設(shè)成清潔、綠化的城市,使之區(qū)別于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等鄰國,為競爭獲得外資集聚比較優(yōu)勢(Lee,2000)。由此,城市綠化運(yùn)動逐漸展開,“花園城市”設(shè)想逐步變成現(xiàn)實(shí)。政府特別注重環(huán)境和經(jīng)濟(jì)的雙重可持續(xù)發(fā)展,李光耀在20世紀(jì)60、70年代就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濟(jì)活動對環(huán)境的影響要最小化,讓環(huán)境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相兼容。新加坡第一個概念規(guī)劃(1971年)就在土地使用上為城市未來發(fā)展預(yù)留和保證綠色區(qū)域,環(huán)境治理也始于70年代,以公共衛(wèi)生、廢物管理、污染控制和能源效率為主要領(lǐng)域,日漸實(shí)現(xiàn)水和空氣的清潔和安全。
目前,新加坡被世界銀行評為全球最適宜經(jīng)商的國家,其優(yōu)勢除了高效的政府和可預(yù)期的易商政策,良好的基礎(chǔ)設(shè)施和集聚的全球高端人才,更基礎(chǔ)的是“花園城市”綠色宜居的環(huán)境品質(zhì)(Auger,2013)。在其他國際評級機(jī)構(gòu)的榜單中新加坡也表現(xiàn)優(yōu)異,譬如名列瑞士國際管理發(fā)展學(xué)院(IMD)2014全球競爭力第三位;美世(Mercer)生活質(zhì)量調(diào)查中2014年亞洲第一;ECA國際人力資源咨詢公司2012年亞洲外派員工調(diào)查的世界最佳城市等,這些都是優(yōu)質(zhì)環(huán)境服務(wù)于經(jīng)濟(jì)成功的有力證明。
(二)綠色植被是國家發(fā)展不可或缺的構(gòu)成元素
新加坡政府特別重視植被和綠茵的規(guī)劃和建設(shè),使其在城市化進(jìn)程中比重不斷增加。1986年全國人口270萬,國土面積666平方公里,植被率為36%,而這一比率在人口達(dá)到460萬,國土經(jīng)填海造地達(dá)到700萬平方公里的2007年反而增長至47%。土地規(guī)劃(概念規(guī)劃和總體規(guī)劃)從整體上注重綠色空間的預(yù)留和保護(hù)。如在2001年概念規(guī)劃中,市區(qū)重建局計劃在未來40-50年將綠色空間由2500公頃增加至4500公頃,2003總體規(guī)劃進(jìn)一步提出再增設(shè)1200公頃綠色空間和120公里全島公園綠道以銜接現(xiàn)有18個自然區(qū)域和4個自然保護(hù)區(qū)。同屬于國家發(fā)展部的市區(qū)重建局與公園局達(dá)成共識,認(rèn)為保護(hù)自然遺產(chǎn)和擴(kuò)大綠色空間是新加坡成為獨(dú)特和充滿活力的城市的關(guān)鍵,既滿足人們生活休閑娛樂需要又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支持(MND,2013)。新加坡的樹木、花園和公園系統(tǒng)由國家公園局作為“綠色資產(chǎn)”進(jìn)行統(tǒng)一管理,隨著綠色空間的不斷建設(shè)發(fā)展,保護(hù)自然和綠色空間的生物多樣性已上升為主要的政策目標(biāo)(Ng,2008)。
簡言之,“花園中的城市”最根本的涵義是可持續(xù)發(fā)展,它是增加綠茵、水道和保護(hù)自然遺產(chǎn)的綠色發(fā)展,最少能源損耗的高效發(fā)展,以及零污染的清潔發(fā)展,是為了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增長長期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可持續(xù)化的雙重目標(biāo)。邁向“花園中的城市”堅持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原則,將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機(jī)會、活力和優(yōu)質(zhì)生活在城市中的有機(jī)結(jié)合。
(三)動員全社會參與是優(yōu)質(zhì)城市環(huán)境的支撐
新加坡政府在城市綠化中重視公眾、政府和私人部門(People, Public and Private)三者的伙伴關(guān)系,注重政府主導(dǎo),企業(yè)和社會共同參與。這一進(jìn)程是與國際上環(huán)境管理的范式變遷(從管理、參與式管理到治理)相一致(楊立華、張云,2013)。政府在“花園城市”發(fā)展和維護(hù)中主要負(fù)責(zé)園林規(guī)劃建設(shè)和管理、文化創(chuàng)新、技術(shù)支持和教育科普等,如由公園局維護(hù)歷史悠久的新加坡植物園,指導(dǎo)濱海灣花園等國家級項(xiàng)目興建,為全島綠化設(shè)置標(biāo)準(zhǔn),以及開發(fā)創(chuàng)新已在全球70多個城市應(yīng)用的“生物多樣性指數(shù)”(City Biodiversity Index, or Singapore Index),和國際交流等等。全民參與則表現(xiàn)在1971年至今,每年都舉行植樹節(jié)和清潔綠化活動月;始于2005年的“花開社區(qū)”項(xiàng)目讓企業(yè)和公眾參與住區(qū)、學(xué)校、醫(yī)院和辦公區(qū)域的花園建設(shè),成果顯著;各種專業(yè)和職業(yè)背景的人士組成園藝愛好團(tuán)體和互助社交網(wǎng)絡(luò),交流合作和共同美化維護(hù)社區(qū)花園,并得到國家公園局的指導(dǎo)和支持;非政府組織也有效發(fā)揮作用,新加坡自然學(xué)會(Nature Society Singapore,NSS)于1992年成功抵制了將雙溪布洛自然保護(hù)區(qū)發(fā)展成高爾夫球場的提議,2001年NSS又以專業(yè)而熱忱的提議阻止了對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烏敏島部分區(qū)域進(jìn)行土地開墾。
新加坡五十年來的城市環(huán)境綠化是其國家能量的銘證,它標(biāo)示出政府在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和促進(jìn)國家發(fā)展上可能達(dá)到的水平和成就。新加坡各類公園和花園的價值不僅在于園林本身,更體現(xiàn)出政府履行職責(zé)和實(shí)現(xiàn)承諾的能力和效力。縱觀歷史,花園總是一個國家的榮耀,文化品位和文明發(fā)展的標(biāo)識(Gothein,1928;Thacker,1979)。在這一點(diǎn)上,新加坡“花園城市”的實(shí)現(xiàn)和邁向“花園中的城市”愿景提示著世界,優(yōu)質(zhì)的環(huán)境將更加助力城市化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走向卓越。
三、新加坡打造“花園城市”和“花園中的城市”的實(shí)施機(jī)制
(一)以融合環(huán)境考量的長期整體土地規(guī)劃為依托
新加坡從“花園城市”到“花園中的城市”發(fā)展依托于融合環(huán)境考量的法令性的“概念規(guī)劃”(Concept Plan)和“總體規(guī)劃”(Master Plan),從70年代開始,綠化作為國家戰(zhàn)略目標(biāo)就貫徹于城市建設(shè)開發(fā)的每個環(huán)節(jié)中。由市區(qū)重建局制定,概念規(guī)劃指導(dǎo)未來40-50年的城市發(fā)展,每10年復(fù)審一次,是土地和交通的長期整體規(guī)劃,它保證人口增長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長期土地使用需求,并全局性地平衡城市住房、工業(yè)、商業(yè)、公園與休閑、交通、國防和社區(qū)等土地劃分。總體規(guī)劃則詳細(xì)安排中長期10-15年土地發(fā)展,每5年復(fù)審一次。自20世紀(jì)90年代起,新加坡就將土地劃分為55 個小區(qū),每個小區(qū)都制定詳細(xì)的發(fā)展指導(dǎo)藍(lán)圖, 提供每個地區(qū)的規(guī)劃前景、土地用途、發(fā)展密度、建筑高度和綠地率等控制參考指標(biāo)(Khublall & Yuen,1991)。新加坡雖為城市化國家, 但除道路、廣場、建筑等外, 均為綠地。每塊土地開發(fā)前,市區(qū)重建局都提供一些開發(fā)條件, 除上述指標(biāo)外, 對該范圍內(nèi)的樹木、花卉還提出具體的保留、栽植建議。
(二)以健全的法制為保障
在“花園城市”建設(shè)方面,新加坡政府的立法體系始于1975年出臺和生效的《公園和樹木法案》(Parks & Trees Act)。此后經(jīng)過歷次重大修改,特別是2005年的修改法案,并輔之以其他配套法案,如1996年《國家公園法案》修改后重新實(shí)施的2005年《國家公園委員會法案》等,形成了新加坡城市環(huán)境綠化保護(hù)的專門法律制度⑦,既賦予相應(yīng)政府機(jī)構(gòu)(也就是歷經(jīng)發(fā)展的國家公園局)法律效力,又為政策推行提供了法律依據(jù),起到了維護(hù)生態(tài)自然和保持與擴(kuò)大綠化成果不可或缺的作用。1975年《公園和樹木法案》目的是開發(fā)、保護(hù)和管制公共公園、花園以及樹木和植物的生長維護(hù)及相關(guān)事務(wù),作為法律強(qiáng)制性的規(guī)定道路建設(shè)必須提供植樹空間(Tan & Tan,2013);2005年經(jīng)整體性修改,該法案再次明確種植、維持和保護(hù)國家公園、自然保護(hù)區(qū)、遺產(chǎn)道路防護(hù)綠地、樹木保存區(qū)域和其他特殊區(qū)域的樹木與植物以及負(fù)責(zé)其他相關(guān)事務(wù)是法律賦予相應(yīng)機(jī)構(gòu)和人員的權(quán)力。值得指出的是,各項(xiàng)法案的制定和出臺都會吸納各利益相關(guān)方,即除地產(chǎn)行業(yè)外,科研機(jī)構(gòu)和專業(yè)人士、公眾、非政府組織等的意見和建議,以有效平衡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發(fā)展與自然保護(hù)。
(三)以政府各相關(guān)部門的協(xié)調(diào)為動力
“花園城市”建設(shè)中,新加坡政府主導(dǎo)的制度環(huán)境和治理模式,以及中央一級政府直接負(fù)責(zé)整個城市國家建設(shè)發(fā)展的政府結(jié)構(gòu),大大提高了政策的執(zhí)行力度和效率。通過設(shè)立具有法律效力的負(fù)責(zé)機(jī)構(gòu)和協(xié)調(diào)一致各部委及下屬法定機(jī)構(gòu)的目標(biāo)、方向是綠化政策執(zhí)行的重要推動力(Van Wassenhove et al,2013)。1973年,李光耀提議設(shè)立了以綠化植樹為首要目標(biāo)的“花園城市行動委員會”(Garden City Action Committee),其成員代表了全部國家部委和法定機(jī)構(gòu),協(xié)調(diào)配合是該委員會設(shè)立的題中之義。委員會負(fù)責(zé)與綠化相關(guān)的一切事務(wù)和議題:聽取執(zhí)行和維護(hù)報告,實(shí)施街景綠化,公園開發(fā),新加坡植物園建設(shè)以及自然保護(hù)區(qū)問題等。李光耀對各高級政務(wù)官明確提出須要加大“花園行動”的資源投入。至1980年,除去通貨膨脹因素,政府對“花園行動委員會”的預(yù)算投入近乎1973成立時的十倍(Auger, 2013)。在政府內(nèi)部,委員會有效協(xié)調(diào)各重要機(jī)構(gòu),如市區(qū)重建局、建屋局、公用事業(yè)局和陸路交通局等,使各機(jī)構(gòu)的項(xiàng)目開發(fā)都能適應(yīng)配合“花園城市”愿景的實(shí)現(xiàn)。
市區(qū)重建局和國家公園局同設(shè)于國家發(fā)展部,是新加坡舉足輕重的國家機(jī)關(guān)。前者是國家土地規(guī)劃的權(quán)威機(jī)構(gòu),后者則統(tǒng)一規(guī)劃管理全島公園、綠化、連道系統(tǒng)和開放空間,以及自然保護(hù)區(qū)等。同屬國家發(fā)展部使二者能在土地使用中整合、融入綠化目標(biāo),合理推進(jìn)“花園城市”建設(shè)。如《2001公園和水體藍(lán)圖》就是市區(qū)重建局和國家公園局緊密配合、共同籌劃的新加坡未來40-50年的城市遠(yuǎn)景之一。此外,市區(qū)重建局更是協(xié)調(diào)各部門土地使用摩擦的權(quán)威機(jī)構(gòu),由各相關(guān)方(機(jī)構(gòu))代表組成,由市區(qū)重建局領(lǐng)導(dǎo)的總體規(guī)劃委員會(Master Committee)專門通過多輪會議、協(xié)商和妥協(xié),調(diào)解和裁決各部門政策目標(biāo)的優(yōu)先性,其原則是促進(jìn)國家的整體目標(biāo)。而一旦委員會的最終決定不能解決爭議,會議的級別即可上升至部長級,甚至可能需要總理做出最后決定⑧,這是政府協(xié)調(diào)各機(jī)構(gòu)的重要機(jī)制之一。
(四)以詳細(xì)計劃方案為依據(jù)
“花園城市”的實(shí)現(xiàn)方案是城市綠化帶網(wǎng)絡(luò)化,各類綠地形成“點(diǎn)、線、面”相結(jié)合的合理布局,園林綠化、植物配置經(jīng)歷了綠化、美化、多樣化和藝術(shù)化的過程,處處層次豐富,草地、灌木、喬木自然搭配。國家公園局出臺“樹木保護(hù)區(qū)”(Tree Preservation Area)政策,“遺產(chǎn)道路計劃” (Heritage Road Scheme),“遺產(chǎn)樹木計劃” (Heritage Tree Scheme)和“保護(hù)自然”計劃 (Nature Conservation)等。街景綠化藍(lán)圖(Streetscape Greenery Master Plan)作為道路空間美化的總體藍(lán)圖,不僅推行路旁綠化,還吸納水濱道路、鄉(xiāng)村道路、雨林公路的理念,是“花園中的城市”建設(shè)的重要導(dǎo)向。
“花園中的城市”旨在建構(gòu)和維護(hù)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花園城市”基礎(chǔ)上,新加坡正著力增建和升級公園系統(tǒng)及其配套設(shè)施,目標(biāo)于2030年實(shí)現(xiàn)每千人0.8公頃公園覆蓋率;延長公園連道網(wǎng)絡(luò)和連接全島公園綠地和開放空間,至2020年達(dá)到360公里,并建設(shè)長150公里的環(huán)島綠道,由此,使步行和騎行的綠色網(wǎng)絡(luò)聯(lián)通和環(huán)繞整個城市;加強(qiáng)自然保護(hù)區(qū)和自然區(qū)域及其動植物群落多樣性的維護(hù),建設(shè)生態(tài)走廊和動植物棲息地。超越單純建設(shè)基礎(chǔ)設(shè)施的思路,“花園中的城市”注重在狹小的城市國家空間中盡最大努力保護(hù)和聯(lián)通自然區(qū)域,這也符合新加坡城市地理的天然特點(diǎn),根據(jù)國家公園局的研究,新加坡很可能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密度最大的地區(qū)之一,即在2800公頃的自然保護(hù)區(qū)內(nèi)生存2000多種動植物群落。未來城市居住區(qū)、公園連道、水體乃至自然保護(hù)區(qū)的連接將使城市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融為一體,為新加坡可持續(xù)發(fā)展創(chuàng)造獨(dú)特的生態(tài)模式。
四、新加坡世界級“花園中的城市”范例——“濱海南”綜合功能發(fā)展區(qū)
前文介紹了新加坡打造“花園中的城市”的政策理念、執(zhí)行機(jī)制和政策配套。現(xiàn)在我們從“濱海南”綜合功能發(fā)展區(qū)融合生活、工作、休閑于一體的世界級“花園中的城市”社區(qū)來看上述指導(dǎo)原則如何具體實(shí)施,從而提升新加坡城市國家的品質(zhì)和競爭力的。
“濱海南”(Marina South)綜合功能發(fā)展區(qū)將于2017/2018年動工,它東臨新加坡海峽,西靠新加坡最優(yōu)美的城市園林杰作——“濱海灣花園”,是“花園中的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⑨。“濱海南”的規(guī)劃由國家發(fā)展部市區(qū)重建局主導(dǎo)和精心籌劃,吸納了科研機(jī)構(gòu)(如新加坡國立大學(xué)、新加坡建筑學(xué)會等)和社會(如專業(yè)人士、專家學(xué)者等在創(chuàng)意投標(biāo)競賽中的投標(biāo))的創(chuàng)意與合作,通過詳細(xì)的總體規(guī)劃予以設(shè)計和指導(dǎo),預(yù)期建成為新加坡城市未來地標(biāo)式中央核心區(qū)。通過綜合發(fā)展商務(wù)和住宅區(qū),“濱海南”將更加便利人們在工作地點(diǎn)附近居住、生活和休閑,在面積為21.5公頃的城市中心區(qū)域,“濱海南”將成為中心商務(wù)區(qū)延伸出的綠野和生態(tài)友好型都市社區(qū),不僅為人們提供9000套住房,更通過可持續(xù)發(fā)展原則設(shè)計的綠化美化、交通模式、建筑標(biāo)準(zhǔn)等基礎(chǔ)設(shè)施為人們打造“花園中的城市”,使之成為城市綠色空間的有機(jī)組成。“濱海南”使城市中心向海濱延伸,并銜接起中央商務(wù)區(qū)與居住區(qū),預(yù)計為新加坡增添更多國際元素和城市活力,成為城市的海濱花園和特色經(jīng)濟(jì)增長點(diǎn)。
“濱海南”地處新加坡城市中心的黃金位置,西鄰結(jié)合高科技元素的園林美景“濱海灣花園”,東接新加坡海峽,具有延伸三十公里的海濱;它還將與附近公園、開放空間和自然區(qū)域無縫連接;計劃興建的綠色走廊(Green Corridor)和生態(tài)走廊(Eco-corridor)將進(jìn)一步擴(kuò)大綠色網(wǎng)絡(luò)空間,使“濱海南”乃至整個海灣坐落在人造美景和生態(tài)自然環(huán)境的緊密環(huán)繞中。交通方面,“濱海南” 以快速軌道交通(Rapid Transit System)和步行與騎行為主,主路實(shí)現(xiàn)無機(jī)動車輛,區(qū)域內(nèi)任意地點(diǎn)可以步行5分鐘到達(dá)最近的公交節(jié)點(diǎn)。步行網(wǎng)絡(luò)的核心是經(jīng)過景觀美化的長800米、寬30米的步行街,兩側(cè)以綠色和開放空間為主,分地表和地下兩層,是漫步路線和社區(qū)活動的主要場所。此外,濱海南還將架設(shè)高架通道并進(jìn)行空中綠化,專供行人來往于東西兩側(cè)的海岸線和濱海灣花園。
建筑方面,濱海南將是新加坡最先進(jìn)的環(huán)境友好型社區(qū)之一,實(shí)行比普通標(biāo)準(zhǔn)高30%的綠色建筑標(biāo)準(zhǔn),建筑物采用生態(tài)友好措施,實(shí)行雨水收集、廢水回收循環(huán),屋頂綠化、垂直綠化和空間綠化,以及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等。適應(yīng)海濱地區(qū)地理特點(diǎn),濱海南利用海風(fēng)冷卻空氣,創(chuàng)造涼爽、舒適的微氣候環(huán)境,同時降低熱量、節(jié)約能源。社區(qū)主干道和人行道的方向設(shè)計與季風(fēng)方向一致,成為風(fēng)的走廊“Wind Corridor”,街區(qū)中的建筑高度設(shè)計也以促進(jìn)人行路面的空氣流動為目標(biāo)富有變化,從而增加行人和街區(qū)的涼爽。濱海南建筑的高度也以符合人體感官尺度為準(zhǔn),從人行道到主干道,從近濱海花園到遠(yuǎn)濱海花園,建筑的高度由低到高依次提升,優(yōu)化了景觀的視覺體驗(yàn),整個社區(qū)使地上慢行空間、地下商場和走廊與“空中花園”相結(jié)合,通過多層空間為打造“花園中的城市”環(huán)境。
五、新加坡“花園城市”和“花園中的城市”環(huán)境對中國的啟示
(一)將城市環(huán)境建設(shè)上升到國家戰(zhàn)略層面,加強(qiáng)頂層設(shè)計
新加坡在工業(yè)化和城市化起步時就把城市環(huán)境治理和城市綠化上升至國家戰(zhàn)略高度,通過土地整體規(guī)劃、環(huán)境治理法案和政策執(zhí)行機(jī)制長期堅持環(huán)境綠化,明確環(huán)境和經(jīng)濟(jì)增長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雙重目標(biāo)。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資源環(huán)境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人口增長和迅速城市化進(jìn)程中受到巨大消耗和破壞,已成為經(jīng)濟(jì)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中迫在眉睫的問題。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應(yīng)以何種狀態(tài)和速度進(jìn)行,并同時使環(huán)境生態(tài)得以治理和保護(hù)是近年來中國城市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新加坡的城市環(huán)境綠化策略,特別是制度設(shè)計和執(zhí)行機(jī)制對其環(huán)境品質(zhì)的提升為中國相關(guān)城市政府提供了可資借鑒和已得到檢驗(yàn)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模式。
(二)政府在環(huán)境治理中起主導(dǎo)作用并注重政策的執(zhí)行力
新加坡的城市環(huán)境綠化和治理采取以政府為主導(dǎo)的治理模式,政府不僅提出發(fā)展戰(zhàn)略和規(guī)劃藍(lán)圖,還負(fù)責(zé)組織動員、協(xié)調(diào)推進(jìn)、以強(qiáng)有力的制度、法律、組織和財力等推動政策實(shí)施。更重要的是,在規(guī)劃方案的執(zhí)行中政府善于統(tǒng)籌和協(xié)調(diào)相關(guān)部門、機(jī)構(gòu),使政府有機(jī)統(tǒng)一邁向城市國家共同的政策目標(biāo)。新加坡綠化美化的城市環(huán)境政策具有長期性和與時俱進(jìn)的特征,邁向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生態(tài)自然保護(hù)并行的“花園中的城市”反映了政府的政策主導(dǎo)作用和有效的政策執(zhí)行能力,值得中國城市政府借鑒。
(三)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環(huán)境政策
新加坡的城市環(huán)境政策一方面具有長期性,始終服務(wù)于國家吸引外資、人才和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目標(biāo),另一方面也因側(cè)重點(diǎn)不同而體現(xiàn)出階段性,從“花園城市”到“花園中的城市”是綠化建設(shè)隨時代而進(jìn)步最好的詮釋。目前,新加坡各局部區(qū)域如前文提到的“濱海南”,“榜鵝生態(tài)新鎮(zhèn)”和“裕廊湖區(qū)”等,都以“花園中的城市”為目標(biāo)進(jìn)行環(huán)境建設(shè),不僅融入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理念,同時結(jié)合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相適應(yīng)和創(chuàng)新的科技方案等。由此,我們認(rèn)為,中國各城市也應(yīng)結(jié)合自身特點(diǎn),因地制宜地開展城市環(huán)境治理,根據(jù)地理區(qū)位、人口規(guī)模、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歷史文化、資源稟賦和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目標(biāo)等因素制定適合的城市環(huán)境政策,使之服務(wù)于經(jīng)濟(jì)社會的進(jìn)步。
(四)培養(yǎng)公眾環(huán)境意識,引導(dǎo)全民參與環(huán)保
新加坡政府在城市環(huán)境建設(shè)中扮演了主導(dǎo)作用,但并非包辦一切。作為環(huán)境治理的重要一環(huán),政府之外的民眾、社區(qū)和專家學(xué)者的參與和多元協(xié)作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環(huán)境關(guān)乎城市和國家的發(fā)展全局,更關(guān)乎當(dāng)代和后代的生活和生存,政府因而特別重視引導(dǎo)企業(yè)、社會和個人以主人翁的精神關(guān)心和參與環(huán)保,從而增強(qiáng)公眾的環(huán)境意識和責(zé)任感。
從2011年開始,中國的城鎮(zhèn)人口比率首次超出了農(nóng)村人口,進(jìn)入了城市化快速發(fā)展的階段。近年來,中國的大城市空間規(guī)劃和社會建構(gòu)也逐步出現(xiàn)了從“統(tǒng)治”到“治理”的轉(zhuǎn)變。在這一過程中,一些社會矛盾仍然較明顯的存在(蔡禾,2012)。不少學(xué)者提出了從國際經(jīng)驗(yàn)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城市化問題以及建立新的理論和政策范式(如馬駿,2012;葉林,2012)。我們認(rèn)為,除了西方的經(jīng)驗(yàn)外,新加坡也提供了中國大城市發(fā)展的很好借鑒。雖然新加坡是個城市國家,它的文化和制度與中國有某些共通性。近年來新加坡在蘇州、天津和廣州推動的中新合作項(xiàng)目以及新加坡成為中國最大的外來投資國這一事實(shí)也使得新加坡的經(jīng)驗(yàn)獲得更為廣泛的重視,如在人才戰(zhàn)略方面(劉宏,2012)。本文的案例顯示,新加坡的“花園中的城市”從理念的產(chǎn)生、演變和成型,都經(jīng)歷了政府、市場、社會和專家等幾個不同的利益相關(guān)者的協(xié)同參與和討論,從而保證城市的建筑空間與社會空間的和諧發(fā)展。中國城市政府也應(yīng)學(xué)習(xí)新加坡,引導(dǎo)全社會特別是既得利益群體去認(rèn)識在發(fā)展中不僅應(yīng)重視物質(zhì)資源形式的財富與利益最大化,更應(yīng)著重生活質(zhì)量、環(huán)境效益等無形利益的最大化及其可持續(xù)性問題,認(rèn)清優(yōu)質(zhì)的環(huán)境是經(jīng)濟(jì)和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備的基礎(chǔ)和支撐。
注釋:
①新加坡的歷次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20世紀(jì)60年代走工業(yè)化道路,發(fā)展勞動密集型經(jīng)濟(jì);70年代末勞動力短缺,向技能密集型經(jīng)濟(jì)轉(zhuǎn)變;80年代中期發(fā)展資本密集型產(chǎn)業(yè),如煉化,倉儲,精密工程等;90年代發(fā)展科技密集型產(chǎn)業(yè),如生物醫(yī)藥,高端化工等;進(jìn)入21世紀(jì)升級為知識密集型經(jīng)濟(jì),著力發(fā)展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近年來開始提出把科技創(chuàng)新與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相結(jié)合提高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質(zhì)量。
②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16 December 1968), vol 28 at col 396.
③國家公園局(National Parks Board, NParks)于1996年成立,隸屬新加坡國家發(fā)展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是新加坡城市綠化美化、公園維護(hù)等相關(guān)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的重要國家機(jī)構(gòu);其前身是上世紀(jì)60年代末國家發(fā)展部下屬的市政工程部(Public Works Department, PWD)之下設(shè)立的公園與樹木單元(Parks & Trees Unit),是當(dāng)時植樹綠化行動的主要執(zhí)行機(jī)構(gòu),1975年改設(shè)為公園與休閑部(Parks and Recreation Department, PRD),前文提到的1991年全島公園連道系統(tǒng)建設(shè)就是由該部門負(fù)責(zé)的;1996年公園與休閑部被并入新成立的國家公園局(Nparks)。
④“‘City in a Garden’ Plan set out for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11 December 1998); and “Green Piece”, supra n 5.
⑤“可持續(xù)發(fā)展部際委員會”于2008年成立,由國家發(fā)展部部長(Minis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和環(huán)境與水資源部部長(Minster of Environment & Water Resources)聯(lián)合領(lǐng)導(dǎo),以實(shí)現(xiàn)新加坡可持續(xù)發(fā)展為目標(biāo)。
⑥公園綠地系統(tǒng)由沿岸公園、自然公園、水庫公園、城市公園、新鎮(zhèn)公園、鄰里綠地和組群綠地構(gòu)成;綠化系統(tǒng)由以海岸線成片綠地、植物園、風(fēng)景區(qū)和中央水源森林保護(hù)區(qū)為主, 以市區(qū)公園、街頭綠地和快速公路道路旁的綠帶為輔, 以鄰里綠地及建筑的窗口、陽臺、屋頂及人行天橋上的花卉為點(diǎn)綴。
⑦Legislative history: Parks and Trees Act.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w3p;ident=b2b259b6-ec75-4b04-b5b1-2af4a4001482; orderBy=date-rev, loadTime; page=0;query=DocId%3Ac6871e24-cb16-417e-8dd5-81bdd6c1ff3c%20%20Status%3Ainforce%20Depth% 3A0;rec=0;resUrl=http%3 A%2F%2Fstatutes.agc.gov.sg%2Faol%2Fbrowse%2FtitleResults.w3p.
⑧由新加坡市區(qū)重建局行業(yè)與工業(yè)發(fā)展處主任Caroline Seah女士(Director, Professional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口述講解新加坡政府如何協(xié)調(diào)各部門和機(jī)構(gòu)在土地使用中的摩擦和目標(biāo)沖突。
⑨本節(jié)的資料來源主要取自新加坡市區(qū)重建局網(wǎng)站關(guān)于“濱海南”的規(guī)劃:http://www.ura.gov.sg/uol/masterplan/View-Master-Plan/master-plan-2014/master-plan/Regional-highlights/central-area/central-area。
[1]蔡禾.從統(tǒng)治到治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大城市社會管理.公共行政評論,2012,6.
[2]劉宏.新加坡的國際人才戰(zhàn)略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第一資源,2012,1.
[3]劉宏,王輝耀.新加坡的人才戰(zhàn)略與實(shí)踐.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15.
[4]馬駿.中國公共行政學(xué)研究:反思與展望.公共行政評論,2012,1.
[5]楊立,華張云.環(huán)境管理的范式變遷:管理、參與式管理到治理.公共行政評論,2013,6.
[6]葉林.城市發(fā)展與治理:國際經(jīng)驗(yàn)與中國實(shí)踐.公共行政評論,2012,2.
[7]Auger,Timothy.(2013).Living in a Garden: The Greening of Singapore.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8]Chua, L.H.(2002).Singapore Green Plan 2012: Beyond Clean And Green: Toward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Singapor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https://app.mewr.gov.sg/data/ImgCont/1342/sgp2012.pdf
[9]Gothein, M.L.(1928).A History of Garden Art.New York: Dutton Publishing.
[10]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MCSD).(2009).A Lively and Livable Singapore: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Growth.Singapore: th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http://app.mewr.gov.sg/data/imgcont/1292/sustainbleblueprint_forweb.pdf
[11]Johnson, H.D.(2008).Green plans: Blueprint for a sustainable earth.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2]Khublall, N.& Yuen, B.(1991).Planning Law and Development Control in Singapore.Singapore:Longman.
[13]Lee, Kuan Yew.(2000).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and Times Editions.
[14]Ministry of Environment.(1992).The Singapore Green Plan: Towards a model green city.Singapore:SNP Publishers.
[15]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ND).(2013).A High 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for All Singaporeans: Land Use Plan to Support Singapore’s Future Population.Singapor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http://www.mnd.gov.sg/landuseplan
[16]Ng, Lang.(2008).A City in a Garden, Ethos, World Cities Summit Issue, June, pp.62-68.
[17]Thacker, C.(1979).The History of Gardens.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8]Tan, M.B.N.& H.T.W.Tan.(2013).The Laws Relating to Biodiversity in Singapore.Singapore:Raffles Museum of Biodiversity Research and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http://rmbr.nus.edu.sg/raffles_museum_pub/biodlawsgp.pdf
[19]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1991).Living the Next Lap: Towards a Tropical City of Excellence.Singapore: URA.
[20]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2008).Master Plan 2008.Singapore: URA.
[21]United Nations.(1989).Prospect s of World Urbanization 1988.New York: UN Publications.
[22]Van Wassenhove, Luk, Fernando, Ravi, Hamelin, Hazel.(2013).Singapore-City In A Garden: A Vision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INSEAD Case Study.
[23]Yuen, Belinda.(1996).Creating the Garden City: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Urban Studies, vol.33,no.6, pp.955-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