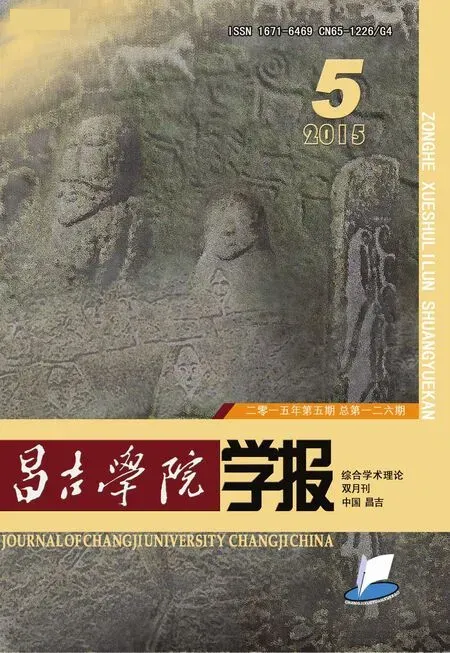從女性家族小說看“瘋女”形象
——以《玫瑰門》、《媽閣是座城》為例
肖蓉蓉
(安徽大學文學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從女性家族小說看“瘋女”形象
——以《玫瑰門》、《媽閣是座城》為例
肖蓉蓉
(安徽大學文學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以女性家族小說為切入點,展開了對新時期以來女性作家筆下“瘋女”形象的研究,以《玫瑰門》、《媽閣是座城》為例,獨特的女性視角,歷史為引、避重就輕,描繪出了在紛繁詭譎的歷史背景下司猗紋、姑爸、梅吳娘、梅曉鷗的人性嬗變和命運悲劇,以及她們在特定的時空下所遭受的多重壓迫:男性特權、封建政權、女性個體自身的放逐和墮落;探究造成女性言行失常、精神變異的深層原因;通過對男權政治和社會文明的批判,達到對當下女性文學的辯證思考以及未來兩性話語權的重新建構。
瘋女;性別反叛;精神變異;菲勒斯主義
家族即“以婚姻和血緣關系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組織,包括同一血統的幾輩人。”[1]女性家族小說作為新時期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學界對此并未完全界定,“她們把女性意識帶入到了家族故事中,將家族文本與性別文本融為了一體,試圖以女性的視角來審視家族歷史,主要是來重新書寫家族故事中被男權文化遮蔽的女性歷史”。[2]小說大多由女性作家創作,以一個或幾個女性人物作為敘事的中心,講述了一個或幾個家族在歷史進程中的變遷,特別是對女性自我生存體驗和情感經歷的關注。小說試圖通過在宏大歷史的消解中,回歸到對日常生活的觀照;對母系譜系、家族史的追溯,進而找到自己在社會文明中的身份皈依;對父權文明、男性欲望膨脹的批判,達到對自我的重新審視和認同。
女性家族小說的發展得力于20世紀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批判理論的傳入,在經歷了80年代的嘗試和試驗后,她們以一種不同于男性作家寫作的內部視角,將關注點放到了女性在傳統家族中的個體生存體驗和男性文明批判上,進入90年代,文學呈現出多元發展的狀態,在西方理論和創作實踐的支撐下,女性家族小說思想開始越來越成熟,創作手法上不斷翻新,涌現了大量優秀作品,鐵凝的《玫瑰門》、張潔的《無字》、徐小斌《羽蛇》等等。
女性家族小說中一改傳統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圣母和惡女),深入女性的真實內心,創作了一批深刻復雜的女性,她們或邪惡、或善良,或潑辣、或溫順,她們是黑暗與光明的結合,其中,“瘋女”是作家普遍關注的一類人物,這里的“瘋”,“是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所表現出來的一種非正常狀態,而這種‘瘋人’形象在現當代文學中已然成為一種文化癥候里的‘瘋’”。[3]總而言之,“瘋女”就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在政治、文化的擠壓中脫離了正常言行,有著某種精神病態的女性形象。
一、“瘋女”形象的塑造
(一)言行失常的性別反叛者——姑爸
姑爸是《玫瑰門》里的一個性別意識分裂的人物,首先從名字上看來,“姑”是一個非常確定的女性化稱謂,但是其后卻緊跟著一個男性符號“爸”,這在讀者閱讀伊始人產生一種困惑。接下來,小說以一個小女孩眉眉的視野帶我們走近了這個復雜的個體,眉眉第一次來到外婆家,“那是一個男人,不,那是一個女人,不,那是一個男人。她不能立刻確定他的年齡,他個子偏高,駝背,無胸,留下一個連耳朵也遮蓋不住的分頭,耳垂兒肥大;他的眼不精神,卻不失洞察一切的神色;眉毛不黑但是寬闊,離眼稍顯遠些。”[4]在孩子的眼里,她一方面無法毀滅已然存在的女性生理性別,另一方面又極力希望通過這種消除女性外在特征,衣著言行完全男性化的做法來成為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社會話語權的男人。因為當年婚姻的破滅,她蔑視一切與女性有關的東西,甚至養的貓都是公的,認為一切與女性、母性相關的東西都是骯臟的。她把她所有的感情都投注在大黃的身上,除此以外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都無法引起她的注意,但是當有一天,大黃因為偷吃了鄰居的肉被活活車裂而死的時候,她才終于認識到以前一切的改變都沒有改變自己的命運,她又變成了那個在新婚之夜被狠心的丈夫拋棄的女人了,她眼睜睜地看著貓被殺死,心中的郁憤連同當年的屈辱一并爆發,在黑夜里她憤怒地向那些劊子手提出控訴,最終引火燒身,在經歷了那個瘋狂年代的血腥傷害后,她徹底地瘋了,她一邊大力地嚼著大黃的尸體,一邊挪著鮮血淋淋的下身,緩緩地走到每個人面前,大聲地懺悔,訴說著她的“罪”,為了贖罪,她生生地吃掉了整個的大黃。
(二)精神變異的施虐者——司猗紋
司猗紋是一個貫穿整部小說始終的靈魂人物,一出場時就是作為眉眉的婆婆而存在,中間間或穿插她的回憶。她的瘋癲主要變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次是在18歲為了反抗包辦婚姻,與自己的心上人私奔,司猗紋出身名門,在享盡父母的寵愛的同時,還接受了新式教育,并結識了當時的進步青年華致遠,兩人的情投意合遭到了封建父母的強烈反對,為此,她出于反抗決定與華致遠私奔,并獻出了女孩子最寶貴的忠貞,但是懦弱的華致遠在黎明到來時一走了之,為了完成母親的遺愿,司猗紋被迫嫁入了莊家。婚后的生活,丈夫的肆意凌辱和打罵為她的性格轉變埋下了依據,她還從丈夫那里感染上了梅毒,在痛哭之后,她改變了自己一貫的溫順恭良,將復仇的利劍直指莊家最高統治者——莊老太爺,在惡毒地強奸了自己的公公之后,這種亂倫式的女性對男性的反叛,使她終于獲得了一種復仇的快樂和滿足。第三層“瘋”,從此司猗紋在黑暗的深淵里愈行愈遠,最終不可自拔,“文革”時期,政治的顛覆,集體性暴力沖突無形中把她的瘋狂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她懷著嫉妒的心理窺視著兒子和兒媳的生活,頑固地控制、占有外孫女眉眉的成長,甚至殘忍地設計讓眉眉撞見自己的舅媽竹西偷情的場面。不管是任何人,她都想通過偷窺別人的“思想問題”來打倒他們。這種精神上的異化、變態最終演變成了對別人的傷害凌辱,也使得眉眉失去了最美好的童年時光。
(三)善惡交替的大地母神——梅吳娘
“大地母神”即“原型母神”,“母親形象是一個‘原型’,誕生于遠古‘母神文明’時代的‘原型母神’。‘原型母神’說認為,女性作為生命的創造者能包容整個世界。她本身就是大自然和大地,是宇宙萬物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再生者、保護者和養育者,是一切生命的母親,這位母親在終極意義上,是大地,是大地上的女人直到無數世代的母親們和女兒們的代表。”[5]女性作為生命的創造者,是萬物的來源,具有一種強大的包容性,是母親存在的精神內核。梅吳娘在小說《媽閣是座城》中的內容并不多,她是作為梅曉鷗的精神指引者而存在的,梅吳娘是中國千千萬萬個母親中的一個,但是她決然、狠毒地殺死了自己的三個兒子,因為丈夫嗜賭成性,留給家庭的只有無盡的生活重擔和精神傷害,她被迫承擔起養家的責任,在她的身上,有著中國傳統婦女的堅韌、能干。為了下一代不會走上賭博的老路,她一次次地親手將剛出生的兒子溺死在馬桶里,唯一存活下來的兒子也是純屬僥幸。梅吳娘并不是一個天性嗜殺的母親,相反,她人性中的母性絲毫不亞于任何一個母親。在發現兒子竟然私自參與賭博時,梅吳娘渾身的血液都憤怒了,梅大榕的賭性之根在兒子身上得到了延續,為了拯救兒子,她平靜地將放在手心的一根燒紅的銅條直直地塞進梅亞農的嘴里,這種自殘和傷害行為絲毫不亞于滿清酷刑,自此,兒子終身不碰賭,最終光宗耀祖,無限尊榮。
(四)賭性膨脹的復仇者——梅曉鷗
梅曉鷗作為梅吳娘和梅大榕第五代孫女,在她的身上奇跡般的糅合了賭徒的賭性和母性的救贖。她第一次反叛、離家出走就是為了報復母親,從此遠離了家庭,也是她遠離正常人生軌跡的開始,在金錢的誘使下她糊里糊涂地成為了盧晉桐的情人,又糊里糊涂地成了母親。原本無所謂的生活因為有了孩子變得不同,為了孩子日后的正常生活,她狠心離開了盧晉桐,為了生存,更是出于一種對于男性嗜賭成性的報復,她并沒有選擇一種平靜簡單的生活,而是憑借自己的聰明、漂亮成為媽閣賭場的一個疊馬仔,“一方面,她在女人‘不應該做’的賭場掮客,以極端個人主義的仇恨心理,以開發精英男人的賭性為報復手段,在構筑自己經濟王國的過程中,試圖一箭雙雕俘獲情感與財富”。[6]但是,另一方面,在她狠辣的手段背后又存在著母性救贖的瘋狂,對于自己的兒子、對于曾經愛過的那些男人們,她無法做到真正的棄之不顧,甚至通過免除債務希望能夠換來老史的浪子回頭,對于盧晉桐在重病之下的請求也是全權接受,甚至是對待無賴段凱文也是屢次相幫,最后,終于能夠放下一切來到了老史居住的溫哥華,與兒子開始了新的生活。
二、“瘋女”形象形成的原因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說過:“從生理、心理或是經濟因素,沒有任何的既定的命運可以決定人類中女性在社會中所表現的形象。決定這種處于男人和閹人中間的、有著所謂女性氣質的人種的是整個文明體系。只有另一個人蓄意所為,一個人才會被確定為他者。”[7]在女性主義理論批評家看來,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是父權文明、男性話語建構下的產物,是生活在鐵閨閣中的人,“這里的‘鐵閨閣’則是以鐵屋中的弱勢女性群族為吸納對象,指涉女性在傳統宗法父權體制下的深閨大院中的內囿處境即所謂‘男外女內’的內囿機制。”[8]“瘋女”更是在社會、性別、自我的三層壓迫下一步步由一個個正常人走向癲狂的生命本質。
(一)菲勒斯、男性中心主義的戕害
人類文明史實際上就是父權文明和男性壓迫史,由于女性在物質資料的獲取、經濟的獨立上處于被動的位置,女性在歷史上一直是邊緣人,失去了社會話語權,“女人已經成了相對于本質的非本質,男人是主體,是絕對的,而女人總是‘他人’。女人即便不說是男人的奴隸,至少也仍是他的臣仆。”[9]隨著近代社會的發展,女性由原來的男性純粹附屬品慢慢覺醒,有了一定的主體意識,在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支持下,中國的女性作家開始進行爭取女性話語權,但是傳統的男性菲勒斯主義仍然是社會的主流思想,女性作家遇到了極大的阻礙,因此,在她們的筆下出現了一些為了爭取自由、性別解放的女性即使撞得頭破血流也絕不后悔,她們在不斷的嘗試中逐漸失去了生命的常態,走向了變異。
《玫瑰門》里的姑爸是一個飽受封建男權、婚姻壓迫的形象,她的命運在新婚之夜從此被改寫,她帶著青春、活力,對未來的美好愿望坐上了花轎,卻發現新婚時新郎無端消失了,三天后她被送回了娘家,在那樣的年代,女子的名聲比生命還重要,出嫁后被送回,不管是不是女方的錯,這個后果都由女性來承擔,從此,她對于女性的軟弱無助的社會性別深惡痛絕,才會變成一個不倫不類、不男不女的“怪物”。
司猗紋是一朵罪惡之花,但是澆灌她的卻是父權對她的傷害。貞潔是封建社會女性最重要的東西,女性作為丈夫的私有商品,一旦貞潔不在,女性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出于愧疚和后悔,司猗紋自從當了莊家少奶奶就一直想做一個恪盡職守的賢妻良母,但是惡毒的丈夫從未給過她機會,他不僅在新婚之夜夜宿妓院,還不斷在外拈花惹草,甚至將其帶到家里凌辱司猗紋,她一直活在欲望與壓制、追求與求而不得的痛苦之中,所有的婚姻幻想都將覆滅,為了反抗,她最終報復性地強奸了公公來換取心靈的滿足。
梅吳娘是一個典型的農家婦女,從十六歲到二十六歲,因為梅大榕幾次將掙的錢葬送在了賭檔里無臉回來,她足足等了丈夫十年,這十年的時光是一個女孩子最好的歲月,但是除了每日漫長的等待,女性別無他法,終于將嗜賭成性的丈夫等了回來,可是這才是痛苦的開始,整日流連賭坊的梅大榕對家庭、孩子一概不問,最終因賭而死,從此梅吳娘對賭真可謂仇恨之至,為了斬斷“賭”之根,她只得忍痛將孩子溺死。
如果說梅吳娘的時代是少數人的賭,那么今天的媽閣就是一個能夠讓所有人賭性無所遁形的“城”,本雅明曾說:“寫一部小說的意思就是通過表現人的生活把深廣不可量度的帶向極致。”小說以媽閣這座小城折射出男性特有的貪婪和無盡的欲望。“男性‘大我’在迷失膨脹中異化為自私、獨尊、貪婪、嗜賭如命的人性惡的代表。”[10]女性在男性心中始終是一種商品的姿態出現的,盧晉桐的包養、老史明知道梅曉鷗對他的愛慕,他也不推不就,段凱文和梅曉鷗的公開調情都是男性把女性當成了權欲、貪欲、性欲的消費品。
(二)血腥的社會暴力
《玫瑰門》中以“文革”作為敘述的背景底色,女性作家專注于描寫女性在社會變革和暴力沖突中承受的苦難,從而提出對那段瘋狂的血腥年代的批判,姑爸的悲劇是當時千千萬萬個女性悲劇的一個,時代的快速變革并沒有引起姑爸的注意,她仍然沉浸在自己的簡單世界中,但是罪惡的黑手依然伸向了她,人性中的自私、窺探、破壞欲等等黑暗面在政治的洪流中肆意橫行,集體無意識的瘋狂、人性的淪喪、道德的扭曲等等最終將一個無辜的女性逼向了死亡的邊緣,因為政治地位、家族歷史問題,姑爸這樣的人物在當時首當其沖是被“革命”的對象,眼看著大黃受盡折磨而死,女性和動物是處于同樣的命運,大黃所受的車裂之刑,姑爸的下身被插入了一根通條,最后慘死。
同處于同一個時空,司猗紋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態度迎合“文革”的需求,她一方面迅速將財物上交以求表功,從而獲得社會的認可,另一方面“文革”的動蕩、混亂為司猗紋這樣的投機分子提供了機會,她不僅通過偷窺和占有達到對欲望的滿足,還通過揭發親妹妹來獲得升遷,也因此飽受良心上的譴責。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她只能適應這個黑暗的社會,并最終在此沾染下完成了人性由善到惡的變遷。
而梅吳娘和梅曉鷗在社會壓迫方面存在共同性,貪欲是人性中無法磨滅的弱點,從梅大榕再到現代的盧晉桐、老史、段凱文,他們的身上都隱藏著人性中的貪婪,正是由于貪婪,他們逐漸失去了理性、愛人的能力,也使得女性失去了原本應得的溫暖,為此,她們開始變得暴虐,瘋狂地展開復仇。
(三)女性的自我奴役和流放
鐵凝曾經說過:“在中國并非大多數女性有解放自己的明確概念,真正奴役和壓抑女性心靈的往往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11]外部的環境壓迫是造成女性瘋癲、悲劇的重要原因,但是內部因素也不容忽視。女性在男權文明的擠壓下,很多人變得順從、妥協,對于自我的存在意義毫無察覺,只能慢慢被時間吞沒。有時為了生存,她們無奈地遵從封建父權、夫權,將男人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撐,一旦遭到拋棄就會惶然不知所措,在自我放逐中最終走向瘋癲。
《玫瑰門》里的姑爸的性別意識混亂,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女性的懷疑與反叛,但是這種在日常言行方面的“變裝”,或多或少是一種對女性人生的逃避和否認,面對未婚夫的逃婚,她沒有歸責于任何人,卻將無辜的自己推向了變異的生活中。“文革”的到來,政治狂亂不容許任何人置之度外,姑爸希圖以明哲保身來換得平安,但是人是社會的產物,始終無法脫離社會,在面對政治風暴到來時,姑爸缺乏察覺危險的能力和應對問題的方法。暴力最終仍然將她釘在女性的十字架上。
司猗紋在環境中不斷地成長,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傳統文化反抗者和病態者,在婚姻開始的時候,她因為失貞而對丈夫和夫家的凌辱一忍再忍,始終不曾抱怨過,原本接受西方思想的新女性變成了一個傳統女性,甚至一廂情愿地想討丈夫的歡心,做一個合格的家庭主婦。所以,在她的退讓中,丈夫越來越得寸進尺,輕則打罵,重則將妓女直接帶回家,因此,司猗紋最終遭受的傷害才會比原來的深遠。不幸的婚姻讓她心生怨恨,如果感情上的壓制得不到正確的釋放,它就會采取某種非正常化的極端的方法表現出來,最終走上精神病態的道路。
《媽閣是座城》中的梅吳娘為了不讓兒子將來走上賭徒的老路,不惜殺害自己的孩子,這種極端做法是對于男性的報復,在丈夫久不回家的時候,她仍然堅守著傳統社會女性應該堅守的家庭責任:撫養孩子、贍養老人、振興家族。對于丈夫的嗜賭,她表面上并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而是將憤恨施加在那些尚未獲得男性權利的兒子身上,通過這種自傷、自虐的方式去反抗。
梅曉鷗在報復的同時,深深地悲哀于自己的發現:不管自己如何痛恨這些男人,但是自己又無時無刻不是在利用男性喜歡柔弱、花瓶般女人的心理弱點,無時無刻不得不周旋于這些人中,做自己最深惡痛絕的事情。即使是在追討債務的時候,梅曉鷗仍然擺脫不了女性對心上人的不容拒絕,甚至希望用盡一切方法讓他回頭,只是祈求他們允許自己能夠繼續愛他。
三、“瘋女”形象的寫作意義
(一)對傳統男性筆下“瘋女”、“圣母”的反叛
性別視域在作家的創作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相對于男性來說,女性是作為男性的附屬品而存在的,她們始終無法做到與男性平起平坐,為了欺騙、壓制女性的自我覺醒和才干,他們一遍遍敘說了優秀女性的標準,以求將女性禁錮在家庭的牢籠中。而女性正是為了顛覆傳統,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歷史,因此,她們有意識地解構了男性筆下的“圣母”形象標準,這既是對男權社會的強有力地直接反抗,同時也是回歸到生活本真,還原女性最原始的心理狀態,尋求新的自我解放。例如姑爸、司猗紋、梅吳娘、梅曉鷗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女人”形象,她們的自私、欲望、傷痛、反抗都脫離了男性筆下女性形象的制約,顯得復雜生動,具有真實的人性和歷史的質感。
(二)女性生存體驗的真實折射
心理分析學家波里揚·艾卓森曾經說過:“每個人都要形成自我,任何一個自我都具有性別,性別如同自我的其他側面一樣,是一整套通過敘事、幻想、角色認同而形成的,得到家庭和社區認可的信念系統。隨著身體的成熟,個人會積累大量帶有情緒負荷的機體經驗和社會經驗。自我與他人的聯系和區分都經過無數的幻覺和想象。”[12]女性作家家族小說中塑造的“瘋女”形象,通過一個個泣血的女性刻畫,全方位、多層面地展現了女性在幾千年文明史中作為權利失語者、性別被壓迫者的歷史悲劇,為女性失語者吶喊助威。著名理論家巴赫金曾說過:“‘社會學詩學’中,聲音是意識與思想觀念的代名詞,對于所有被迫沉默的社會邊緣人群來說,‘發聲’具有生死攸關的含義。”[13]女性作家正是運用自己手中的筆為女性代言,作為女性在歷史進程中的生存體驗的真實折射,最終實現了女性的權利找回。姑爸的被傷害,司猗紋在社會、性別、自我的三層壓迫下漸漸脫離了正常人性,梅吳娘的自虐和殺子,梅曉鷗的毀滅性報復都是女性在面對壓迫時的真實、正常心理轉變,也為女性家族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三)自我的隱喻與救贖
幾乎所有的“瘋女”類形象都是一種對于女性人生、精神的象征,這里的“瘋癲”都是她們面對現實壓迫的一種極端狀態的回應。女性作家透過“瘋女”的內部視點,在對女性形象刻畫、父權文明批判的同時也是對于自我的重新審視和回顧,這是女性家族小說寫作的一個主要意圖。“她們把內化為女性自我束縛的文化禁忌與圈套層層地剝離,讓那被壓抑和扭曲了的自我還原復活,這是女性的自救與新生,也是女性尋找自我的過程,盡管這種尋找和剝離的過程充滿了‘血淚與心靈撕裂的陣痛’,而女性的這一自審視角也取代了以往的男性視角,以鮮明的女性立場,反撥了文化立場上的父權審美機制和男性話語。”[14]不管是在“玫瑰門”,還是在賭城“媽閣”,都具有一種女性人生的象征意味,在這里,女性的喜怒哀樂都得到了真實的表達,也展現了作者對女性生存的深刻反思。
“瘋女”形象的塑造是女性家族小說的一個獨特的敘事策略,通過對這種非常規的生命存在、精神變態的刻畫,完成了對社會政治、歷史主體、性別意識的重新評價和反思,在這里,主要比較了兩部作品,四個人物,通過文本細讀的方法,對“瘋女”形象的塑造、形成的原因、以及創作背后的社會、文學意義進行了簡要的分析,當然這并不是女性瘋癲的全部敘述,但是仍然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以女性家族為主的歷史敘事,試圖建構一個女性個體生存體驗為主的,男女性別平等的新歷史,仍然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Z].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655.
[2]郭冬梅.論新時期以來女作家書寫的家族小說[D].曲阜師范大學,2006:2.
[3]李敏.試論女性文學中的“瘋女”書寫——以《玫瑰門》、《羽蛇》、《無字》為中心[D].北京:北京語言大學,2009:1.
[4][11]鐵凝.玫瑰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31,1.
[5][6][10]王紅旗.以家族倫理重釋性別文化——嚴歌苓《媽閣是座城》、張翎《陣痛》之比較[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12,13,15.
[7][9]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19,184.
[8]蔣麗.20世紀中國女性作家筆下的“瘋女”形象[D].西北大學,2006:4.
[12]波利揚·艾森卓.性別與欲望:不受詛咒的潘多拉[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9.
[13]蘇珊·S蘭瑟.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M].黃必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3.
[14]馬圣霞.陳染女性主義小說個案解讀[J].瓊州大學學報,2001,(1):53.
I207.4
A
1671-6469(2015)05-0001-06
2015-09-15
肖蓉蓉(1990—),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